Newsletter 06/14 | 夾邊溝裡的記憶與敘事和夏初的閱讀成長史
編者按:中國民間檔案館6月13日發文《夾邊溝親曆者和鳳鳴辭世:一位捍衛記憶的女戰士》,紀念2025年6月4日去世的甘肅西北民族學院退休女教師和鳳鳴女士。1957年同在甘肅日報社工作的和鳳鳴和她的丈夫王景超被劃為“右派”,1960年王景超餓死在夾邊溝。 40年後,親眼目睹當年慘狀的和鳳鳴,用10年的時間,將自己經歷一一記下,血泣成書《經歷:我的一九五七》(敦煌文藝出版社,2001年3月)。這是最早將夾邊溝的故事寫成書的作品。隨後,2002年5月,天津作家楊顯惠將2000年起在《上海文學》連載的系列短篇小說結集《夾邊溝記事》出版(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10月,甘肅作家邢同義歷時數載寫成的《恍若隔世——回眸夾邊溝》出版(蘭州大學出版社)。 2005年4月,上海《文學報》發表特稿《翻開一頁塵封四十年的歷史》,夾邊溝的故事首次在媒體出現。 2007年,著名公共知識分子、書評專欄作者徐賁發表《「反右」 創傷記憶與群體共建》,從此,夾邊溝被認為是中國的「古拉格群島」。此後,著名紀錄片導演王兵在2007年完成《和鳳鳴》、2018年完成《死魂靈》兩部有關夾邊溝的紀錄片。獨立紀錄片作者、民間歷史研究者艾曉明在2017年完成紀錄片《夾邊溝祭事》。書評特別推薦以下一組紀念文章,紀念和鳳鳴女士和夾邊溝裡的死魂靈。
學者徐賁在其文章說到:
前苏联“古拉格”创伤叙述者基本上都是古拉格集中营的幸存者,如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金斯伯格(Evgenia Ginzburg),沙拉莫夫(Varlam Shalamov)和马青柯(Anatoly Marchenko)。他们的文学再现使得苏联的集中营成为共产极权的公认象征。有了古拉格,苏联的斯大林主义统治便有了可以辨认的特征。 同样,有了夹边沟,中国的毛泽东式统治便有了可以辨认的特征。和“古拉格”创伤叙述者不同的是,“夹边沟”创伤叙述者中有的并不是夹边沟的幸存者,而是同情者。“夹边沟”创伤叙述因此也成为一种“后记忆”叙述。
夏初先生在「文革」時期讀《紅字》以學英語,同時讀中國《史記》。他的閱讀回憶撫今追昔,在《紅字》與《史記》之間徜徉徘徊,在中西兩種文化和歷史之間探尋思考,把自己的成長經歷和時代變遷結合起來,在讀書中理解歷史與現在,同時也展示了一個人、甚至是中國一代人的精神史。特別推薦《夏初 | 在<紅字>與<史記>之間:我的閱讀成長史》,書評亦開設「我和書的故事」欄目,歡迎投稿。
《贺卫方 | 急庇仑事件之后:司法独立为何在近代中国失败》《傅国涌|120年后,宋教仁在哪里?》兩篇精彩文章為賀衛方和傅國湧兩篇新書書摘,在日本Amazon上均有銷售;美國的季風書店和《波士頓書評》不久也可以買到,請讀者留意書評信息。
紀念和鳳鳴女士:
羅小虎 | 夹边沟里的记忆
編者按:2005年4月28日,上海《文学报》刊发特稿《天津作家杨显惠、甘肃作家邢同义不约而同先后走进那片沉重的土地:夹边沟,翻开一页尘封四十年的历史》。这是中国媒体第一次报道夹边沟。第二年,徐贲在其名篇《五十年后的“反右”创伤记忆》中特别提到这篇特稿。2009年,这篇特稿作者特别前往夹边沟,凭吊这段历史。
徐賁 | “反右” 创伤记忆和群体共建
在1949年以后发生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和事件中,反右和文革可有说是留下最深、最持久社会创伤的两次灾难。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在《文化创伤和集体身份认同》一书中,把“创伤”定义为人们所经历的“可怕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的难以磨灭的痕迹。” 对于那些受害者和同情受害者的人们来说,“可怕的事件”就是灾难。可怕事件的历史痕迹构成了对人有持续伤害作用和后果的记忆。[注1]
我和書的故事
夏初 | 在《红字》与《史记》之间:我的阅读成长史(上)
编者按:十九世纪的波士顿是美国文化中心和美国本土文学发祥地,小说家霍桑以其出生地、今天波士顿郊区Salem赛勒姆镇为故事背景的小说《红字》,至今是美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经典。该小说的诸多主题(如家庭关系,男女关系,罪与罚,欧洲殖民地与土著人关系,宗教与社会、政治和司法的纠缠等等等等)在今日美国依然多是悬而未决,且时常爆出火花。夏初先生在“文革”时期读《红字》以学英语,同时读中国《史记》。他的读书回忆抚今追昔,在《红字》与《史记》之间徜徉徘徊,在中西两种文化和历史之间探寻思考,把自己的成长经历和时代变迁结合起来,在读书中理解历史与现在,同时也展示了一个人、甚至是中国一代人的精神史。
夏初 | 在《红字》与《史记》之间:我的阅读成长史(下)
编者按: 中国读书人读书追求“融会贯通”,即对文本的细节包括细微措辞以及主题主旨要争取做到了然于心,也能将文本与其他文本以及世事、历史、人情联系起来,从而使书本内外的知识相互发明,相得益彰。夏初先生通过回忆在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初读美国文学杰作《红字》与中国史书巅峰之作《史记》,力图将他的文学阅读与他对中国/美国历史、他的家人及文革时代的中国人的经历的思考贯通起来。“在《紅字》与《史記》之间:我的阅读成长史(下)”展示了作者以自己的能力追求司马迁式的融会贯通,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包括反思/思考文革时期的人面临危及生命的酷刑时的不同应对之道与由此而来的无解的伦理道德难题,以及霍桑的美国与今日的美国之间发生的沧桑之变。他的阅读成长史显示,融会贯通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无尽的…
書摘
贺卫方 | 急庇仑事件之后:司法独立为何在近代中国失败
编者按:1821年9月23日广州急庇仑事件之后,在中国与西方的早期交往中所发生的由于法律制度与法律观念之间的龃龉和冲突却成为一个难于解决的问题。法学家贺卫方教授,从急庇仑事件出发,探讨了中国古典司法制度的特点,指出其高度集中于地方官员,缺乏分权与制衡,司法、行政、立法职能合一,导致审判易受主观影响。科举制度虽带来一定公平性,但也强化了儒家思想对司法的内化影响,使法律适用缺乏专业性和独立性。相比之下,西方强调司法独立与程序正义,上下级法院无行政隶属关系,法官平等且依据法律自主判断。
傅国涌|120年后,宋教仁在哪里?
編者按:1905年4月16日,东京,上野公园的樱花大开,年轻的流亡者宋教仁目睹了人山人海的盛况。这一年,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已经达到八千人。这一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集结在“中国同盟会”旗号下的中国人,则在东京悄悄开始了创立民国的伟业。“新名词、新术语,裹着新思想、新观念、新学问,狂风暴雨,排空而来,铺天盖地,无处不在,搅得出版界、教育界、新闻界、学术界沸沸扬扬,面貌大变……”在东京重造中国,是那个时代一部分中国人的梦想,其中就有宋教仁。在作者看来,“回到宋教仁,就是回到建设共和政体的起点上。”
書訊
Benjamin Nathans | To the Success of Our Hopeless Cause: The Many Lives of the Soviet Dissident Movement
To the Success of Our Hopeless Cause: The Many Lives of the Soviet Dissident Movem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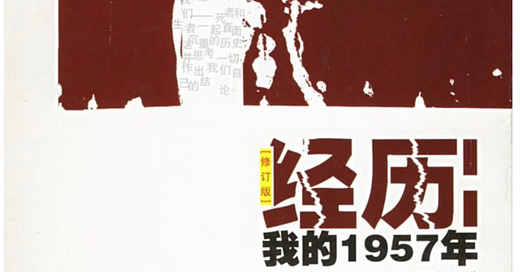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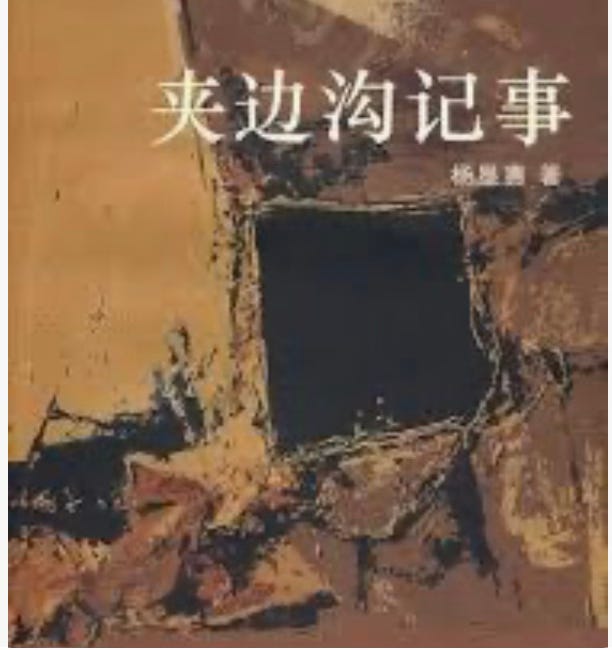





![金观涛 / [美] 华国凡|控制论与科学方法论](https://substackcdn.com/image/fetch/$s_!pioQ!,w_280,h_280,c_fill,f_auto,q_auto:good,fl_progressive:steep,g_auto/https%3A%2F%2Fsubstack-post-media.s3.amazonaws.com%2Fpublic%2Fimages%2Fdf1af8f4-93d2-4714-bda5-8be3a49cc7fc_1140x1692.he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