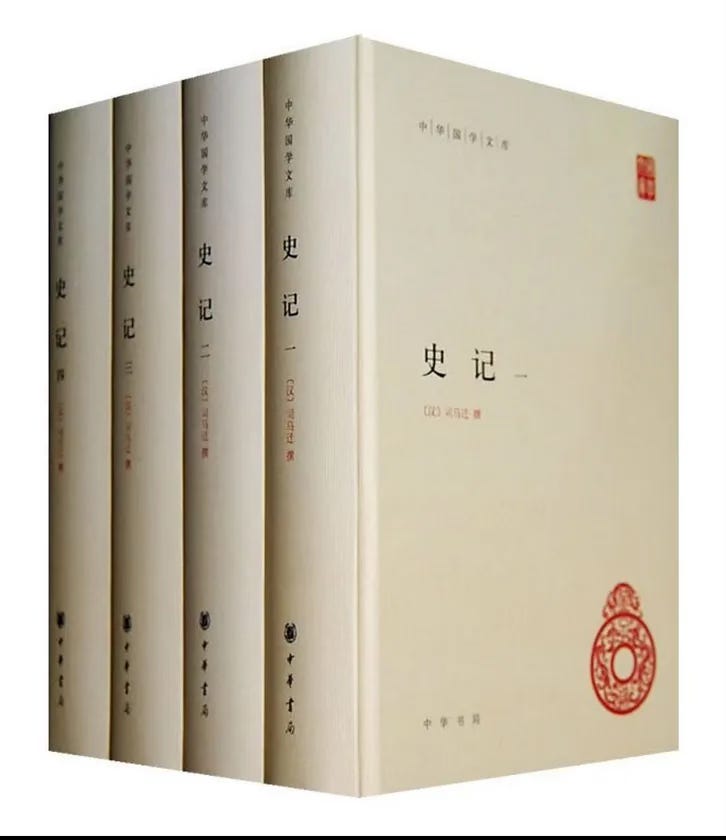编者按: 中国读书人读书追求“融会贯通”,即对文本的细节包括细微措辞以及主题主旨要争取做到了然于心,也能将文本与其他文本以及世事、历史、人情联系起来,从而使书本内外的知识相互发明,相得益彰。夏初先生通过回忆在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初读美国文学杰作《红字》与中国史书巅峰之作《史记》,力图将他的文学阅读与他对中国/美国历史、他的家人及文革时代的中国人的经历的思考贯通起来。“在《紅字》与《史記》之间:我的阅读成长史(下)”展示了作者以自己的能力追求司马迁式的融会贯通,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包括反思/思考文革时期的人面临危及生命的酷刑时的不同应对之道与由此而来的无解的伦理道德难题,以及霍桑的美国与今日的美国之间发生的沧桑之变。他的阅读成长史显示,融会贯通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无尽的过程。
《波士頓書評》免费订阅及相关事宜发送邮件:boshidunshuping@gmail.com,一杯咖啡支持書評前行:Zelle,PayPal:boshidunshuping@gmail.com 用戶名:Boston Review of Books;或是點擊下面成為付費讀者。
【如今的塞勒姆Salem村 万圣节景象,1692年-1693年發生的塞勒姆审巫案便是發生在這個村莊。《红字》作者霍桑的高祖父约翰·霍桑(John Hathorne)是一名商人和地方法官,是塞勒姆审巫案最早涉入的法官之一。他将许多“女巫”判处绞刑,因此也被称为“绞刑法官”。納撒尼爾·霍桑耻于跟高祖父同姓,便在自己的姓中加添字母“w”,使之变成Hawthorne。(photo credit:波士顿书评)】
“文革”时期在父亲的指导下正式进入英语文学阅读,开始读《红字》,是跟在他指导下读《史记》几乎同步的。
父亲是一个传统的读书人,认为中国最好的史书就是《史记》,司马迁的文笔和人品是超一流的,后来的史家和史书都一代不如一代,不能跟司马迁和《史记》相比。他赞美司马迁的人品高洁(冒着惊人的风险在骄横的汉武帝面前为李广将军的孙子和战俘李陵说公道话并为此遭受极刑),赞美他的学问精湛和文笔生动。在这方面,父亲跟赞扬《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鲁迅绝对是同党。
父亲尤其是称赞太史公喜欢用最浅显的语言展示最深刻的道理。他认为,司马迁作为史官追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气势恢宏的历史观,一举将上下古今、东南西北、天上人间囊入他的历史。司马迁的这种宏伟史观不但在世界文明史上属于远见卓识,可以经得起最苛刻的挑剔,而且司马迁用来表达这种史观的语言也深入浅出,是优秀文笔的范例。
在司马迁和霍桑之间、在《史记》和《红字》之间悠游徜徉是一种特殊的体验。司马迁的句子是简约的典范,霍桑的句子则是细腻的典范。司马迁和霍桑的共同特色是文字讲究,经得起推敲,而且他们的文字表达都很清晰: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以上这两段话来自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即使是当今中学生古文阅读能力不强,只要慢慢细读读,也可以理解其大概或大意。
父亲对司马迁文章的评论是:司马迁两千多年写的文章,今天的人也可以大致读懂,这非常了不起;什么是最好的文章?这就是了;司马迁文字工致,深入浅出;写文章追求明白晓畅,通俗易懂,绝不装神弄鬼故弄玄虚,他在引用难懂的古书时也尽量使之通俗化,让读者容易明白,最好的文章就应当是这样;他爱憎分明,但又不滥情…。
***
读司马迁的文章让我有一种眼界大开的感觉,意识到原来自以为熟悉的常用词(府,端,符,决,极,托,列)居然有这样那样的意想不到的用法和含义。司马迁的文字确实是寓教于乐,让读者能够在愉悦中加深对汉语的理解。
就寓教于乐的语言学习而言,霍桑的文字可以说跟司马迁的文字有一拼。在这里不妨再从《红字》的作者导语中摘一段话作为例证。为了迎合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时代的读者喜欢段落简短的口味,另外也为了清晰醒目,不妨把这段话切割为几段:
...here, with a view from its front windows adown this not very enlivening prospect, and thence across the harbour, stands a spacious edifice of brick. From the loftiest point of its roof, during precisely three and a half hours of each forenoon, floats or droops, in breeze or calm, the banner of the republic; but with the thirteen stripes turned vertically, instead of horizontally, and thus indicating that a civil, and not a military, post of Uncle Sam's government is here established.
….在这里,从前面的窗户望下去,那景色可不是让人感觉很振奋。再往前望,可以看到港口对面矗立着一座宽敞的砖头建筑。每天上午有三个半小时,它的房顶最高处会有本共和国的国旗在微风中飘扬,或在无风时下垂。但那旗帜的十三根条纹是竖直的,不是水平的,显示那是山姆大叔政府的民事据点而不是军事据点。
Its front is ornamented with a portico of half-a-dozen wooden pillars, supporting a balcony, beneath which a flight of wide granite steps descends towards the street. Over the entrance hovers an enormous specimen of the American eagle, with outspread wings, a shield before her breast, and, if I recollect aright, a bunch of intermingled thunder- bolts and barbed arrows in each claw.
那建筑的前廊装饰着六根木柱,其上是一个阳台,其下是宽阔的花岗岩台阶通向街道。正门入口上面蹲着一只硕大的美洲雕,翅膀展开,胸前是一个盾牌。假如我记忆无误,两只雕爪各自抓着一束闪电和带倒钩的箭
With the customary infirmity of temper that characterizes this unhappy fowl, she appears by the fierceness of her beak and eye, and the general truculency of her attitude, to threaten mischief to the inoffensive community; and especially to warn all citizens, careful of their safety, against intruding on the premises which she overshadows with her wings.
这闷闷不乐的猛禽特点是喜怒无常,嘴眼锐利,姿态凶猛,看上去像是随时会让没有冒犯它的人们吃苦头;它又像警告所有的在意自己安全的公民不要入侵它的羽翼所笼罩的境界。
Nevertheless, vixenly as she looks, many people are seeking at this very moment to shelter themselves under the wing of the federal eagle; imagining, I presume, that her bosom has all the softness and snugness of an eiderdown pillow. But she has no great tenderness even in her best of moods, and, sooner or later--oftener soon than late--is apt to fling off her nestlings with a scratch of her claw, a dab of her beak, or a rankling wound from her barbed arrows.
不过,它虽看上去脾性暴躁,但这时候还是有很多人要到这联邦之雕的羽翼下寻求庇护。我猜想,他们是以为它的胸怀犹如鸭绒枕那样松软舒适。但它在心情顶好的时候也谈不上有多么温柔,迟早(更经常地是早而不是迟)它会利爪一刨,尖嘴一啄,或用带倒钩的箭一扫,把它羽翼下的雏幼掀出去。
《红字》作为小说很有趣,这小说的作者导语也很有趣,很有料,如以上这些文字。霍桑当年以鲜明形象、生动的语言对美国政府和政制发出的讽刺、讥讽(“喜怒无常,嘴眼锐利,姿态凶猛,看上去像是随时会让没有冒犯它的人们吃苦头”)至今依然有效,有用,令人不禁莞尔而笑。
***
读霍桑跟读司马迁的感觉是相通的,因为两位先生都对自己不得不受其辖制的政权有明显的不满。另外,两者的文笔都很讲究——毕竟都是前互联网时代的写手,写字不容易,因此下笔都要用心思,不会没完没了乱写一气。
下笔用心的最明显的表现之一就是讲究句法,即通过句法的安排使读者得以发现寻常的词语有奇妙的意义或用法。例如,From the loftiest point of its roof, during precisely three and a half hours of each forenoon, floats or droops, in breeze or calm, the banner of the republic(在每天上午的三个半小时里,它的房顶最高点会有本共和国国旗在微风中飘扬,或在无风时下垂)。
但霍桑的文字也与司马迁的有显著的差异,最明显的大概就是他们在谈政治时的笔调和态度。司马迁在提及或谈论政治时更为谨慎和简约,几乎总是惊鸿一瞥一带而过(“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霍桑则更为肆意和畅言,借着评述美国国徽上的白头雕的机会指桑骂槐,对美国政府和政体大放厥词,揶揄挖苦,比喻和语气很是辛辣。
司马迁和霍桑的这种差异所反映的显然不仅是时代、文化或作者身份或目标读者的差异,更是社会政治制度的差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司马迁时代到现在,中国人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没有霍桑那种表达自由。但奇妙的是,偏偏是容忍霍桑辛辣讽刺挖苦和攻击的那个共和国政体更为稳定,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天朝反倒总是风雨飘摇,危机四伏,倾覆翻船的恐惧是经常性的,因此以言治罪是中国长盛不衰的政治传统,几乎连续不断,时常高潮迭起。
貌似观念极其成问题的《红字》至今是美国人所骄傲的美国文学经典,世界文学名著。霍桑之后的美国历代爱国者之所以对他听之任之,没什么人对他挞伐批判,听任他的颠覆性语言和思想流传泛滥至今,并不是因为美国人不分好歹或是非,或缺乏政治敏感,缺乏对美国革命(独立战争)的认同,而是因为对政府的不信任和警惕是美国人的政治基因之一。另外,美国人也知道霍桑说到底还是自家人,他虽然对其共和国有强烈的不满,但他对当时信奉君权神授的美国前宗主国英国更不认同。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所言只是后来重读《红字》的思考和心得。今天重读《红字》,更是惊觉上文所谓的“美国人”之说已经碍难成立,现在的美国总统自比国王,公开声言“国王万岁/Long live the king” ,声言他获得总统职位是因为他获得神的拣选。这种说辞与美国革命所针对的自称君权神授的英国国王如出一辙,几千万美国选民不但不以为意,而且还感觉很中意,很自豪。显然,时代变了,今天的美国已经不是霍桑的美国,今天的美国人也不是霍桑所熟悉的美国人了。
以上所言只是今天的政治觉悟。1970年代初读《红字》时自然不会有这样的觉悟。当然,要求当时的或现在的一个中国中学生有这样的觉悟也是勉为其难,揠苗助长。强行要求只能是让学生失去学习兴趣。
好在父亲信奉因材施教,没有不明智地追求高精尖,而只是做最简单的讲解。例如,在解说上面一段话的时候,只是说美国国徽是一只白头雕,霍桑讽刺美国国徽,讽刺那凶猛的白头雕,就是讽刺山姆大叔即美利坚合众国,也就是霍桑说的“本共和国”。
那时还没有互联网,罕见的百科全书也成了烧火材料,因此无缘看到美国国徽究竟是什么样子,只能想象霍桑所说的那只美国鹰。后来,看到了美国国徽的真容,发现当初的想象居然跟实物八九不离十,不由得佩服霍桑的讽刺挖苦式描述确实惟妙惟肖。
***
《红字》所讲的故事梗概是,十七世纪中叶,一个年长的英国学者一心追求医术学问,将他年轻美貌的妻子先送到还是英国殖民地的北美大陆新英格兰地区波士顿一带,准备以后在北美安家立业。两年后,那学者也来到北美,赫然撞见妻子因婚外恋怀孕生子被当作淫荡通奸犯受到公开审判和羞辱的场景。
政教一体、奉行清教徒信条的新英格兰殖民地当局要那妻子供出犯罪的另一方是谁,并且许诺她只要供出便可免受惩罚。那妻子选择宁可受罚也不要供出另一方,并选择胸前戴大写的红色字母A继续在那里生活和抚育孩子。
后来,赫斯特·普林(小说女主人公、婚外恋生子的那位人妻)在当地社区善行多多,赢得众人的敬重。以羞辱来惩罚她的当局原本希望众人将她佩戴的大写字母A理解为Adulteress(女通奸犯)的首字母,众人到头来却把它理解为Able(能者)的首字母。她的情人亚瑟·迪梅斯戴尔牧师带着沉重的犯罪感生活、布道,他的虔诚和谦卑更是赢得了众多信众。与此同时,赫斯特·普林的丈夫罗杰·奇林沃思一心一意复仇,试图找出在他看来令赫斯特堕落的罪犯,结果却是一场空,害人又不利己。
总而言之,《红字》的故事可以说是由好几条相互交织的富有反讽的故事情节构成——犯罪者实际是好人或变成了好人(赫斯特·普林,迪梅斯戴尔牧师);试图追究和惩罚犯罪的人则是或变成了恶人或伪善的人(奇林沃思、当时的总督等等)。
父亲带我读《红字》只是要我注意故事就好,并没有大力突出和强调这些反讽。他顶多是对这些反讽一带而过,指出事情发生有趣的逆转。但他引导我特别注意《红字》中那些拥有各种权力(奇林沃思的夫权、州长的政教合一的政权、迪梅斯戴尔牧师的同事威尔逊牧师的神权)并以此自命不凡或将弱势者玩弄于股掌之上的人。他反复向我指出,在描写这些人的时候,霍桑的笔端总是带着含蓄又尖锐的讽刺和憎恶。
父亲带我读《红字》时所展示的这种注重次要人物的解读可谓与众不同。只是多年之后,我才算是完全理解了他的这种与众不同跟他作为毛时代的一个普通中国知识分子的经历和处境有关。
记得当时父亲多次以霍桑写小说的口吻跟我讲,对亿万中国人拥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的伟大领袖以“幽默”和“善意”的口吻要作家和评论家胡风的朋友揭发被他打成“反革命分子”投入牢狱的胡风,要他们把自己跟胡风的私人通信交出来以便给胡风添加罪证;毛通过他的喉舌媒体对他们直接发话:那些私人通信“交出比保存或销毁更好些”。
父亲还以同样的口吻跟我讲,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所谓“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展开时,他所在的学校有一个对普通教师拥有生杀予夺之权的干部找他谈话,要他交代问题,并且“好心”地跟他说,“不要思想负担太重。”
当时听父亲讲这些话,感觉似懂非懂,有些滑稽,也有些怪异,不理解为什么他对《红字》中的那些看似次要的(但是有权有势的)人物的言行那么看重,不理解他为什么对伟大领袖说“交出比保存或销毁更好些”的话以及那个学校干部“好心”地跟他说“不要思想负担太重”要那么耿耿于怀。直到自己长大了,也有过类似的经验之后,我才算是彻底理解了父亲,才算是意识到他当年带我读《红字》,以亲身经历现身说法是精深的文学教学。
***
从某种意义上说,《红字》、胡风案件以及“清理阶级队伍”的共同点都是所谓的“交代问题”,也就是当局要当事人当众自认有罪并检举揭发其他“犯罪分子”。暴政独裁统治者通过强迫被统治者进行这种当众认罪自辱和相互检举揭发,彻底摧毁他们的自信和自尊,并使他们感到孤立无援,抵抗无用,只能自暴自弃,或自甘下流,这一切当然有利于统治者肆意随时对被统治者给予歼灭性打击且不会招致反抗或怨言。
父亲憎恶伟大领袖的“幽默”,憎恶那个掌握着对普通教师的生杀大权的干部的“好心”,是憎恶独裁暴政捉弄和玩弄毫无反抗能力的弱者(有如猫捉老鼠玩弄)。那时的暴政后来连中国共产党当局自己都承认是一场“浩劫”,连中共的元老、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也死于那场浩劫(应当补充一句:刘少奇自己也行暴政,是暴政的凶狠打手/杀手,整死很多人)。
在初读《红字》的时候讲到交代问题,父亲还给我讲了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运动期间发生在他学校的故事:一位体育教员被抄家,红卫兵发现他保存的(或没来得及销毁的)1949年前的旧相簿,其中有一张照片是他身穿国民党军官制服,站在美国小汽车旁边。
这下好了,发现了一个隐藏的国民党军官,而且是超高级的,有小汽车的,可见级别之高。于是,那位老师被推入刑讯室,被蒙上眼睛吊起来毒打。但他死活不承认他是国民党军队高官,称他只是借别人的官服站在别人的汽车边照相,就是图个好看。用刑的人听他这么说,对他打得更凶,要他休想拒不交代蒙混过关。那位教员被打得死去活来,最后没被活活打死实属万幸。
与此同时,还有一位教员在清队(即清理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隐藏的阶级敌人)期间被认定是个特务。在口含天宪、无法无天、可以随意给人定罪的调查人员找他调查、要他交代问题时,他心领神会,机动灵活,安详坦然,积极配合。调查人员要他承认他是多高级的特务,他就承认自己是多高级的特务,要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要他揭发谁也是特务他就揭发谁。于是,他不但免受了皮肉之苦,而且还被树立为积极交代问题的模范,供其他教师效法学习。
最后,清队运动过去,给被调查的人做结论,那两位教员都被认为是没有问题。
父亲说:看,就这两个人,一个是坚决不肯说假话,结果差点被活活打死;另一个人见势不妙,抵抗无用,便积极配合,什么假话都说,反正说真话不但不会被采信,反而可招来灾祸甚至招致丧命,说假话可以免遭皮肉之苦,可以保命;但最后两人都被宣布没问题;这两个人该怎么说呢?哪个更好?对谁好?
多年过后,父亲也去世多年,直到今天,我还是不知道该如何回答父亲当年提出的这种伦理道德难题。我也由此更加佩服他,因为他只是客观地陈述事实,提出问题,不做结论,颇有莎士比亚之风,也颇有莎士比亚式的深邃,睿智。
我由此也感觉算是理解了耶稣基督那么坚强为什么还要祷告神“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耶稣的祷告词中的“试探”又可以翻译为“考验”,“试炼”。
从各种意义上说,后人和外人对父亲所说的那两位经历试探的先生都无权品评,因为那两位先生所遭遇的是具有超人的坚强的耶稣基督也竭力试图回避的考验。
父亲多次说,他在毛时代经历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都是侥幸苟免,苟全性命于乱世。
谢天谢地,父亲如此苟全性命于乱世,如此苟免于毁灭性的试探,让他得以带着后怕庆幸自己的好运,又让我得以庆幸自己的好运——我不希望看到父亲宁死不屈被打死或打残,也不希望看到他为了保命而被迫咬别人,让无辜的他人受害,让他让我都被受害者及其家人永远诅咒。
***
在手头的好几种《红字》版本中,有一本是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的“世界名著·经典电影·双语阅读”版。这个版本可以说是装订良好,印刷良好,但也可以说是装订和印刷良好但明显是骗钱的粗制滥造。
说它明显是骗钱,是因为这双语版的书说是它的翻译是“编译”,却拒不说明是根据谁人的翻译编译的。这就难免使人不能不认为它是盗用别人的翻译骗钱。
说它是粗制滥造,是因为它双语对照居然还能中间缺了一页英文原文和一页中文译文。显然,那两个“编译者”只是把他人的翻译拿来,然后再上网找到已经没有版权问题的英文原文,然后闹着玩似地把他人的翻译和英文原文一页一页地对应排版,少了一页也没注意,甚至干脆是不在乎。
从技术上说,英汉双语对照读物能把一页原文和一页中文双双弄丢也是一种高技术,因为主事者至少有两次明显的机会察觉缺失并予以补正。主事者或是发觉译文缺失一页,或是发觉英文原文缺失一页,无论是发现哪张缺页,都会使对应的一张得以补正。察觉不到这样的双倍明显的缺失,恐怕只能说明是高度的不负责任或高度的恶作剧——发现少了一页懒得费力去寻找,而是再顺手抽掉跟缺失的那页对应的一页,以使读者难以察觉。
那缺失的一页是《红字》第16章“林中的散步”的一部分,其英文原文和我的翻译如下:
Thus conversing, they entered sufficiently deep into the wood to secure themselves from the observation of any casual passenger along the forest track. Here they sat down on a luxuriant heap of moss; which at some epoch of the preceding century, had been a gigantic pine, with its roots and trunk in the darksome shade, and its head aloft in the upper atmosphere.
她们这样说着话,走进了森林,进得足够纵深,让不经意间从林中小路上经过的人也看不到她们了。她们在一堆茂盛的青苔上坐下;在前一个世纪的某个年代,这堆青苔曾经是一棵巨大的松树,树根树干在暗影中,树冠高耸天际。
It was a little dell where they had seated themselves, with a leaf-strewn bank rising gently on either side, and a brook flowing through the midst, over a bed of fallen and drowned leaves. The trees impending over it had flung down great branches from time to time, which choked up the current, and compelled it to form eddies and black depths at some points; while, in its swifter and livelier passages there appeared a channel-way of pebbles, and brown, sparkling sand.
她们坐在一个小小的谷地中,两边是撒满落叶的缓坡,一条小河从中穿过,河床是给水淹没的落叶。高耸在小河上的树木有粗大的树枝不时搭下来,水流受阻,被迫形成一个个水湾,有的地方还形成黑潭;在水流比较湍急的地方可以看到卵石的水道,闪光的褐色沙砾。
Letting the eyes follow along the course of the stream, they could catch the reflected light from its water, at some short distance within the forest, but soon lost all traces of it amid the bewilderment of tree-trunks and underbrush, and here and there a huge rock covered over with gray lichens.
顺着水流看去,她们可以看到森林中不远处水流的反光,但反光很快被纵横交错的树干和灌木完全遮挡。不时可以看到一块巨石,上面覆盖着灰色的地衣。
All these giant trees and boulders of granite seemed intent on making a mystery of the course of this small brook; fearing, perhaps, that, with its never-ceasing loquacity, it should whisper tales out of the heart of the old forest whence it flowed, or mirror its revelations on the smooth surface of a pool. Continually, indeed, as it stole onward, the streamlet kept up a babble, kind, quiet, soothing, but melancholy, like the voice of a young child that was spending its infancy without playfulness, and knew not how to be merry among sad acquaintance and events of sombre hue.
这些大树和花岗岩巨石都好像有意要使这条小河神秘莫测,或许是因为害怕它喋喋不休的絮语会泄露它流经的古老森林的心事,或水面平静会反射出它的秘密。小河向前不断流,水流汩汩,和善静谧,令人欣慰,但带着忧郁,好像是一个小孩子发出的声音,那孩子年龄幼小却不好玩好动,不知道在悲哀的熟人和在阴郁的事件当中可以如何欢乐。
***
以上展示的《红字》当中的一页,可谓货真价实的随机抽取的一页——没有人能猜到两位“编译者”会丢失哪一页,两位自己也没想到。如此随机选取的一页很能代表作者霍桑文笔的一个特色,这就是他善于将风景描写跟心理刻画共冶一炉。
这一页说的是小说主人公带着非婚生的女儿走进森林(“林中的散步”),去会她的秘密的情人、小女孩的生父即那被众人敬仰的牧师,商讨如何应对看似越来越紧的追查他的风声。这一页也是一个桥段,向这对母女即将发生的互动过渡——母亲是社区的一个反面教材(即今天的人们所谓的“被社死”的人),给这样的单亲妈妈带大的女儿自然又不自然地与一般的孩子不一样,“年龄幼小却不好玩好动,不知道在悲哀的熟人和在阴郁的事件当中可以如何欢乐。”
这样的母女会有怎样的沟通?母亲该不该跟女儿讲、可以怎样讲她的来历?超敏感的小女儿会如何应对她那难以对外人言的生父?她的生父面对她母女俩,尤其是面对她会有怎样的感觉,怎样的表现,会怎样说话,会说什么?这一页包含着这些对小说情节发展很重要的悬念。这一页被随机删除,相当于随便在一件精美的瓷器上砸出一个窟窿。
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样的桥段本身就是一景。它既是人生或生命演进的寓言(“在前一个世纪的某个年代,这堆青苔曾经是一棵巨大的松树,树根树干在暗影中,树冠高耸天际”),又是小说人物心理状况/活动的翻译(“这些大树和花岗岩巨石都好像有意要使这条小河神秘莫测,或许是因为害怕它喋喋不休的絮语会泄露它流经的古老森林的心事”)。它像是一颗钻石,有多个小平面,从不同的角度看会闪现出不同的光彩。
当年在父亲的带领下读《红字》的时候,霍桑的这种文笔让我很喜欢。这小说的故事很有趣,但它的风景描写更有趣,更耐咀嚼。霍桑真是善于描写风景,善于把风景描写跟心理描写天衣无缝地融合起来。
《红字》就是我的美国文学入门。如今重读霍桑,还是很喜欢他这种饱含人情的风景描写。这样的文字富有魅力和魔力,在任何时候读,都可以立即随着这样的文字进入一种深邃静谧的境界。
冬季的一个阳光明媚、冰冷刺骨的一天,沉浸在重读《红字》的喜悦和回忆中。
时时抬头看窗外。几次看到狐狸在窗下草地、林中空地上迈着迟疑的狐步走过。纳闷它们在这样的天气中能找到什么吃的,会不会死于冻馁交加。
注:本文中的中译文都是作者本人的翻译。
夏初 | 在《红字》与《史记》之间:我的阅读成长史(上)
编者按:十九世纪的波士顿是美国文化中心和美国本土文学发祥地,小说家霍桑以其出生地、今天波士顿郊区Salem赛勒姆镇为故事背景的小说《红字》,至今是美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经典。该小说的诸多主题(如家庭关系,男女关系,罪与罚,欧洲殖民地与土著人关系,宗教与社会、政治和司法的纠缠等等等等)在今日美国依然多是悬而未决,且时常爆出火花。夏初先生在“文革”时期读《红字》以学英语,同时读中国《史记》。他的读书回忆抚今追昔,在《红字》与《史记》之间徜徉徘徊,在中西两种文化和历史之间探寻思考,把自己的成长经历和时代变迁结合起来,在读书中理解历史与现在,同时也展示了一个人、甚至是中国一代人的精神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