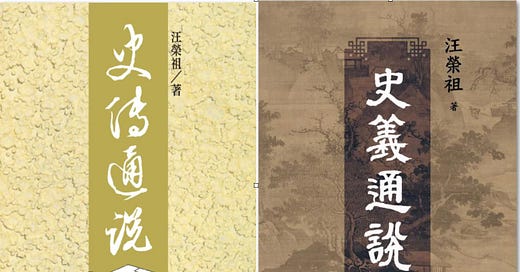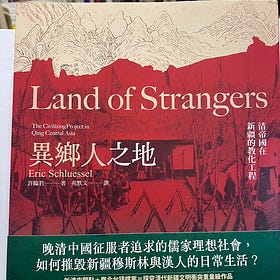Newsletter 05/31 | 夏初:读“汪荣祖访谈”想到的问题(读者来信)
编者按:本周汪荣祖访谈(上、下)刊发之后,引发不少读者的讨论,尤其是有关汪荣祖对“新清史”的批评部分。新清史起源于1990年代美国汉学界,代表人物包括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罗友枝(Evelyn S. Rawski)、欧立德(Mark C. Elliott)等。他们主张从“内亚”(Inner Asia)视角重新审视清朝(1644-1912),强调清朝的满洲特性、多民族帝国属性以及与蒙古、藏族、维吾尔等群体的互动,而非仅将其视为汉族主导的传统中原王朝。这种视角挑战了中国传统史学中以汉族为中心、强调“华夷之辨”的叙事。“新清史”学者使用大量满文、蒙文等非汉文史料进行研究,认为清朝是多民族的“内亚帝国”,满洲统治者通过灵活的民族政策(如满、蒙、汉、藏等多语行政)维持帝国统治,而非完全汉化,而清朝的统治是多元治理模式。而传统史学则强调清朝是中华正统王朝,继承了明朝的儒家文化和政治传统,满洲统治者通过汉化融入中原文化;强调清朝的统治核心是汉族文化,边疆民族政策是次要的。还有读者指出,汪榮祖先生在访谈中谈到新清史是受日本研究影響的,欧立德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主要是冈田英弘教授,这其实是一种帝国主义的解构史学(deconstructive historiography of imperialism)观点,以后现代主义殖民主义眼光,批判和重新审视传统帝国主义历史叙事。同时读者还指出,“新清史”的源流甚至可以追溯到荻生徂徕与其弟荻生北溪。而读者夏初更是认真,为此认真写下自己阅读之后的问题。书评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阅读和讨论的平台,欢迎这些认真的阅读和讨论,并希望讨论仅限于学术范围。
夏初 | 读“汪荣祖访谈”想到的问题
读“汪荣祖访谈”,感觉很受启发。由汪先生的启发想到许多问题。先前留言评论表示了一点个人意见。因为一挥而就,结果多处有表达不清晰、不通顺的问题,甚至有明显错误。很是抱歉。
现在想纠正错误,并扩展一下先前的比较简短的评论,从文学和社会科学的角度发表一点不那么急就章的评论。
在访谈的开始,汪先生谈中国史学,开宗明义说了这样一段话:
中國現代史學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橫植西方史學,未能縱承傳統史學加以創新,雖不必縱承《史記》的紀傳體,但是不能輕易放棄數千年纍積的史學成果,不應專注橫植而忽略蹤承,不然中國固有的文史之學,便有絕響之虞。
这段话,以及汪先生接着对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张之洞的赞扬性提及,显示了汪先生大致还是在张之洞的体用说框架内想问题。这一现象让我感觉非常有趣。
我兴趣的点在于,提出中体西用说的张之洞及其追随者似乎都没有认真想过一个如今看来是非常明显的问题,这就是,“体”和“用”的关系往往比连体双胞胎更紧密,更密不可分,难解难分。因此,将“体”与“用”分开再合并的“中体西用”之说到头来往往流于空话或废话,甚至难免沦为有意无意的自欺欺人。
看汪先生谈张之洞的中体西用以及中国固有的文史之学有成绝响之虞,让我不禁想起中国固有的医学即中医。中医可谓实践“中体西用”的绝佳场域,也可以用来做一个形象生动的例子,充分显示“中体西用”的滞碍难通。
例如,一个人染上Covid-19,西医说是病毒致病并可以拿出电子显微镜照片证明。中医则说是阴阳不调,虚火上升。中医如何中体西用呢?这个问题大概就像是问:如何画出一个正方的三角形呢?当然,现在我们也已经知道,以中国国家之力推广的所谓的中西医结合防治Covid-19的主打药物莲花清瘟胶囊只是国家级诈骗。此外,许多论者指出,在当今中国,中医中药行业一直是诈骗成灾的产业。
不错,中国是有数千年积累的史学成果,就如同它有数千年积累的医学成果。中医的例子似乎告诉我们,作为后人,在思考传统的学问/知识的继承问题时,有用或有效的着眼点应当是明辨先前的学问/知识是否真确,可靠,而不是中西辩证或体用辩证问题,也不是学问/知识只要是历史足够悠久就应当或必须保留。
在“汪荣祖访谈(上)|如此現實,中西史學如何對話?”中,汪先生用了很多篇幅对所谓的新清史提出强烈的批评。例如,
新清史認爲漢化是錯誤的概念,是大漢沙文主義的產物,甚至痛斥此詞“觀念不清,思維乏力,在實際的歷史研究上沒有價值”,並情緒性地抨擊“大漢沙文主義”。哈佛中國史教授Peter Bol也認為漢化用詞不妥,建議以“文明化”來替代漢化,卻不知當時的文明就是漢文明,不是多此一舉嗎?
在我看来,说清代文明就是汉文明,这种观点很难立得住。
以维吾尔人为例。人家维吾尔人一直有自己独立的文明/文化。据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维吾尔人历史学者卡哈尔·巴拉提(Kahar Barat)博士说,“维吾尔族的现代化教育实际上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其实早于汉人。在(中国清朝末年学者)康有为提出要开设学校时,新疆已经早就有了十几所西方式的学校,老师都是从莫斯科、喀山和伊斯坦布尔来的。” (见2015年7月12日巴拉提博士接受美国之音中文网采访的访谈记录。)
作为一个汉人,汪先生的意思显然是,在清代,汉文明之外的其他民族的文明不是阙如就是可以忽略不计、只有汉文明才是唯一上得了台面的文明,这种看法恐怕会被维吾尔人和其他非汉族的族裔认为是难以接受的傲慢与偏见。假如这种看法可以成立,那么,藏传佛教文明算什么呢?蒙古人的文明到哪里去了?主宰汉人的满人的文明也不算数吗?这种忽视乃至蔑视其他民族的文明/文化的看法难免被认为是展示了一种惊人的、类似于种族主义的大汉族主义(大汉沙文主义)。
说到这里,汪先生当然可以说,他并不是要否定其他民族的文明/文化,他只是想说,其他民族的文明都融入到汉文明当中了,所以说当时的文明就是汉文明。但这种说法显然也很符合大汉族主义(大汉沙文主义),颇类似于俄罗斯总统普京所奉行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不承认乌克兰文明/历史。
如今辨析这种历史和文明之争不是针尖上可以站几个天使那样的无害玄学思辨,而是有严重的现实意义。在俄罗斯导弹不断炸死炸伤乌克兰人之际,在千百万维吾尔人、图博特人(西藏人)、蒙古人因试图维护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权利而遭受迫害甚至被监禁之际,具有起码的人文关怀的人不能不意识到这种沙文主义的可怕。
汪先生对新清史还有很多批评。在我看来,其批评常常令人困惑。
例如,他说,“新清史否認漢化”。然而,这种说法显然有误导或曲解新清史之嫌。汪先生自己就说,“新清史認為:清朝採取的理藩院等制度,是解決與‘內陸亞洲’民族之間政治認同的關鍵措施;清朝統治者對漢文化的接受與推崇、對漢族的籠絡政策,則是一種戰略上的考量和手段,旨在為政治統治服務,而非心甘情願地主動漢化。”这些话显示,汪先生也清楚地知道,新清史并没有否认清朝统治者的汉化。
再例如,
滿漢兩族經過“同質化”而終於“同化”,帶有滿族血統的漢人增大了漢族的總數,而極大多數的滿人在長期漢化下,趨向認同中華民族。到現代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員。根據1978年的人口調查,滿族有2,650,000人,因漢化之故,在身體與文化上幾無法辨別,漢化如何能否定得了呢?新清史卻一再不認為滿人接受漢人的生活方式,習慣說漢語而疏於母語,不認為滿洲王朝延續中國傳統的政治制度,漢籍官員不佔官僚體制內的重要地位,不認為滿漢已經融合,沒有認同上的差異等等,莫不是違實之論,豈非無理取鬧嗎?
汪先生的这种论述难免令人感觉逻辑跳跃太大,有些说法也很成问题。
“極大多數的滿人在長期漢化下,趨向認同中華民族” 这种说法显然有时代错置,因为含义是融合中国各民族的“中华民族”的说法是梁启超1902年即清朝末年才想出和提出的。而且,在当今中国,中华民族这种说法也没有被非汉人广泛或欣然接受,至今依然可以引起激烈争议。关于这一点,汉人的中共政权对当今中国境内诸多非汉人的严酷的文化/语言/宗教/政治的打压便是明证。近年来,这种打压更有向海外扩散的势头。
再者,在上述论说中,汪先生用满清王朝崩溃66年之后的人口调查来证明满清王朝的汉化情况,这种论证很难有说服力或解释力。
另外,在满清王朝,汉籍官员到底占不占官僚体制内的重要地位呢?历史记录显示,满清王朝统治者拒绝让汉籍官员占体制内重要地位,从而使当时中国社会各界对满族/旗人统治者实行族裔平等的新政的诚意丧失希望,而这种绝望是促成二十世纪初推翻满清统治的革命的一个主因。
鉴于满清统治者基于族裔而对汉籍官员进行这种政治排斥,人们根据常识、逻辑、历史事实应当得出的结论是,新清史不认为满汉完全融合,新清史的观点是有道理的,而声言满汉已经融合、没有认同上的差异才是违实之论,才是无理取闹。但汪先生观点正好跟常识、跟逻辑、跟事实相反。
为什么呢?对我这个读者来说,这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这个令人困惑的未解之谜或许是源于访谈文字编辑有误或有错漏。然而,即使是读者把文字错漏考虑在内(并进而从汪先生论说中拿掉或添加一个或两个“不”字),这未解之谜依旧令人感到困惑难解。
或许,汪先生接下来说的话有助于为读者解惑:
旗人在族群上自然認為是滿人,然而滿人與漢人同屬一國,難道清朝的滿人與漢人有不同的國家認同嗎?中華民族的發展無疑是以漢族為主體、華夏文化為核心的共同演進,並強化與少數民族共同的心理狀態和國家感情。北京民族大學的鍾焓教授的研究更指出蒙族、藏族、維吾爾族都認同清朝是中國,更無分滿漢。
以上这段话大致意思是清楚的。然而,认真的读者读到这里也可以说,撇开大成问题的所谓“中华民族的发展”不谈,清朝的满人与汉人当然可以有截然不同的国家认同,根本就不是汪先生赞赏的鍾焓教授所说的各族“都认同清朝是中国,更无分满汉。” 假如我们相信锺教授的话,我们就难以解释为什么在辛亥革命之后,先前由满人占据/垄断政府要职的局面彻底改变。但用国家认同有异则很容易解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一直不认同满人统治的国家,他们先前只是不得不忍气吞声,敢怒不敢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类的大屠杀不是儿戏,即使事情过去了将近三百年,他们还是有记忆)。
汪先生对新清史还有很多批评,如,
其三、新清史誤以西方殖民帝國的概念來看滿清帝國,中國自漢唐以來的帝國,有其特色,清朝向西擴張僅求納貢與形式上的臣服,不作直接統治。研究邊疆史有成的吳啟肭研究員指出:清帝國在蒙古與西藏地區僅有象徵性的駐軍,在新疆的駐軍也不以高壓統治為後盾。建立“宗藩”關係,實行傳統中國的羈縻政策,除名義上的加封外,不設官置守,也不干涉內部事務,更不介入各部之間的紛爭。承襲二千年來中原王朝的傳統,以保障農業地區的安全為主,仍不脫傳統中國保守的防禦性質,與西方列強以武力奪取殖民地,任命總督,掠取殖民地的原料、勞力與市場,並灌輸其宗教與文化價值,有意壓制自主意識,截然不同。
以上这段话在我看来包含一系列问题。为了控制篇幅,不妨在这里仅仅指出其中一个——“(满清王朝)建立‘宗藩’關係,實行傳統中國的羈縻政策,除名義上的加封外,不設官置守,也不干涉內部事務,更不介入各部之間的紛爭。承襲二千年來中原王朝的傳統,以保障農業地區的安全為主,仍不脫傳統中國保守的防禦性質...”。汪先生这些话给人的印象好像是两千年来中原历代统治者没有对外扩张,即使有扩张也都是兵不血刃或和平演变,其他民族不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就是波澜不惊不知不觉地易主。然而,中原地区周边的其他民族大概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或感受。
此外,假如我们相信汪先生的话,我们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这就是,现在的中国汉人统治者是中国历史上的异类,是在以不人道的方式跟中国爱好和平的悠久历史逆向而行,大大不如被辛亥革命推翻的满人统治者。
以上是“汪荣祖访谈(上)”的一些读后感。访谈给我的启发、使我想到的问题很多,这里只是挑选了一小部分来说。
在“汪榮祖訪談(下)|名山事業,蕭公權著作不會因時間的流逝而失去價值”中,汪先生提出了更多的有趣的观点/话题。
在这里,我想评论一个我最感兴趣的话题,这就是,汪先生悲叹说,“白話文没有源頭活水(即文言文),以至於有今日會出現絮絮叨叨,詞不達意的白話文。” 然后,汪先生话锋一转,
孰料文革之後,竟然出現錢鍾書先生以典雅古文寫的《管錐編》,以文言闡釋中西玄理,毫無窒礙,點亮舊學復興的曙光。我受錢先生的鼓舞,所以有《史傳通說》《史義通說》兩書的寫作,雖希望能依附驥尾,師承遺風,但人微言輕,不敢盼望旋轉乾坤。近年偶見若干年輕學者如山東大學的劉曉藝教授能寫上乘的古文與詩詞,南開大學的程平山教授能結合訓詁與考古重建上古史乘,大有天涯何處無芳草之感,然星星之火能否燎原,尚無樂觀的把握。
我不敢说我清楚汪先生所说的“白话文没有源头活水”究竟是具体指什么,但我对钱锺书的文言文表达能力确实做过一番认真的研究。我的研究发现是:钱锺书用白话翻译外文可谓多是得心应手,挥洒自如,巧妙贴切,用文言文翻译则是频频捉襟见肘,词不达意,丢三落四。我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虽然钱锺书在当代中文世界被认为是文言文一流好手,但即使钱锺书这样的好手在他最擅长的文学表达领域也玩不转文言文,使用文言文对他来说明显是削足适履,或带着脚镣跳舞,出力不讨好,而且常常会坏事。
至于说山东大学的刘晓艺教授或南开大学的程平山教授能写古文/文言文,我虽然没有对两位先生的古文/文言文表达能力做过研究,但诸位读者可以马上做一个有趣又简单的思想试验——假如两位先生需要寻求医疗帮助,或需要书写(或监督书写)租房/买房协议,他们会用或愿意他人用文言文/古文吗?答案:不会。
为什么不会?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古为今用”是有限度的,今人的日常生活需求和表达需求大大超出古人,超出古文的表达能力;古文/文言文欠缺今人所必需的太多太多的词汇和句型,今人强行使用不好用/不堪用的古文/古语进行书面或口头表达,不但是自讨苦吃,而且很可能会吃大亏,甚至可能无端招致生命危险。(顺便问一下,“青霉素过敏”用古文/文言文可以怎样表达且不会导致使人无端丧命的风险呢?)
以上的思想试验不但适用于刘晓艺和程平山,也适用于文言文表达能力跟他们一样好甚至更好的钱锺书。
附记:
上文提出了我对钱锺书语言表达力的研究发现:钱锺书用白话翻译外文资料可谓多是得心应手,挥洒自如,巧妙贴切,用文言文翻译则频频捉襟见肘,词不达意,丢三落四。
以下是两个想必足以说明问题的例子。比如,钱锺书用白话文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片段:
The lunatic, the lover, and the poet
Are of imagination all compact.
One sees more devils than vast hell can hold;
That is the madman.
The lover, all as frantic,
Sees Helen’s beauty in a brow of Egypt.
The poet’s eye, in a fine frenzy rolling,
Doth glance from heaven to earth, from earth to heaven;
And as imagination bodies forth
The forms of things unknown, the poet’s pen
Turns them to shapes, and gives to aery nothing
A local habitation and a name.
疯子、情人和诗人都是满脑子结结实实的想像。疯子看见的魔鬼,比广大的地狱里所能容纳的还多。情人和疯子一样癫狂,他从一个埃及人的脸上会看到海伦的美。诗人转动着眼睛,眼睛里带着精妙的疯狂,从天上看到地下,地下看到天上。他的想像为从来没人知道的东西构成形体,他笔下又描出它们的状貌,使虚无杳渺的东西有了确切的寄寓和名目。
钱锺书的这种白话翻译可谓得心应手,挥洒自如,巧妙贴切。然而,我们再来看钱锺书用文言文同是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片段:
This is an art
Which does mend
Nature, change it rather, but
That art itself is Nature.
人艺足补天工,然而人艺即天工也。
这种翻译用捉襟见肘,词不达意,丢三落四来形容可谓恰如其分。懂英语的读者一眼就可以看出,钱锺书在这里的翻译跳过了原文的“change it rather”,这种跳跃/丢弃可谓明显错误,因为这个短语承担着重要意义,并非可有可无。莎翁这话严格按照原文翻译可以是:
这就是艺术,修补自然,更是改变自然,但这艺术本身便是自然。
在这里且撇开钱锺书把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学的一个关键词nature翻译为成问题的“天工”不谈,单说说为什么同是翻译莎士比亚,钱锺书会有这种刺眼的翻译质量差异。
一个解释可以是,他用白话文翻译更用心。另一个显然更为合情合理的解释则是,文言文对他来说也是很不顺手,碍手碍脚,于是,为了图痛快或图方便,他就把“change it rather”给丢弃了。
許臨君蔡偉傑對談:兩代“新清史”研究的異同
編者按:喬治華盛頓大學現代中國史副教授許臨君(Eric Schluessel)的新書《異鄉人之地:清帝國在新疆的教化工程》最近由台灣黑體文化推出。1月27日,黑體文化舉行《異鄉人之地》的新書座談會。許臨君教授向數十位讀者介紹了自己的新書,並與嘉賓、台灣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蔡偉傑對話,談美國中國現代史研究的情況,還回答了讀者的精彩提問。此次講座由黑體文化編輯涂育誠主持,《波士頓書評》整理,增加標題,分三部分發表。文字經由蔡偉傑教授審定。
專題 | 許臨君與美國“新清史”研究
喬治華盛頓大學副教授許臨君(Eric Schluessel)的新書《異鄉人之地:清帝國在新疆的教化工程》最近由台灣黑體文化推出。在他的同學、台灣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蔡偉傑看來,他的著作可以看做是美國“新清史”研究的第二代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