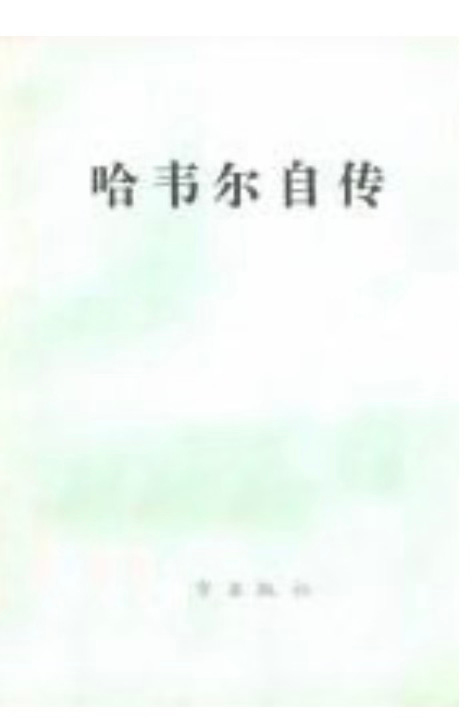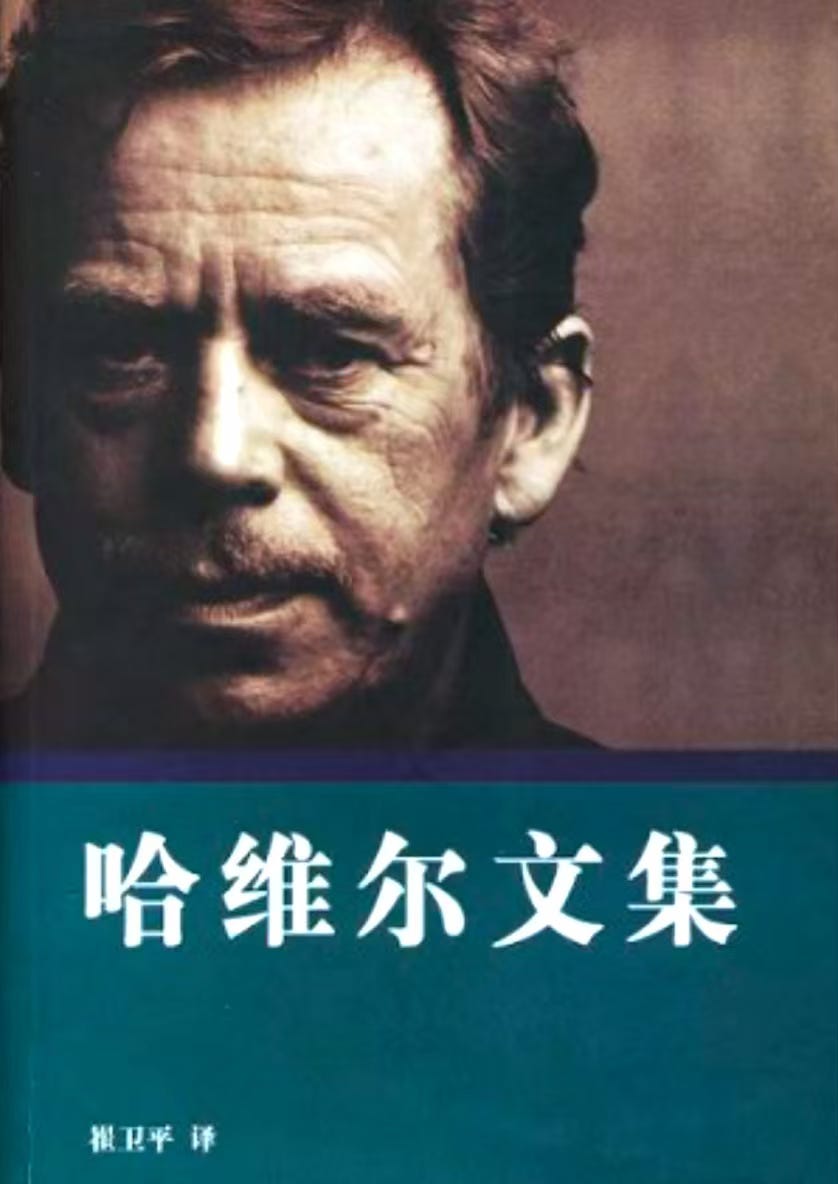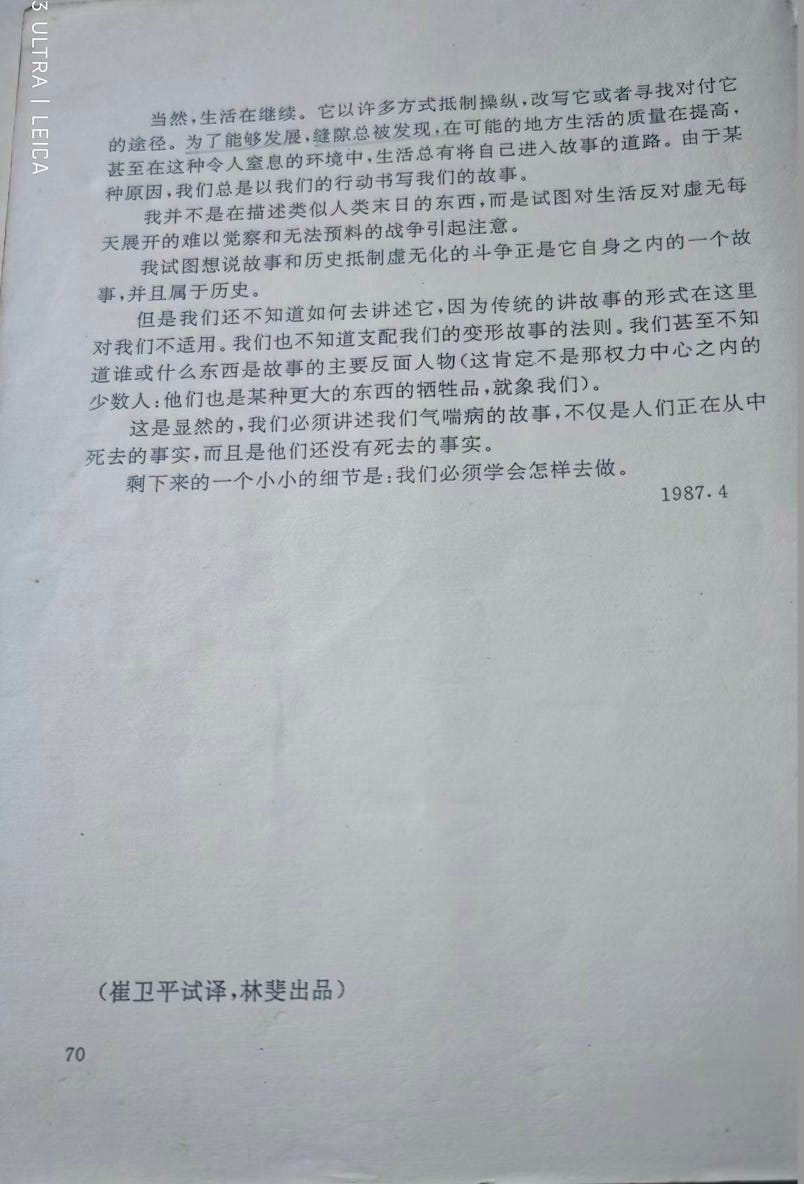書評特稿|哈維爾是如何傳入中國知識界並影響幾代知識分子的:part3 崔衛平教授訪談
編者按:哈維爾是如何傳入中國知識界,如何影響幾代知識分子的呢?這一直是一個謎。書評尋訪到了《無權者的權力》最早中文譯本(手抄本)的譯者劉康教授、採訪了香港《哈維爾選集》譯者羅永生教授和《哈維爾文集》譯者崔衛平教授,一起談論哈維爾在中文界的傳播與閱讀,以及對今天的我們的價值。昨天書評刊發了第一部分劉康教授訪談和第二部分羅永生教授訪談,今天刊發第三部分崔衛平教授訪談。未經許可,禁止轉載。
圖片說明:崔衛平教授近照
1989年6月4日,中國北京發生震驚世界六四屠殺,從此改變了中國民主自由化的道路。而就在同一天,波蘭團結工會在議會選舉中以壓倒性優勢擊敗執政黨波蘭統一工人黨,東歐民主化開始。隨後柏林墻倒塌、匈牙利去共產化以及立陶宛宣布獨立、蘇聯解體等一系列變化,最終東歐與蘇聯共產的結束。在此期間,1989年12月29日,東歐劇變開始後的首次捷克斯洛伐克選舉中,出獄七個多月的異議知識分子、劇作家哈維爾被選為捷克斯洛伐克總統。在當時,哈維爾對於中國知識分子來說,是一個陌生的名字。至今,因為審查原因,他的政論著作都未能在中國大陸公開出版發行。然而,幾十年來,哈維爾的著作和思想在中國知識界卻得到廣泛的普及和研究,得到了許多異議分子的共鳴,甚至被認為是無權者反抗極權中國的最有效的工具。但是,哈維爾是如何傳入中國知識界,如何影響幾代知識分子的呢?這一直是一個謎。
在中國大陸,到目前為止,除開1992年3月東方出版社出版過一本《哈韋爾自傳》(內部發行,發行量1500),2004年上海書林出版公司出版了《哈維爾戲劇選》之外,沒有出版過任何哈維爾的任何政論書籍。
在這個時期,在中國知識分子當中,有一份神秘的手抄本的中文譯本《無權者的權力》在小團體內流傳。翻譯者署名為:吳小洲、張婭曾、劉康譯,劉康校對。吳小洲是誰?劉康是誰?這份手抄本從何而來?多年來,一直是一個謎。
至今能找到的最早的中文哈維爾作品是1992年5月香港基進出版社出版的《哈維爾選集》。 1990年5月,流亡海外的劉賓雁為這個選集寫序《為<哈維爾選集>所寫的前言》,其中一位譯者羅永生教授為這本書寫序《哈維爾的“政治”》,在中文圈影響深遠的哈維爾文章《無權勢者的力量》最早便來自他的翻譯和這本選集。雨傘革命和香港革命爆發後,當時的學生運動領袖鐘耀華將這篇文章一字一字錄入電腦,分四期發表在2016年12月端傳媒上,號召人們重新閱讀和思考哈維爾,哈維爾的話“活得磊落真誠”最終成為香港人最後的反抗。
2003年,崔衛平出版的(的)《哈維爾文集》可以說是當代中國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在她和丁東、徐友漁等知識分子的推動下,哈維爾成為大陸知識界的一顆啟明星,影響了幾代知識分子的思考與寫作。雖然,《哈維爾文集》並沒有正式出版,甚至至今大陸也未出版過任何哈維爾的政論作品。有知識人評價說:在中國大陸,哈维尔是只有特殊渠道能读到,因此有机会看的基本都是同道了。那麼,哈維爾是如何在中國閱讀和傳播的呢?
書評尋訪到了《無權者的權力》最早中文譯本(手抄本)的譯者劉康教授、採訪了香港《哈維爾選集》譯者羅永生教授和《哈維爾文集》譯者崔衛平教授,一起談論哈維爾在中文界的傳播與閱讀,以及對今天的我們的價值。此為第三部分。未經許可,禁止轉載。
Part 3 崔衛平——《哈維爾文集》譯者:哈維爾思想建立在自我反省之上
在中國大陸,讓知識界熟知哈維爾的,首推崔衛平教授。1978年2月,崔衛平考入南京大學中文系,1982年本科畢業,1984年研究生畢業。此後在北京電影學院任教。早年,崔衛平做先鋒詩歌研究,九十年代初開始閱讀和翻譯哈維爾。不僅僅是哈維爾,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期至今,崔衛平教授還執著研究東歐思想和歷史,東歐異見知識分子的生活和思想,是國內東歐異見思想研究和傳播第一人。
然而有一個奇怪的現象,雖然哈維爾被中國知識分子所熟知,甚至許多人都援引哈維爾思想來作為自己思考,然而至今在大陸,未能正式出版一本哈維爾的政治著作。然而哈維爾在中國知識界的影響卻並不亞於寫了《極權主義起源》漢娜· 阿倫特。異議知識分子更是把哈維爾的思想作為最重要的思想武器,對抗現實中正在進行的極權體制。
哈維爾是怎麼進入中國,如何在知識分子中間傳播的呢?為此,書評採訪了通過郵件和電話採訪了崔衛平教授。
圖片說明:崔衛平與哈維爾。2009年在捷克「同一個世界國際人權紀錄片影展」(One World Film Festival)上,崔衛平與徐友漁、莫少平一道,為劉曉波與零八憲章簽署者領取Homo Homini人權獎,哈維爾為頒獎人。
問:您自己是如何遇到哈維爾的?
崔:在談我自己之前,我想先說兩撥在我之前翻譯哈維爾的人,人們還不怎麼說到這兩撥人。第一撥人就是那本手抄本,手寫的《無權者的權力》,這篇文章翻譯部分應該有5萬多字,我不知道它具體什麼時候出現的。 估計應該是六四之後,當時人們都在尋找精神出路,手稿後面有署名:吳小洲、張婭曾、劉康。這個手抄本可能在1990年或1991這段時間內,在一個圈子裡流傳。劉東在2000年之後才給了我。這是第一撥人。
還有一撥人就是在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以前的中央團校,主要是一個叫張勇進的老師。他應該是看到了這一份手抄本的複印件,他很感興趣,想进一步讀哈維爾,就請當時在海外的樂黛雲老師往國內帶哈維爾的書。樂黛雲老師至少帶了《生活在真實中》這本書。那個時候大家都很苦悶,正如哈維爾說的里面人說不出來,外面人看不見的這種氛圍,所以張勇進和他的朋友們从哈維爾这里感到了一種精神力量。其中組織者也包括青年政治學院的王東成老師,參與翻譯者有梁曉燕,還有吳思,張勇進本人也翻譯了。
此外,還需要提一下,1992年東方出版社已經出版了一本《哈韋爾自傳》。當時官方有擔心1989年以後,又重新回到閉關自守的狀態,要理解國際上情況,所以這個《哈韋爾自傳》有「內部發行」字樣的,有點像當時60年代做的灰皮書。這是在我接觸哈維爾之間的幾個情況,在我接觸哈維爾之前,對這些我都不了解。
問:那您自己是如何接觸到哈維爾的?
答:1993年,我從家裡書架上取下了一本英文書叫《open letters》。這是一本哈維爾文集,這本書是一個叫中文名字叫戴邁河的人留在我家的。他是加拿大人,研究中國詩歌。 1989年前後,他經常和中國年輕詩人在一起,經常來我們家。 1989年之後,他離開中國,把他的一批書,包括這本《open letters》,還有關於蘇聯解凍文學的一些書,把它們都留給在了我家。我後來也用過其中的一本,選譯了《戰後中東歐詩選》中的一些詩作。
我是中文係出身的,不以英文為自己的閱讀和工作語言,所以書留在家裡也沒太注意。有一天,百無聊賴,在書架上隨便拿書看,就拿了這本《open letters》。一眼就看到其中有一個句子說,他自己最多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他大概接受過馬克思主義的一點東西,但是從來沒有成為共產主義。因為共產主義包羅萬象的評論把世界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都說完了,而他的評論認為這個世界比共產主義者眼中的更複雜、更神秘。我又翻了一頁,看到書裡的作者說,他也許相信一點什麼?相信生活吧。這兩段話非常迅速地擊中了我,擊中我內心深處的一些東西。但是那個時候我沒有聽說過哈維爾,沒人跟我說過,也沒人告訴我,他是總統。如果有人告訴我,我可能就不會去看這個書了,因為我不知道我和一位總統有什麼關係。
我還記得那一天,我要出門,去接孩子,她放學回來吃完飯再送走上學之後,我就開始讀這本書,往前一翻,哇,是個總統,那不管了,反正我已經喜歡上他了。這是1993年。1994年,我在單位體檢查出患有肺結核,正好有一個機會可以有一個完整的時間坐下,不用上課,於是我就嘗試做一點翻譯。當時我的肺部感到很緊張,但是更加緊張焦慮的是我的頭腦,六四之後陷入一種完全失語的狀態,也是一種精神上的混沌狀態,因為無法理解眼前的世界而感到沉重悶氣。讀哈維爾的文字,讓我有大口呼吸的感覺,覺得重新找到了理解周遭世界的語言和框架。面對陌異的世界能夠獲得理解和精神上的秩序,這對我來說很重要,最初想到的並不是反抗。當然我也知道這個東西會有點敏感。
問:可是您翻譯的書2003年才出版?
崔:準確地說,這個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出版,是samizdat。
我給你慢慢說,我先要說到一些幫助過我的人。 1994年夏天開始坐下來翻譯,首先要提到邵燕祥老師,我覺得他給了我很好的鼓勵。邵燕祥1989年前是《詩刊》副主編,跟年輕人接觸比較多,對年輕人也好。我跟他談過我在翻譯哈維爾的事。記得當時還沒印出來,我把手寫的譯稿給他看過。我記得有一篇叫《故事與極權主義》,是邵老師告訴我說,極權的“極”字應該是極端的“極”,不是“集體”的“集”。還有一次,我遇到一個人名,我不知道是誰。我就模仿拼給他聽,他說這是哥特瓦爾德,就是1953年去世的捷共第一書記。他對我閱讀哈維爾嘗試翻譯哈維爾這個事情,始終採取積極鼓勵的態度。
你知道我當時身處在先鋒詩的圈子嘛。這個圈子一個特色就是稱之為“地下出版”(samizdat)。那時候,尤其1989年前,包括1989年之後,我們家郵信箱裡面隔三差五是花花綠綠,全國各地的詩歌民刊。那時候覺得在民刊上發表是特別榮耀的事情,等再出現在公開的詩刊,國家的文學刊物上,都覺得是昨日黃花了。因為有這個背景,我就很自然地想到把我的譯稿,試著印出來。 1995年時還沒有電腦,要到誊印社請人家錄進去,然後再修改。我不記得花了多少錢,但是我不久前我發現那本1995年的電腦印刷稿的後面有一個叫“林雯”的人“出品”。這個人我現在一點印像都沒有了,但我可以斷定這個人是肯定詩歌圈的,而且應該是他出的誊印費。
圖片說明2:誊印本封面
圖片說明2:誊印本封底
我很清楚記得印了60份,然後我就開始把這60份譯稿往外寄,給我能想得起來的人寄,大部分人沒有回音;有的給我打電話。給我鼓勵。最感興趣的人有兩個,一個是廣州的林賢治,他給我打了長電話,積極肯定哈維爾的思想意義。他當時手上有個刊物《散文與人》,是不是稍後還發表過一兩篇,我不記得了,但林先生這個人有一個名聲在外就是——他經常用自己寫的敏感稿子,把別的雜誌寫垮了;他自己的雜誌不發敏感東西。我記得1999年的時候,他就把《北京文學》第五期給寫垮了。還有一個給我積極鼓勵的人是河南的耿占春,詩評家,我一直很看重他,有思想,表達也很準確,很有才華。他也一直就哈維爾與我互動,包括推薦給他身邊的朋友。
我還記得給王蒙寄過,也不認識人家,寫一個作家協會的地址就寄出去了,沒有回音。
1997年春天,我去《讀書》開作者的座談會,在會上認識了徐友漁。這是我活動圈裡面第一個不在文學圈之內的人。我帶了一本給他。徐友漁一看就非常感興趣,他在後來哈威爾推廣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把我翻譯的這部分帶到了文學之外的圈子。徐友漁進入推廣哈維爾之後,我認識人也多了,我又把哈維爾拿去複印再往外寄。就在北師大校园里的誊印社複印的,我記得當時連複印加掛號信是11塊錢,就寄出一份,再重新複印、寄出一份又11塊錢。這個期間陸續又寄出去大概有20來本,加上之前複印的60本,大概八九十本吧。我自己後來也沒有了,前幾年,我在耿占春家,海南找到了這本原件,謝謝他珍藏這麼久。
大約這個時候美國黃貝嶺找到我,黃貝嶺手上有哈威爾著作版權。他來見唐曉渡,看到我翻譯的東西。黃貝嶺把我和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張勇進就拉在一起,說你們合作出版吧。這當然是好事。我和張勇進他們大概至少見過兩次面。一次是在當時捷克駐中國使館的文化參讚的公寓裡,我們跟黃貝嶺見面。還有一次就是張勇進有一次來我的電影學院的辦公室。我們談怎麼合作。我記得張勇進說他們翻譯的哈維爾沒有我翻譯的多,為什麼?因為哈維爾那本《生活在真實中》,這書不是很厚,其中有一半的內容,還不是哈威爾寫的,應該坐牢的時候,他的朋友們紀念他或者造聲勢,聲援他的文章。我跟張勇進有一篇翻譯重了,就是1975年哈維爾給胡薩克的那封信。
肯定是徐友漁提出,讓李慎先生寫一個序吧。所以實際上請李慎之寫序,最早是打算給我和張勇進他們合作出那本《哈維爾文集》的。那是1998年秋天,梁曉燕來我家送來了一批東西,包括羅永生老師翻譯的香港的版本,還有就是張勇進他們的翻譯。再加上我這邊的翻譯,好多紙片都沒裝訂,我就送去给李慎之先生。
李先生寫好了,打電話叫我去拿稿。那是1999年「五一」的時候,五一長假我回江蘇看父母時接到電話,李先生讓我某天某日去他的社科院辦公室拿他寫的序言。我一算日子,就是我從鹽城回北京的當天。那時候火車要十幾個小時到北京,下了北京站,我直接從北京站一路走到社科院大樓。我提了個行李,直接上了李先生的辦公室,李先生就把他寫好的序言給我。請他寫序言時,我也把東方出版社出版的《哈韋爾自傳》給了他。後來李先生把書還我的時候,書裡留有很多李先生用紅筆的勾勾畫畫,老先生讀得非常認真。李先生還教我這本《哈韋爾自傳》中的“哈韋爾”,應該譯作“哈維爾”,他並用口型示範“维”字給我看,他用上嘴唇蓋住下嘴唇那樣發音。後來聽說李先生在新華社做駐外記者培訓時,他是個超級好老師。當年沒多久,李先生就寄來了他的那篇《風雨蒼黃五十年》,寄到我們家的,我當時頓時覺得這是一個重要的思想事件。
順便地說,關於東方出版社的這本《哈韋爾自傳》,有一次我去到人民出版社總編輯薛德震先生的辦公室裡——東方出版社是從人民出版社派生出來的嘛——從他辦公室的書櫥裡取下了四本積存的这本小書,全部拿來送人了。這位薛先生是我的一位遠房親戚,八十年代討論人道主義馬克思主義時,他也是一個積極人物。加上邵燕祥先生,李慎之先生,他們當時都屬於年輕布爾什維克。這些故事告訴我們,在哈維爾轉播過程中,也有一些歷史能量傳遞到了我這裡,由我再把它們傳遞出去。
在拿到序言之前 ,我們就開始找出版社,我不太會做這樣的事情,主要是丁東幫忙找的。反正兩三家都沒成。賀雄飛當時在做“黑馬文叢”,賀雄飛說,他來做。然後他就把我們的書拿過去了,拿到內蒙出版社,也沒有跟出版社編輯說什麼,没提敏感什麼的,就給人家了。不管怎麼說,結果官方知道了,這應該是2000年春節的事情,大年初三,有關部門直接找到了編輯的家,當時年還沒過完呢,此時這本書已經到了三校的程度。這個消息傳來之後,我們就斷了這個夢,不去想公開出版的事情了。
問:2003年的《哈維爾文集》是怎麼出版的?
崔:又是“出版”,叫“印製”,好不好? (笑)2003年4月,李慎之先生因肺炎過世。當時是非典期間,大家不好去醫院告別,丁東發動大家寫文章,懷念李慎之,於是就有了一批文章。後來丁東就想把這批文章變成自印書,在2003年,他先印了《懷念李慎之》,应该是两卷本的上册。我跟丁東住得很近,他在新街口那邊,我就在小西天,自行車就可以來往。看到他印書我也想印,他說「好」。但是,他又說你不要弄別人的譯文,你只能用自己的譯文,應該是由我自己來承擔責任的意思。所以我就沒有用其他人的譯文。於是,當他印《懷念李慎之》下冊時,我就跟著他一起印《哈維爾文集》。在哈維爾開始傳播之後,我陸陸續續又譯了一些,平時我主要也在做別的事情嘛,文學評論詩歌評論什麼的,但是一有人提起這件事說這事有意義,我得到鼓勵之後,就會再譯一點。我就把後來譯译的這些加進來,就有了這本《哈維爾文集》,我也把李慎之的序放上去了。
我去拿序言的時候,李慎之先生還說:除了我的序,最好你和徐友漁兩個人也要有人再寫一篇。我轉身告訴徐友漁的時候,想都沒想,就把這句話變成了──友漁,李先生說,讓你也寫一篇序言,於是就有了徐友漁的那篇序。这書印出來的時候,在我們家又堆了一堆在那,我就開始送人。我家的車後備箱總放著一箱書,好送人。
記得那年秋天大約十月份吧,胡傑的《尋找林昭的靈魂》紀錄片出來,有一天下午在我們家“首映”,錢理群老師和丁東都來了,還有電影學院從事紀錄片的朋友,雙方為紀錄片的風格發生爭執,天還沒黑,我就宣布“散會”,也沒留飯,因為我家車裡整整一箱子書,當晚要送走。記得要送到南四環那邊的徐友漁家和許亦農老師家。那時候沒有導航,轉來轉去還迷路了。不過還好,我倒沒有因為《哈維爾文集》這本書而受驚動。
問:除了您的自印書之外,哈維爾有沒有其他途徑的傳播呢?
崔:那時候我們和丁東住得很近,丁東也在幫忙推薦哈維爾的東西。他熟悉許多編輯。例如他的朋友謝泳教授,當時主持《黃河》雜誌,在1998年第六期發表了哈維爾的《給胡薩克的信》和《說出真實總是有意義》,這兩篇將近25,000字呢,發在同一期上面。然後還有《莽原》也刊發過,《莽原》發的是“政治與良心”。還有《北京文學》1999年發了1萬字的《無權者的權力》的節選。這個時候還有一件值得記載的的事情。《上海文學》1998年(的時候)約我們寫稿,約徐友漁、秦暉和我一人寫一篇哈維爾和昆德拉的比較。最後秦暉沒交稿,就我和徐友漁在上海文學1998年第十期發了兩篇文章,專門談這個問題。這應該是在公開出版的刊物上,第一次公開談論哈維爾,並引進了哈維爾和昆德拉比較的這個角度。
2000年4月份的時候,我給南京大學李永剛用電郵發去了我自己翻譯的《哈維爾文集》中的部分,他創辦了中國第一個思想性網站——「思想的境界」。他很快就上傳在他的網站上。從他的這個網站,大家了解到網路不只發流行的那些東西,還可以發思想性的東西。很多人是從這個網站上了解哈維爾的。那時候也有網絡組織線下的論壇,有人約我去講哈維爾,有一段時間就好像沒有審查制度似的,什麼都可以說,至少雙方都在嘗試和探索新的底線。可以說,大約從1998年到2003年這段期間,有一個小小的「哈維爾熱」。我特別願意提到的兩件事情,第一,2004年胡佳第一次被警察帶走時,他隨身帶了這本《哈維爾文集》,在被關押的地下室裡一邊絕食,一邊從書中汲取營養;第二,聰明智慧的查建英有一次把這個沒有版權頁的書(看上去和一本真正的書一樣),帶到了她哥哥查建國的牢房裡。能弄出一本書來,讓被關押的良心犯得到精神上的支持和鼓舞,這是我覺得自己這輩子做的最值得的事情。
圖片說明:中國讀者根據網絡流傳的哈維爾文字自製圖書
問:那對你個人來說,為什麼東歐捷克他們的經驗或者他們的理論會特別吸引你呢?
答:這是一個好問題!跟你約好要談哈維爾這件事情之後,我一再問了我自己這個問題。我覺得有兩個因素:
第一,與我當時的頭腦配置有關係。哈維爾屬於戰後作家,他1936年生的,成長在戰後,處在一個現代主義文化氛圍之內,他寫的是荒誕派戲劇嘛。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我與許多文藝青年一樣,沉湎於現代主義文學藝術電影什麼的。簡單地說,所謂「現代主義」是兩次世紀大戰的產物,它傳達了一個很重要的東西,是“疏離感”,有著對於戰爭、英雄主義、宏大敘事、主流敘事、“時代最強音”那樣一種旁觀的态度,或者對於任何“乘風破浪”的東西,採取一種局外人的態度,我從加繆、薩特、陀思妥耶夫斯基、克爾凱郭爾,包括伯格曼的電影裡學到了這些東西。當然還有米蘭·昆德拉,喬治·歐威爾,都有對於稱為「正義」及其殘酷的深入反省。
說個實話吧,我沒怎麼參加六四遊行,是因為不喜歡「萬人大悲歡」這種東西,強烈的感情不適合我。這與我小時候目擊文革的經驗也有關,那時候我也是一個疏離者,小小的默不出聲的觀察者,對於在大街上發生的和流行的,抱有深深的疑懼。後來最喜歡的作家是加繆。在哈維爾的著作中,也正有著許多內省的東西,他的思想既是對於極權的揭露譴責,也是對於自身的反省,他提醒人們問自己——作為生活在這種制度下的個人是否要這樣繼續下去。而即使反抗,他也不想因為反抗而變成一座雕像,變得不會笑,尤其是不會嘲笑自己,他說那樣就寫不出第二個宣言來了。李慎之先生說哈維爾是“後現代”,繞來繞去的,但是,的確,既想與黑暗作鬥爭,又不想被黑暗所吞噬,可不是需要繞來繞去嘛,即需要很多限制與設定。
二與我的性格有關。不好意思說,我是一個比較率性而為的人,像我母親。我女兒說我母親是“神仙”,她彷彿行走在別人的目光之外,不理會別人說什麼,而只管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我沒有她的那個境界,但是也更願意聽從自己內心的聲音。我可以比較沒有負擔地拋開一些東西,比如不走學術體制的那種道路,寫那種面目可憎的論文,开那种极其无聊的会议,拿那種科研基金,得到那種獎勵,我完全不在乎,真的不在乎,彷彿自己有其他什麼神靈護佑似的。這就使得我能夠持續不斷地來完成這件事情。這樣的個性,就是蠻追求真實,也蠻追求自由的,不受那個束縛。但我也要說,這種追求自由的結果,就是我後來實際上遭遇了更多的限制。 (笑)自從1995年譯介哈維爾,到2004年開始被談話被監視跟蹤和傳喚,彷彿自由的天地沒有變大,而是變小了。 (大笑)但是一個人嘛,可以為自由而遭罪,不能為了不自由而遭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