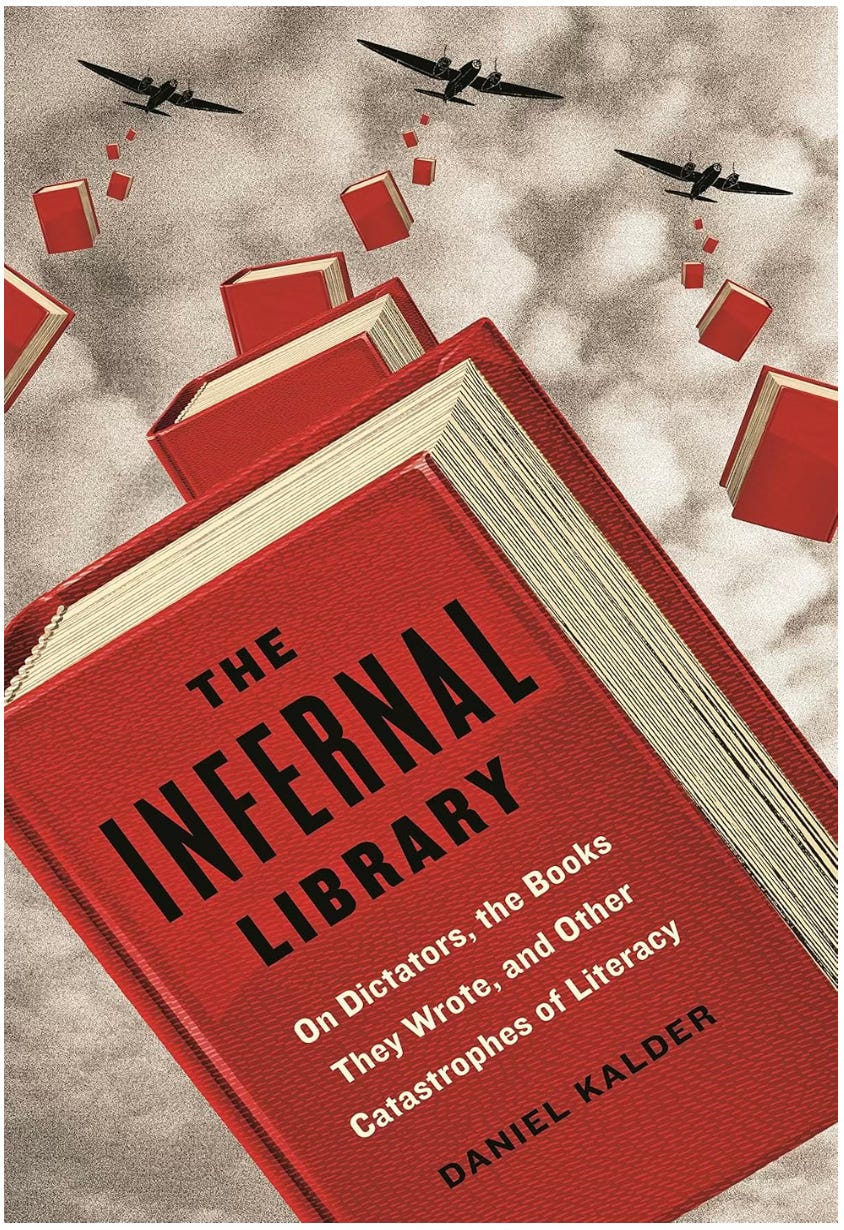編者按:丹尼爾·卡爾德的《地獄圖書館》以20世紀獨裁者(如列寧、希特勒、毛澤東)的著作為切入點,揭示語言如何在極權統治下異化為控制工具。卡爾德通過閱讀這些邏輯混亂、空洞冗長的「毒書」,分析其將閱讀從自由思辨扭曲為忠誠儀式,語言從溝通工具淪為權力延伸的機制,並探討獨裁者從「失敗作家」到強迫民眾接受其文本的心理轉變。學者徐賁強調該書不僅反思歷史上語言暴政的運作邏輯,還警示當代信息社會中算法、煽動性話語等新形式的語言控制,呼籲保持批判性閱讀與語言自由,以維護思想獨立與文明發展。
本文亦為徐賁專欄最新文章。
免費訂閱《波士頓書評》及相关事宜发送邮件:boshidunshuping@gmail.com,隨意打賞:Zelle,PayPal:boshidunshuping@gmail.com 用戶名:Boston Review of Books;長期支持請點擊下面訂閱,升級為付費訂閱。
《地狱图书馆》(The Infernal Library: On Dictators, the Books They Wrote, and Other Catastrophes of Literacy)是英国作家丹尼尔·卡尔德(Daniel Kalder)于2018年出版的一部独特非虚构作品,副标题为《论独裁者、他们写的书,以及其他文字灾难》。这部由Henry Holt and Company出版的著作,以一种既讽刺又严肃的笔调,深入剖析了20世纪那些臭名昭著的极权领导人——从列宁、斯大林到希特勒、墨索里尼,从毛泽东、卡斯特罗到卡扎菲、萨达姆——所留下的文字遗产。
卡尔德用"地狱图书馆"这一形象的隐喻,精准地概括了这些独裁者著作的本质特征。这些文本往往逻辑混乱、冗长乏味、重复空洞,然而正是因为其作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地位,它们却成为了亿万民众必须学习、背诵甚至信仰的圣典。在这种扭曲的现实中,阅读——本应是通向自由与思辨的桥梁——被彻底异化为灌输与压迫的工具。
更为可贵的是,卡尔德并没有满足于简单的批判和嘲讽。作为一名自称的"异议读者",他花费数年时间强迫自己通读这些"毒书",试图从内部理解它们的结构逻辑、修辞模式与影响机制。这种近乎自虐的阅读体验,让他得以从读者的切身感受出发,深刻反思文字是如何一步步成为暴力机器的有机组成部分的。
《地狱图书馆》展现出了非凡的洞察力。它揭示了在意识形态的绝对支配下,语言如何失去其本真的意义,却反过来制造出一种虚假而强烈的意义感。更令人深思的是,在那些权力结构尚未完全崩解、民众意识尚未彻底觉醒的灰色地带中,阅读行为本身发生了根本性的质变——它不再是个体的自主选择,而沦为集体顺从的仪式。这种语言、权力与身份认同之间复杂而隐秘的共谋关系,恰恰构成了极权专制的核心特征。
因此,《地狱图书馆》不仅仅是一部政治文学评论,更是一部深具思想史价值的著作。它不但为我们理解20世纪极权专制的文化机制提供了独特的切入点,更为当下关于后极权写作、身份漂移与语言失效等问题的探讨,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在一个信息泛滥而意义稀薄的时代,重新审视文字与权力的关系,或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和必要。
一 文字的蜕变与语言的专制
卡尔德最重要的论点之一,是指出这些独裁者的著作并非"思想"之作,而是"统治"之书。这一洞察揭示了极权主义文化生产的根本特征:文字不再承载思辨的功能,而是沦为权力意志的直接延伸。这些著作往往充满冗长的空话、重复的口号、逻辑的混乱,缺乏真正的分析和怀疑,却被精心包装成不可质疑的"真理文本"。
在这种语言的专制化过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词汇的内容被掏空,语言的指称功能被彻底颠覆。独裁者的文字不是为了描述现实,而是为了重新定义现实。"人民"不再指向具体的个体,而成为抽象的政治符号;"自由"不再意味着选择的权利,而被重新阐释为服从的义务;"真理"不再需要验证,而成为权威的同义词。这种语言的异化过程,实际上是对人类认知能力的系统性破坏。
更为深刻的是,这种文字的蜕变不仅仅是表达方式的问题,而是认知结构的根本性扭曲。当语言失去了其沟通和思考的本质功能,转而成为灌输、命令和控制的工具时,阅读者的主体性也随之消解。读者不再是文本的对话者,而成为文本的接受器;不再是意义的创造者,而成为意义的被动消费者。在这种语境下,文字从通向自由的手段堕落为强化奴役的机制,这种转变的彻底性和隐蔽性,正是极权主义文化统治的精妙之处。
然而,这种语言的专制化并不仅仅是历史现象,它在当代社会中同样存在着更为隐蔽的形式。在信息过载的时代,语言的碎片化、标签化和情绪化,同样可能导致思辨能力的退化。当复杂的社会现象被简化为简单的标签,当深度的思考被快速的反应所取代,当多元的声音被单一的话语所覆盖时,我们或许正在经历另一种形式的语言专制化。
因此,重新审视文字与权力的关系,不仅是对历史的反思,更是对当下的警醒。在一个信息传播日益便捷而意义生产日益稀薄的时代,保持语言的批判性和思辨性,或许是抵抗各种形式的文字专制的根本途径。这正是《地狱图书馆》给予我们的最深刻启示:真正的阅读应该是一种批判性的对话,而非被动的接受;真正的写作应该是对现实的质疑,而非对权威的复述。
二 作为服从仪式和驯服行为的“阅读”
卡尔德敏锐地指出,在极权和专制独裁政体中,阅读这些独裁者文本并非出于真正的兴趣或求知欲,而是一种政治义务的履行。斯大林全集、毛泽东语录、金日成著作、卡扎菲《绿皮书》或希特勒《我的奋斗》被强制学习与背诵,形成了一种深刻的"阅读的虚假性"。这种阅读不是为了理解世界的复杂性,而是为了在公共空间中展现忠诚与顺从,从而彻底消解了阅读本身所固有的批判性与个体化特质。
这种阅读仪式化的过程,实际上是对人类最基本认知活动的系统性扭曲。传统意义上的阅读是一种对话性行为——读者与文本、与作者、与自身经验进行多重对话,在这个过程中产生新的理解和批判性思考。然而,在极权语境下,这种对话性被彻底切断。读者不再是文本的质疑者和阐释者,而成为文本的复述者和传播者。阅读从一种主动的智识活动,退化为一种被动的模仿行为。
更为深刻的是,这种仪式化的阅读创造了一种虚假的共同体想象。当千万人同时诵读同一段文字、背诵同一套话语时,表面上形成了思想的统一,实际上却是个体思维的集体消失。这种看似壮观的集体阅读场景,掩盖了思想多样性的彻底丧失。每个人都在"阅读",却没有人在真正思考;每个人都在"学习",却没有人在真正质疑。
这种阅读方式的危险性在于它的自我强化机制。一旦阅读成为展示忠诚的工具,批判性思维就会被视为危险的异端。那些试图在文本中寻找矛盾、提出疑问的读者,不仅会面临政治风险,更会在心理上感受到巨大的道德压力。久而久之,自我审查成为一种内化的习惯,批判性阅读的能力在不知不觉中萎缩消失。
值得深思的是,这种阅读的仪式化现象并不局限于传统的极权社会。在当代社会中,我们同样可以观察到类似的现象:某些文本因为其权威性或社会压力而被强制性地"必读",读者往往更关注是否读过、是否能够引用,而非是否真正理解和批判。社交媒体时代的"打卡式阅读"、学术界的"经典崇拜"、企业文化中的"价值观学习",都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复制这种仪式化阅读的模式。
因此,重新激活阅读的批判性功能,成为抵抗各种形式文化专制的关键所在。真正的阅读应该是一种冒险的行为——它要求读者有勇气质疑文本的权威,有能力识别话语的陷阱,有智慧在不同观点之间进行判断。只有当阅读重新成为一种个体化的、批判性的、对话性的活动时,文字才能重新获得其解放的力量,而不是沦为奴役的工具。
这或许是《地狱图书馆》给予我们的最重要警示:在任何时代,保持阅读的独立性和批判性,都是维护思想自由的最后防线。当我们面对任何声称不容质疑的文本时,最好的回应不是盲目的服从,而是勇敢的提问。
三 权力与文本的共谋结构
卡尔德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悖论:恰恰是这些书的糟糕程度——它们的极端、虚假、荒谬、暴力、伪善、空洞、难以忍受——最直接地展现了权力的全能性。这些文本之所以能够广泛传播、大量出版、被奉为不朽的"圣典",并非因为其思想价值或文学成就,而完全是因为权力意志的强制推动,使它们得以凌驾于一切质量标准和理性判断之上。在这种机制下,"写作"不再是个体创造性的表达,而成为极权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语言的生产直接服从于权力的再生产逻辑。
这种权力与文本的共谋结构,揭示了极权主义文化生产的深层机制。在正常的文化生态中,文本的价值通过读者的自由选择、批评家的专业评判、时间的历史检验等多重机制来确立。然而,在极权体制下,这些自然的筛选机制被人为地中断或扭曲。权力直接介入文本的生产、流通和接受过程,创造出一套完全脱离质量标准的评价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文本的"伟大"和"英明"不取决于其思想深度或艺术成就,而取决于作者的政治地位和权力意志的需要。
更为深刻的是,这种共谋结构具有自我证明的循环逻辑。糟糕文本的广泛传播本身就成为权力威慑的一种展示:既然连这样明显缺乏价值的作品都能被强制推广,那么权力的触角究竟能延伸到何种程度?这种"以糟糕证明全能"的逻辑,实际上是对理性评判体系的公然挑战。它向民众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在绝对权力面前,任何客观标准都是无效的,任何个人判断都是多余的。
这种权力与文本的共谋还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生产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写作不再是为了表达真实的思想或情感,而是为了服务于权力的政治需要。作者——无论是独裁者本人还是其他被指派的写作者——都成为权力机器的一部分,他们的创作活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生产而非文化生产。这种模式的危险性在于,它彻底颠覆了文化与政治之间的正常关系,使文化完全沦为政治的附庸。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共谋结构在当代社会中同样存在着新的表现形式。在商业资本主义体系中,某些文本的成功同样可能与其内在价值无关,而更多地依赖于权力资本的推动、媒体的炒作、网络效应的放大。虽然这种商业化的文本生产机制与极权主义的政治化生产在性质上有着根本差异,但其背后都存在着权力(政治权力或经济权力)对文本价值判断的直接干预。
此外,数字时代的算法推荐机制也可能产生类似的效应。当文本的传播不再主要依赖于读者的主动选择,而是由算法根据某种预设逻辑进行分发时,我们同样面临着"权力意志"(此时是技术权力)介入文本流通的问题。虽然这种技术性介入在表面上显得中性和客观,但其背后同样隐藏着特定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考量。
因此,理解权力与文本之间的共谋结构,不仅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更是对当代文化生产机制的深度反思。在任何时代,当文本的价值不再由其内在品质决定,而是由外在权力确定时,我们都应该保持高度的警觉。真正健康的文化生态,应该是一个文本价值能够通过多元化、开放性的评判机制得到公正确立的生态。只有在这样的生态中,写作才能重新成为自由表达的行为,阅读才能重新成为独立思考的过程,而文字也才能重新获得其启蒙和解放的本源力量。
四 历史记忆与阅读“毒书”的必要
尽管这些文本令人深感不适,卡尔德坚持认为"必须阅读它们",否则我们将永远无法真正理解极权主义是如何通过语言这一看似无害的工具来构建和操控现实的。他以"异议阅读者"自居,以一种既反讽又严肃的姿态勇敢地进入这些"地狱文库",试图从中解剖语言暴政的深层机制。他发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警告:如果我们不正视这些文字历史,不去理解它们运作的逻辑,那么它们的幽灵很可能会借尸还魂,以更加隐蔽和狡猾的新形式重返当代政治舞台。
这种"毒书"阅读的必要性,实际上触及了历史记忆保存的根本问题。传统的历史记录往往侧重于事实的记述——谁做了什么,何时何地发生了什么事件。然而,卡尔德的工作提醒我们,仅仅记录外在的历史事实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深入理解那些推动历史事件发生的思维模式、话语结构和意识形态机制。这些"毒书"虽然在思想上贫瘠,在逻辑上混乱,但它们却是理解极权主义内在运作逻辑的珍贵"化石"。通过分析这些文本的修辞策略、论证方式、情绪动员手段,我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极权统治者是如何一步步瓦解理性思维、操控民众情感、重塑社会现实的。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毒书"阅读具有强烈的预警功能。历史的悲剧往往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以变异的形式螺旋式地回归。当代政治中的民粹主义话语、极化的意识形态对立、简化的敌我二分法、情绪化的政治动员,都可能在这些历史文本中找到相似的修辞模式和操作手法。通过深入研读这些"毒书",我们能够培养出一种"免疫力"——当类似的话语模式在当代政治中出现时,我们能够迅速识别其危险性,而不会被其表面的合理性或情感的煽动性所迷惑。
然而,这种"毒书"阅读也面临着巨大的伦理和心理挑战。正如卡尔德在书中坦言的那样,长期浸润在这些充满仇恨、谎言和暴力的文本中,对读者的心理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这种阅读不仅仅是智力上的挑战,更是道德勇气的考验。它要求读者既要保持足够的理性距离以进行客观分析,又要承受这些文本所传递的负面情绪和扭曲价值观的冲击。这种矛盾的阅读体验,恰恰体现了历史记忆保存工作的复杂性和艰难性。
在当代社会中,这种"毒书"阅读的必要性变得愈加迫切。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传播具有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用于洗脑的APP程序、各种极端思想和煽动性言论能够在很短时间内获得大量传播。在这种背景下,培养民众识别和抵抗有害话语的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效和方便。通过研读历史上的"毒书",我们能够建立起一套相对完整的"话语病理学"知识体系,为识别当代政治话语中的危险因素提供重要参考。
同时,这种阅读还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在许多国家,对极权主义历史的教育往往停留在事实层面,很少深入到话语和意识形态的层面。通过引导学生阅读和分析这些历史文本(当然需要在适当的指导和保护措施下),我们能够帮助他们更深刻地理解极权主义的本质,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历史敏感性。这种教育不是为了培养仇恨,而是为了培养智慧;不是为了延续分裂,而是为了防止重蹈覆辙。
因此,卡尔德倡导的"毒书"阅读,实际上是一种勇敢的历史担当。它要求我们不仅要记住历史的光明面,也要直面历史的黑暗面;不仅要传承人类文明的优秀遗产,也要深入理解人类堕落的深刻教训。只有通过这种痛苦而必要的阅读,我们才能真正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才能在面对新的挑战时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立场。这或许是《地狱图书馆》给予我们的最珍贵的礼物:它教会我们如何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如何在绝望中保持希望,如何在面对人性之恶时依然坚守人性之善。
五 失败的作家与成功的独裁者
卡尔德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许多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独裁者都曾怀抱着成为作家和诗人的梦想,但他们在文学创作上的失败,恰恰促使他们通过获取政治权力来强行实现"写作的胜利"。希特勒、毛泽东、卡扎菲等人在青少年或青年时期都曾试图成为艺术家或诗人,当这些梦想在正常的文学竞争中破灭后,他们最终将整个国家变成了被迫的"读者"。这种现象揭示了创作欲与控制欲之间深层而危险的心理关系,也反映了语言在现代政治中所呈现的"变态性"特征。
这种从"失败的作家"到"成功的独裁者"的转变,实际上暴露了一种扭曲的补偿心理机制。在正常的文学生态中,作家必须通过作品的内在价值来赢得读者的认可,这个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和脆弱性。优秀的文学作品需要深刻的洞察力、精湛的技巧、真诚的情感,更重要的是,它需要经受时间的考验和读者的自由选择。然而,对于那些在这种自然竞争中失败的人来说,政治权力提供了一条"捷径"——通过强制手段获得本应通过才华赢得的关注和"崇拜"。
这种心理机制的危险性在于它将文学创作的失败转化为政治控制的动机。当一个人无法通过正当途径获得文学上的成功时,他可能会试图通过控制整个话语体系来实现这种成功。在这种扭曲的逻辑中,如果读者不愿意主动阅读他的作品,那就强迫他们阅读;如果批评家不认可他的才华,那就消灭批评家;如果文学史不收录他的作品,那就重写文学史。这种从说服转向强制、从竞争转向垄断的心理转变,恰恰体现了极权主义的核心特征。
更深层次上,这种现象反映了现代政治中"表演性"和"叙事性"的重要作用。在传统社会中,政治权力主要通过暴力、血缘或宗教来合法化,但在现代社会中,政治权力越来越依赖于话语的构建和叙事的塑造。在这种背景下,那些具有强烈表达欲望但缺乏真正才华的人,往往会被政治舞台的巨大诱惑所吸引。政治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创作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他们可以将整个国家当作自己的"作品",将全体民众当作自己的"读者"。
这种错位还揭示了艺术冲动与权力冲动之间复杂而矛盾的关系。表面上看,艺术追求的是美和真理,权力追求的是控制和支配,两者似乎截然不同。但在某些心理结构中,这两种冲动可能共享着相同的根源:对关注的渴望、对影响力的追求、对不朽的向往。当艺术冲动无法通过正当渠道得到满足时,它可能会寻找其他的出口,而政治权力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看似有效的替代性满足途径。
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失败作家"现象在当代社会中同样存在着新的表现形式。在社交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有了表达和"出版"的机会,但这种机会的普及也加剧了注意力的竞争。那些无法在正常的内容竞争中获得关注的人,可能会转向更加极端、更加煽动性的表达方式。虽然他们可能无法获得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权力,但他们可以通过网络暴力、仇恨言论、极端观点来强制获得关注,这在某种程度上复制了"失败作家转向独裁者"的心理机制。
此外,这种现象也提醒我们反思现代社会中"成功"的定义和实现路径。当社会过度强调竞争和成功,却缺乏对失败的包容和理解时,那些在某一领域失败的人可能会寻找其他更加危险的补偿方式。因此,建立一个更加多元、包容的社会评价体系,为不同类型的才能提供不同的发展空间,或许是防止"失败作家"转向"成功独裁者"的重要途径。
最终,卡尔德揭示的这种错位现象,实际上是对现代文明的一个深刻警示:当文字的自由竞争被政治的强制垄断所替代时,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文学的多样性,更是整个社会的自由和尊严。真正的文学成功应该建立在才华和努力的基础上,而不是权力和强制;真正的政治领导应该服务于民众的福祉,而不是个人的虚荣和补偿。只有当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这种错位的危险性时,我们才能更好地保护文学的纯洁性和政治的正当性。
结语:
《地狱图书馆》揭示了文字与权力结合时的毁灭性力量。卡尔德的敏锐阅读向我们展示,极权主义如何将人类最基本的智识活动——阅读与写作——转化为心灵控制的工具。这部作品的核心价值在于揭露了语言暴政的完整机制:词汇被掏空意义,阅读沦为政治仪式,权力直接操控文本生产。当"人民"、"自由"、"革命"、"真理"等词汇失去真实内涵,成为权力操控现实的符号时,个体的主体性和批判能力便彻底瓦解。
更令人警醒的是,这种语言专制化并未随历史终结。在当代信息社会中,算法推荐、回音室效应等新现象正以不同形式复制着历史上的语言控制模式。"失败作家转向独裁者"的心理机制,在社交媒体时代有了新的表现——那些无法在正常竞争中获得关注的人,转向极端煽动性表达来满足虚荣心。
因此,《地狱图书馆》不仅是历史反思,更是现实警示。它提醒我们:真正的阅读应该是冒险行为,要求我们质疑文本权威,识别话语陷阱,在多元观点中独立判断。只有保持这种批判性阅读姿态,文字才能重获启蒙和解放的本源力量,而非沦为新的奴役工具。
在信息传播前所未有地迅速和广泛的今天,培养批判性阅读能力,维护语言多样性,建构健康文化生态,不仅是对历史的致敬,更是对未来的责任。这部"地狱图书馆"的最珍贵启示是:保持思想独立和语言自由,始终是人类文明延续发展的根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