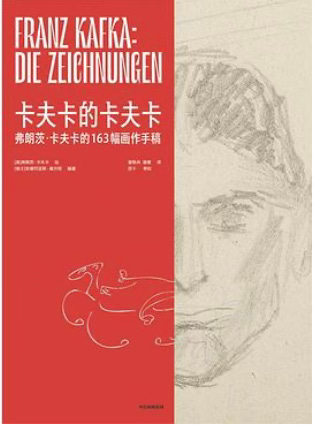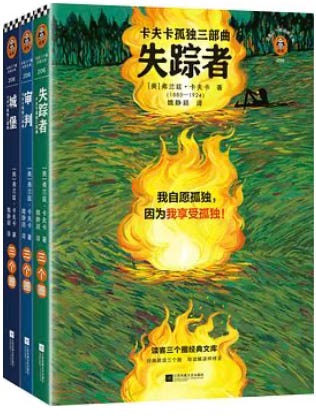徐兆正 | 想想卡夫卡!——关于《卡夫卡谈话录》的一些札记
編者按:6月3日為卡夫卡去世100週年,大陸出版界也出版了特別紀念圖書《卡夫卡孤獨三部曲》和手稿《卡夫卡的卡夫卡》。波士頓書評特別編發卡夫卡紀念專題。今天刊發徐兆正博士的《想想卡夫卡》,明天推出作家廖偉棠的《不變形的卡夫卡》。
“那么创作倾向于宗教。”
“我不想这样说,但它肯定倾向于祈祷。”
——卡夫卡
“这两人都没有自我的深刻的历史,没有危机和生死时刻,他们的思想并不就是一部传记,在康德那里只是他的头脑的历史,在叔本华那里只是其性格和对反映、对智力的兴趣的记录。叔本华的思想中没有冒险时间,没有传奇,没有灾难。想想帕斯卡尔!”
——尼采
一、“语言的应当性”与“主题的应当性”
在雅诺施(Gustav Janouch)记录的这些见缝插针的日常谈话里,卡夫卡关于创作,尤其是涉及到他人创作时的某些看法,是这本谈话录的主要价值。具体的人名也许并不关紧,因为但凡关系到这一点时,它们指向的都是卡夫卡本人关于写作的认识,其中既有肯定,也有否定。
否定的一面,主要见于他对达达主义、表现派以及阿波利奈尔等人的看法。如当雅诺施将德国达达主义领袖希尔森贝克(Richard Huelsenbeck)的一份报告拿给卡夫卡看时,后者径直点出了达达主义的命门:“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人的巨大渴念”。对王尔德的论文集《目标》,他同样持否定态度,他认为王尔德的写作犹如拿真理做游戏,他缺少一种静观与肃穆,因此也就无法揭示生活的本来面目。布罗德在《卡夫卡传》里有一段回忆,谈及大学期间他和卡夫卡在阅读旨趣上的分歧,后者其时“在真正的狂飙突进中欢迎一切奇异、放荡不羁、肆无忌惮、玩世不恭、无节制、夸张过火的东西”(如梅特林克的作品),卡夫卡对此则予以摒弃。为了说明他中意的东西,他引用了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的一句话:一座门厅里湿石头的味道。布罗德在书中回忆道:“他沉默良久,没补充什么话,仿佛这种暗藏的、不显眼的东西必定会不讲自明似的。”这类“隐于不言”的旨趣卡夫卡迹近贯彻一生,后来他与雅诺施的谈话同样显示了这一点:“这就是极其深刻的世界——只是悄悄地吐露心曲。”
卡夫卡极为看重语言的应用,无论是日常交谈,还是文学创作。当他看到别人写给雅诺施的辱骂信件时,先是“用指尖把它放到最远的桌边上”,随后才发表看法:“每一句骂人的话都是对人类最大的发明——语言的破坏。……因为说话就是斟酌并明确地加以区分。话语是生与死之间的抉择。”这是对卡夫卡排斥一切过火态度的进一步说明:因为我们在占用语言的同时便也遗忘了语言的真正归属(“它属于死者和未出生者”),所以每一个字都必须精确加以界定,伤害语言无异于伤害感情。在这本谈话录里,雅诺施对卡夫卡的“务求明确”另有记述:“他的语言由于内部的张力而显得有棱有角:每个字都是一块石头。他的语言的刚硬是由追求精确得当地表达的渴望造成的,因此,他的语言的这一特点不是由被动的群体特点,而是由主动的个人性格决定的。”我发现,在布罗德那里同样也有着对卡夫卡性格中执著于精确一面的追忆。譬如他不仅在谈话中有意地界定每一个字,还频繁地表达对他人做出决断的钦佩。这种精确并非来自胆怯,它反映的是卡夫卡性格中极为坚定的那一面,要我说,即是对不可动摇的、不可摧毁的真理的信仰。
谈话录里有一组非常具象的对比:雅诺施给卡夫卡带来一期载有阿波利奈尔长诗的杂志,他的态度恰如布罗德所说:“凡是使人感到是杜撰出来的,是效果显著、有才智、有艺术性的东西,他一概摒弃。”因此,虽然他称阿波利奈尔为能手,其时尚不满二十岁的雅诺施已然感觉其中暗含保留。果不其然,他随后就给出了对这类“艺术性”作品的总的判断:“我反对任何一种熟巧。能手由于有骗子的熟练技巧而超越于事情之上。但是,一个作家能超脱事物吗?不能!他被他所经历、所描写的世界紧紧抓住,就像上帝被他所创造的造物紧紧抓住一样。为了摆脱它,他把它从身上分离出来。这不是熟巧行为。这是一次诞生,一次生命的繁殖,与其他任何一种诞生一样。您听说过,妇女是诞生孩子的能手吗?……熟巧是给骗子保留的。没有艺术家的地方,这些骗子就出来活动。”
由此观之,卡夫卡对语言精确性的理解,即是对“语言应当性”的确信。他拿出一本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的小说,说道:“他的一生是在人和命运之间幻影似的紧张关系的压力下度过的,他用明确无误的、大家普遍理解的语言照亮并记述了这种紧张关系。”“语言的应当性”又来自于对“主题应当性”的认识,在后面的谈话中他多次谈到这个问题:“主观的自我世界和客观的外部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人和时代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一切艺术的首要问题。”布罗德认为卡夫卡“从不用寓意的手法,但在象征性方面却达到很高境界”,是他的解人之语:“寓言”仅仅代表了单方面的一个终点,象征却同时处在两个层面:我们对个别性的把握越是深入,也就越是能够照亮经验中的普遍性。布罗德对寓言与象征的比较,其实也进一步言明语言和主题在卡夫卡那里的关联。如同一羽箭矢,如要射向永恒,就必须将目标瞄得更高更远:“形式不是内容的外在表现,而是它的刺激,是通向内容的大门和道路。这种刺激发生了作用,隐蔽的背景也就显现出来。”
二、指向救赎的“文学行动”
意识到卡夫卡的写作不仅仅是“写作”很有必要。因为“卡夫卡的注意力不是放在作品上,而是放在写作上”(彼得-安德列·阿尔特《卡夫卡传》)。阿尔特所说的写作是一类行动,但就像卡夫卡对雅诺施倾诉的那样,它是一项更“倾向于祈祷”的行动,而非纸面的擦写。同时,倘若我们把以下几位作者请将出来:帕斯卡尔、克尔凯郭尔、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维特根斯坦——大抵就会看出写作乃是他们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卡夫卡亦是如此。他曾在日记里写道:“人类有两大主罪,所有其他罪恶均从其中引出,那就是:缺乏耐心和漫不经心。由于缺乏耐心,他们被驱逐出天堂;由于漫不经心,他们无法回去。”说出这番话的人还是一个作家吗?我不讳言自己正是如此看待卡夫卡的:当他把艺术看作是一次祈祷,祈祷是对神圣生活的澄清,或者说当他战战兢兢地占用语言以“体验”人与命运之间的紧张关系,行动的写作与宗教的祈祷在他那里就成了一件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目光经由他的写作转入下一处时,那个临近之点只能是救赎。
人类何以获得救赎?卡夫卡无疑对人类的真实处境有着深刻理解,诚如他对律法的最终总结:“……也许只有一个主题:缺乏耐心。由于缺乏耐心他们被驱逐,由于缺乏耐心他们回不去。”在他眼中,人类始终在缺乏耐心的狂信与缺乏耐心的不信之间摇摆不定,所以他又是如此强调耐心的必要:我猜测这份认识来自他对犹太人处境的思考。有一次他和雅诺施在老城环形街道散步,他在一座犹太会堂前停下来,然后略显突兀地由这座建筑谈起了犹太人的问题:“犹太教堂现在已经低于街道。然而人们还在继续干下去。他们将消灭犹太人,企图以此摧毁犹太教堂。”本书还有一处不起眼的谈论,涉及的内容看似是雅诺施的琐事,但仍然包含着他对犹太人必须保持忍耐的看法:“这是一个重大的胜利。迫使敌人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也许是我们能达到的最大胜利。因为我们不能期待彻底消灭恶势力。彻底消灭恶只能是荒唐的梦想,非但不能削弱恶,相反只能增强恶的力量,使它更快地发生作用,因为有了这种幻想,人们就会看不见恶的真实存在,把现实编织成自己的、充满迷惑人的愿望的想象。……摧毁恶的梦幻只是一种因失去信仰而产生的变成画面的绝望感。”在后来经犹太思想家施特劳斯对前启蒙思想与启蒙思想作出的区分里,同样有着这层认识。
由布罗德整理的笔记《对罪愆、苦难、希望和真正的道路的观察》,是卡夫卡唯一一次对那种不可动摇的、不可摧毁的真理——抑或是他所理解的救赎——进行的诠释。但他又显然不认为我们能够通过定义而把握真理。这似乎不是一个可以描述的问题,而仅仅是体验,是认清、奔向与经历之事。一劳永逸地给出定义,如同执一根看不见的拐杖,但“真理总是深渊”。不过,正因为他又“相信一个绝对的世界”(“上帝,生活,真理——这些只是同一件事实的不同名字”),他才会在人世的旨趣与俯仰的观察之间反复穿梭,也才会变换着看似懦弱与实则坚定的两副面孔。卡夫卡一生都致力于用写作沟通这不可兼容的两者,他的身上散发着因激烈的自我否定与努力接近神性对峙产生的光芒。布罗德认为文学写作是他“与生俱来的力量的正确使用”,这一点非常感人,尤其是当布罗德引用塔尔丰拉比《先辈箴言》中的一句格言来纪念这位朋友时:“你不善于完成这项事业,但你还是不可以避开。”于是我们发现,恰恰是文学行动的祈祷本质,将他最终引向了这样一个悖论:对自己的作品全盘否定。
昆德拉批评过布罗德对卡夫卡进行了“卡夫卡化”的歪曲,然而昆德拉是否想过,这一“歪曲”的种子,此前正暗藏在卡夫卡的作品之中?雅诺施对卡夫卡人格的看重(“我所认识的活生生的弗兰茨·卡夫卡博士比他的书、比那些被他的朋友马克斯·布罗德拯救出来免于毁灭的书伟大得多”),庶几与他记述的卡夫卡对惠特曼的意见一致:“我对他的作品的了解比不上对他的生活的了解。因为生活就是他的主要作品。他写的东西,他的诗和文章,只是一个坚定地生活和劳作的信仰的火把留下的闪着火星的灰灶。”——对这位“布拉格波希米亚王国工伤事故保险局职员”来说,既然信仰不单纯是认识,它还势必要过渡到行动这个阶段(若非如此,便不足以获得拯救),那么这种从信仰出发的“文学行动”,其重心就落实在“行动”之上。
他在《致父亲的信》中谈到了婚姻问题:“结婚成家,生儿育女,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上抚养儿女,甚至还加以引导,我坚信这是一个人所能达到的极限。乍一看,许多人似乎轻而易举地做到了,这并不足以引为反证,因为首先,真正做到的人为数并不多,其次,为数不多的成功者大多并非主动‘为’之,这些事只是‘发生’在他们身上了;这虽然不算那个极限,却也十分了不起,十分光荣了(尤其因为‘为’与‘发生’并非泾渭分明的)。话说回来,问题根本不在于这个极限,而只在于某种体面的遥相呼应;要取暖不必飞到太阳中心去,钻到地球上的一小块干净地方,阳光时不时地照进来就行了。”这是一个例证——它证明了行动之于卡夫卡不仅有写作这一种方式,婚姻同样是有所承担的示范,是一个对人类如何获救的演示。
三、跨进法的大门
小说《审判》的《在大教堂里》一章,神甫对K讲述了这么一则故事:“在法律的引言中,讲述着这样的错觉:在通往法的大门前站着一个守门人。有一个从乡下来的人走到守门人跟前,求进法门。可是,守门人说,现在不能允许他进去……”如果说卡夫卡对人类处境的认识起源于他对犹太人处境的思考,那么这个“法”肯定就不是简单的人间法律。以下当然仍是我的推测:
卡夫卡所说的“法”,或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提出的“自然法”;它与阿奎那沿袭亚里士多德区分的四种律法更为接近(永恒法,自然法,人类法,神圣法)。在这个被称为《在法的门前》的故事中,法之为大门,根源在“永恒法”——上帝统治万物的法;表现为“自然法”——被人类认识的“永恒法”;乡下人则被代表“人类法”的守门人拒绝——现实社会中“自然法”的具体实践;最后,乡下人所以对跨进法的大门念兹在兹,是因为他还有着信仰“神圣法”的意志。小说结尾之黯淡,毋宁说是缺乏“见识”的乡下人被充满“见识”的“人类法”,抑或“人类法”的执行者玩弄。不过,“永恒法”不仅不否决,还紧密地关切着人类的获救。至此,我们再一次看到了荆棘与光亮同在的卡夫卡式困境。卡夫卡始终面对着巍然紧闭的法的大门,但他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凭借诉诸体验的预备行动,凭借着耐心,这扇门最终是可以向我们敞开的。
因此,这句话或许可以作为卡夫卡唯一的格言:跨进法的大门,然后成为这个地球上充分有效的公民。
2015年4月17日写
2024年3月25日修订
卡夫卡的卡夫卡
卡夫卡的卡夫卡 作者: [奥]弗朗茨·卡夫卡 / [瑞士]安德烈亚斯·基尔彻 / [美]朱迪斯·巴特勒 / [瑞士]帕维尔·施密特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团 出品方: 春潮Nov+ 副标题: 弗朗茨·卡夫卡的163幅画作手稿 原作名: FRANZ KAFKA: DIE ZEICHNUNGEN 译者: 曾艳兵 / 曾意 出版年: 2024-1 内容简介 ◈ 卡夫卡逝世100周年重磅纪念,迄今最完整的163幅画作手稿,中文世界首次出版 作这些画是多年以前,它们当时给了我无与伦比的满足感。——弗朗茨·卡夫卡
卡夫卡孤独三部曲(全3册)
卡夫卡孤独三部曲(全3册) 作者: [奥] 弗兰兹·卡夫卡 出版社: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品方: 读客文化 副标题: 长篇小说全集(含失踪者、审判、城堡) 译者: 魏静颖 出版年: 2024-5-15 内容简介 我自愿孤独,因为我享受孤独! ----------------------- 编辑推荐: ●卡夫卡逝世100周年纪念套装!包含《失踪者》《审判》《城堡》的长篇小说全集。 ●卡夫卡一生描写的主题都是现代人的孤独。家庭孤独、社会孤独、面对陌生世界孤独……每一个内心充满焦虑、迷惑、困扰,但又无可奈何、找不到出路的人,都能狠狠共鸣!
卡夫卡谈话录
卡夫卡谈话录 作者: [奥] 弗朗茨·卡夫卡 口述 / [捷] 古斯塔夫·雅诺施 整理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译者: 赵登荣 出版年: 2024-5 页数: 272 定价: 55.00 内容简介 【编辑推荐】 1.卡夫卡与忘年交的谈话记录,媲美《歌德谈话录》。 2.从文学艺术到为人处世,从思想困境到社会现实……布拉格街道上和办公室里无所不谈的交流,真实记录下卡夫卡思想的闪光点和人生境况。 3.北大德语系教授、资深翻译家赵登荣经典译本,著名学者、卡夫卡研究权威叶廷芳专文导读。 4.特别收录卡夫卡罕见画作与详尽卡夫卡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