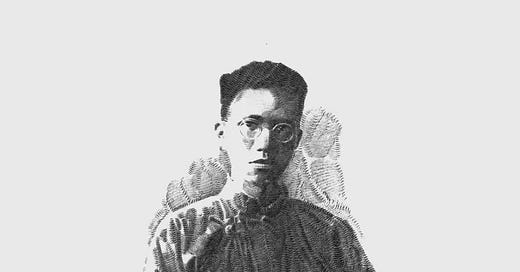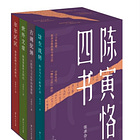访谈|张求会:陈寅恪警示过的那些问题还未解决
编者按:1994年,还在华南师范大学读研究生的张求会,征得业师管林先生的同意,把研究义宁陈氏诗歌确定为毕业论文的选题,从此三十年,张求会教授一直致力于陈寅恪及其家族研究:2000年出版《陈寅恪的家族史》;2024年《陈寅恪四书》出版。用张教授本人的话说:“此后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我都和陈先生在一起,即便偶尔走开,走得也不远,总和他的亲朋故旧挨着连着。”
张求会教授研治陈学多年,素以钩沉史实见长,辅诸趋谒请益或亲身经历,将纸上所得与个人体悟熔冶于一炉,在细笔勾勒、发覆祛疑的同时,写就一段段不诬前贤、不误来者的信史。他的研究往往从陈寅恪的个人经历与时代背景结合出发,不仅将陈寅恪生平研究细致化,更是将其置于近现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宏大语境中,分析陈寅恪的学术成就与文化意义。“他的研究为后人提供了一个较为立体的陈寅恪形象,既展现了其学术成就,更反映了陈寅恪作为知识分子在动荡年代的坚守与挣扎”。张求会教授认为:“一生负气”是陈寅恪自我认可的形象标签,它一再提醒人们,这是一个从来不屑于说违心话的孤傲者。
近日,随着《陈寅恪四书》出版,张求会教授接受了书评采访。
书评:香港学者陈君葆和陈寅恪在许多方面理念不同,却为何对陈寅恪一直关爱有加?陈寅恪与竺可桢同班又同桌,他真的会向老同学当面批评华罗庚吗?
张求会教授:陈君葆先生与陈寅恪先生抗战时期在香港大学成为同事,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介绍他们认识的,可能是同在港大任教的许地山先生。许地山在世时,是二陈交往的重要枢纽。许地山去世后,陈君葆对陈寅恪的敬重、关爱丝毫没有减弱。1949年新中国成立,陈君葆表现出对于新政权的热烈拥护和坚定支持。陈君葆的四个子女,有三个返回内地参加工作,其中一个儿子还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可见他对新中国的拥护和支持是发自内心的,并不是什么投机行为。正因为如此,陈君葆对于陈寅恪的一些“落后”言行(包括其文章)是不认同的。但这并未影响他在代购药品等方面给予陈寅恪极大的、持久的帮助,即便在日记中偶尔也会有不胜其烦的零星记载。
陈君葆对陈寅恪一直关爱有加的原因,我尝试着概括了三点,不一定恰当,姑且抛砖引玉。三点原因是:首先,关爱陈寅恪这位“国宝”级大师,几乎是当时学界的共识;其次,陈君葆待人真诚,特别爱帮助人;再次,二陈之间没有深交,反倒容易维持朋友关系。
说起关爱陈寅恪,不能不提傅斯年。傅斯年尽管有时对陈寅恪十分不满,但在关键时刻始终施以援手,因为认定陈寅恪属于百年难遇的奇才,必须为国家为民族留存这样的读书种子。陈君葆对陈寅恪的关爱,最重要的原因也是这一点。陈君葆特别爱帮助人,人缘非常好,这也是不少朋友及其家人喜欢陈君葆的重要原因。举个例子:1942年5月初,陈寅恪一家即将离开香港秘密返回内地,不巧陈君葆的弟弟被日本宪兵部关押起来,在奔走营救、万般煎熬之际,陈君葆依然牵挂着陈寅恪远行之事,一连三次到陈家准备入住的旅馆去探视,虽然每次都扑了空,依然想最后再见上一面。因此,我在书中感叹:“笃于友情,常人难及。”(《陈寅恪四书·古调犹弹》,第162页)此外,陈君葆与陈寅恪并无深交,加上大多数时间两人分隔两地,从未发生任何正面冲突,而在经济条件和办事能力方面,他比陈寅恪更具有优势。简而言之,二陈是朋友,甚至称得上患难之交,但不能算挚友或知己。
陈寅恪与竺可桢1908年曾在复旦公学同学一年,不但同班,而且同桌。关于陈寅恪当面批评华罗庚的说法,来源于竺可桢1957年2月18日的日记。原文是这样的:“渠意颇不以华罗庚为然,说其过去曾建议蒋介石成立科学青年团,认其有创造能力,但其言论作风之味不佳云。”(《陈寅恪四书·古调犹弹》,第374页)这段话里有三个“其”,除了个别学者认为第一个“其”指代陈寅恪、第二和第三个“其”指称华罗庚外,绝大多数人都会认为三个“其”指代的全是华罗庚。换句话说,陈寅恪确实当面向老同学竺可桢批评过华罗庚的为人。
我们知道,陈寅恪一生献身学术,是一个十分纯粹的学者,从来不曾主动介入政党之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给自己定下了不臧否人物的规矩,以免招惹是非。陈寅恪和华罗庚应该没有个人恩怨,之所以向老同学吐槽,估计是华的某些言行突破了陈的底线。这条底线,就是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里写下的那段名言:“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陈寅恪著《元白诗笺证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5页)华之“创造能力”,有口皆碑;但他在不同时代的某些表现,显然无法得到陈的认同。这应该是陈对华不满的主要原因。
书评:中国读者说起陈寅恪,最深的印象莫过于他在王国维纪念碑铭中写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古调犹弹》所收六篇文章,以夏鼐、刘节、郑天挺、陈君葆、梁方仲、竺可桢等六位学人的日记为原始材料,我好奇的是,在朋友亲人的日记和书信中,陈寅恪是一个什么形象?还是一个严肃思考的学者形象吗?
张:这十个字,有学者评价为“十字箴言”。其意义和价值,绝不仅仅局限于读书人如何安身立命。只要提到陈寅恪,一代代读者的第一反应几乎都是这十个字,可见人心不死、文字有神。人们一直好奇,能够写出如此文字的人,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存在?人类有造神的传统和喜好,不知不觉间陈寅恪也一次次被神化了。北大李零教授有一本书《去圣乃得真孔子》,我很喜欢这个书名,因为同样适用于陈寅恪研究。
日记的私密性、真实性、即时性,决定了它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古调犹弹》以六位学人日记作为原始材料,让读者在原汁原味的文字中发现另一个陈寅恪。比如,1934年夏鼐选修了陈寅恪的“晋南北朝隋史”这门课,考试得分是S+,陈寅恪的评语是:“所论极是,俱见读书细心,敬佩!敬佩!”(《陈寅恪四书·古调犹弹》,第11页)这样的评语,值得今天的导师们学习学习,因为真性情任何时候都是可爱可敬的。夏鼐在1937年某日的日记里还记载了一件趣闻:陈寅恪在德国留学时,曾经被人用段子编排过。有人套用《儒林外史》的句法,说“赵元任雍容大雅”,“徐志摩文采风流”,“陈寅恪呆头呆脑”,“罗志希怪模怪样”。“俞大维有一次请客,陈寅恪央求排座位的人,不要将他排在女人旁边。”(同前,第14页)年轻的陈寅恪,一方面知识渊博、志向高远,另一方面在异性面前内向、害羞,明显具有今人所称“社恐”的行为特征。这样的陈寅恪,比起“十字箴言”光环下的那个老学究,明显地更接地气,令人在忍俊不禁之际又怜又爱。
再说陈君葆日记。1942年4月22日,陈君葆派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的两位工作人员给陈寅恪家送去大米16斤、罐头肉7罐。两名工作人员回来告诉陈君葆,陈寅恪“已挨饥两三天了”。(同前,第158页)这次救助,无异于雪中送炭。过了几天,4月27日,陈寅恪亲自送给陈君葆“衣料一件、信笺一盒”(同前,第159页),显然是对数日前受赠食物的回馈。一来一往间的患难真情,也能把陈寅恪从神坛上拉到人世间——他也是很讲人情世故、懂得知恩图报的。1957年5月11日,陈君葆受邀来广州开会,顺便看望了陈寅恪、陈耀真、陈国桢等老友。闲聊时说起当天上午粤剧名角红线女发言用北京话——“很标准的北京话”,陈君葆称她真是“绝顶聪明的女子”,陈寅恪太太唐筼说她能讲话,“我也讲不过她”,陈寅恪接过话题:“这自然咯,唱戏的不会讲话,谁会讲话呢?”(同前,第196页)别人怎么看这番对话,不好瞎猜,我总觉得夫妇二人这一回颇有些“八卦”。其实,友朋间的这类玩笑话根本就无伤大雅,既然是闲聊,没有一点八卦精神,也就寡淡无趣了。
除了《古调犹弹》,我在《世外文章》里还披露了唐筼写给大姑子陈康晦的三封信,也属于和日记性质相同的私人文献。唐筼的信,无论用词,还是语气,较之陈寅恪写给弟弟方恪的信,更加亲切、温婉。唐筼在信里不止一次提到给康晦汇款的事,恰可和她的三个女儿的回忆形成互证:陈寅恪每月领到工资后,第一件事就是提醒家人:“别忘了给康姑寄钱啊!”1962年,陈康晦病逝,唐筼和女儿们一直没敢将消息告诉陈寅恪。(以上详《陈寅恪四书·世外文章》,第208-214页)说白了,陈寅恪也是平凡人,注重亲情、友情,痛恨背叛、欺骗,和常人没有两样。类似的点点滴滴,共同塑造了一个书斋之外的陈寅恪。将伟人陈寅恪、常人陈寅恪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真实的陈寅恪。
书评:陈寅恪在披阅父执陈衍的《宋诗精华录》时留下了哪些精彩点评?
张:陈衍(号石遗)是陈三立的诗友,晚清“同光体”诗派最重要的理论家,属于陈寅恪的父执。陈寅恪当年在《宋诗精华录》上留下批语,其本意肯定不是为了发表。后人披露这些批语,绝不是为了制造噱头,而是挖掘其中蕴含的文学及史学等方面的价值。就陈寅恪研究而言,至少可以借而管窥陈寅恪的诗学主张。这篇文章(《陈寅恪手书〈宋诗精华录〉批语辑注》)最早发表在2006年第1期《文学遗产》,此次略作修订,收入《陈寅恪四书》第三册《世外文章》。您的问题,提醒我重新作了一次统计,结果如下:19条批语中,只有1条(第17条)是正面肯定的,其余18条都以负面评价为主——有些措辞甚至称得上“酷评”“辣评”。
第1条,针对陈衍为《宋诗精华录》而写的叙言,陈寅恪的批语是:“此数语有所指。其实近人学宋诗者,亦非如石遗所言,大抵近体较佳,七律尤胜,乌睹所谓‘仅有土木而无丝竹者’耶?石遗晚岁颇好与流辈争名,遂作此无的放矢之语,殊乖事实也。”(《陈寅恪四书·世外文章》,第58页)开宗明义,这里所批评的与事实不符,恰好体现了陈寅恪的史家本色。第2条,针对帝㬎《在燕京作》而作:“此诗疑是伪托。若果伪托,则评语殊无谓矣。”(同前,第60页)表达的仍是以史实为首要标准的品评取向。第5条,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元微之亦‘熏心富贵’之人,其《遣愁怀三首》却极沉痛。”(同前,第64页)换言之,字面人格与真实人格有时并不一致,千万不能掉入陷阱。王安石《明妃曲二首》作为名篇,也被陈衍收进了《宋诗精华录》,他的评语同样引起陈寅恪的不满,留下了一条篇幅最长的批语(第6条),批评最严厉的依然是史实有误这类硬伤:“欧阳永叔《居士集》卷八《和介甫〈明妃曲〉》二首皆仁宗嘉祐四年所作,即介甫原诗亦作于嘉祐之确证。其时神宗未为君,介甫未为相,‘低徊’二句何得谓‘汉帝之胜于神宗’?‘汉恩’二句亦何得有‘与我善者为善人’意?故说诗而不考史,未有不流为臆说者也。”(同前,第66页)说诗首重考史,方可避免臆说,这大概是史家陈寅恪评诗的最大特色。
1919年,吴宓在哈佛第一次见到陈寅恪,就深深折服于其学识之渊博:“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吴宓诗话》,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96页)这一点,在陈寅恪留于《宋诗精华录》之上的批语中也有体现。比如第3条,陈衍认为郑文宝《阙题》一诗(“亭亭画舸系寒潭,直到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与风雨,载将离恨过江南。”)“首句一顿,下三句连作一气说,体格独别”。陈寅恪不以为然:“此诗首句及第二句为一节,第三句、第四句为一节,并非第二、三、四句‘连作一气说’也,何谓‘体格独别’耶?”(《陈寅恪四书·世外文章》,第61页)第4条,欧阳修《丰乐亭小饮》第五、六句:“看花游女不知丑,古妆野态争花红。”陈衍原评是这样的:“第六句写得出。第五句以太守而说游女之丑,似未得体,当有以易之。”陈寅恪亲手作了如下批注:“此处所谓‘丑’,即‘古妆野态’之意,虽出自太守之口,本无‘得体’”与‘不得体’之问题也。”(同前,第62页)换言之,陈寅恪认为陈衍对原诗理解有误,由此得出的评论当然也只能是“臆说”。第18条,针对陈衍批评刘克庄“律句多太对”,陈寅恪持不同观点:“律句太对并不足为病,惟视两联之思想及意境如何耳。”(同前,第80页)所有这些,都能显示出其眼界、手段较诸陈衍确实更高一筹。
书评:为什么说那些严肃的“陈寅恪研究”相较于陈寅恪的道德文章,也不过“尔尔”?为什么说真正需要“陈寅恪研究”的,并非陈寅恪本人,而是与陈寅恪同时代的同胞,尤其是作为后辈的一代代中国人?
张:我先引用《陈寅恪四书·尔尔区区》导语的一段话:“无论被尊崇还是被践踏,无论被纪念还是被遗忘,陈寅恪的道德文章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一点,陈寅恪有着足够的自信和自觉。换言之,真正需要‘陈寅恪研究’及其再研究的,并非陈寅恪本人,而是陈寅恪以外的其他人——与他同时代的同胞,尤其是作为后辈的一代代中国人。因此,即便是认真、严肃的‘陈寅恪研究’及其再研究,相较于陈寅恪的道德文章,不过‘尔尔’;而那些故作惊人之语的‘研究’或‘再研究’,对于陈寅恪的历史地位而言,犹如蚍蜉撼大树,恐怕连‘区区’都称不上。”
一方面被尊崇、被神化、被拔高,另一面被遗忘、被批判、被侮辱,截然不同的两种表现,都曾经真实地发生在同一块土地上。为什么会出现如此魔幻的一幕?会不会再次发生同样的场景?对这些问题背后的历史场景予以还原,进而探究其成因,应该成为陈寅恪研究的组成部分。
《陈寅恪四书》从构思到定稿,前后经历了四年。不管修订旧作,还是撰写新篇,陈寅恪先生上个世纪初所言“幽忧之思”确实如影随形,时时萦绕脑海,偶尔诉诸笔端。第一书《馀生流转》有一篇文章只留存了篇名,正文未被收录,幸而导语里的这段话得以保留:“当‘选择性呈现’已然相伴而生,谁能保证‘选择性遗忘’不会接踵而至?一旦‘选择性呈现’和‘选择性遗忘’成为群体性习惯,谁又能确保灾难只会‘选择性重现’而非‘必然性再临’?”(《陈寅恪四书·馀生流转》,导语第6页)
《陈寅恪四书》的某次分享会上,有一位书友让我对陈寅恪先生的影响和意义排一个顺序。我想一想,给出了这样一个排序:人格力量第一,思想观点第二,学术贡献第三。这个排序,无形之中和他父亲陈三立的名字也是契合的。“三立”者,“立德、立功、立言”。按照这一标准,陈先生足以骄傲地步入史册。剩下的问题,留给了我们。
如前所述,《尔尔区区》对陈寅恪研究的既有成果大致作了一个划分:前者虽然意义有限,终究可以解决今人的生计,想来陈先生不会怪罪我们;后者成因复杂,不排除蹭热度、博出位的用心,固然陈先生眼不见为净,我们却不能熟视无睹,有必要予以指摘。这本书可能会引发不满或遭到指责,但是我在写作、校对过程中反复作了核验,所批评的内容皆是白纸黑字的客观存在,即便措辞或许有些严苛,也都是必须面对的事实。我也欢迎一切读者对《陈寅恪四书》展开批评甚至批判,当然,前提只有一个——用事实说话。
书评:您是如何看待当下陈寅恪研究的?有什么学者的著作是值得注意和阅读的?您如何评价您本人的陈寅恪研究? (我这里还有您的《陈寅恪家史》一书)
张:3月22日在杭州,3月29日在厦门,我分别请了刘克敌教授、谢泳教授作为我的对谈嘉宾,与当地书友进行新书分享。他们二位既是我一向敬重的兄长,也是陈寅恪研究的同道。两位教授不约而同地将陈寅恪研究与鲁迅研究、钱锺书研究作了比较,认为“陈学”在研究队伍、研究平台、社会影响等方面有必要借鉴学习“鲁学”和“钱学”。此外,两位学者还对陈寅恪研究的两类方法作了对比和分析。按照他们的观点,陈寅恪研究大致可分为“史料派”和“史观派”(名称是我后来取的,未必恰当)。他俩都把我归入“史料派”,对此我深表认同。
顾名思义,“史料派”重在不断寻找新史料,“史观派”重在不断发掘新意义。我不由得联想起1932年陈寅恪先生在“晋南北朝隋唐文化史”开课之初对该门课程要旨的概述:“以往研究文化史有二失:(一)旧派失之滞。其缺点是只有死材料而没有解释,读后不能使人了解人民精神生活与社会制度的关系。(二)新派失之诬。新派书有解释,看上去似很条理,然甚危险。他们以外国的社会科学理论解释中国的材料,有适用之处,也有时不适用,因中国的材料有时在其范围之外。所以讲大概似乎对,讲到精细处则不够准确,而讲历史重在准确,功夫所至,不嫌琐细。本课程的学习方法,就是要看原书。有的人不看原书,‘说食不饱’,这样不好,要从原书中的具体史实,经过认真细致、实事求是的研究,得出自己的结论。一定要养成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评态度。”(卞僧慧纂《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45-146页)
套用一下陈先生当年的观点,今日之“史料派”和“史观派”各有其不足:前者也容易“失之滞”,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陷入为考证而考证的泥淖;后者也容易“失之诬”,带着预设的结论,专门寻找有利于论证的材料。理想状态当然是二者彼此渗透、深入融合,但目前看来还要走上很长一段路。
在众多陈寅恪研究的专著中,我最推崇的四本书是:《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陈寅恪诗笺释》《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我把它们比作后母戊大方鼎的“四足”——稳稳当当,扎扎实实。(《陈寅恪四书·尔尔区区》,第189-190页)这个书单,当然是我的个人喜好,别人不一定认可。不过,试着用“史料派”与“史观派”相结合的标准来衡量,我觉得这四本书依然站得住脚。
我本科时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时学的是中国近代文学专业,从事近代史研究纯粹是半路出家,一直到现在都还没入门。从事义宁陈氏家族研究30余年,我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从陈三立开始,然后到陈宝箴,再到陈寅恪。考订史实既是个人一贯的兴趣,也是花费心思最多的地方,这也许正是刘教授、谢教授将我归为“史料派”的原因。和其他陈寅恪研究者相比,我对陈氏家族数代人都有涉及可能算得上一个特点,但是缺陷与不足也紧随其后:陈寅恪先生最有价值、最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比如隋唐史研究的“寅恪三稿”、敦煌学研究的系列作品等,我至今还没有完全看懂,更谈不上精深、别致的研究。《陈寅恪四书》虽然萃集了个人多年的研究精华,解决了一些局部性、阶段性问题,但仍然只是陈寅恪研究的外围产品、基础产品,远远称不上核心产品、高端产品。我的朋友山东大学李开军教授是研究陈三立的领军人物,他为自己定的目标是“四个一”——一部陈三立全集,一部陈三立年谱,一部陈三立诗文笺注,一部陈三立传记。在我看来,这个目标同样适合于陈寅恪研究。从预设目标来讲,我希望《陈寅恪四书》能够从多个维度发力,共同构建立体式研究陈寅恪的大格局,为其他研究者提供可以采信的材料。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就是这套书的最大价值。
《陈寅恪四书》的周边产品有一张明信片,正面是年轻陈寅恪的画像,一开始我有些不习惯,后来越看越觉得有味道,确实能传神。明信片背面,印着我写在《陈寅恪四书》后记里的一句话:“只要陈寅恪先生在其著作中警示过的那些问题还得不到解决,那么,一切通过还原历史场景、揭橥真实意愿来帮助人们准确理解陈先生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用的。”就用这句话结束这次采访吧。谢谢!
张求会 | 起始于肉身“流转”,终结于魂魄“永驻”:《馀生流转》导语
编者按:《馀生流转》,“陈寅恪四书”第一种。书名取自陈寅恪诗《己丑清明日作,用东坡韵》:“楼台七宝倏成灰,天堑长江安在哉。岭海移家春欲暮,清明上冢梦初回。馀生流转终何止,将死烦忧更沓来。纸烬不飞鸦铩羽,眼枯无泪溅花开。”“己丑清明日”,值公元1949年4月5日,陈寅恪流寓岭南的第77天。既有史料足以证明:在1951年9月之前,陈寅恪、唐筼夫妇并没有完完全全将广州当作人生的最后落脚点。本书所收十篇文章,串起的正是1948年后陈寅恪的“馀生流转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