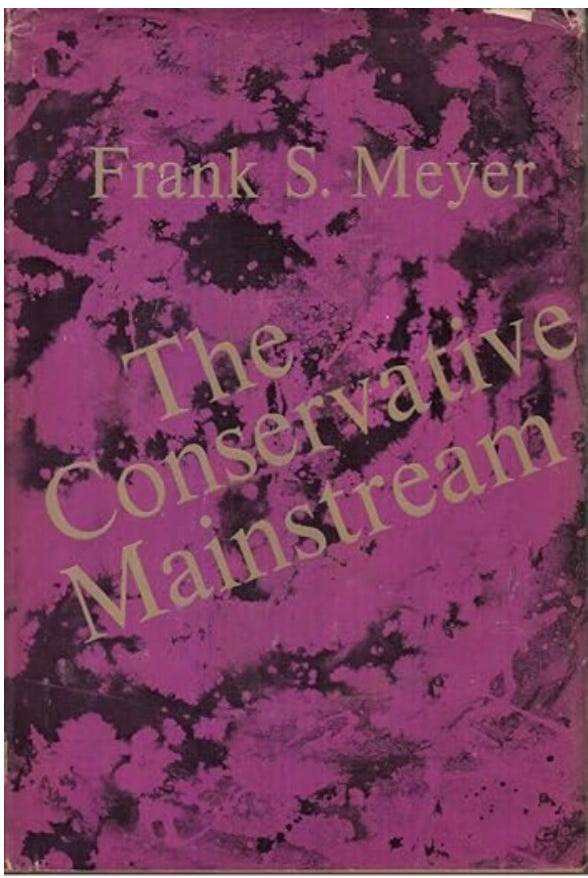弗蘭克·梅耶(Frank Meyer) | 麥卡錫主義的意義
譯者按:弗蘭克·S·梅耶(Frank S. Meyer, 1909–1972)是美國二十世紀保守主義的創始者之一,以其提出的「自由與美德融合論」(fusionism)而聞名。此融合論是當代美國保守主義核心理論之一。梅耶早年受左翼思想吸引,一度加入共產黨,然而在三十年代與組織決裂退黨,從而轉身為堅定反共人士。五十年代起,他作為《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的核心撰稿人,對冷戰高峰期的美國右派思想方向具有決定性影響。
1958年,梅耶寫成《麥卡錫主義的意義》一文,最初發表於《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後收入梅耶文集《保守主義主流》(Conservative Mainstream)。梅耶撰文之時,麥卡錫1954年遭參議院譴責的餘波未平。直到今天,美國公共論述普遍視「麥卡錫主義」為偏執與政治獵巫的同義語。甚至現在許多從未考察一九五零年代史實的人,也動輒引述「麥卡錫」之名扣帽子,指控對方有「反民主」傾向,這麼做實則重述且強化半世紀前所形成的刻板印象。然而梅耶撰文時,依靠的則是自己對遠東革命、紅色間諜滲透本國與大眾恐懼的新鮮記憶。他指出:若僅將麥卡錫理解為個人臆想偏執,便會無法理解這位參議員之所以能在美國社會中獲得廣泛迴響的深層原因,以及他行動所揭露的美國自由主義根本弱點。
自從投身於保守主義,梅耶便一貫批判流行於美國精英階層的相對主義,並將此歸咎於自由主義理論本身。根據他的判斷,美國精英受現代自由主義理論熏陶,故標舉「不作價值判斷」甚至走到宣稱「沒有敵人」的地步。在精英看來,彷彿在自由社會中,一切價值差異都可被視為「另一種生活方式」,可以用和平方式處理。然而在梅耶看來,這種姿態使建制自由派在對抗致命敵人時,極度暴露軟弱。正因拒絕判斷,他們喪失了對敵人本性和野心的清醒理解,使自由社會出現防衛真空。在文章末尾,梅耶提出一個深邃論點:當代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存在深層的相同之處:「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並無不可調和的差異,僅在手段與方法上不同。」
需要指出,這一論點在保守思想家陣營中並非梅耶所獨有。1963年,列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在名作《城邦與人》序言中寫道:「西方計劃雖然以自己的方式對抗了之前所有形式的邪惡,但它卻無法對抗這種新的形式,無論在言辭方面還是在行爲方面。曾經有一段時期,似乎足以說,儘管西方運動和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目標一致——由自由平等的男女組成的普遍繁榮的社會,但手段不一致。」此說法正與梅耶《麥卡錫主義的意義》重合。然而過去學界習慣以為這種重合只是思想氛圍使然,而排除兩人之間曾有互相啟發。
時至2025年,丹尼爾·弗林(Daniel J. Flynn)發掘並公布1961年施特勞斯—梅耶通信,則有力顛覆了以上成見。在通信中,施特勞斯提及梅耶的《麥卡錫主義的意義》,稱他對文章“心存感激”,“完全贊同其觀點”。可以推測,施特勞斯贊同梅耶文中對當代自由主義弱點的理解。而《城邦與人》序言與梅耶1958年論點的重合,實出於兩位志同道合者對於根本問題反復切磋之後達成的共識。
《麥卡錫主義的意義》不但重現冷戰時期關於麥卡錫爭論原貌,也展示了梅耶作為美國保守主義創始者的思想深度。六十餘年後重讀此文,仍能感受梅耶論說對美國流行思潮的針砭之力。
如今,距離麥卡錫參議員的逝世已一年,距離他遭到華特金斯委員會政治處決已三年有餘,或許我們終於可以用較為客觀的態度,來評估那場思想和行為上運動的意涵,即自由派 (Liberals)稱為「麥卡錫主義」的運動。 也許要從永恆的視點(sub specie aeternitatis)理解其意義還為時尚早,但我們距離 1950 至 1954 年那幾個非凡歲月的喧囂已足夠久遠,可以撇開表面現象,超越麥卡錫參議員本人的长短,開始描繪出那些喧嚷之下的深層事物——那些賦予那幾年如此強烈緊迫感的真正根源。
也許探討這一問題的一種方法,是考察自麥卡錫被逐出政治舞台以來發生了什麼變化。如今,生活已平靜許多。當他仍然活著但已失腳之時,生活其實也很平靜——那是 1956 年 11 月,我們各自忙於日常瑣事之時,我國的榮譽卻在败坏,我們的朋友之血灑滿布達佩斯街頭。今日则大致平靜(當然,我們多少有些憂心經濟衰退),我們一邊與殺人者討價還價、準備在某個高峰會議上相見,一邊又在大都會歌劇院起立致敬,向那些殺人者的國歌致意。
我們社會的制高點,現由那些宣揚「平靜」的人掌控。當然問題還是有的——要在太空競賽中超越「斯普尼克」、要在宣傳戰中勝過赫魯雪夫、要贏得蘇卡諾、尼赫魯、納瑟等人的友誼與好感——但這一切似乎都只是共存遊戲中你來我往的環節。少數人發出警告之聲,卻幾乎無人聽見——警告說與一個誓言要摧毀西方文明的敵人「共存」是不可能的,那樣的共存只會導致敵人的勝利與我們的失敗。然而,兩黨中的自由派穩坐在高處,從那裡向我們不斷傾瀉安撫套話,直到把警告之聲淹沒。
那麼,在麥卡錫時期,是什麼打破了這層迷霧?是什麼刺穿了那平靜的假象,讓這個國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能理解那逼近的危險?這實在與麥卡錫參議員的「手段」無關。那些手段只是美國政治中的零錢——數十年來每場政治爭論的各方皆曾使用。我認為,是這一種理解打破了迷霧——有時表達粗糙,有時卻精確犀利——對於過去四十年來美國乃至整個西方政治的悲劇性真相的理解: 在這四十年間逐漸佔據主導地位的自由主義,其本質特徵使得我們現今的領導階層既無法抵禦共產主義在內部的滲透,也無法在對外部的共產威脅上形成有效戰略。
正是美國广大民眾對這一點的本能察覺——對某種錯亂的直覺感受,雖難以界定,卻深信不疑——讓麥卡錫喚醒了。當然,麥卡錫本人在界定這一問題上貢獻不多;他所作的一切,並非出於分析,而是憑藉勇氣、堅持,以及替數百萬被噤聲歪曲的美國常識所作的雄辯。
誠然,這種出自大眾本能的表達,無論在理性或审美上,都不是最妥善或最有效的。每個社會都需要能夠以理性與傳統智慧闡釋其基要本能的知識分子。 但當社會中絕大多數自詡為知識領袖的人去「叩拜别神」,而他們的文化傳統與專業訓練本應使他們能夠抵抗那種誘惑,那又該怎麼辦呢?與其为错误做精巧的辩护,不如道出粗糙的真相。
令人遺憾的是,「知識分子的背叛」——他們對真理職責的背棄——導致整個社會對知識分子本身的懷疑,產生了那個含混不清的蔑稱「蛋頭(egghead)」。令人遺憾的是,腐化的知識界使得「知識性」本身蒙上嫌疑。令人遺憾的是,在這樣的情勢下,麥卡錫主義對危險思想與其擁護者的攻擊,竟如此容易被誤解為對「思想」與「知識分子」整體的攻擊。知識分子的本分是表達社會的精神,所以那些背離本分而遭人譴責的知識分子正是咎由自取。社會急需以真理為歸旨的知識分子,而那些人卻無濟於事。
對麥卡錫的攻擊——指責他是粗魯無知、仇視思想與文化的人——其實是為了混淆他大声疾呼的真正議題。
在那時,美國人表達對既有權威不滿的正常渠道——總統選舉——已被封閉。反對建制派自由主義的人,在選舉中一屆又一屆地看著共和黨淪為新政民主黨思想的淡化版本,两党實在越來越難辨別。自 1930 年代初以來,一場寧靜而不流血的革命已經佔據了美國社會的決定性地位——不僅在政治領域,也在日益強大的大眾傳媒、學校與大學中,甚至滲透到大量講壇之上。
一個建立在「個人尊嚴至上」原則上的文明,正被逐渐集体化。
對脚踏实地、傳承祖先信念但缺乏辯證技巧的公民而言,這是難以抗衡的過程,因為每一步集体化的推進,皆以「愛與團結」這些高尚但迷惑的理想為修辭包裝。對於共產主義,一個公民尚能辨識,那種公開的唯物主義,及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的執念顯然是邪惡的。 雖然與當代集體主義自由主義同出一源,共產主義卻拋棄了所有道德禁忌,這些禁忌基于一種傳統,已為自由派之理智所拋棄,而依然為其情感所持守。自由派在宣傳中訴諸此傳統,也在生活中受其影響。
美國人民拒絕將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劃上等號固然是正确的,但這種拒絕,卻使他們看不清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相似之處及其危險性。這種不信任依然存在於民間,但經歷三〇年代的鬥爭與二戰中自由派領導下的全國團結之後,給這種不信任命名越來越難:共產主義是邪惡的;民主是良善的;而既然自由派不是共產主義者,那麼當 1945 年後共產主義威脅抬頭時,他們難道不也有資格領導國家度過危機嗎?
這個問題的答案,在 1948 年的希斯(Hiss)案中闖入全民視野。當時,自由派建制幾乎一律挺身支持希斯。然而,儘管希斯拥有诸多有利條件,錢伯斯(Whittaker Chambers)卻憑他一人證詞說服了陪審團與廣大美國民眾希斯確實有罪。於是問題更尖銳地暴露:自由派領導自由社會的資格何在?
希斯案是一記重擊,但單靠它仍不足以揭示自由主義的真相。畢竟希斯只是单个人——他長於言辯、頗具魅力;他的同僚或許只是受其人格所惑。希斯案虽然揭示了许多,但仍不足以像錢伯斯在《證人》(Witness)中那樣昭示真相:
「新政的趨勢正通往社會主義,
雖然多數参与者自命为自由派,无论是主导者还是追随者……
新政實際上是一場革命,其最深的目的並非
在既有傳統框架內改革,而是根本改變
國內的社會結構與權力關係。
它不是暴力革命,而是以帳簿與立法進行的革命。
我終於明白,為何政府中會聚集那麼多隐匿的共產黨人,
且他們能那么自由行動而幾乎不懼被揭發。
因為在一知半解的革命者與深思熟虑的革命者之間,
後者必然佔據了絕佳的操縱位置。」
自由派與共產主義者在目標上趨同社會主義、以及自由派無力保護自身與國家免受共產主義更深邃、更兇險的計劃,這都被麥卡錫的誇張行動暴露出来。麦卡锡能夠在生存层面表達自己对以上關聯的洞察,加以運用分析方法,正因如此,他獲得眾人的支持,並讓他們憂慮的意義撥雲見日,長期以來,那些憂慮過於模糊,乃至不著邊際。正因這些——而非因為他所謂的「手段」,那些手段與茶壺山醜聞(Teapot Dome)或布萊克委員會的調查並無二致——他才招致了整個自由派建制的全力報復。在那一刻,自 1932 年以來自由派的領導地位似乎首次面臨嚴肅挑戰。
假如當時負責塑造輿論的知識分子能認識到麥卡錫主義所代表的基本真理,並詳細闡述其意涵,則會明白哪些事情?我們不妨這麼設想,雖然這麼做已經於事無補了。
當代自由主義在最根本的一點上與共產主義一致——承認社會主義為必要且可欲;
它否認一切傳統價值——神學的、哲學的、政治的——具有內在的德性與權威;
因此,它與共產主義之間並無不可調和的差異,僅在手段與方法上不同;
基於這些意識形態特徵,自由派既不適合領導自由社會,也無法對共產主義的進攻構成嚴肅的抵抗。
然而,建制派的陣營中並未出現這樣的裂口。除少數例外,全國的公認領袖一齊反對麥卡錫。甚至那些在反共鬥爭中光榮立功、心知麥卡錫根本上是對的人,也加入了反麥卡錫的兵團。「麥卡錫總之妨礙了反共」,他們這麼囁嚅道。
麥卡錫參議員敗北了,然後死了。 自由派深怕麥卡錫主義成為組織化運動,結果則是:他一死他的主義便雲消霧散。在他敗北後而尚未去世之前,便發生了匈牙利之恥;如今這個春天,我們又不發一槍,將印尼拱手讓給共產黨。「共存」與「文化交流」是眼下時尚。 我們矯揉造作,為舉辦高峰會議的條件嘀嘀咕咕,卻從未在原則上拒絕與殺人者與奴役者和平會晤,而在過去,我們絕不會與希特勒那樣的人會晤。
無論自由派建制再怎麼喧嚷,他們的思想前提註定他們無法徹頭徹尾將共產主義視為不可調和的敵人。若要概括他們的信條,可以借用三〇年代法國的口號:「Pas d’ennemis à gauche——「左方沒敵人」,至少,沒有不可調和的敵人。麥卡錫主義比共產主義更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