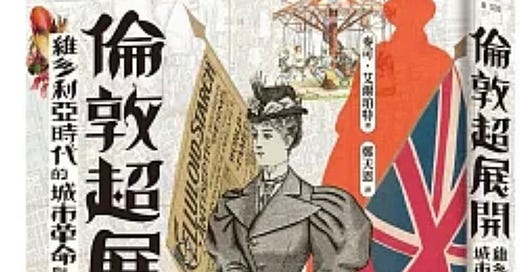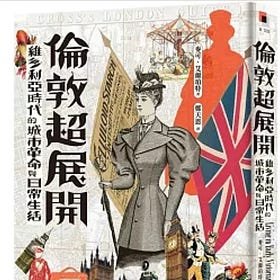麥可・艾爾珀特|維多利亞時代的倫敦市民吃什麼?
編者按:在維多利亞時代,倫敦經歷了史上最劇烈的變革,塑造了今日這座現代化大都會的基礎。鐵路興建、街道鋪設、醫療進步、衛生條件改善……技術創新為城市帶來繁榮,卻也讓社會底層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維多利亞時代倫敦的日常生活》透過犯罪紀錄、法院文件、新聞報導、日記與文學作品,重現19世紀倫敦的街頭巷尾帶領讀者穿梭於一八三七至一八五○年代的倫敦,不僅描繪了街頭的熱鬧與混亂,更生動再現了當時倫敦普通市民的日常。讀者能看到煤氣燈下的華麗店鋪與骯髒貧民窟,聽到市場喧囂與馬車聲,聞到泰晤士河的惡臭與酒館的麥芽氣味,如同身臨其境。作者麥可・艾爾珀特畢業於劍橋大學,1974年雷丁大學(University of Reading)博士畢業。西敏寺大學(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退休,獲榮譽教授。
《維多利亞時代倫敦的日常生活》由台灣黑體文化5月出版上架,本文選自該書第三章《他們吃什麼、去哪裡購物、又穿些什麼?》,出版社授權刊發。
第三章 他們吃什麼、去哪裡購物、又穿些什麼?
你想要與我們共進晚餐嗎……?
瑪莉亞與腓特烈.曼寧計畫要謀殺派崔克.歐康納。他們邀請他在一八四九年八月九日星期四傍晚五點三十分,到他們位在伯蒙德的住處共進晚餐。人們何時吃晚餐,標誌了他們的社會階級。五點三十分曾經是十八世紀上流階級通常的用餐時間,但經過幾代後,高級社會的晚餐時間已經延後到七點三十分。對「中間」的中產階級而言,晚餐會在六點鐘上桌。曼寧夫妻屬於中產階級的下層,所以他們比這個時間早半小時用餐。
但在當時的時尚中,晚餐甚至變得更晚。數以千計的讀者在喬治‧雷諾茲(George Reynold)非常成功的系列小說《倫敦之謎》(一八四六年)中,會讀到這樣的內容:
宴會在七點準時上菜。當格林伍德先生的事業在世界各地興旺時,他漸漸讓自己的晚餐時間晚上一個小時;他還決定,如果他當上男爵,絕不會讓自己的膳食在八點半之前端上餐桌。
對普通的勞動大眾來說,「dinner」這個字指的不是晚餐,而是他們在中午或下午一點吃的主餐。在晚上,人們通常直到八點甚至更晚,都還沒結束勞動。它們通常會在下午四點進行「午茶」(tea),並在更晚的時間用「晚飯」(supper)。到了夜深時分,貧窮人家的小孩會從父親的晚飯中,分到一盎司的火腿與幾小片的起司。他們的身影會出現在炸魚店裡,選購幾片美味可口的鰈魚。可是,就像特里斯坦抱怨的,炸薯條或薯片這時還不是和炸魚類似的佐餐物,且在倫敦幾乎不曾發現。
新聞工作者薩拉寫到,勞工的晚飯時間通常要晚到深夜十一點。接著,他又用或許是半開玩笑的語氣這樣說:
對一個勤勉可靠的技工而言,當抽完最後一縷菸絲,他會讀起借來的報紙,和愉悅可人、同樣認真勤奮的伴侶一起討論今天的大小事,以及未來一週的展望;依偎在雙手老繭的主人身旁,妻子會為他裝滿菸斗,為他倒滿啤酒,縫補孩子的短褲。
他們都吃些什麼?又得花上多少?
就像現在打電話叫外帶一樣,在商店或小攤子裡,準備了許多外帶食物:布丁、派、用牛油和鹽烤過的半便士馬鈴薯、熱鰻魚以及豌豆湯。對那些一有錢就想吃點東西、卻又沒有什麼烹飪設備如壺、平底鍋甚至盤子的窮人而言,他們並不期待在家裡擺上一頓豐盛的菜餚,所以會在隨時隨地能買到食物的地方買菜,並吃下他們所能想像的一切東西。一名住在倫敦東部貧困地區――白教堂區的商人,告訴前來調查的新聞工作者梅休(Henry Mayhew)說,他一天可以賣出三百個一便士的派,大部分都是賣給男孩子。他們會說:「這是剛出爐的嗎?我愛死它了!」
大衛.科波菲爾(David Copperfield)對自己早年生涯的小說式記述,反映了狄更斯對那個時代的記憶――當他十歲的時候,曾在靠近亨格福德橋、華倫地區的一家鞋油工廠裡,幫瓶瓶罐罐貼紙標籤。在小說中,大衛在米考伯家寄宿的錢雖有他的繼父、殘酷且鐵石心腸的摩德斯通先生來付,但他每週賺的六到七先令薪資,每一分錢幾乎都得花在食物上。他的早餐通常是一條一便士的條狀麵包(loaf)或者麵包捲(roll),再配上價值一便士的牛奶(如果是街上或附近牛棚現榨,還會是溫熱的)。至於他的晚飯,則是另外一便士的條狀麵包與一片起司。如果起司得花上一便士,那他一週就得耗掉兩先令又四便士在這上面,因此留給他當正餐的錢,就只剩下一週四先令左右。有時候他實在餓到不行,根本等不到午餐時間,所以只好買一些放在糕餅店外面、不新鮮的半價餡餅來充飢;再不然就是――
一個厚厚的白布丁,又重又鬆鬆垮垮,裡面還隨意散布著大顆扁平的葡萄乾。它在我那時候幾乎每天都會熱騰騰登場,在無數歲月裡,我就吃這個當中餐。
當大衛有辦法把錢留到晚上的時候,他會去買一條乾臘腸和一便士的條狀麵包,或是一盤四便士的牛肉,又或者是麵包、起司與一杯啤酒。「午茶」通常是一品脫咖啡,配上一小片麵包與牛油。當年長大衛回首自己的童年時,毫不意外會看到一個每天從早工作到晚,從康登鎮走到泰晤士河畔,然後又走回來的十歲小孩身影;這孩子成天飢腸轆轆,只會花費每一分額外掙到的錢在食物上。他的早餐和晚餐不只欠缺營養,還很枯燥無味。如果他在這一天中能吃到一頓適度均衡的餐點,那或許並不是什麼要緊的事;但在倫敦工作,卻甚至無法像大衛這樣賺到一星期六、七先令來維持營養的孩子,又有多少呢?
除了最富裕的人以外,對所有人來說,食物都是家庭預算中最主要的開銷,而麵包又是家庭食品菜單的重中之重。難以消化、潮濕、淺灰色的四磅重大麵包(quartern loaf)――它之所以如此得名,是因為它通常被切成四等分(quarter)來販賣,且依據一八二二年的倫敦麵包法案規定,每一塊都是重四磅又十五盎司,也就是稍低於五磅或二點二公斤――,在一八四六年的價格是八便士又半文錢。當穀物法在這年被廢除、同意便宜穀物進口時,大麵包的價格略有下跌,但直到美國與俄羅斯的鐵路發達、以及廣泛使用蒸汽船的便宜海運普及以前,倫敦窮人都無法從這些遙遠地方生產的大量小麥中獲得好處。
一杯「好茶」(Nice Cuppa)
在一八三三年之前,東印度公司享有茶葉的壟斷輸入權,這導致茶的價格居高不下。茶也被課予很重的稅;正因如此,在維多利亞時代早期,每一磅茶得結結實實花上三先令才行。這導致人們常常把茶沖得既淡且薄,所以消費量也相當低。可是,就像生活的許多其他層面一樣,改變正在到來。茶稅在一八五三年被降低,同時印度和錫蘭的新貨源也在穩定發展;於是,茶的消費量開始上揚。
牛奶本身被飲用的量並不是太多。畢竟不管怎麼說,大部分的人都很難常保牛奶新鮮,特別是在夏季更是如此,所以倫敦人會每天從擠牛奶女工那裡買下一壺牛奶;這些女工會從後院的乳牛取奶,然後用軛將兩個沉重的奶桶扛在肩上,沿著當地街道販賣。加很少甚至不加牛奶的薄茶通常需要靠糖提味,糖的價格此時已經跌到了一磅五便士。在英格蘭與威爾斯,每人平均要消費高達三十六磅的糖;自然,這種糖癮也意味著不習慣使用牙刷的英國人,蛀牙的情況日趨嚴重。
人們食用的食物種類與數量,有賴於他們的收入。培根被認為很便宜,一磅只要八便士。它只需要生火就能輕易烹煮,但精打細算且有些烹飪技巧與時間的家庭主婦,則也會買肉販粗切完肉之後的餘料,這些餘料一磅只要四便士,甚至更少。最高級肉販的肉通常很昂貴、不會這麼用心留下餘料,就算有餘料,也不會像培根這樣容易烹煮。
對比較窮的人而言,他們的考量則多多少少受到準備食物能力的影響。許多人沒有灶台、也沒有自己的壁爐,甚至只有一把煎鍋而已。不只如此,如果婦女成天和男人一樣辛勤工作――或許是為賺取微薄薪資而縫紉、又或許是為上等家庭洗衣,那花在準備食物上的時間就顯得很不划算。在二十世紀下半葉,超市裡有採收齊全的蔬果、還有現成的菜餚與切削合宜的肉類,這些都能用現代可信賴的瓦斯或電子炊具,來滿足快速烹煮的需求。相較於此,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和十九世紀初並沒有太大不同)的生活中,特別是在冬天,菜販能提供給倫敦家庭主婦的選擇則是非常貧乏,頂多就只有一些滿是泥巴的受損馬鈴薯、外表破破爛爛的萵苣、變形的紅蘿蔔,以及生蟲的蘋果;而一隻必須自己殺、自己拔毛的雞,又顯然太奢侈了。
短評|權力如何記憶:普丁對俄烏戰爭的敘事
編者按:9日,在莫斯科紅場上盛大的閱兵儀式,普丁可謂深諳此道:他利用歷史記憶來激勵他的軍隊,同時在他的敘事中,被他侵略的烏克蘭為復活的納粹主義——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正是二戰時被納粹屠殺了六百萬人的猶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