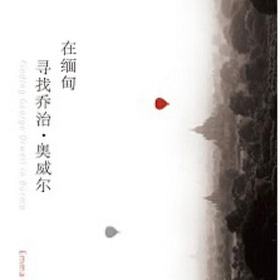訪談 | 艾玛·拉金:在缅甸有一种替代真相
1995年,在泰国出生、长大的艾玛·拉金(Emma Larkin)第一次到缅甸旅行,手里拿着乔治·奥威尔的一本小说《缅甸岁月》,这是当时她能找到的不多的缅甸读物。在曼德勒一条大街上,一位缅甸男子向他走来,笑着对她说:“请将我们对民主的渴求,告诉全世界——人民已经受够了。”就在这一瞬间,艾玛意识到,缅甸并非表面看上去的那般,她惊讶地发现,她眼前所看到的缅甸与70多年前奥威尔所描写的缅甸有很多相似之处,尤其是社会氛围。乔治·威尔小说对极权主义的预言与描写,是否与缅甸有着某种关系呢?
1903年,奥威尔出生于英属印度比哈尔邦摩坦赫利(莫蒂哈里)一个政府下级官员的家庭,父亲理察·普雷亚为印度总督府鸦片局副代理人,母亲梅培尔·李莫桑为缅甸木材商之女。1905年除父亲仍留在印度外,全家人都返回英国。1921年,奥威尔从伊顿公学毕业,因家庭经济困难无力供他升学,他报考公务员,加入了英国在缅甸的殖民警察,在缅甸服役五年。1927年,奥威尔退役,回到英国,从此再也没有回到缅甸。
奥威尔在缅甸五年究竟经历了什么呢?艾玛发现,奥威尔所有的传记对这一段都语焉不详,而在艾玛看来,奥威尔在缅甸的经历与他的小说有着某种隐秘的联系,“这种联系开始于《缅甸岁月》,小说记录了英国殖民时期的缅甸。1948年缅甸从英国独立不久,军事独裁者就将国家隔绝于世,启动‘具有缅甸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讲缅甸建设成亚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奥威尔的《动物农庄》讲述了同样的故事,在这部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是如何失败的寓言小说里,一群猪推翻了人类农场主,又毁灭了农庄。最后奥威尔在《一九八四》里描述了一个恐怖并且缺少灵魂的反面乌托邦,精确地描绘出今日的缅甸的图景,这个国家由世界上最野蛮和最顽固的独裁者之一统治。”
这不仅仅激发了艾玛对奥威尔的兴趣,更是激发了艾玛对缅甸的兴趣。在随后的几年里,她一边在伦敦的东方与非洲学院(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攻读缅甸历史与语言的硕士课程,一边在缅甸寻找奥威尔的痕迹。这便是2004年在伦敦出版的《在缅甸寻找奥威尔》。
2016年,这本书中文版由中央编译出版社推出。羅小虎为此采访了當時在泰国的艾玛·拉金。
艾玛·拉金 | 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
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 作者: [美] 艾玛·拉金 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品方: 三辉图书 原作名: Finding George Orwell in Burma 译者: 王晓渔 出版年: 2016-10 页数: 280 定价: 42.00元 装帧: 平装 内容简介 20世纪20年代,乔治·奥威尔曾作为大英帝国的警察在缅甸生活了五年。五年后,他突然毫无预兆地返回英国递交辞呈,开始了写作生涯。而缅甸则以各种形式在他的书中出现:《缅甸岁月》《动物农庄》《一九八四》,以及他未完成的作品《吸烟室的故事》等等。
問:Emma Larkin是你的真名吗?我听说,《在缅甸寻找奥威尔》出版后,你不得不用假名字隐居在泰国。这是真的吗?这本书的出版给你带来过麻烦吗?
艾玛:Emma Larkin 是一个笔名,我用来保护我在缅甸的信息源。大多数外国写作者或是记者,若是想写军事独裁统治下的缅甸,只要他们动笔写点负面的东西,就会上黑名单。所以我用了这么一个笔名,这样我就可以不断前往缅甸,可以长时间地呆在那里,让我可以写有关这个国家的第二本书。我的第二本书叫《对这个国王来说没有坏消息》(这本书另一个名字是《所有的东西都破碎了》),讲述了军事独裁统治下的缅甸最后几年的事情。
这本书(指《在缅甸寻找奥威尔》)出版后,我从来没有受到过威胁,也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故事,这大概是谣言。我那时确实常常被缅甸军事情报部门的人跟踪,但他们从来没有把我的笔名或是书与我联系起来,因为他们不知道我正在做什么。当我去采访一些与反对政权有关的人,或是去一些外国人很少去的地方,于是他们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不过,我的书没有给我带来什么麻烦,尽管这么多年我一直在那里做研究。确实,我也很紧张,我不想他们中的任何人为此受到牵连,尤其是那些在缅甸帮助过我的人。
問:你书中采访过的那些缅甸人怎么样了?在你书出版后,有没有遇到过麻烦?
艾玛:我一直非常注意这个问题,非常小心不给他们带来任何麻烦。我换掉了这本书中大部分人的名字,甚至一些人连他们的所在地我也换了。完成这部书稿后,在准备出版之前,我带着手稿去了缅甸,给了一些我信任的缅甸朋友看,他们也做了一些改动(非常小的改动,如一些个人细节,以免可能认出是某个人),以保证这本书里所涉及的每一个人的安全。
問:你什么时候对缅甸开始刚兴趣的?
艾玛:我是在泰国曼谷(Bangkok)长大的,第一次去缅甸是1990年代中期,并开始对隔壁这个被封锁的国家感到好奇。之后,我继续我的研究生课程学习,一个亚洲历史的硕士学位。我选择了缅甸的历史与语言。之后,我就有了写一本书的想法,并且特意去缅甸,花了一段时间考察是否可行:我在那里时间呆的越长,我就越是着迷。最后,我完成了一本那个时候我想读却没有的有关的缅甸的书,哈哈哈哈……
問:《在缅甸寻找奥威尔》的企鹅出版的出版于2005年。你是什么时候做的采访呢?你去过缅甸多少次?在那里呆了多长时间?
艾玛:《在缅甸寻找奥威尔》最早是在伦敦John Murray出版社出版的,书名用的是《隐秘历史SECRET HISTORIES》。我的采访时在2000年到2003年之间做的,因为花了很长时间与被采访对象和联系人培养信任。那个时候,你不能简单地跑到一个大学校园,说:“我对乔治 奥威尔感兴趣,我应该和谁去谈谈?”我必须小心地建立起各种渠道,与那些人一个一个见面,然后取得他们的信任,逐渐地,我被介绍给更多的人。有时候,觉得自己见的人太多了,或是觉得已经引起军事情报部门的注意,我会离开缅甸一段时间,然后再返回。所以我去了缅甸很多次,每次尽可能呆到我的签证期满,不过,每次签证最多也只能呆三个月。我只告诉极少数的人我在缅甸做什么,我要写一个我正在研究的缅甸语言的封面故事,这也是真的,只不过不是全部真相。
問:你是如何取得他们的信任呢?
艾玛:在我的经验里,如果你想写一个人的故事或是询问一些信息,有很多方法取得对方的信任,其中真诚是最重要的。如果一个人看到你是真心在意你所做的事情,而不只是想剥削他们的故事或是想做一个轰动的新闻,他们会乐意告诉你的。当然,要证明诚意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想时间能起作用:再来,第二次,三次,四次,然后也许第五次见面,最终才有可能打破个人保护壁垒,进行对话。在缅甸工作时,我被很多人拒绝过,有时很沮丧,但我完全能够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很简单,在缅甸,说这样的故事是危险的——所以,如果他们感到不舒服的话,我从不会促使或是说服他们接受我的采访。对于那些愿意告诉我故事的人,我尽可能地向他们保证,让他们知道我会尽力保护他们的安全。事实上,我用笔名写作起了很大的作用,还有就是我在书中改变了他们的名字。
問:那个时候,你或是你采访的人预见到了缅甸2015年的变化吗?我是指昂山素季被释放,并在2015年举行选举。
艾玛:至于缅甸后来的变化,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不是一个政治分析家,只是一个作家,,所以我所做的只是收集故事。我的第二本书写的就是转型前几年的事情,很明显,人们渴望改变,但是它是否会来不是必然的:事实本身就非常有趣,也表明军队过去是多么不透明,事实上,至今依然是……
問:有多么不透明?你能否举个例子?
艾玛:缅甸军队依然是,一直是一个非常机密的机构。我的第二本书便关注这一点,尤其着迷于谣言如何变成人们的“替代真相”(alternative truth),因为没有办法知道这个政权的真正的真相是什么。当一个国家由这么一个机密的专制的实体运行时,在普通大众和统治者之间就会存在着这么一层额外的“真相”。在缅甸,我看到把各种谣言当做是衡量人们希望与害怕的一个可信赖的“晴雨表”——一种解读缅甸的方法和衡量一个新闻不自由、意见调查被视为是颠覆行为的国家的大众的心情的方法。
至于军政府如何影响普通人的生活,这就涉及到它统治这个国家的方式。它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最厉害的一方面是真相被扭曲的方式,这也是我最感兴趣的。在我看来,军政府是一个大规模的,全国性的“现实控制器”,它通过审查抹去真相,并用国家资源制作的宣传来替代真相。这台机器通过永远存在的军事情报人员靠恐惧运转,这些军事情报人员总是在监视着人们,直接地或是通过一个庞大的信息网络间接地监视着。
問:奥威尔曾写道奥威尔曾经写过,在四种情况下,权力会丧失:外部征服、底层叛乱,中产的崛起及其不满,还有统治阶级本身的道路自信没了。从奥威尔的观点出发,你认为他会怎么看今天的缅甸的转型?
艾玛:好问题!不过我认为用一个公式去谈论缅甸的情况也许过于简洁了。第三点,中产阶级的崛起是不适合缅甸的情况的,我也不认为其他三点本身也可以来解释缅甸的转变,不过奥威尔提到的其他三点也许相关:外部征服(在经济上来自中国的)、底层叛乱(叛乱也许过于严重,但肯定有一直来自全国民主联盟和其他积极分子的持续反抗,以及多民族国家一种有的冲突)和统治阶级的自信丧失(在2008年纳尔吉斯气旋风灾之后,这是有可能的,当时政权阻止了关键的援助到达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极大恶化了这个毁灭性的大灾难)。
奥维尔不仅是社会底层的捍卫者,而且是一名实用主义着。因此,我想他会以平衡的眼光看待缅甸的变化—— 从将近50年的军事专制中挣脱出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看起来军方似乎不可能回到权力舞台,但是若要带领证据向前发展以及弥补几十年来的伤害 —— 体制的和心里的伤害 ——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問:你能描述下这种伤害吗?
艾玛:有很多种伤害——体制的、社会的、个人……对我来说,我所观察到的一个关键要素是我之前说过的——信任。在军政府统治下,秘密警察和线人在社会每一个层面都运行,信任你的同事和邻居,甚至有时候是你的家庭成员都是危险的。如果你的观点或是行为和统治权威所要求的有所不同,他们就有可能告密。所以信任在这样的集体中被侵蚀掉了。在《一九八四》中,奥威尔描写了生活在这样环境下的后果,在那里,你必须让自己与你周围的人隔绝,封闭自己:“除了头骨中的几厘米外,没有什么是你的。”我认为信任的崩溃是一个权威统治最可怕的后果之一。在这样的体制下将近50年后,这已经影响了一代代缅甸人,而且还将会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造成不可估量的心理伤害。
問:那你是怎么看待缅甸的转型呢?
艾玛:嗯,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不确定我读到过任何真正准确描述或是解释转型如何发生的东西。我想,除非军政府有更多公开的资料,否则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地缘政治肯定起了作用,关于这方面,有一本很好书,Thant Myint-U的《中国在哪里遇到印度:缅甸与亚洲的新十字路WHERE CHINA MEETS INDIA: Burma and the New Crossroads of Asia》。至于过去几十年缅甸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喜欢读那些充斥在故事另一面的东西。我在缅甸工作时,只能会见和采访那些政权之外的人。如果能阅读一些军队生活、一些高级将领的野心和害怕,政府审查员的充满压力的工作,一个军事情报员的每日的挣扎,因为他不得不去跟踪别人和汇报反政权活动,这会是一个很迷人的翻转。这些也是缅甸不能说的故事。我想,如果我们知道这些故事,可能会对缅甸为什么和如何发生转型有一个比现在看到的更好的理解。
問:你是否和书中你采访过的人依然保持联系呢?他们现在生活怎么样?他们是如何看待自己国家的转型?
艾玛:书出版后,我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见过面,也和他们中的一些人保持联系。军政府时期有一种让人愚蠢懒惰的东西——缺乏经济的、智力的、社会的可能性。在我为第一本书做研究的时候,人们有时间在茶馆坐几个小时,甚至一整天。现在,随着进步的可能性出现,人们变得不可思议的忙——缅甸现在有很多事情要去做;越是有事情要做;人们也就越有动力。我应该澄清,我指的是城市里的生活,即仰光和曼德勒,那里,可能有更多的工作和以前没有过的新工作。比如,我的一个缅甸朋友,曾经经营一本月刊。那时我正在为《寻找奥威尔》找资料,他很和善,花了很多时间和我坐在茶馆里,教我有关审查的知识——它是如何工作的,如何避开它等。他一直梦想做更多,而不仅仅是一本月刊。他的梦想是做报纸,这在军政府统治下是不可能的,因为所有的报纸都国家经营的。在过去几年中,由于政治变化,我的朋友终于能够开始做他一直梦想的报纸。所以不用多说,他不再有太多时间在茶馆里闲聊!
問:你最近回缅甸是什么时候?你发现了什么变化?
艾玛:在我最近一本书出版后,我还是经常去缅甸,不过现在我有一年没有去缅甸了。写这两本有关缅甸的书的灵感主要是想记录一些不能说的故事,想记录一些有消失危险的秘密历史。现在,随着审查制度废除,缅甸人可以说他们自己的故事、记录自己的历史。这是一个令人兴奋充满挑战的时刻。虽然我会继续跟踪在那里发生的事情,不过,我不再觉得有再写它们的必要了。
問:多一个人阅读奥维尔,就多一份自由的保障。你是什么时候第一次阅读奥威尔的?你是怎么看待他的作品的?他怎么影响了你?
艾玛:我第一次读奥威尔是他的《动物庄园》,是学校强制阅读书单上的一部分,那个时候我并没有对奥威尔产生兴趣,直到1990年代中期,在我去缅甸的路上,读到了他的《缅甸岁月》,我才开始对他着迷。它令我震惊,因为我所看到的缅甸还与奥威尔所描写的缅甸一样,因为它的孤立——部分是因为它的地理、社会和文化,同时也有政治原因。阅读殖民时期的缅甸强烈地与军政府统治下的缅甸形成了共鸣——在气氛上它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在控制、压迫和政府的方法上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可以说是缅甸把我带到了奥威尔那里。
如今,奥威尔依然影响着我。我重读了他的小说,更经常地定期地阅读他的文章。他的写作因简单、诚实、有着持续的影响而富有启发性。比如说他的小说《保持叶兰繁茂, KEEP THE ASPIDISTRA FLYING》,尽管写于80年前,那时的世界与现在不太一样,但依然可以解读为一个艺术家面对一个肤浅的争名夺利的世界所做的挣扎的有关研究。
問:你认为奥威尔的缅甸生活经历影响了他的著作吗?今天,他的著作影响了缅甸和缅甸人们吗?
艾玛:我想写《在缅甸寻找奥威尔》的部分原因是那个时候没有一位奥威尔传记作者去过缅甸看过他生活的地方,把他在缅甸可能过的生活拼凑起来。每一部传记都有一个标准的章节是他在缅甸的,但是,却好像毫无生气或是没有内容。因为缅甸在过去那么多年,大部分时候与世界隔绝,外面的人不太可能旅行到缅甸去看看奥威尔曾经生活的地方,像奥威尔在1920年代时候所经历的那样。这让我深切体会到那个国家以及当警察的经验对他的影响,你看他的散文《射杀一只大象》,作为一位警察,他是统治和控制这个国家的殖民政权的压迫机器的一部分,我认为这一点让他恐慌,同样地,这也让他着迷。这个经验肯定会在他后期的小说中不断回应。
写作《在缅甸寻找奥威尔》的另一个前提是一个玩笑,奥威尔不是写了一个有关缅甸的小说,而是三个:缅甸历史的三部曲,开始是《缅甸岁月》(殖民时期),《动物庄园》(社会主义时期),和《1984》(军政府时期,也是我写这本书的时期)。那时,我在缅甸人那里找不到一本《缅甸岁月》,直到前几年,这本书才被翻译成缅甸语出版了,甚至还得了一个奖。
另一方面,泰国(我所生活的地方)现在是被军政府统治。《在缅甸寻找奥威尔》最近也被翻译成泰语,我认为现在对奥威尔重新感兴趣不是一种巧合——在一个书店,我注意到一个书架,曾经只有两三本他的书,现在有超过两排的奥威尔的书。我非常确定,对奥威尔感兴趣与压迫政府试图控制人们如何想、如何行动和如何感觉之间有着直接的关系。
問:为什么那时你找不到一本《缅甸岁月》?
艾玛:我不清楚。我认识一些缅甸书商,他们没有人能够找到一本《缅甸岁月》,他们中的一位在一个私人图书馆里拍了一张封面的照片,所以我知道有这本书。我不能说这本书肯定被禁,但这是一本有关缅甸人对权威体制下的生活回应的很关键的书,所以,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它很难找到。
問:泰国如今也是军政府统治,是不是像你所写的缅甸?
艾玛:我可以简短说说泰国,不过我必须小心我说的,因为现在泰国是军方统治。在写了两本有关缅甸的书之后,我想,我对审查制度和它如何影响作者、读者和民众有了一个很好的了解。然而,现在,从我在泰国的经验,我发现除非它直接对你造成影响,否则是不可能对审查制度有一个彻底的了解。我是在泰国长大的,我一直生活在泰国。虽然我是一位外国人,但我认为泰国就是我的家。当我完成了第二本有关缅甸的书后,我决定写一本有关泰国的书,因为社会变化也正来到这里。我花了五年的时间写完这本书,但是,就在我写完后,我立即意识到,我没有办法在出版这本书后还能继续生活在泰国。目前,泰国军政府非常敏感任何对这个国家的批评,还有一条国王的法律,禁止批评君主制。就像很多我在这本书中采访过的人说的,出版这本书会很危险,所以我决定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出版这本书。写这本书的过程,以及放弃这本书稿的出版,是在审查制度方面以及它如何影响写作和作者方面一个很大的教训。
問:你来过中国吗?中国人也一直对奥威尔感兴趣。
艾玛:我去过中国,但是我对这个国家知道的非常少,将中国与缅甸对比,我很难说出什么。不过,我很有兴趣读到相关话题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