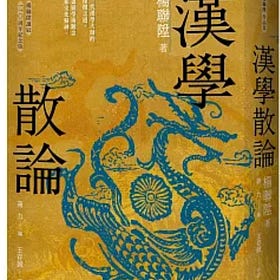周保松 | 思想的力量
編者按:我們至此可以總結說,理解政治觀念的起源和意義,在公民社會耕耘這些觀念,以及運用這些觀念去詮釋和批判世界,就不是可有可無,而是社會改變的前提。在此意義上,只要我們不缺席於時代,政治哲學就永遠不會來得太遲,思想就必然有它的力量。本文為周保松新書《左翼自由主義:公平社會的理念》導論,亦為周保松專欄文章。
一
每個公民︱每個自由、平等的公民︱都有要求得到國家公正對待的權利。1這不是乞求,而是人作為社會成員的基本權利;也不是施捨,而是國家對待公民的基本責任。當個體意識到這項權利並努力捍衛時,國家便不能只靠暴力來統治,而必須提供理由來爭取人民的支持。我們擁有的權利,讓我們可以堂堂正正地參與公共事務,理直氣壯地監督政府。
政治的道德性,來自我們視自身為道德存有,並堅持站在道德的觀點去理解和規範政治:政治不應只是利益計算和權力爭奪,也不應只看黨派不問是非,而應重視人的權利和制度的公平。當這種信念植根於公共文化並得到社會普遍認可,我們就不會認為政治與我們無關,而是自覺我們都是國家的主人,開始懂得運用道德能力去評價政治,甚至身體力行去參與政治。這種文化也會為公民社會提供寶貴的思想資源,容許公民運用這些概念和價值去提升公共辯論的品質和改善政府的施政水平。
要求正義的權利,是自由主義的起點。可是,個體為什麼擁有這項權利,因而使得政治必須講道德,並受到正義原則的規範?我們基於什麼理由,相信這些原則可以得到合理證成,並應用到社會基本制度?最後,這些制度具體應該如何安排,以形成一個公平而有效的合作體系?這是本書要探討的主題。
二
政治必須講道德,和我們如何理解人與國家密切相關。一方面,我們理解人擁有自由意識和價值意識,可以對世界做出反思和評價。另一方面,打從出生起,我們便活在國家之中。國家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要求我們對其無條件服從。面對這一境況,我們就可以合理地問:如果我生而自由,國家憑什麼統治我?
對於上述問題,國家不能說,因為我擁有權力,所以你必須服從。如果是這樣,那就是不需理由和問責的統治,近乎暴政。如果不想這樣,國家就有義務提出理由說服我們,為什麼它享有統治的權利(right),而不是只有統治的權力(power)。從權力到權利,是個尋求「正當性」(legitimacy)的過程,而正當性的基礎,必須是公民經過充分反思後普遍認可的理由。缺乏正當性的統治,往往給個體帶來巨大傷害,例如剝奪人的自由和踐踏人的尊嚴。「政治離不開道德」這個說法,並非描述既有事實,而是召喚一種可以實現的理想:我們希望活在一個有道理可講、有對錯可言、權力須向人民交代的社會。2
本書取名《左翼自由主義》,副題為「公平社會的理念」,旨在闡述和論證一種自由主義的觀點,即以構建公平社會為它的最高目標。它要處理的問題是:社會由人組成,每個人有自己的利益和追求,同時每個人又有足夠的正義感願意參與社會合作,那麼國家應該基於怎樣的一組原則,以及建立怎樣的一種制度,才能夠給予每個人公平對待?3
這個問題關乎社會制度的基礎,影響每個人的權利和福祉,其重要性自不待言。我在本書將提出我的觀點,並邀請讀者與我一起開展一場知性之旅,看看左翼自由主義如何想像和建構一個公平社會。我提出的理由或許未必能完全說服你,這很正常。真正重要的,不是共識,而是在探索過程中,我們學會如何思考這些問題,看到自己的選擇背後的理由,以及這些理由為何重要。本書分為六部分,每部分都有特定主題。當我們將不同部分整合起來,就會形成一個正義社會的完整圖像。儘管如此,由於每章相對獨立成篇,讀者大可根據自己的興趣自由選讀。
三
第一部分「政治與道德」是全書起點,主要論證政治道德如何可能,以及為何重要。只有對這兩個問題有較為滿意的回答,我們才能進入左翼自由主義的實質討論。本部分有兩個概念特別值得留意,那就是「要求正義的權利」和「反思性認可」(reflective endorsement)。前者是個道德命題,後者是個證成方法。簡單來說,我們作為國家公民,也作為道德存有,有要求得到國家公正對待的權利。而當我們運用這項權利去要求政治時,那些約束我們的制度和法律,就必須得到我們的反思性認可。這裡的「我們」,是指擁有基本理性思考和道德反思能力、在乎自己利益和關心正義,並享有平等地位的公民。個體看似很微小,而國家貌似很強大,可是我們一旦接受個體擁有這項權利,整個社會制度的建構,就不能外在於個體的正義訴求。這是本書的基本立論。
第二至第五部分,是本書主體,我將從不同角度去論證左翼自由主義的基本立場,包括:基本自由的意義及其優先性、個人自主的價值,民主的精神、市場和正義的張力、產權和自由的關係,以及自由主義如何回應多元文化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挑戰等。更重要的,是我花了頗多篇幅,去回應右翼自由主義(又稱自由放任主義、經濟自由主義,或新自由主義),包括海耶克、諾齊克 (Robert Nozick) 和傅利曼等代表性思想家的觀點,從而彰顯左翼自由主義的理論特色。在閱讀過程中,大家當清楚見到,我的思想深受穆勒(J. S. Mill)、柯亨 (G. A. Cohen) 和羅爾斯(John Rawls)等哲學家影響,而我心目中左翼自由主義的代表作,是羅爾斯的《正義論》。4
具體而言,一個自由主義式的公平社會有以下制度特點:主權在民,公民享有一系列由憲法保障的基本自由和權利、普及而平等的民主選舉、滿足機會平等和保障勞工權益的市場經濟、健全的社會福利政策(教育、醫療、房屋、失業和退休保障等)、每個社會成員都能從中受惠的經濟發展,以及建基於平等尊重的多元文化社會等。
這幅圖像背後,反映這樣的信念:每個公民都是國家的平等成員,不管其社會背景和能力高低,都有要求得到國家公正對待的權利。在這樣的社會,沒有人受到制度的忽略、排斥和歧視,也沒有人只是他人或集體的工具。相反,每個公民都應享有充分的基本自由、公平的平等機會,以及足夠的社會和經濟資源,去發展自己的能力和活出自己認可的人生。就此而言,自由是我們的根本利益,平等是我們的道德關係,正義則是平等的自由人公平地生活在一起的基本原則。這三項價值,不是非此而彼,也不是互相對立,而是構成公平社會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這樣的自由主義,自然反對威權主義和極權主義,因為它將保障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權利放在首位,並要求權力必須得到人民的授權。與此同時,它也反對自由放任的市場資本主義,要求政府通過政治和經濟制度上的安排,確保每個人從出生開始,便盡可能享有公平的教育和競爭機會,並在經濟條件許可下,通過稅收和財產分配制度,為所有公民提供完善的社會福利,尤其是關顧弱勢階層的需要,並採取必要措施防止貧富差距無止境地擴大,因為這樣會對民主政治的有效實踐,以及公平的機會平等帶來極壞影響。自由左翼和自由右翼最大的分別,是它將「公平社會的理念」放在首要位置,並從這個角度去看待和規範市場。左翼不是反對市場本身,而是認為市場是社會制度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不能先於和獨立於社會正義。
本書最後一部分,主題是「往事與時代」。這組文章,記載的是我多年的公共實踐以及對這些實踐的哲學反思,也可說是個人的時代見證。正常的政治哲學著作,不會有這些文章,因為那會顯得不夠純粹和學術。我幾經考慮後,還是決定將它們收錄,一來這些文章能印證我所說的公共哲學的理念,二來我的哲學思考其實離不開這些個人經歷。政治哲學作為一門規範性學科,本身就有實踐的一面,畢竟它不是在描述世界,而是在要求世界。而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活在一個不自由的社會,去到某些關鍵時刻,一如其他公民,覺得有必要站出來表達自己的態度,實在自然不過。這組文章不是冷靜的學術書寫,筆端有我許多個人情感,希望讀者理解。
四
本書的主題,是政治理論,難免牽涉學術名詞,也有各種概念分析和哲學推論,不過,我有一個很大的心願,就是一般讀者也能夠讀得進這本書。所以,在寫作過程中,我很有意識地在做一種寫作實驗,就是盡可能地清楚和明晰。不過,有人或會說,抽象晦澀是哲學的本質,因此最好留給學者在象牙塔研究,普通人既沒興趣、也沒能力思考這些問題。
我不認同這種看法。首先,政治哲學的工作不應只局限於學院,而應面向所有公民,因為它處理的問題,關乎公民的根本利益。其次,認定人們對這些問題沒有興趣,其實沒有道理。多年來,我有許多機會,在不同場合和人們公開討論政治哲學。我發覺,無論是在廣場、咖啡館、書店,還是網路平臺,大部分參與者都對哲學討論有極大熱情,並且能夠提出很有深度的問題。最後,要推動社會轉型,前提是要有大量關心公共事務的公民,而要培養出這樣的公民,活躍的思想討論不可或缺。
這樣一種面向公眾的政治哲學,今天看來可能很不尋常,可是在二千多年前的雅典城邦,蘇格拉底(Socrates)實踐的正是這樣的哲學。蘇格拉底終其一生,都是在雅典街頭,和一般老百姓討論哲學,探究什麼是真理、美德和正義,結果被告上法庭,以「荼毒年青人」及「不相信本邦神靈」的罪名公開審判,並遭五百零一人的陪審團判處死刑。5 蘇格拉底向我們展現的,就是一種公共哲學:在城邦,以公民身分,用大家能夠理解的語言,和其他公民一起,反思重要的人生和政治問題。來到我們的時代,政治哲學同樣可以在社會發揮類似作用,例如:設定值得社會關注的重要議題、推廣公共說理的精神、理解政治觀念的意義、批評不合理的法律和政策,以及提出社會改革主張等。
公共哲學的工作,有助於公共文化的發展;而公共文化的發展,又對推動社會進步有莫大作用。為什麼呢?我們總是活在某種文化之中,文化會為我們提供必要的思想養分。社會要改變,需要人的行動;人的行動,需要價值和思想的指引;價值和思想,來自我們的公共文化。如果文化本身欠缺足夠的道德資源,人們就很難去做出有意義的反思和批判。此外,政治權力的行使,必須滿足正當性的要求,而後者很大程度上來自全體公民的反思性認可。在反思過程中,公民可援用的道德資源,同樣離不開我們的文化。我們因此須明白,在公共領域從事文化建設,就不是可有可無,而是具有重大的實踐意義。
五
儘管如此,我們也須清醒地認識到,即使政治哲學有它的角色和位置,社會轉型往往需時甚久,而且極為艱難,因為轉型意味著制度的根本改變,遭到既有勢力的頑強抵抗自是理所當然。社會轉型要成功,需要許多條件配合,例如新觀念的傳播、民眾的覺醒、反對力量的形成、公民社會的團結,以及政權內部的矛盾和分裂等。要逐步形成這些條件,需要許多代人的努力,而在最後成功之前,沒有人能夠告訴我們,我們需要為此堅持多久以及付出多大代價。這種不確定性,對活在歷史當下的我們,是很大的考驗。
舉例說,臺灣的民主轉型,相較許多國家已算順利。可是回溯歷史,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時,一九六○年《自由中國》被查封及主編雷震先生入獄時,以至一九八○年「美麗島事件」大審時,相信當時沒有人能夠預料得到,臺灣要到一九九六年,才有第一次民主總統直選。在這個漫長的抗爭過程中,無數人失去家庭、事業、自由和生命,甚至在曙光未見之前,許多犧牲者已在歷史長河遭人遺忘。
既然如此艱難,抗爭者憑什麼堅持下去?最重要的,一定是對某些價值的堅持。他們必定相信,自由和民主是極重要的價值,值得為此付出。他們也必定深信,即使當下遭受重大挫折,也總會有相同信念的人願意接力下去。如果革命只有激情,卻沒有經得起理性檢視的價值,在步入歷史低谷的時候,人們很容易就會自我懷疑和自我否定,認定之前所做一切皆是虛妄,未來所有努力盡是徒然。既然如此,堅實的信念如何建立?這是不容易回答的問題。可能來自我們對人類抗爭史的瞭解,也可能來自友儕之間的互相砥礪。不過,至為關鍵的,是對我們所堅持的價值,有足夠的認識。認識的過程,無可避免牽涉到對各種觀念(ideas)的理解、修正、揚棄和肯定,因為我們的價值體系,由觀念構成。
我年輕的時候,初次讀到伯林(Isaiah Berlin)的〈兩種自由的概念〉,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在文章開首告誡讀者,千萬不要低估觀念的力量,因為哲學家在書房中孕育出來的觀念,可以摧毀一個文明。6 我當時只覺得這個說法頗震撼,卻沒有很深的體會,直到近年才慢慢明白,那是因為人是觀念的存有。人創造觀念,然後通過觀念瞭解自我和認識世界,並為行動賦予意義。觀念一旦改變,我們看世界的方式就會跟著改變。觀念的革命,才是最根本的革命。
誠然,任何觀念的產生、成長和衰落,不會無緣無故,而是有特定的社會脈絡和歷史條件。可是,一個觀念的內在理路和價值意涵為何,確實有賴從事觀念工作的人的知性努力。最明顯的例子,是自由。自由是人人珍惜的價值,在社會運動街頭,許多人都會大喊「為自由而戰」。可是,自由卻是個一點也不簡單的觀念。在西方思想史上,從霍布斯(Thomas Hobbes)、洛克(John Locke)、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到康德(Immanuel Kant)、黑格爾(G.W.F. Hegel)、馬克思(Karl Marx)、穆勒,再到當代的伯林和羅爾斯,就各有不同的關於自由的學說。如果自由對我們重要,我們到底在談什麼版本的自由,就是須先弄清楚的問題。只有在這個基礎之上,我們才能確切知道,我們什麼時候是自由的,實現自由需要什麼制度條件,以及不自由的狀態為何如此難以忍受。
我們至此可以總結說,理解政治觀念的起源和意義,在公民社會耕耘這些觀念,以及運用這些觀念去詮釋和批判世界,就不是可有可無,而是社會改變的前提。在此意義上,只要我們不缺席於時代,政治哲學就永遠不會來得太遲,思想就必然有它的力量。7
本文注釋:
1 本文源自〈我們非如此不可〉一文,由於已大幅度重寫,故另起新題。原文見周保松,2020,《政治的道德:從自由主義的觀點看》(第三版)。中文大學出版社,頁xvii-xxvii。又,我會在本書交替使用「正義」和「公正」指涉英文justice一詞。
2 羅爾斯便認為,政治哲學其中一個角色,是追求「有機會實現的烏托邦」(realistically utopian)。John Rawls, 2001, 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 ed. Erin Kelly,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 4.
3 如果國家能夠合理地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就可以說,這個社會是正義的,國家權力的行使就具有很高的正當性。
4 John Rawls, 1999, A Theory of Justice (revised edition),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5 詳情可見柏拉圖,2004,〈蘇格拉底的申辯篇〉,《柏拉圖對話集》,王太慶譯。北京商務印書館,頁25-55。
6 Isaiah Berlin, 2002,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in Liberty, ed. Henry Hard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167. 此文最初發表於一九五八年,是伯林就職牛津大學政治理論講座教授時的演講辭。
7 馬克思認為,「哲學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而黑格爾認為,在指導世界應該怎麼樣這個問題上,哲學總是來得太遲。馬克思,1972,〈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中共中央編譯局編。人民出版社,頁19;黑格爾,1996,《法哲學原理》,范揚、張企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頁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