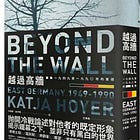林育立|挑戰流行敘事,寫下不為人知的東德史
編者按:1990年10月3日,柏林圍牆倒下,一個國家——東德消失。這個長期被描繪成一個單調的灰暗的共產主義國家是怎麼樣的?歷史學家霍伊爾以全新作品《越過高牆》,重新撰寫這個已經被消音的國家。她運用了大量訪談、書信和檔案紀錄,讓東德各式不同意見得以發聲,以萬花筒般的新視野來描繪這個鐵幕國家,揭示之前不被看見的豐沛社會與文化景觀,並聚焦於極權統治下充滿活力的東德人民,他們有落淚與憤怒的時刻,也有歡笑與榮耀的時刻,他們的生命故事組成了書中所敘述的國家。
作者Katja Hoyer是一位德裔英國歷史學家、記者和作家,1985年出生於東德。她在東德出生後不久,隨家人移居英國,她的父母曾在東德政府部門工作,這使她對東德歷史有個人聯繫,同時也具備外部觀察者的視角。與傳統歷史書寫聚焦政治精英或史塔西(Stasi)監控不同,Hoyer將普通東德人的經歷置於中心,探討他們如何在社會主義體制下生活、適應和反抗。Hoyer利用了新近解密的檔案資料和東德普通人的口述歷史,為學術研究注入了第一手資料。這些資料包括個人日記、信件和政府檔案,幫助重建東德人的日常生活和心態。例如,書中提到東德政府試圖通過社會福利(如低廉的住房和教育)來換取民眾忠誠,這種“社會契約”分析為研究東德統治合法性的學者提供了新線索。Hoyer挑戰了西方對東德作為單純“壓迫性獨裁政權”的簡單化描述,提供了更細緻的歷史圖景。書中強調東德社會的複雜性,涵蓋其經濟困難、社會福利成就(如高女性就業率、免費托兒服務)以及文化生活,試圖平衡對東德的負面刻畫。根據《泰晤士報》評論,該書被視為“修正主義歷史”,揭示了東德在教育、醫療和社會流動性方面的進步,這些往往被冷戰宣傳忽視。這種視角為學術界提供了一個更全面的框架,促進對東德社會運作的重新評估;同時,Hoyer因淡化史塔西的恐怖統治而受到批評。
7月,台灣八旗文化出版了該著作中文版《越過高墻:1949至1989年的東德》,本文為旅德記者林育立所寫導讀,出版社授權刊發。
免費訂閱《波士頓書評》及相关事宜发送邮件:boshidunshuping@gmail.com,隨意打賞:Zelle,PayPal:boshidunshuping@gmail.com 用戶名:Boston Review of Books;長期支持請點擊下面訂閱,升級為付費訂閱。
談起共黨統治的東德,台灣人的印象不外乎貧窮落後、蘇聯附庸或情治機關無所不在的監控。這個隨著兩德統一從地圖上消失的國家,彷彿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僅剩下負面的聯想。本書就是要打破這些刻板印象,提醒大家不要忘了東德留下的豐富歷史和文化遺產,甚至是認識今日德國和歐洲的重要切入點。
作者霍伊爾一九八五年生於東德,定居英國逾十年,本業是歷史研究。《越過高牆》二○二三年在英國出版,出版後即備受好評,馬上成為暢銷書,隨後在德國也引發熱議。今年十月,德國統一即將屆滿三十五週年,這本以東德歷史為主軸的新書有什麼特色,為何值得一讀?
首先,過去與東德相關的著作,主旋律是回顧威權過去,說出被壓抑的幽暗記憶,凸顯政治高壓的一面。回顧德國二十世紀歷史,戰敗後與納粹決裂,在廢墟中重建民主自由是最常見的敘事,即便因冷戰對立被迫分裂,最終還是達成美好的統一結局。東德同一時間固然存在,卻被視為無足輕重的配角,因為獨裁體制,還經常被拿來與納粹相提並論。
霍伊爾的出發點是東德不像一般描述的那麼糟糕,多數東德人既非對黨國體制絕對效忠,也不是挑戰禁忌的異議人士,他們接受體制而且與圍牆和平共存。霍伊爾想挑戰時下流行的敘事,用新觀點寫出東德從建國到消亡的故事。
其次,霍伊爾出生四年後,柏林圍牆即倒塌,不算真正經歷過東德;不過,她從小耳濡目染,見證東德消失和兩德統一對身邊親友的衝擊;她收集大量訪談,將個人親身經驗放進大時代來看,執筆盡可能不評價,讓讀者自行判斷。我們既讀到獨裁政權對個人生活的介入,也讀到樂觀上進的精神。
東德與西德一樣位於冷戰最前線,內政外交受美蘇兩大超級強權左右。圍牆倒後不到一年兩德統一,從制度來看是東德併入西德,從此談東德多從外交和政治面切入,聚焦蘇聯附庸和體制壓迫的一面。事實上,東德領導人對蘇聯又愛又恨,而且東德發展歷經不同階段,難以一概而論,讀了本書我們才發現存在四十一年的東德,比想像中豐富許多。
本書從最早的萌芽階段講起,一群對史達林崇拜的德國共黨人士,在二戰結束前從莫斯科回到柏林,打造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和經濟國有化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段歷史是理解東德的關鍵,可惜過去很少人提。
一九五○年代,這個全新的國家必須支付蘇聯戰敗的賠款,還得負擔與西歐軍力抗衡的軍費,經濟很快就陷入危機,靠蘇聯坦克鎮壓才得以平息全國性的大示威。為阻止人民出走西德和西柏林,一九六一年興建圍牆,德國分裂從此成為常態。圍牆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競爭的分界,撕裂家庭和對逃亡者格殺勿論,也讓圍牆成為壓迫的象徵。
一九七○年代,東德生活水準提升,外交上獲國際認可,開始與西德來往,不過內政上也發展成高效率的警察國家。到了一九八○年代,東西德交流漸趨熱絡。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一九八五年上台,渴望與西方交往,東德領導人卻思維僵化,與中東歐風起雲湧的民主運動背道而馳。終究人心思變,人民不僅推倒圍牆,還要求與西德統一,為東德的命運劃下句點。
一如作者所言,東德的經濟、文化與社會傳統,不會在一夜之間消失。東德存在的時間,其實比同一世紀的威瑪共和與納粹統治都要長,影響到今天仍在,卻是談到德國時經常被忽略的切入點。舉例來說,由亞歷山大廣場和卡爾.馬克思大道構築的東柏林市中心,當年曾富含理想和進步的精神,東德建築至今仍主宰柏林的景觀。在東德,公寓租金低廉是常態,由於就業率高和完善的托兒服務,出身東德的女性往往比西德更有自信,這些都成了德國社福政策的施政目標。
德國統一後,東德人將全部力氣用在適應新體制之上,每個人的工作和生活都歷經巨大的斷裂,被迫與過去一刀兩斷。他們先是無暇回顧,過去重要的一段人生經歷彷彿虛度,加上對經濟期待的落空,在與西部磨合的過程中充滿摩擦。每隔五年和十年,德國總是大肆慶祝統一週年紀念日,東西德的生活水準差距每次都成為話題,統一似乎只能從物質生活的角度談,少有深入探討東德人的觀點,也缺乏東西德的對照。
近年,情況終於好轉,包括霍伊爾在內,多位出身東德的作者推出新書,在全國引起熱烈討論。其中奧施曼(Dirk Oschmann)的《東德:一個西德的發明》(Der Osten: eine westdeutsche Erfindung)尤其頗受爭議。奧施曼與霍伊爾一樣,反對將東德簡化到只剩下獨裁和監控,他指控西德對東德的征服和掠奪,從未把東德當成主體,不在乎東德人的想法。身為文學史教授,奧施曼在學術生涯中受夠了西德人的侮蔑和嘲諷,把壓抑三十年的憤怒一股腦兒發洩出來,果真寫出了一本驚世之作,高踞暢銷排行榜。
歷史學家依爾可—科瓦卻克(Sascha Ilko-Kowalczuk)在新作《自由的震撼》(Freiheitsschock)中,批評東德人雖然推倒圍牆獲得自由,卻沒有負起相應的社會責任,思維至今仍受威權統治思維的宰制,因此傾向美化獨裁過去,這是對極左勢力最近在東部崛起的批判。前總理梅克爾任內少談東德,卸任後出版的傳記《自由:回憶錄1954-2021》卻大篇幅回顧過去,原來東德的青少年階段對她從政風格有決定性的影響。
霍伊爾這本書在德國也是暢銷書,讚譽者稱她從人民的角度寫出真正的東德,批評者則指她美化威權,不提意識形態和政治高壓對人的烙印,讓人誤以為東德是一個成功的故事。
無論如何,圍牆倒下後三十多年的今天,中生代的寫作者拉開時間和距離,似乎更能打破偏見,擺脫意識形態的對立,冷眼回看東德和檢視統一的進程。人的故事是本書的核心,在威權底下的生活有期待、有失望,也可能多采多姿。本書只是開始,東德留下的豐富歷史、文學和藝術遺產,正等待世人去發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