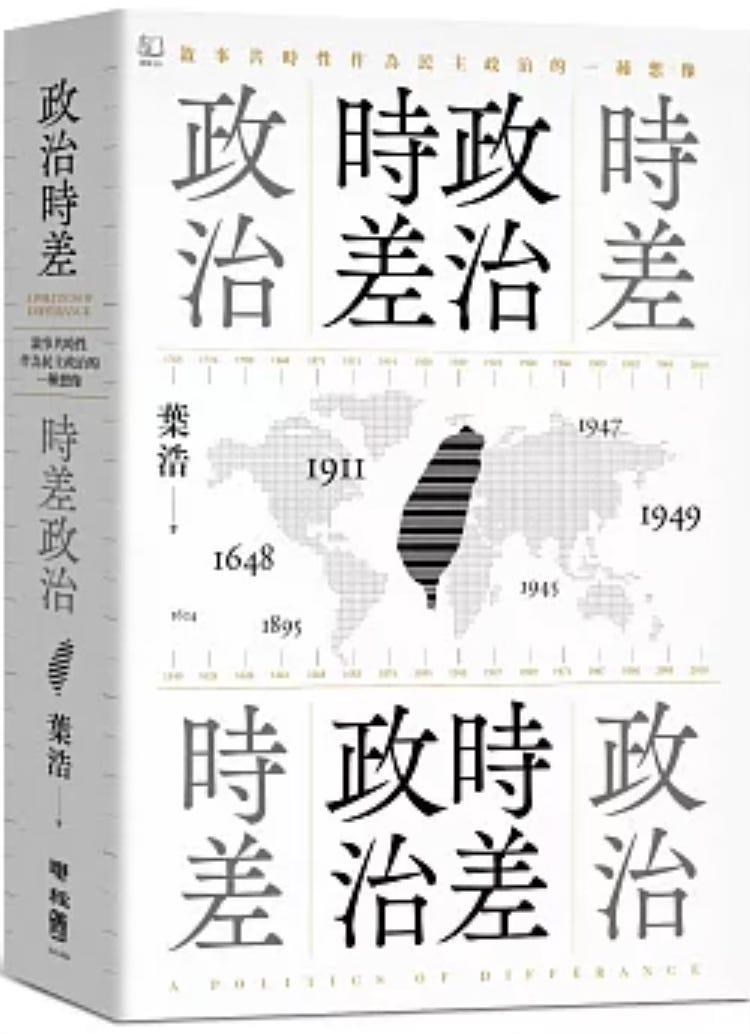葉浩訪談 | 台灣美國何去何從(下):台灣和美國問題都不是單純的左右問題
編者按:台灣從哪裡來又往哪裡去?1987台灣民主化之後,台灣開始了自己的敘事和思考。然而,誰才是台灣人?三百多年來,一批一批移民進入台灣,他們各自有著自己歷史記憶與未來的想象。如何看台灣文化與政治的“亂象”?7月,聯經出版台灣國立政治大學政治係教授葉浩新書《政治時差.時差政治:敘事共時性作為民主政治的一種想像》,用一個全新的概念“政治時差、時差政治”來分析台灣歷史與政治的特殊性。他認為移民和移植造成了臺灣特有的「雙螺旋時差結構」,既成就了文化思想的多元,也分裂了政治認同及諸多議題上的共識。這也是台灣需要面對和解決的問題。訪談中,他還用“政治時差”分析了特朗普出現的原因,和美國民主面臨的危機。8月初,葉浩教授通過電話接受了波士頓書評採訪。訪談分為上下兩個部分,昨天書評已經刊發《葉浩訪談 | 台灣美國何去何從(上):台灣的最大的問題是史觀》,此為下部分《葉浩訪談 | 台灣美國何去何從(下):台灣和美國問題都不是單純的左右問題》。
葉浩訪談(下):台灣和美國問題都不是單純的左右問題
書評:那你有沒有對台灣未來的想象?或是說,台灣如何走出時差政治的格局呢?有沒有共時性的開端這種可能性?
葉浩:當然對未來有想像。最好的狀況是我在書中所說的「敘事共時性」,narrative synchronicity。首先要說的是,這裡的「共時」不是「同時」。同時是一種物理上的同一時間。人類學及比較政治學者安德森曾認為現代印刷技術促成了民族主義。因為,那讓人們可以在同一天看到同一份報紙,接受同樣的資訊,因此對特定的事情有了共同的認知,而媒體報導的人事物也會逐漸塑造出一個眾人想像彼此生活在一個共同體邊界。民族國家就是這樣的一種「想像共同體」,即使多數人彼此不曾相見,但卻能感覺到彼此活在同一個社會,是同一個政治社群的成員。
我說的共時性,不是這一種同時性。共時指的是生活在同一個時序,同一個政治時間當中。一個社會是由已離開世界的前人、生者及尚未出生的來者所共同組成的。這三種人當然不可能活在同一時間,共享同一物理時間的各種認知。能共享的是一種敘事,也就是鄂蘭所謂的「故事」, story。對她來說,唯有親身經歷的過去才是自己故事,才是真正的「歷史」。這種歷史不是套用任何一種「史觀」或史學方法論的結果。相反,那看重的是一群人的真正經驗,經歷,包括前人篳路藍縷地來到了某一地方,共同打造了一個社群,後人接續了他們的故事,也有意識地認為自己是他們的後代,願意延續那一個社群的繼續存在。當活著的人是如此,尚未出生的來者也能繼續,繼承一個傳統,傳承一個故事,並未這一個故事增添了屬於他們自己時代的情節,那就是一個專屬於一群人的真實故事,活的故事。「敘事共時性」是我從鄂蘭的政治思想,從她的文本當中提煉出來的一個概念,指的就是這一種真正的、活的故事。作為一種歷史,那沒有未卜先知的能力,也不該完全不顧過往的人他們的真實經歷。那是硬套史觀的人最常做的事,例如進步史觀就是一種把前人當成是替自己鋪路的人,甚至後人也必須走在自己鋪好的路。統一史觀,循環史觀也是。那不允許活人去開枝散葉,去打造他們自己故事,新故事的可能。歷史,被當成早就寫好的劇本,而且所有人都被指定好了角色,既不准更改劇情內容,也不能更換角色。敘事共時性想法剛好相反。那承認每一個世代都有專屬於他們的故事,都是那一段故事的共同主角。而不同世代的人的故事,若要有連結,那必須是後代的人願意認同前人的故事也是他們的故事,願意把前人的故事當作他們故事的前一段,甚至是開端,然後將那故事延續下去,創造屬於他們自己時代的精彩。
如果下一代人,尚未出生的人也能繼續認同下去,那麼,這故事就是死者、生者,來者所共同生活的一個時間順序。這種狀況就是我書中說的敘事共時性。雖然不是活在物理上的同一時間,也彼此不曾見面,但卻像是活在同一個故事當中的共同主角。活者願意接續前人的敘事,也為後人保留一個開放的未來,擁有他們自己故事的可能性,不管那意味著為已經存在的共同故事增添了屬於他們自己的情節,或是去開創一個全新的、專屬於他們自己的故事。只有當這可能性存在而後人仍願意接續時,不同「世代」的人才能是這一個故事的「共同主角」。
主張這一種敘事共時性,也意味著我的書作為一個政治哲學理論的嘗試,不能把故事說死,把未來給說死。相反,那最多只能把問題講清楚,把過去到現在的實際狀況講清楚,至於未來人們將走向哪一個方向,開創什麼樣的故事,那不是我這一種政治哲學的工作。不過,那不意味著我不能指出幾種可能性,或有個人偏好。我在書中提出了未來有許多可能,但也負責任地指出那些可能性的內在風險。我對台灣其實抱持著一種比較悲觀的想法。幾百年來,台灣這一塊土地上,主要的族群從來沒有決定自己的命運過。即便是在現在,台灣的命運也不會是完全由台灣人來決定,比如說如果你真的要獨立,你還要國際社會的承認、認可、支持,而且還要某種程度中國共產黨要讓步。所以台灣這個土地的人民,並沒有辦法完全的掌控自己的命運,這是一個現實,這是幾百年來的一個現實,這是蠻悲哀的。但這不代表不能夠做點什麼,所以我提了幾個可能性,從國是會議的召開,要不要大幅修憲,要不要立憲,要不要宣布進入下一個共和,等等諸如此類。
國是會議,都已經足以引起中共跳腳;如果你說要立憲,那它應該會很有理由要發生一些衝突了,宣布進入下一個共和等等,也都可能引起一些衝突,這一些我當然希望能夠做,可是,如果要做就必須要付出高昂的代價,但這是不是台灣人願意付出的?這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個實質主權國家,如果想要成為一個國際社會認可、可以加入聯合國的法理上的主權國家就一定要付出一些代價,不管類似烏克蘭或其他國家那樣,這是從19世紀開始,就已經在國際上出現的一個潛規則。伴隨著19世紀民族主義來的,是一個自決的概念。民族主義主張每一個民族都可以獨立建國,建立一個屬於他們自己的民族國家。但是你要怎麼做到這一點?你要打仗!從19世紀開始,在國際政治思想或國際法學上都允許民族自決,都說人們有這種法理上的權利。但國際社會要求想獨立的民族必須證明給人我,為什麼你是一個獨立的民族。所以從19世紀開始,即便是約翰彌爾這一類捍衛民主的自由主義者也明確主張,唯有拿起槍桿子捍衛自己的群體才能稱得上一個民族,要不然別人不會認真把你當作一個值得獨立的一個群體。我們現在的國際法仍是如此。
事實上,二戰之後,有三部重要的相關文件:《聯合國憲章》、《世界人權宣言》,以及《人權兩公約》,這三份文件都很清楚地主張人民自決權利, 使用的字詞是「self-determination of all peoples」。這是國際法的部分。二戰剛結束的時候,許多前殖民地採用了公投的方式,進行了各種各樣的制憲公投並宣佈獨立。這是因為二戰結束的時候,殖民帝國如大英帝國、法蘭西殖民帝國等,願意放棄殖民地,讓殖民地都可以在聯合國的監督或託管底下,進行公投,然後宣布獨立。可是台灣沒有趕上這一波。除開這一波公投建國的之外,大多數是靠打仗來實現的。聯合國允許了公投自決,但想獨立的人民還是得證明給國際社會看。白紙黑字的規則之外,還有一個潛規則的存在。所以我在新書的第三部分,指出了多種方法,但這些方法是台灣人民願意的嗎?如果引起那麼大的騷動,中共決定不惜一戰的時候,那我們是否有足夠的意志去貫徹到底?如果爭的是從實質主權轉為法理主權,這是逃不掉的,國際社會不會平白無故送你一個法理主權的資格,這是癡心妄想。不管實質上的獨立有多久,都不會自然形成一個法理主權國家,如果法理主權指的是國際社會的認同並加入聯合國。意志的展現及政治行動是必須的,包括代價。
書評:那有沒有消除政治時差的辦法?
葉浩:調整時差的方法其實有許多種,剛剛談過的敘事共時性就是一種,讓島上的人活在一個共同時序當中。實踐上那指的是鄂蘭所謂的開啟一個新的故事,也就是用政治行動來開啟一個新的故事,讓大家有一個全新的開始,而且不同族群都是共同主角。比如召開國是會議,讓不同的黨派、學者及關心島嶼共同未來的人都能參與,在社會上至少三個月到半年的時間來討論,讓議題發酵,讓大家來好好吵一下台灣到底是什麼,然後要制憲還是要公投,還是要進入下一個共和。也藉此讓社會清楚認知到,這幾種可能性的實現究竟包括了哪些必須付出的代價。這是最激烈的一種,也相當符合鄂蘭個人藉討論美國獨立及革命所提出的政治主張。在這裡,「講故事」三個字是一個動詞。那意味著以政治行動來開始一個新的故事,專屬於此時所有台灣人的共同故事。
不過,講故事也有另一種理解,那就是重新講述台灣的歷史。這時候,重點在於「故事」兩字,是名詞。簡單說,重新修正台灣的歷史認知,包括重新書寫歷史課本。教科書歷史一直以來在台灣是個大問題。誰執政的時候,誰就要去改寫中小學課本的歷史,但我們從來都沒有把台灣的歷史寫成一個移民島的歷史。我們太習慣採用單一民族的角度來看帶過去,然後把特定民族或族群的集體記憶當作所有人都必須要接受的共同歷史,而且都是要背的。我認為把台灣歷史寫成一個移民島嶼的歷史,是最符合所有族群實際經驗與史實的方法。這是第二種調整時差的方式。當中並沒有藏著一個線性史觀,只是承認了所有不同族群的經驗,不同的集體記憶,包括原住民及漢人的集體記憶。重點在於讓歷史書寫與歷史經驗吻合,成就鄂蘭所謂的「故事」。希望我這樣講也解釋了為何我不支持單一民族的史觀,尤其是將那種民族主義硬套在台灣。
第三個方法就是處理威權時代的遺緒,讓台灣的民主能夠比較好地運作下去,也就是先處理轉型正義的一部分的問題,打造一個比較適合民主政治運作的政治文化。其實台灣還有很多人在某種意義上活在白色恐怖的時代。在那年代,如果要抗議政府一定是採取絕不妥協的激烈手段,比如說自焚當烈士,也只有這樣的方法才能夠展現道德高度。或許也因為柏楊當年寫了一本《丑陋的中國人》,把妥協跟醬缸文化做了連結,因此在台灣人們提到妥協時會覺得那就是一種道德上的不堅定,騎牆派,甚至是向強者的屈服,是一種懦弱的行為等等。柏楊的說法的確直指了在白色恐怖時代底下的一種社會現象。實如此。不過,那一種不溝通,不對話,不談判,不妥協的作法卻維持到現在。整個社會基本上缺乏對話能力及論述能力。藍綠兩邊都沒有,白的也一樣。欠缺論述能力本身就沒辦法有能力對話,也因此無法把自己的想法清楚地呈現,然後再來討論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哪些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事,因此該如何折衷或取得某一種平衡。簡單說,也就是欠缺妥協作為一種政治技藝的能力。我們已經進入民主時代了,雖並不完善,但怎麼說也有一個立法院,而立法院照理說就是一個讓大家好好吵架的地方。
吵,指的是因為認同特定的想法及價值,所以有情緒,有堅持,也是為了把話講清楚,但我們連吵架都不會!一來是許多人怕吵,懷念歲月靜好的日子,覺得就是不和諧,不懂得和諧。二來則因為民主制度並非內生的,因此不是在多數民眾認識並認同民主價值,熟悉它的運作方式之後才有的。相反,民主是外來的政治理念,是借來的,甚至是抄襲來的,因此民眾尚未有西方民主國家所具備的認知,政治人物也尚未培養出論述、溝通及說服的政治藝術。其結果是兩種極端。格外關心台灣前途的公民團體及社運人士,持續堅持不妥協的態度來運作民主制度,無法理性對話。另一邊則是維持白色恐怖時代那一種怕談政治,甚至轉為討厭政治的群眾。他們不管政治,相信專家,相信凡事都有標準答案,包括政治的事,例如政治就該拼經濟,拼經濟就是拼GDP。這種想法不僅非常符合前面提到的新自由主義,也弔詭地促成了人們對強人政治的懷念,甚至回過頭去把獨裁者當偉大的國家經濟擘畫者、經濟奇蹟的締造者來歌頌。
懷念強人及靜好歲月,相信專家治國,不在公共場合談政治,甚至許多單一議題的公民團體在倡議時都會以「我們不談政治」當起手式,加上那進入議會或政府機構,仍堅持不對話、不妥協的政治文化,基本上都是威權時代的遺緒。正視這種遺緒的存在,然後開始補課,學習民主制度的運作方式,培養適當的政治文化,也是一種調整時差的方式。如果獨立建國這種偉大事業暫時做不到,我們至少可以先重這件事開始做起。它調整的是什麼時差呢?民主制度與政治文化的差距。這是一種時差,因為那是拿著過去威權時代的心態、想法、期待與習慣來操作著此時的民主制度才產生的問題。我在書中把這種落差稱為時差性「政治異化」。
第四個書中提及的主要解決方案,是讓國內法跟國際人權法接軌,也就是真正去落實在2009年已經成為位階上進次於憲法、高於一般法律的人權兩公約。雖然這一部國際人權法已進入了國內法,但其實一般大眾對它並不熟悉,甚至可以說不以為意。對我來說,它指向了一個明確的社會改革方向,也可以某程度上轉化藍綠或者是左右的問題。因為兩公約已經是我們的法律了,照理說一步一步去執行兩公約的內容是必要的,包括內容本身所包括的轉型正義、廢除死刑以及人民自決。當然,如果人民自決此時做不到,那至少可以先修改國內法使之符合兩公約,讓法律一來變得比較有連貫性、一致性,二來則藉此調整了國內法及國際人權法的時差。當然,這件事情本身當然不可能直接解決統獨,但過程當中社會也能更好地認識人權、法治等概念,甚至因此能以這些理念作為凝聚認同的基礎。
書評:你剛才說,威權主義的遺緒去運行民主制度是一種异化,这个“异化”的概念和观念的差异、政治时差有什麼區別?
葉浩:好問題!「時差」是我試圖分析台灣政治爭議的切入一種角度,也是針對現實的一種描述,但到現在還沒說細說為何我們必須正視時差的事實。原因是時差能造成一種異化,也就是alienation。我在書中把諸多時差產生的問題稱為時間性政治異化。主要體現在四個層次。一是不同的族群之間的意識形態衝突。不圖的政治時間想像,意味著對同一政治事件可有相當不同乃至對立的理解,甚至可以同時引發兩邊的亡國感——只是亡的是兩個不同的國家!第二是民主制度跟政治文化之間存在的嚴重落差。那不但會讓民主難以運作,更會讓人們因此斷定民主不是個好體制,或不適合台灣,甚至不適合中國人。第三個層次的異化在於台灣的民主政治和國際人權建制之間的距離。這距離一方面指當前運作的法律尚未接軌已納入國內法的人權兩公約內容,尤其是兩公約所指向該落實的轉型正義、廢除死刑及人民自決,另一方面則指台灣跟國際社會的嚴重脫軌。正是因為這種脫軌,才會讓許多人完全無視2010年起聯合國致力於在全球推動的轉型正義。事實上,目前效仿南非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國家有三十七個。認同德國那一種更嚴厲的司法起訴模式,也就是制定所謂「除垢法」(Lustration)的國家,也有十二個。但如此愛談國際觀及國際社會的台灣人民,有一半卻毫不知情,甚至認定那不過是一種仇恨政治,既無視那是馬英九政府在2009年批准兩公約入法之後即必須努力實踐的事,更把之後開始來台灣的國際人權觀察組織當作綠營的政治操作。
然而最值得關注的異化或許是第四種,也就是中華民國的公民普遍對於中華民國曾經在國際人權建制形塑過程中的貢獻相當陌生。剛剛提過了奠定當前國際社會規範及人權建制的三份文件,也就是《聯合國憲章》、《世界人權宣言》,以及《人權兩公約》。事實上,中華民國除了是聯合國的共同創始會員國之外,安理會代表張彭春更是《世界人權宣言》的共同草擬人,當時甚至認為孔孟之道與奠定於基督教神學的人權相通。《人權兩公約》則是根據《世界人權宣言》進一步條文化的結果,於1966年年底通過之後,中華民國在第一時間即簽署了該公約。當然,2009 年才正式批准,就是一種相隔四十二年的時差,但更重要的是此時的國民黨及多數台灣人對中華民國曾與許多國家共同打造的那一個國際社會,那一個國際人權建制不僅陌生,甚至認為那是西方人的東西,不具普世價值。借用馬克思的講法,認不出自己生產出來的東西,甚至是活在一個自己曾參與打造卻認不得的世界,那就是一種異化。相當標準的異化!我在書中有論及「異化」概念如何源自於猶太教,馬克思和黑格爾等哲學家如何改造那概念,以及這概念的應用層次和意義。上述的四種時差所引起的政治異化,分屬在不同層次的運作上。區別它們,才能更進一步分析並找尋克服或至少因應的方法。
無論如何,上述不同層次的政治異化,意味著不同的時差必須克服。例如,剛剛簡單提到的那一種害怕談政治的現象,就是民主制度與政治文化有時差的結果。其實,台灣政治一直存在一種嚴重的過度狂熱跟過度冷漠的問題,而且那可以是呈現在同一個人身上,也就是可以對特定的議題超冷漠的,對另外一個議題又超狂熱。白色恐怖時代將大家養成了避談政治的傾向。即使到現在,好多的宗教團體和社運的團體還是如此。他們大部分都是單一議題的倡議團體。口頭禪是什麼呢?「我們不碰政治!」更令人詫異的是,即使在現今也會有政治系的老師告訴學生:別碰政治!我們是政治科學家,要客觀、中立,所以不能過度關心或直接參與。
書評:你不是政治大學政治系嗎?
葉浩:對呀!政大常常被笑說是黨校,因為創校人是蔣介石,而且過去跟黨國的關係相當密切。事實上,政治大學本身是效仿倫敦政經學院創立的,而且政治系早期許多老師都曾就讀於倫敦政經學院,而且深受創辦該校的費邊社(Fabian Society)及他們提倡的社會福利和漸進式社會改革思想有很深的關係,也因此曾經有一種公共知識份子的精神。不過,白色恐佈時期基本上摧毀了這種精神。另一方面,當時國民黨也採取了鎖國政策,只留下了目的在於為黨國舉才的中山獎學金作為出國深造的出口,而報考資格之一是五年的國民黨黨齡。那不僅意味著能出國的人是層層篩選過的忠黨愛國者,更意味著他們認識政治的方式是透過黨國的視角。批評黨國或意識形態不正確者當然不能出國。認同黨國教育所教導,相信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而不是民主社會所說的「關乎眾人之事」的人,才能出國。不意外,參與黨外政治或社運的人,拿不到獎學金。加上三十五歲以下的年齡限制,許多人從高中就入黨並開始監視其他關心眾人之事的學生。可以想像從1960到2000年可以培養出多少不關心公共事務或只能從黨國立場來思考政治的學者吧?至少兩代人吧!敝校當然也是黨國的中流砥柱。不過,必須強調的是,我在這裡談的不是道德問題,而是學術界如何篩選人才,如何培養精英,加上當時送出去的人主要是去了美國,受到了什麼學派的影響。為黨國舉才本身並非錯事情,但當時的標準本身相當保守,相當政治正確,等同排除了改革政治的力量。主要留學國在當時又剛好流行一種強調客觀、中立的社會科學精神,源自芝加哥的行為主義及新自由主義是當時的學術霸權,主張政治就是拼經濟,社會及政治的研究就是進行計量研究並且恪守不做價值判斷的科學精神。盛行於美國的學派剛好在許多方面符合黨國舉才的需求。容我對事不對人地說,透過這種方式移植入台灣的政治科學本身恐怕是台灣民主的一股保守力量,甚至在某方面是一種阻力。
以前學校教的都是孫中山所說,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是政府及專家的事情。這句話還寫入了政大的校歌。可想而知,這種政治觀對社會影響重大。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包括我在內。當然,這不是說人不會變,過去支持黨國者就不會有價值觀轉變甚至徹底翻轉的一天。重點在於國家的制度可以一天就崩壞或說變就變,但人的思維習慣不可能一夕之間就改。今日的台灣民主政治,確實還存在很濃厚的過去黨國教育影響。有的人狂熱,願意當烈士的那種狂熱;有的人又很冷漠,甚至以客觀中立來包裝冷漠。好多人是對於一件事情特別狂熱,對於其他政治議題則很冷漠。這些政治異化到最後容易掉入相對主義跟虛無主義。藍綠一樣爛,政治人物都爛,再進一步就是我對什麼政治都不關心的,覺得國家大事干我啥事。
書評:我們再來談談美國。當下美國,就是大選在即,特朗普再次出來競選,左右割裂很大。很多人認為民主的危機,你怎麼用政治时差这个来解释当下美国美國政治的狀況和特朗普的出現?
葉浩:「政治時差」概念的確是可以用來分析美國政治,而第一件事情我想說的是美國政治曾發展出一個特別的方式來因應憲法做為國家根本大法所造成的政治時差,那就是修憲制度。美國憲法是1787年起草,1788年頒布的。不意外,現在的人跟兩百多年前的制定者,在想法上一定會有差距。這基本上是一種時間軸拉長很多的代溝。美國長久以來都是採取釋憲及修憲方式來克服這一種政治時差。一部憲法若常修改,那既難以稱得上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更會損其身為最高法律的尊嚴。透過釋憲來讓它跟上時代,是一種不損及尊嚴又能與時俱進的方法。倘若做不到,才採取最小幅度的修憲。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現在的人喜歡把「憲政」與「民主」聯想在一起,但事實上兩者可能有衝突的時候。畢竟,憲法是前人所制訂,反映了制定者當時的想法和集體意志,而民主作為一種此時活著的人民之意志展現。讓前人的憲法與此時的人民意志保持在一種平衡關係,堪稱是美國的憲政民主最成功的特徵之一。即使政治爭議升級到了大法官釋憲的階段,當釋憲案達成決議時,爭議雙方也就必須接受,不得再議。這正是這國家的民主政治成熟之處。
不過,我們也知道近幾年來,爭議似乎不必然止於釋憲決議了。從政治時差的角度來說,那表面上意味著前人與此時人民的思想代溝加深了,單靠釋憲難以自圓其說,似乎來到了或許該修憲的時刻,但深究下去則可發現爭議其實在於此時的不同黨派對於前人的立法意圖有不同理解。換句話說,這一種政治時差不是死人與活人之間的代溝,而是不同的活人各自宣稱自己才真正懂前人的想法,才能代表立法意圖的爭議。
我沒辦法斷定這一種政治時差會如何發展下去,但可以確定的是時間與政治的關聯性愈來愈密切。憲法政治蘊含的代溝之外,崛起於1960年代的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可說是始作俑者。不斷在美國各個社會科學領域攻城掠地的這個學派,到了1980年代已經把所有的人類生活領域都改造成一種拼經濟的活動,尤其是政治。伴隨而來的則是曾經讓美國民主能良好運作的那一種「慢」,徹底消失了。
19世紀中葉,法國政治理論家托克維爾發現美國的民主之所以能好好運作的原因之一是,美國人懂得投資,也就是不急著享受,願意把錢先放在其他地方,期待未來能獲取更大利益。這種「慢」就是當時的資本主義核心精神。不急躁並願意延後享受的思維方式及習慣,產生了一種外溢效用,那就是對政治的要求也不講求急功近利。於是政治人物可以去談論國家的未來方向,擬定比較遠大的計畫。我認為這是他的《民主在美國》的一大洞見。如果資本主義本是一種投資精神,延緩獲利、延緩享受的行為模式,那資本主義的盛行也會讓人們願意對政治人物有信任,讓政治成為一種對未來的投資。銅板的另一面是,當這種投資精神轉為自私跟投機,問題就會開始浮現。芝加哥學派經濟學成為取得霸權地位的80年代,就是這樣的年代。雷根主義當道的美國崇尚個人利益的追求,政府更是採取一連串的政策來配合。高效率意謂著快,意味著快速獲利,愈快愈好。托克維爾所指出的那一種“慢”徹底改變,消失。消失之後,一切求快,一切求效率。於是對政治人物也不再相信他可以規劃未來,沒有任何一個人能談什麼五年後十年後的政策。一方面,他不一定會連任。另一方面,選民也不願意等待。這讓美國也陷入了一個政治上非常急躁的過程。
這種快速政治在冷戰之後的全球化時代,也更加劇烈了。此時許多政治人物才一當選,就得思考連任的事,炒短線於是成了一種必要。因為選舉是四年一次,想連任者必須在第三年就能拿出政績,取得黨提名,那意味著政績是兩年即可看得到且最好有數據當證據的政策。不意外,蓋大樓,招商引資,GDP成長,降稅甚至退稅,成了主要政績。不管是政治人物還是選民,都一樣,期待與成效都不斷再加快。
另一方面,新自由主義帶來全球化,全球化又帶來了貧富差距的拉大。這裡的工廠關了,到中國去投資,留下一堆失業的人。然後失業的人怪政府無能,怪政府招商不力,刺激經濟成長無能。若採取增稅,大資本家就以腳代替選票。採取減稅,政府補貼就難以維繫,醫療資源更加短缺。全球化底下有贏家,也有輸家,政府該怎麼辦?輸家要怎麼辦?另一種快速政治於是應運而生。那就是選民期待一個強人出現,而投機的政客投其所好。這種政客取悅於選民的方法,就是宣稱他一上台即可解決多年沈痾,可以趕走搶了工作的移民,可以築起圍牆不讓難民進入。而方式就是放鬆各種監督機制,規避冗長的民主程序,甚至是程序。
民主制度原本就內建了各種讓決策可以緩慢的機制。權力制衡,切割成上議院和下議院或眾議院和參議院的國會,政黨輪流發言,辯論及會後的協商。這一切都是為了讓權力不會集中在一個人,或是一個機構手上,也就是為了讓決策不至於躁進。當局勢發展到貧富差距急速拉大,正常民主運作看似不能滿足選民時,不僅他們會願意鋌而走險,期待一位跳過程序的人,而政客也就可以說各種大話,於是有了特朗普。他的方法都是最快的措施。他的崛起本身就是一種時間維度上從慢轉到快的政治現象。
在這一個情境當中,崛起的中國加劇了這種求快的美國政治。始作俑者的新自由主義在冷戰期間曾提供美國一套捍衛自己國家的正當性的論述。它宣稱民主制度能帶來經濟發展,當國與國經貿緊密結合的時候,就不會發生戰爭,而且只要讓中國一部分的人能富起來,這些富人就會開始爭取他們的權利及財產保障,那麼民主將指日可待。這套論述讓美國先是將台灣納入了它的全球經濟佈局,然後又背叛台灣,選擇與中國建交,並以武力去促成許多國家的民主化。冷戰結束之際,這一套論述似乎取得了最後的勝利,甚至讓人類走到了歷史的終結。未料,崛起的中國意味著民主制度及自由市場並取得高速經濟成長的唯一之道。面對中國模式,新自由主義論述一時之間不但使不上力,核心論述甚至是理論預設更是直接遭遇挑戰。威權體制國家甚至是獨裁國家的經濟發展,比美國還好!蘇聯突然垮台、冷戰戛然而止的時候,跌破眼鏡的外交政策專家可以假裝沒事,繼續滾動他們手上的水晶球。那是一個沒有互聯網的年代。但中國崛起卻是在一個全球資訊高度流通的年代。高舉市場自由及民主制度才能拼經濟的新自由主義,難以招架。另一方面,內建於民主制度的放緩機制,不再受人稱讚,選民甚至會把按照程序走的政府視為一種無能。這又是一個讓人期待偉大領導人如救世主般降臨的理由。特朗普於是對號入座,他一方面把政治問題推給反對黨,把經濟問題全推給全球化,推給中國傾銷及墨西哥非法移民,另一方面則把自己包裝成殺伐果斷,能讓美國再次偉大的人。
書評:那就是說这是一个民主危机?
葉浩:是!那是因为选民还有政治人物都没有办法再承受快速的压力,但很多学者也该负责。學者應該回過頭去,告訴大家民主制度珍貴的地方是在人權,是在理念,是在內在價值而不是經濟層面。民主也不是發展經濟的唯一的道路或利器。有趣的是,當年主張歷史已終結的福山在被反咬一口之後回到歷史的現場來了!此時的他承認美式自由民主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難,國內有來自左右兩派極端份子的攻擊,國際上則有來中國及土耳其等反民主政權的挑戰。對此困局,福山一反過往對民主的經濟面向之強調,重申了自由主義的核心內在價值諸如平等與人權。這與收錄於我書中的基調大抵相符。不過,新自由主義在美國學界仍享有霸權,無論是經濟系或政治系都未見改變的契機。更重要的是,新冠肺炎也突顯了西方民主政治理論的另一個預設其實需要檢討,那就是將政府視為人民的主要潛在敵人。事實上,全球化年代底下的敵人,亦可來自於外,威權乃至極權政府也能利用民主社會的開放性來散播假消息,甚至製造內部矛盾。這不是民主制度本身的缺失,而是這始於十七世紀英國的思想傳統此時必須與時俱進,做出必要的理論更新。換句話說,美國民主的問題不同於台灣那樣需要補課,重新認識民主的內涵及制度性限制,以及創造符合體制的政治文化,而是學界必須重新審視全球化對主權國家及不同社會族群的影響,及奠基於這種國家想像的民主理論,才能度過此時的民主危機。幸而,美國學界與政界的關係密切,智庫的影響力也頗大。學界的反省或許能更快反饋到政策當中。這本身也是政治與時間具有關連性的一個例子。開放且自由的學界與政界之間的時差相對較短,是美國社會的一種優勢。若善用這種優勢,或許更能因應此時的民主危機。
Steve Tsang , Olivia Cheung |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Xi Jinping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Xi Jinping
葉浩訪談 | 台灣美國何去何從(上):台灣的最大的問題是史觀
編者按:台灣從哪裡來又往哪裡去?1987台灣民主化之後,台灣開始了自己的敘事和思考。然而,誰才是台灣人?三百多年來,一批一批移民進入台灣,他們各自有著自己歷史記憶與未來的想象。如何看台灣文化與政治的“亂象”?7月,聯經出版台灣國立政治大學政治係教授葉浩新書《政治時差.時差政治:敘事共時性作為民主政治的一種想像》,用一個全新的概念“政治時差、時差政治”來分析台灣歷史與政治的特殊性。他認為移民和移植造成了臺灣特有的「雙螺旋時差結構」,既成就了文化思想的多元,也分裂了政治認同及諸多議題上的共識。這也是台灣需要面對和解決的問題。訪談中,他還用“政治時差”分析了特朗普出現的原因,和美國民主面臨的危機。8月初,葉浩教授通過電話接受了波士頓書評採訪。訪談分為上下兩個部分,此為上《台灣的最大的問題是史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