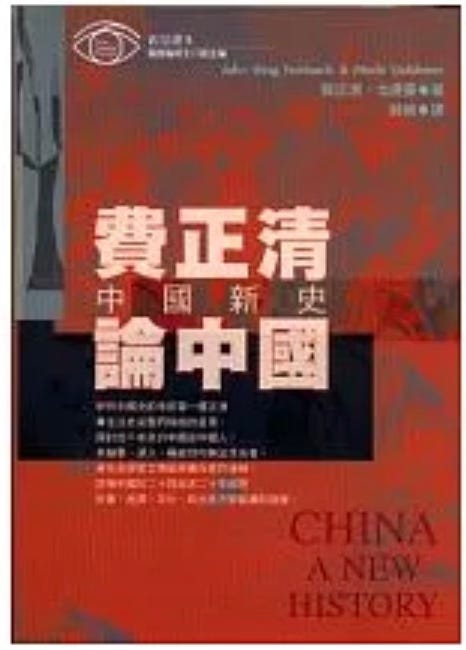羅小虎 | 84岁的费正清为什么重写中国历史
编者按:不知为何,人们总是忽略费正清先生最后一部也是最重要的著作,我想,这种忽略,是对费正清先生最大的不敬。本文为波士顿书评专栏文章,禁止转载。
1
1946年10月27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费正清为白修德(Thodore White)和贾安娜(Annalee Jaceby)的新书《中国的惊雷Thunder out of China》所写的一篇书评《来自中国心脏的挑战A CHANLLENGE FROM CHINA’S HEART》。这篇书评几乎是费正清最早的公开发表的有关中国的文字。白修德是费正清在哈佛大学的学生,本想研究历史,但费正清认为,白修德身上有着斯诺一样的记者素质,建议他做记者。1939年,拿着费正清的介绍信,白修德来到重庆,成为《时代》周刊的特派记者,在这里工作将近八年,可以说是中国抗战的重要的见证者与记录者。
白修德与那个时代大多数驻华美国记者一样,对当政的国民党及其腐败持有强烈的批判。1942年到1943年,河南饥荒,灾民多大几百万,国民党政府毫无救灾计划。白修德深入灾区,对大饥荒进行报道,在美国引起轰动,也使得国民党政府受到巨大的压力。这就是根据刘震云小说改编的电影《一九四二》中的故事原型。白修德的报道虽然在美国引起轰动,但也引发了他与《时代》编辑以及老板亨利 鲁斯之间的矛盾。当时美国与中国是同盟国,美国政府全面支持国民党政府,不愿意看到过多的有关国民党政府的负面新闻。为此,1945年,白修德在发回封面报道的时候还附了一封电报:“如果《时代》有限公司执行的是绝对的、无条件支持蒋的政策,我们就极端地损害了美国千百万读者的利益,并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罪行,他们个人主要关心的问题也是如此......我们希望看您能以公正的态度,毫不偏颇地搜集事实。......我们认为我们杂志应当是超党派的,应朝民主与和平解决方案这一中间道路,如果事情不是这么解决的,我们就考虑将此信作为我们脱离杂志的声明,并请解除我们现行的任务,使我们能够回来至少在主编面前最后解决我们的身份以及我们对于中国的政策问题。”这封电报颇能代表一年后出版的书《中国的惊雷》的观点:对国民党腐败政权的彻底失望。此外,在《中国的惊雷》中,白修德对当时外人知之甚少的共产党抱有审慎的期待。当时,白修德预言,中国必定会发生内战,而且国民党会溃败。
作为白修德的老师,以及当时也驻中国的美国战略情报局官员与新闻署驻华分署主任,费正清当时的观点可以说与白修德的一致,甚至当时一批驻华的美国记者都持有相同的观点:他们富有同情心,对于国民党治下的中国表示失望,并对当时美国政府全力支持国民党政府表示怀疑,同时,他们对于共产党抱有审慎的期待。这批人在美国新闻史被称之为“China Hands”。
这也正是费正清这篇书评的观点。在书评中,他描述了国民党治下的中国,并对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政策表示了怀疑。同时,他也写了对当时共产党的看法:“同样令人惊骇的是那些把历史用作工具、把农民当作原料一般与之共事的共产党人的情景;他们深入到每个村庄的黑暗之处,并从中将其召唤出来。Equally striking is the picture of the Communists, who worked with history as if it were a tool and with peasants as if they were raw material; they reached down into the darkness of each village and summoned from it. ”费正清在这篇书评中,甚至对支持国民党政府的美国政府发出警告,这从这篇书评副标题可以看出《如果不能从我们的民主中得到真正援助,她有可能拥抱共产主义Lacking real ad from our democracy, she may embrace the communist creed》。
这篇书评发表时,费正清已经结束了他在中国的任职,回到哈佛大学教书,同时也正在写他最负盛名的一本书《美国与中国》。1948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这时的费正清41岁,曾在北京当了四年的研究生(1932-1935),1935年离开中国。1936年以论文《中国海关的起源1850-58 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Martime Customs Service,1850-58》在英国牛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回母校哈佛大学任教。1941年被征召至美国情报协调局工作,1942年9月至1943年12月被派往中国,担任美国战略情报局官员;1945年10月至1946年7月再次派往中国,担任美国新闻署驻华分署主任。1946年回国后,回到哈佛大学继续任教。《美国与中国》正是这个时期写成的。
虽然如今看这本书,多是对中国历史通俗性的介绍,但对于当时的美国读者来说,是不可多得的读物。在民国部分,费正清对国民党腐败政权表示失望,并对共产党表示了期待,与1946年发表的书评观点一致。随着时间的延续,这本书也不断修订,1958年,《美国与中国》出版第二版,增加了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和新中国头十年的历史。1971年出版第三版,增加了对接下来十几年新中国的历史,其中他写到:“凡是在 1949 年前到中国各省游历过的人,只要深入到今天的农村,就会在各方面看到大革命的成就——一个面貌一新的民族,一片经过改造的国土。事实仍然说明,它们是值得全中国人民在精神上而不是在细节上学习的活榜样。国家复兴的证据是全国遍地可见的,并且是目不胜收的。一百多万辅助医务人员‘赤脚医生’有采用中国的新医疗法如针刺麻醉和电吸人工流产等,把公共卫生和医药服务带到农村。”
1983年,这本书出版第四版,内容也随之增加到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这便是目前最为普遍的版本的。在1983年版的序言中,费正清说这个版本主要受两件事的影响,一是“在人民共和国实际观察所得”。1972年5月至7月,受周恩来的邀請,费正清与妻子对中国访问了六个星期;1979年又访问了两次。“我们发现这已是崭新的国家和崭新的人民了。”二是“得益于许多国家的学者和记者近年来所发表的几百部重要的专著、论文及文章和报告。”
在这本书中,费正清在解释中国革命过程时,对毛泽东首先做了一番总结性的评价:“毛泽东生平的一些简单事实似乎是难以置信的:在一个4 亿人口的广大国土里,一个28岁的人和其他十几个人成立了一个政党并在其后50 年取得了政权,组织和改造了人民,改变了山河——历史上没有见过比这更伟大的成就。亚历山大、恺撒、查理大帝、欧洲所有的国王、拿破仑、稗斯麦、列宁——没有一个前人的成就比得上毛泽东,因为无论哪个国家都没有像中国这样古老这样大。”
接下来,费正清对中国革命历史和新的人民共和国头几十的历史做了简略的叙述,虽然也触及到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严重的政治灾害,但基本都是简略带过,在叙述到毛泽东去世时,他对毛泽东又做了一个简略的盖棺之论:“毛泽东则像汉朝和明朝的创业皇帝那样,是以崛起于民间的英雄人物身分统一国家的。他胜过前辈,并且能够在长江里游泳,以激励他的人民去利用和征服自然。毛在40 年代的军队并不给农民带来苦难,而是为他们翻身求解放的。他‘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爱戴’, 所以能够从各个地区根据地得到粮食和兵员。他吸引了大学生去掌握他的行政机构。他的思想意识以承担历史使命为己任,虽然没有公开说是受命于天。一旦掌了权,他的政府就把土地和人口一起加以考察、分类和重新进行分配。他靠暴力起来执掌政权,但他仍然保护中国文化,雇用学者整理前一政权的档案,并指出其衰亡的教训。他用古典体裁的诗词来庆贺革命胜利,他的书法点缀了许多公共场所。他的榜样对周围国家有很大影响。在北京,他在巧世纪明代帝王修筑的大宫殿前修起了一个大广场,让东南亚和西方地区的代表团到那里去观看盛大的游行仪式。如今毛的遗体仍用防腐设施保存在该广场的中央。”
费正清对中国革命的乐观与理想性期待,更为明显地表现在他的著作《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这本书出版于1986年,涵盖的历史从1800年到1985年,即从清末、民国再到人民共和国的 历史,用费正清的话说这是一部“关于中国长期灾难、斗争和再生的个人记述”。在费正清看来,“1949 年没有一个人能否认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公公正正地征服了中国。”他举了一个例子:“最近的调查研究工作,弄清了中共是怎样赢得东北的。他们先把农村动员好,一如他们在华北所做的那样。他们带着精力充沛的华北干部渗人到东北后,组织生产、搞乡村宣传教育、土地改革、新干部的思想改造等一系列运动,然后征集新兵,团结他们进行爱国战争。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成就,干部们在强制征兵的同时运用了他们的社会工作技能。东北人民在日本占领下长久以来抑郁难伸,现在对于民族主义和社会革命的号召,无不热烈响应,拥护中共的战争努力。”此后,“1949 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接管中国和新的全国性政权的建立,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性成就。”因此,虽然他在叙述新中国历史的时候,没有避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但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给予很大的肯定的。
类似的评价还散见费正清的其他学术著作、学术文章或是回忆录中,而这些著作,如《美国与中国》《伟大的中国革命》《中国的思想与制度》《中国:传统与变迁》《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等,几乎费正清所有的书都被翻译介绍到了中国大陆,除开一本书外,这就是费正清生前最后一部著作:《中国新史》。
2
1991年9月12日上午,84岁高龄的中国历史研究专家费正清,将自己写了两年的最后一部书的书稿《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China:A New History)亲自送到哈佛大学出版社。下午,费正清心脏病复发,两天后,离开人世。1992年,这本书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1994年,台湾正中书局推出中文版。在这本中文版中,历史学家余英时写了一个简短的序,指出只有配合着读费正清以前的书《美国与中国》《伟大的中国革命》,“才能了解他的’晚年定论’之所在”。而书名中的“new”,余英时认为,“‘六四’屠杀对于美国的中国研究者原是一当头棒喝。不少以前相当同情中共政权的人都在一夜之间转变为暴政的谴责者和人权的维护者,费正清也不例外。他的书名叫做’新史’,这个’新’字恐怕在潜意识中含有’觉今是而昨非’的意思,特别是有关中共政权的论断。”
只要翻开这本书,就会发现,一向对中国未来表示乐观的费正清变得非常悲观,曾经他说,“共产主义虽然在美国是坏事,但它在中国看来却是好事”,但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他认为“中国既有其独一无二的历史,就得有自己独一无二的未来。这个结论尽管令许多人感到不安,却与另一项世界性的共识相重叠,那即是:人类自己正濒于灭绝(这是人类自己再三指明的)。二十世纪已经眼见比以往时代总和还多的人为的苦难、死亡,以及对环境的侵害。也许中国人终于走向外面的世界,正赶上参与世界毁灭。但有少数比较不悲观的观察者认为,到头来,只有中国人三千年来所表现的生存耐力能够救大家。”
在这本书第四卷中,也即1949年之后的中国历史叙述中,费正清不再把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认为是“农民解放和五四以来所揭示的民主和科学种种理想”的不可被压制的革命运动,而是专制王朝的现代翻版。在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他用了一小节专门评价毛泽东,其中他写到:“外人必须发挥一番想象才能够理解毛泽东本人。首先要认清他至尊地位的本质。毛有两个生涯,一个是造反头子,另一个是现代版的皇帝。他已经得到了后者的权势,显然却仍保留着前者的形象不改。由于权威在中国是由上而下的——即便走群众路线也是如此,共党一旦当权,其领导人就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不但是一般人民膜拜的对象,而且在党组织之内也是高高在其他人之上的。中国共产党内部靠毛泽东促成的部分太多,简直可以说党就是他创造的。如果他要改革党,那也是他的特权。我们非得把他看成一朝的皇帝,才有可能想象,素来被训练得忠心不二的共产党领导班子为什么顺着毛的意,让毛把他们一个挨一个地全部消灭。”
费正清在这本书中,不仅对中共及其领导人做出了截然相反的评论,而且还在书中进行了反思,自己过去为什么会回避中共犯下的错误。这一点,余英时先生在序言中特别指出:“最有趣的是他公开表白过去为中国讳饰的心理。他说,西方汉学界有一种职业病,大概出于‘第二爱国’或‘爱中国’的心理,即不肯暴露他们所研究对象的坏处。他特别在附注中加上一条‘夫子自道’:我在1972年十月号《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 》的一篇文章中竟说:‘毛泽东的革命’对于中国人民而言,是数百年来仅此一件的‘最好的事’(页176)。这样的公开的自责,确表现了学人的良知。”
1986年5月9日,白修德去世。美国著名作家、保守主义政治评论家、《国家评论》的创办人小威廉·法兰克·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为白修德写了一篇讣告,赞扬白修德“将杰出的头脑、艺术家的才干和巨大的好奇心结合在一起,是一种完美的健康、对人类真诚的关爱。”并“彻底革新了政治报道的艺术”。不过,他同时也批评白修德犯了一个错误:“他对革命者理想的估价过高,而低估了他们极权主义虐待狂的能力。”巴克利对白修德的这个批评,不仅适合于白修德,也适合于费正清,以及以他们为代表的China hands知识分子圈。
为什么他们会对共产主义抱有好感呢?德裔美国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在1964年出版的《城邦与人》的序言中做过精彩的分析:“曾几何时,共产主义在许多有教养的西方人眼里(姑且不论没有教养的西方人)还只是一个与西方运动并行不悖的运动,就好像这个有一点点不安分、野蛮和任性的孪生子终究会变得成熟、耐心与温和。……不得不承认,西方的筹划以自己的方式做好了防范先前种种邪恶的准备,但无论在言辞还是行动上,它都防不了这种新型的邪恶。曾几何时,我们似乎有充分理由认为,尽管西方运动与共产主义目标一致,即自由与平等的男男女女所组成的普世繁荣社会,但它们在手段上无法达成一致:对共产主义而言,目标是全人类的普遍善好,也是最神圣的事物,它能证明任何手段的正当性;一样事物只要有助于实现最神圣的目标,就能分有目标的神圣性,从而自身变得神圣;一样事物只要阻碍该目标的实现,就是邪恶的。一个共产主义者认为暗杀Lumumba是一场应受谴责的暗杀,隐含的意思就是也可能存在不应受谴责的暗杀,例如暗杀Nagy。因此,我们就能看到,西方运动与共产主义之间的不同不仅在于程度,也在于类别。还可以看到,这种不同关乎道德,关乎手段的选择。换言之,任何流血或不流血的社会变革都不可能根除人心的恶,这一事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分明:只要有人,就有恶意、妒忌和仇恨存在,所以不可能存在一个不需要强制性约束的社会。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再也无法否认下述事实:只要共产主义还在现实中而非仅仅名义上存在一天,共产主义就始终是僭主的残暴统治;随着僭主对宫廷革命的恐惧,这种残暴的统治要么缓和,要么加强。唯一能让西方重拾一点信心的约束,便是僭主对西方强大的军事力量的恐惧。”
3
陈寅恪先生曾说:“凡着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
对于共产主义的认识,在那个时代并非所有人都能够像施特劳斯这样清醒,所以本文并非是对费正清先生的学术进行苛求,实际上恰恰相反,本文试图对费正清先生的学术成就做出一个更为准确的评价,以免对费正清的学术产生误解。不知为何,人们总是忽略费正清先生最后一部也是最重要的著作,我想,这种忽略,是对费正清先生最大的不敬。
最后,向费正清先生的学术良知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