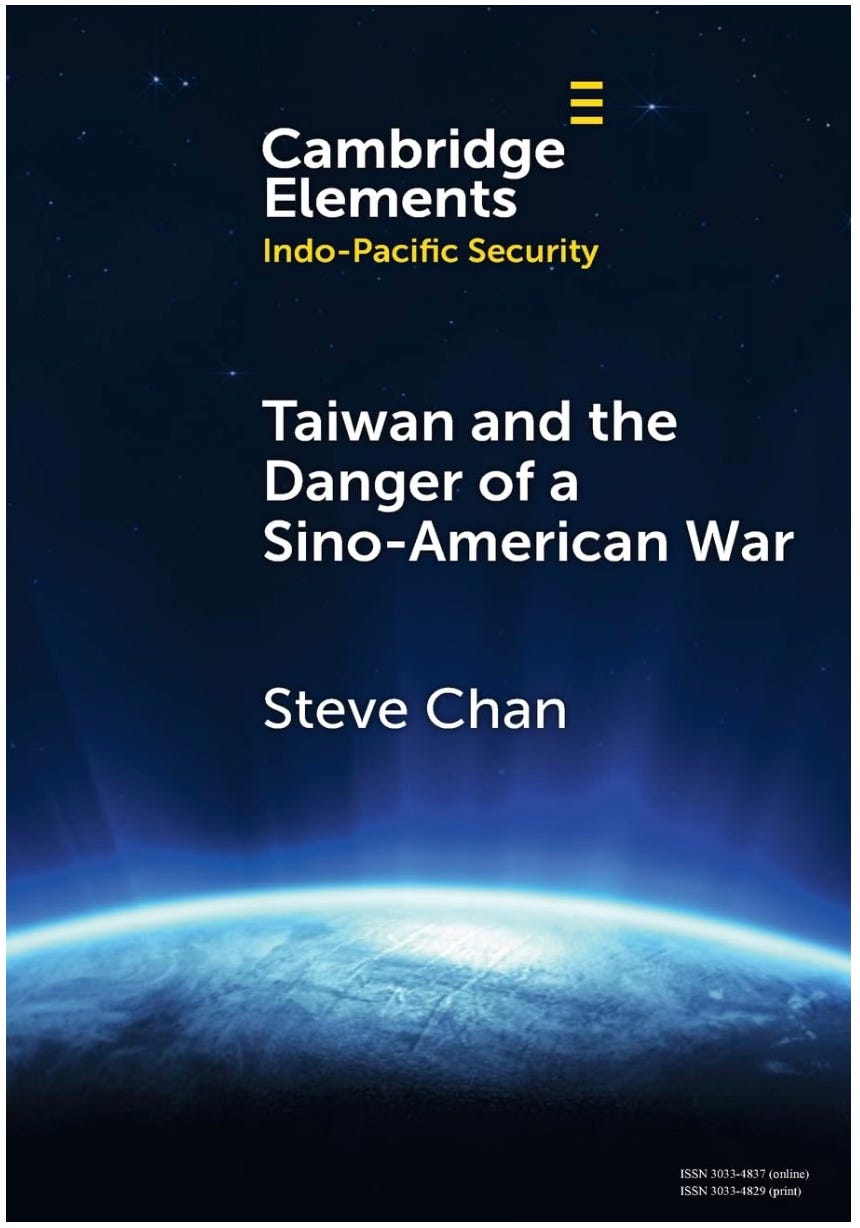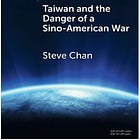书评短评 | 杜如许:台湾作为方法
评陈思德《台湾与中美战争的危险》
编者按:11月7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议会中公开将“台湾有事”视为日本“生存威胁”情势,暗示可能援美行使集体自卫权,引发中国强烈抗议并于11月22日向联合国发文警告若干预将视为侵略并坚决自卫,导致台海紧张进一步升级。如何寻找台湾的未来,如何在台湾和中美关系中寻找更多的可能性呢?陈思德(Steve Chan)教授的新作《Taiwan and the Danger of a Sino-American War》以冷静的现实主义笔触挑战了当下流行的“中美必有一战”叙事,认为台海战争风险远低于悲观论者所渲染。其核心洞见在于:台湾问题本质是地缘政治利益而非价值冲突,中国对统一的“绝对意志”与美国相对薄弱的干预意志,在当前及可预见的未来力量平衡下,将形成持久僵局,而非必然战争。旅美学者杜如许对此既赞赏又保留。赞赏之处在于,陈教授把国内政治合法性与对外战略计算并置,避免了单纯结构决定论;保留之处则有二:其一,他低估了台湾作为美国印太“隔离带”枢纽的战略分量;其二,对“战略模糊”的批判忽略了其作为半个世纪以来“建构秩序之方法”的规范功能——它不仅是威慑工具,更是中美台三方共存的临时框架。但杜如许认为更基本的问题是:在陈思德教授视野中,台湾的重要性来自它的地理坐标,与它的社会和历史内容,没有太大的关系。台湾问题不是中美关系的原因,而是中美关系的结果。对此,杜如许认为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台海和平,不应该只被理解为势力均衡问题;它同时也是建构秩序的问题。这个历史是提供“问题解决方法”的历史——或许台湾本身也可以作为问题的方法。
一、理论分析与政治决策
2021年,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中国海事研究所召集了各方面的专家,从军事科学的角度对中国进行两栖登陆作战的能力,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其总体的结论是,“这个危险的处境尚且留存的余地会让乐观主义者震惊,但也能让最顽固的悲观主义者感到振奋,使其有理由确信,防止(deterring)对台湾的进攻仍然是完全可能的。”(Chinese Amphibious Warfare, edited by Andrew S. Erickson, Conor M. Kennedy, Ryan D. Martinson, Naval War College Press, 2024.)
不过,军事专家们提醒说,与军事科学相比,政治决策更像艺术,没有那么“科学”。言下之意似乎是说,假如我们转向问题相关各方的政治领域,情形可能就没有那么乐观。尤其是近年来的公共舆论、高级别官员的公开言论,以及那些在大众传媒中广为流传的专家意见或理论学说,都在烘托一种中美必有一战的气氛。在这样的悲观气氛下,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陈思德(Steve Chan)教授,继续给了人们“相对乐观”(relative optimism)的理由。他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对台海的战争风险作了理性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中美之间因为台湾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并没有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大。尽管陈思德教授相信自己分析的合理性,他还是不忘补充一个与军事专家给出的类似的“保留条款”:“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防止人们陷入愚蠢、自私或短视。”
这类“保留条款”不只是谦虚之词——实际上,我们可以在陈思德教授的最后一句话中读出相反的意味。这里涉及理论分析与政治决策之间的一条固有鸿沟:理论家不是决策者。这一事实鸿沟是无论何种理论都无法克服的。“实践”也不能克服这个鸿沟——你不可能通过把一个理论家变成决策者就填平这条鸿沟。因为理论家的客观角色,本身就是通过他“并非决策者”这个社会身份建构起来的;一旦这两个身份接近并混淆起来,分析家就会沦为宣传家——他将为某种特定的决策服务;或者更加疯狂的是,他将用他的权力为某种理论立场服务。前者导致剪裁理论,后者导致剪裁现实。
另一方面,理论家与决策者的区别也意味着,任何一种关于决策的理论其实都是不可检验的。因为用来检验的实践——也就是历史——从来不可能终止。在这个意义上,包括国际关系理论在内的所有社会理论从本质上说都不可能在充分的意义上成为“可证伪”或“可证实”的。谈论它们的“对”与“错”,严格说来,并不恰当。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不能谈论它们是否合理。比如,陈思德教授承认,他的分析,就像他所尊敬的李光耀的判断一样,可能是“错的”(wrong);但我们仍然能够从他的分析自身的品质中得出我们的判断,认为它是相当合理的。
这些一般性的看法可能会造成一种误解,以为理论家与决策者之间任何类型的“接近”,都会损害学术研究的中立性。恰恰相反,理论分析与政治决策之间不可克服的鸿沟,反而要求某种特定的“接近”。陈思德教授的分析就是一个恰当的例证。他明确地把他的分析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基础之上:中美双方的政治决策者对彼此的关切、顾虑、利益和红线都有很好的理解(必需强调的是,这不是一个类似于经济学中“理性人假设”的理论命题,而是一个经验判断,因而需要相关的信息加以论证。陈思德教授认为有证据佐证他的判断,他只是没有在这本篇幅非常有限的小册子中集中加以论证)。但是,这个判断或假设必然同时意味着,理论分析者本人对双方的这些考虑都有很好的理解,否则他无法作出这个判断或假设。因为,当他自己对问题的处境没有一个深刻理解的时候,他就没有能力判断,冲突双方各自对对方的理解到底是幻想、误解还是恰当的认知。这等于说,决策者的视角和分析者的视角在这里是重合的,它们构建出共同的问题,并分享共同的思考方式,甚至分享共同的必要信息。也只有有了共同的问题、共同的对象,才会使理论家的分析有特定的意义。
理论家可能有不同于决策者的知识追求。或者他们都追求知识,但各自追求的知识类型仍然是不同的。这是自柏拉图以来就未曾有定论的问题(对此,回想一下他在《理想国》中所作的“线的比喻”就足够了)。即使如此,只要在某个特定的重叠时刻,他们想要思考同一个问题对象,就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谁对问题处境的理解更深刻?谁的视野具有优先性,因此另一方最好模仿他的思考?在这里,决策者固有的一个特点非常关键:决策者始终在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案。解决方案的有效性决定了他们对问题的定义,决定了他们理解的深度。在新的解决方法被穷尽的时候,也是他们对问题的理解达到极限的时候。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决策者对方法的寻求,意味着他始终处在一个有可能改变自己思考前提的位置上。他所握有的权力使他具有这个可能。理论家不具有类似的权力,因而就倾向于以既定的或较为稳定的选择可能性作为自己推理的前提,以此换取客观性或合理性。从智能的角度比较,决策者运作的是更高级的智能。
但让我们抛开这个“智能科学”的层面,回到解决方法与其问题处境之间的关系。举一个历史中的例子或许是有用的。美国联邦宪法上有著名的五分之三条款。这个条款让人误解为是在奴隶制问题上的某种妥协,从而把制宪会议的相关讨论理解为对奴隶制问题的处理。实际上,真正的问题是个狭义的政治问题:如何处理南方各州在众议院代表权上的弱势地位?这个政治问题原本可以通过一种递减方案解决的。可惜,这种递减方案虽然已经提出来了,却未能引起重视。采用了五分之三条款的宪法从此受到奴隶制这个道德问题的诅咒(参见Akhil Reed Amar, America’s Constitution: A Biography, Random House,2012)。与政治决策相关的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也许应该借鉴阿马教授所作的这项宪法史研究。宽泛地说,理论观察者对问题的理解是否深刻,取决于他是否像决策者一样在探索解决问题的更好方法。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曾经把这一类知识探索者称为“中介知识分子”:他们理解了哲人的知识,也把握到了政治家面对的现实困境,而他们的历史使命就是找到眼前问题的解决方法(参见Leo Strauss, On Tyranny, Corrected and Expanded Edition, Including the Strauss-Kojève Correspondence, edited by Victor Gourevitch,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十五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公民人文主义者在相当程度上可以作为这一类知识探索者的原型。正是他们剔除了人文主义知识中的中世纪成分,而锻造出了现代历史撰述的传统(参见Hans Baron, The Crisis of the Early Italian Renaissa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这个传统到马基雅维利的时代可以说实现了一次知识类型的转变,理论与策略之间的区别被相对化了:马基雅维利在他的作品中像他所研究的国务活动家一样思考,无论这位国务活动家是君主,还是共和国公民。作为对照,今天的社会科学研究似乎更多地被“学术”与“政治”的分裂所苦,却完全忘记了韦伯本人在有关学术与政治的两个演讲中,所暗示的那种精神契合。
二、中美地缘政治竞争
陈思德教授的分析是高度学术性的。所以,在这个评论中谈论一些抽象的方法论问题,应该不是不合时宜的。并且,它们同陈思德教授谈论其主题的方式,也不是不相关的。但是在再次回到这些基础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简略地重述一下他的分析,在其自身的逻辑范围内检讨它的融贯性。
陈思德教授的整个分析围绕着下面这个“主要命题”:
这个核心论述的主要命题是,台湾受争议的地位反映的是地缘政治利益上的冲突,因此,中美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不只是理念或价值冲突。尽管情绪——诸如对感受到的不满和持续的权力转移所产生的愤怒和焦虑等情绪——确实在近期两国紧张局势升级中扮演了一定角色,但我认为,争端背后的主因更关乎权力政治的冷酷计算。这些计算不仅涉及地缘战略层面的对外政策关切,而且还同政治家在国内的合法性与政治地位相关。
根据正文的分析,这个主要命题包含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台湾问题的决定性要素是地缘政治冲突。虽然理念与价值——或者说意识形态因素——有一定的分量,但绝不是主要的。证据似乎是不言自明的:美国的对台政策不是始于台湾民主化时期,而是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决定性的因素出自台湾岛所处的地理位置。越来越多的人把这一点视为真知灼见,并进一步引申出,中美之间,无论各自体制如何,哪怕中国采用与美国一样的体制,他们也必然是要敌对的。中国的历史教训当然还有另外一面:哪怕都采用社会主义体制,中苏两国的情况没有两样。在这种现实主义“启蒙”的氛围下,“修昔底德陷阱”这类夸大其词的黑话广为流行,也就不足为怪了。摆脱乌托邦的决定论之后,人们甘心情愿躺到另一种决定论的坑洞里去了。不过,陈思德教授不落窠臼。他甚至表示,难以理解“修昔底德陷阱”这样的理论。毫无疑问,这种所谓理论,只不是把可能导致战争决策的一种可能原因提升到了普遍的高度,况且这种考量因素还不那么理性。对于陈思德教授来说,地缘政治不是神秘主义或宿命论问题,而是一个理性计算的领域。
第二,这个计算所计算的不仅是对外政策,还包括国内政治合法性问题。如果说第一部分意在剥离并排除理念或价值因素的话,那么这个第二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又引入了这些因素。毕竟,是各种理念、价值,连同利益一起,塑造了行动者的意志。在这个方面,陈思德教授对三方都做了一些判断,有一些看起来一目了然,有一些则有推断的性质。比如,他指出,中国政府的任何一位领导人都不可能会放弃台湾。因为中国的文化、法律和民族主义的政治气候,都把统一台湾当作“根本利益”,也就是政治合法性的关键。另一方面,陈思德教授认为,从台湾内部的政治看,台湾的优先选项并不是独立,而是经济或者说民生。至于美国政府,陈思德教授的相关分析,就是要揭示,美国的政治意志比中国的意志要弱。在他对美国政府的战略模糊政策所作的反思当中,他似乎就认为,模糊政策的实质其实是美国没有意愿为台湾打一场代价高昂的战争。
综合起来看,第一部分,也就是理性计算的部分,主要涉及力量对比关系。在地缘政治利益内容既定的前提下,力量对比关系是计算的主要变量。中国军力的发展在不断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天平趋向于平衡。与之相对,第二部分,也就是行动意志方面,则是一种恒常的不平衡:中国方面不变的强意志——也许可以称之为“绝对意志”,和美国方面可能不断减弱的行对意志。
两个部分都促使陈思德教授得出结论,认为中美之间的战争风险,没有通常认为的那样大。我认为,说中美两国力量对比关系趋向于平衡更有利于维持和平,这个分析与我们的常识更加相符。这也是福柯在分析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时所指出的:平等状态将导致僵局,因为战争意味着共同灭亡。陈思德教授进而指出,由于双方的目的不会改变,因此僵局将会持续下去。至于僵局能持续多久,那是一个需要根据变化的条件加以估量的问题。也许这种均衡还有十年、二十年的时间。但即使这个和平时间过去了之后,中美之间依然只有较小的可能性发生战争。由于美国具有较弱的战争意志,假如力量对比真的不断朝有利于中国一方倾斜的话,美国意志只会更加微弱,以至于很难想象美国政府会诉诸战争。
概括起来说,陈思德教授认为,中美两国在台海问题上发生战争的风险比通常认为的要小——这既是指现在演变中的势力均衡有助于遏制每一方的战争冲动,也是指,在将来这种势力均衡继续向有利于中国一边倾斜的时候,美国不会愿意与中国开战。这个分析又反过来进一步支持以下观点,即中国在当前时期不会使用战争手段,因为理性的计算表明时间是站在中国这一边的,所以她更有理由保持和平。与此同时应该说明的是,陈教授的这个分析并不排除中国政府对台湾动用武力的可能性,它只是认为中美之间的战争风险,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在他的分析框架中,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如果必要的话,中国武力统一台湾只是时间问题。
在给定的前提下,上述推理不仅合理,而且可以说是相当巧妙的。但仍然有两个重要的疑问。首先,陈思德教授对美国的战争意志所作的分析,同他认为台湾所具有的地缘政治价值不相匹配。意志问题不能单独在理性计算的框架之外讨论。理性计算自身就已经是意志的一种反映。台湾的地缘政治价值越大,计算的结果就越大,行动的意志就越强。那么,在陈思德教授看来,台湾的地缘政治意义究竟有多大呢?非常大。用陈思德教授的话讲,台湾“是美国在东亚的遏制政策的枢纽”,“假如台湾‘陷落’,那它将会动摇美国在东亚建立的整条隔离带”。按照这样的理解,台湾的地缘重要性应该用整条政治隔离带的重要性来衡量,从而美国政治计算的尺度就应该从台湾海峡往这个隔离带的两端延申。人们无疑会立即想到,美国眼中的台湾问题很可能是南海问题的一个部分。台湾的这种枢纽地位假如是在清晰的理性计算得到的结果,为什么不能使美国产生稳定甚至恒定的理性意志呢?它与非理性的情感相比,难道一定是更加软弱的吗?
其次,陈思德教授对战略模糊政策的批评也是可疑的。他认为战略模糊政策无法有效的发挥遏制作用,因此,战略模糊政策其实很可能意味着美国不愿因为台湾而诉诸战争。他的理由是,真实的威慑才能产生威慑的效果,而战略模糊政策——既然是“模糊”的——就没有表示出真实的威慑。类似的问题在美国的核威慑政策上也被提出来过:核威慑若要有效,就必须让对方确信发出威慑的一方人真的会使用核武器。这在这两年以戏剧性的方式得到了证明。但是,这其中的道理是有条件的。干预的不确定性在特定的条件下,比如在拥有优势力量,或者具备对等的实力的时候,足以发挥威慑的效果。如果我们接受陈思德教授的判断,认为竞争双方彼此都很好地理解了台湾对于各自的重要性,也都冷静地计算各自的得失,那我们就更有理由认为,在此基础上的战略模糊,已经足以达成政策目标了。
更重要的是,战略模糊政策有自身的规范性前提:它跟美国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模糊承认策略有关。虽然不是说模糊的承认政策就意味着战略模糊政策,但战略模糊政策与模糊的承认政策是匹配的,相反的政策则会打破默契,突破法律框架。从这个角度说,战略模糊不只服务于威慑,更服务于一个备受争议但却维持了半个世纪之久的临时秩序。
三、台湾作为方法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更基础的问题。在陈思德教授冷静的视野中,台湾主要是一座占据了一个地理位置的岛屿。它的重要性来自这个位置,与它的社会和历史内容,没有太大的关系。书名《台湾与中美战争的危险》中的这个“与”字,实际上是用来表示台湾在整个问题中的附属性质的:它的作用不是把读者的眼光引向台湾,而是越过台湾,引向中美。台湾问题不是中美关系的原因,而是中美关系的结果。
这个视角当然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当台湾真的只剩下这一地缘重要性的时候,二战后中美关系的历史或许就不能得到完整的理解。我们在上文的第二个批评已经触及这个问题。无论从国内还是从国际的角度看,政治都是一门创造秩序的艺术,竞争、冲突或者战争,都只是这门艺术的局部技术(当然,在今天,核大国之间的全面战争是毁灭而非创造)。而创造秩序的艺术凭借的是结构化的能力或建筑术——从康德的思想建筑术,到立法者的权力建筑术,不一而足。它们都是“解决问题的方法”的用武之地。人们意识到,美国外交上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模糊的承认政策(使用“acknowledge”而不是“recognize”)发挥的正是这种方法论作用。模糊用语的语义空间,在势力相对均衡的前提下,支撑起了一个相互交往的政治空间。这个空间被称为“框架”。(比如Kerry Brown, Why Taiwan Matters: A Short History of A Small Island that Will Direct Our Future, New York: St. Martin’s Publishing Group, 2025.)与此相对应,战略模糊政策反映的正是这个互动框架,同时也维持着这个框架。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台海和平,不应该只被理解为势力均衡问题;它同时也是建构秩序的问题。这个历史是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的历史。欧洲史提供了一个经典案例。欧洲均势本是一定历史阶段中出现的事实和策略的对象。它帮助塑造了近代欧洲国际法,但它无法将“均势原则”本身提出来作为欧洲大家庭的秩序原则。相关的尝试没有成功(参见Edward Gulick, Europe’s Classical Balance of Power: A Case History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One of the Great Concepts of European Statecraft, W. W. Norton & Company, 1967.),它还是只能利用共同的规范性资源来支持这个“国际法大家庭”。直到两次世界大战,欧洲人才通过另一种不同的法律秩序,来取代“均势”这一长期的“权宜之计”。
一旦转向建构秩序、提供方法的层面,就不得不进入相关各方内容丰富的“内部”,把握各种具体态势。在这个方面,陈思德教授的分析本来具有显著的优点。他明确把国内政治的合法性因素当作他的思考的双轨道之一。但他的目的是说明中美各自对台湾的态度,而不是在方法的层面考虑问题。如果我们在方法的层面考虑问题,我们就会意识到两个问题:第一,中国的诉求是统一,台湾的诉求是有他们自由的民主生活方式得到安全保证(当蔡英文就香港问题发表意见,表示对一国两制政策的不接受的时候,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独立”诉求是在他们无法找到恰当的法律方案的时候提出的一个超出法律秩序的“方法”;它本身是非法的,就像北美殖民地的独立运动,也是超出英国宪法秩序的行动,从而构成“革命”一样)。美国的诉求——让我们简单地假设——就是地缘政治安全。现状,也就是由美国的模糊战略建立的关系模式虽然运行了半个多世纪,但它跟欧洲均势一样,仍然无法把自己提升为明确的规范秩序。因为在这个现状之下,三方各自的诉求无法同时满足,而每一方都当然把自己的诉求视为规范上是正当的。
作为方法的“维持现状”也许从美国及其盟友的关系来看是成功的。但它的问题也来自这种成功。五十多年的历史不长,但也不短。它至少长得足以把“三方各自的诉求无法同时满足”当作本体论一样的东西沉淀下来,以至于人们忘记了,只是从七十年代中美接触开始,中国政府才开始寻找解决问题的新方法(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假定,三方各自诉求的冲突是方法论层面,不是本体论层面的)。结果,半个世纪之后,每一方都好像成了各自被封闭在自身边界之内不可穿透的原子。这样总体思想状况又投合了理论家们的喜好,因为它减少了理论家必须处理的变量的数量。
这是否也是美国政治家们的思想状况?如果是,那就不只是美国年轻人的心灵封闭了(参见Allen Bloom, The Closing of American Mind: How Higher Education Has Failed Democracy and Impoverished the Souls of Today’s Students, Simon & Schuster, 2012),而是美国的世界精神被封闭了。有趣的是,更容易被外界观察家当作“不可理解的庞然大物”的中国,反而比作为开放社会的美国更不受成见的限制。早在2011年就有人注意到了坦桑尼亚这个个案1对于中国统一台湾的方案所具有的启发意义,并且意识到它不同于那种始终还在限制美国观察家头脑的联邦制形式。据说,是2009年胡锦涛对坦桑尼亚的国事访问让研究者注意到了这个独特的个案。从那时算起到如今,十多年的时间又过去了。美国的中国研究专家们,似乎仍然没有注意到这种开放的探究精神。他们现在习惯于说:“不,美国的政策是”;“不,那是不可能的”;“看不到变化的可能”,诸如此类。
或许,台湾本身也是方法之一。
坦桑尼亚的“独特个案”指的是该国于1964年4月26日由坦干伊喀共和国(Tanganyika)和桑给巴尔苏丹国(Zanzibar Sultanate)通过和平合并而形成的联合共和国模式。这一模式被视为一种非联邦制的统一框架,具有高度自治的半自治结构(semi-autonomous union),为大陆与岛屿(或分离实体)之间的政治整合提供了创新路径。它不同于传统的联邦制(如美国或欧盟模式),因为它强调单一国家身份下的不对称自治,而非平等分权的联邦分立。这种模式在国际上被视为成功的“非殖民化统一”范例,尤其是在后殖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