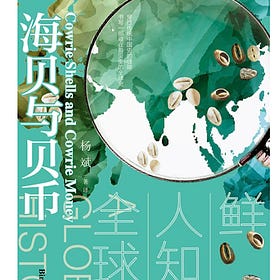关山越 | 前近代西方政治思想札记(三)
編者按:《前近代西方政治思想札记》一共七篇,此為第三篇。上週,2023年亞洲圖書獎揭曉。楊斌教授的《海貝與貝幣》獲亞洲圖書獎。《波士頓書評》推出《Cowrie Shells and Cowrie Money 》的作者楊斌的專輯此外,《波士頓書評》還特別介紹許雪姬的《離散與回歸:在滿洲的臺灣人(1905-1948)》。請看波士頓書評退出的2023年亞洲圖書獎圖書專題。
基督教在面向希腊化世界的传播过程中,渐渐失去了刚健清新的本来面目。“新约时代,基督教人观主要反映在‘登山宝训’的‘天国八福’之中,它是基督徒的生活伦理,而非‘成圣’伦理。从‘天国八福’到‘成圣伦理’,可以说明基督教人观希腊化的走向。《马太福音》的耶稣讲道的主要对象是普通的农夫和渔夫,体现着类似于‘日常生活挑米砍柴’莫非‘道’的禅宗样式。在基督教日渐希腊化之时,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希腊罗马文化重‘教化’和思辨的特点日益渗透入基督教人观之中。成圣伦理是基督教人观希腊化的一个明证。”(《早期基督教的演变及多元传统》,P201)
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以后,基督徒中间弥漫着一片乐观情绪。奥利金的私淑弟子、有“基督教史学之父”之称的优西比乌,便把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视为弥赛亚,把基督教的罗马帝国视为地上的“上帝国”。既然上帝国已经来临,那就“外王”归帝国,“内圣”归教会,教会的使命就是赞襄帝国的千秋洪业。
可是罗马帝国确立基督教为国教尚不足百年,便在诸蛮族的四面入侵之下风雨飘摇。像吉本这样生于启蒙运动时代的史家抨击基督教侵蚀了罗马帝国的根基。如果说“满大街都是圣人”的理学对宋明两个朝代的衰亡负有责任的话,那么在同样意义上基督教对罗马帝国的衰亡也难辞其咎。但正如理学在元朝和清朝延续了中华帝国的文化命脉一样,基督教也在诸蛮族国家林立的欧洲传承了罗马帝国的香火——而且不只是传承,更是裂变与转化,因为基督教在诸蛮族国家林立的欧洲开出了“外王”之道,由此诞生了作为政治和文化共同体的“西方”世界。所谓“西方”,用伯尔曼的话说,“是指历史上发展出来的西欧各民族的文化,这些民族从十一世纪晚期到十六世纪共同效忠于罗马天主教的教皇等级制度,从十六世纪到二十世纪则经历了一系列国家革命,其中每一次革命都在全欧洲引起反响。”(《法律与宗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P147)
毋庸置疑,西方文明是当今世界的强势文明,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超强的政治能力或说“外王”之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并非儒家独有,希腊罗马古典文明及其另外两位嗣子东正教文明和阿拉伯文明也不例外。但西方文明却最终斩断了这一逻辑,“内圣”与“外王”隔绝,“齐家”与“治国”两歧。
西方文明与东正教文明的最后决裂发生在1054年,当时拉丁语的罗马教会宣称圣灵是从圣父和圣子出来,而希腊语的君士坦丁堡教会坚持圣灵只从圣父自己出来。“在希腊人看来,拉丁思路似乎在上帝之内引入了神性的两个独立来源,削弱了圣子和圣灵的重大区别……(东正教思想家)洛斯基认为西方思路必然会导致圣灵非位格化,导致错误地强调基督其人及其作为,会将上帝简化成一个非位格的原则。”(《基督教概论》,P210)——这是否意味着西方思路会由对基督其人的强调开启出个人主义,或是由将上帝简化成原则开启出法理文明?我实在没有能力回答这个问题。不过,提出“圣灵从圣父和圣子出来”这一观念的人是奥古斯丁,而他的《上帝之城》又被后世公认为西方文明“外王”之道的起点,这一宗教决裂便不可能没有深刻的政治意涵。“基督教希腊分支与拉丁分支之间的主要区别是:拉丁教会试图通过教皇革命,把天国的事务和尘世的事务统统交给上帝,而其希腊远亲则选择如下的安排,即将两种事务统统交给尘世的君主……(奥古斯丁)认为:在人类堕落后的世界里,上帝之城完全不同于任何凡夫俗子的城市或社会。奥古斯丁为将凡夫俗子的城市置于上帝城市的掌控之中提供了依据。”(《无法预料的后果》,P119)
可是,说“奥古斯丁为将凡夫俗子的城市置于上帝城市的掌控之中提供了依据”,实属对奥古斯丁的一种简单化的误读。这一误读在历史上一度曾是建设性的,中世纪天主教神学家正是由此确立了教廷对“西方”世界的统治,以及“西方”世界向法理文明的转型。但误读毕竟是误读,奥古斯丁的神主牌位在今天依然无须祧迁,恰是因为他远比误读者所构造的威权形象深邃得多。
410年,西哥特人攻陷“永恒之城”罗马,举世震惊。虽然这次罗马仅失陷三天,西罗马帝国要到476年才正式灭亡,但它足以将罗马帝国即为地上的“上帝国”的神话击得粉碎。很多异教徒罗马人指控基督教要为罗马的陷落负责任。413年,时年59岁的奥古斯丁开始撰写《上帝之城》,虽然起初的立意只是驳斥异教徒罗马人的指控,但从417年撰写第11卷开始,到426年全书杀青,奥古斯丁的论证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护教,正面阐述“双城”的神学主题。这一主题涵盖了创世神学、神学人类学、救赎论、末世论和道德神学等方方面面,但首先是一种社会生活的神学。
我对《上帝之城》的分析,主要倚重芬兰学者罗明嘉的《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中的社会生活神学》(中国社科2008年版,以下简称《奥》),并多处参考国内学者夏洞奇的《尘世的权威:奥古斯丁的社会政治思想》(上海三联2007年版,以下简称《尘》)。二十世纪西方学界关于《上帝之城》形成了以卡莱尔和马库斯为代表的新经典解释范式,我下面的论述即遵循这一范式。夏洞奇在其著作中标举了一些反对新经典范式的新锐学者的研究路径,但我在仔细推敲之后觉得这些路径尚不足以对新经典范式构成有力的挑战,故略而不论。
“原罪”是理解奥古斯丁神学思想的入口。
亚当夏娃偷吃禁果是人类原罪的肇因。在奥古斯丁看来,这不是因为禁果是恶的,而是因为亚当夏娃偷吃禁果的行为违反了上帝的命令。不仅禁果不是恶的,所有被造物的自然本性都不是恶的,因为它们都出于至善的上帝。在此奥古斯丁明确反对摩尼教扎根于存在论意义上的善恶二元论。但上帝虽然是一切自然本性的创造者,却不是一切意志的创造者和管辖者,故而魔鬼可以诱惑亚当夏娃出于骄傲而犯罪。“奥古斯丁认为,上帝对人类的惩罚是公正的。在人类的第一次犯罪中,人不服从上帝;作为惩罚,从此人的肉体不再服从于他们自己的灵魂……由于全人类都起源于亚当,始祖的罪必将遗传给他们的全部后代,使全人类都陷于原罪状态中。相应的,上帝的惩罚不仅针对始祖本身,还株连到了他们的每一个后代。”(《尘》,P73—74)
在人类因为原罪而陷入的堕落状态中,肉身的腐朽重压着灵。但奥古斯丁反对柏拉图主义对肉身的贬抑,认为肉身本身是善的,不是腐朽的肉身令灵有罪,而是有罪的灵令肉身腐朽。奥古斯丁又经常将“爱”与“意志”等同起来,用“意志与爱之重”这个概念描述堕落后的世界。一物的“重量”令其趋于相宜的稳态和静态,而在堕落状态中,悖乱的意志与爱则因其重量坠落下沉,令世界陷入一片混乱。有罪的人根本不可能像柏拉图主义设想的那样以智性的静观注视真理或上帝,而是被悖乱的、向下沉坠的意志与爱所主宰。“对奥古斯丁来说,‘爱’的现象是比“知”的现象更为基本的人类现实要素。爱是生命中的强大力量,人不能够看透或控制它。爱的现象塑造着人类现实,甚于其他一切。”(《奥》,P56)奥古斯丁年轻时经历过浪子生涯,晚年又遭逢乱世,因此他对“意志与爱之重”的体验与洞察,实不亚于另一位伟大的基督徒陀思妥耶夫斯基。
当然,上帝预知一切,不可能不知道人将犯罪,拯救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人类因为悖逆上帝而堕落,也可以因为对上帝的信和爱而得救。在奥古斯丁看来,信上帝和爱上帝是一回事。在末日,上帝创造的世界将会恢复其原初本善的自然秩序,得救的人将会肉身复活,其肉身在天国完全服从于灵,永远不朽。但人类的罪是如此深重,即使是对上帝的信和爱,也不可能出自本然的意志和智性,而只能是来自上帝的恩典所赐予的启示。
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将堕落之后、末日之前的人类生活世界表述为“尘世”。“尘世”的根本特征在于它是两座“城”纠缠在一起,一为“地上之城”,一为“上帝之城”。所谓“城”只是一个用来指代人之群体的意象。两座城的子民均包括了天使与人类,地上之城属于恶的天使与人类,上帝之城属于善的天使与人类,而后者中属于人类的部分又称为“客旅中的上帝之城”或说“朝圣中的上帝之城”。 到了末日审判之时,上帝之城的子民将进入天国得到永生,地上之城的子民将进入地狱承受永罚。而所谓“客旅”,所谓“朝圣”,旨在强调这些子民终究魂属天国,在尘世中只是漂泊的旅人。
“在个人的层面,‘两座城’代表了两种生活方式:一座城属于那些属肉的人,另一座城属于那些属灵的人。必须强调的是,‘属灵’和‘属肉’所表达的不是灵魂与肉体的二元论,而是人与上帝的两种关系。”(《尘》,P92)——这两种关系其实就是两种爱,“属灵”以对上帝的爱(amor sui)为重,“属肉”以对自己的爱(amor Dei)为重。但奥古斯丁并不认为“对自己的爱”和“对上帝的爱”在根本上是相互矛盾的,真正的问题只是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因此后世那种将异教eros(欲爱,亦即寻求自我之爱)与基督教agape(圣爱,亦即自我奉献之爱)对立的论调是不会为他认可的。他毕竟是浪子出身。
不过,“‘双城’的区别不是一种可见的社会学意义上的现实,而是一种神学意义上的现实,只能在信仰中理解。两者之间的区别,不到历史终结之日是不会显现的……人类社会本身在社会学意义上不可分,其中既有上帝之城的存在,又有地上之城的存在。”(《奥》,P102)即使教会也不例外,也是要到末日审判才能将“谷子”和“稗子”分开。当时北非的多纳特派十分强调教会的纯洁性,而奥古斯丁不仅激烈反对此教派,甚至支持罗马帝国以强制手段镇压之,足以证明不能把上帝之城等同于教会,把地上之城等同于罗马。
由此我们可以进入奥古斯丁的政治和社会思想了。奥古斯丁认为,必须将正义看作一个超验的概念,只有末日审判才能实现真正的正义。在尘世,“强制性的社会权力结构之所以存在,不是‘出于正义’,而是‘出于事实’,是作为罪的现实。”(《奥》,P138)秉承柏拉图主义的西塞罗认为,可以在人人皆具的理性基础上建构“自然正义”,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建立在自然正义的基础上,奥古斯丁则否认自然正义的存在,也否认了国家的正义性。
通过否定自然正义,奥古斯丁也颠覆了“人是政治动物”的传统观念,认为“人是社会动物”。在西塞罗那里有一个概念populus,意为“通过对正当的共识和共同利益联系起来的人群”,和后世所说的“人民”非常重叠。但西塞罗只是政治性地运用这一概念,“对正当的共识”导向“自然正义”,导向对国家的构建,populus与国家唇齿相依。而在奥古斯丁那里,populus是一个社会性的概念,意为“通过对爱的对象的共识联系起来的人群”,与国家并无必然联系。这里所说的“爱”是“集体性自私之爱”——因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爱,必然是偏向自爱一方的,是人类集体性自私的表达。能够作为政治社会之基础的,既不是仁爱,也不是真正的正义,而是作为社会生活之悲苦典型特征的那种爱。”(《奥》,P171)
尤其重要的是,在西塞罗看来,不是任何人群都配得populus这一称号,没有自然正义就只是乌合之众,而在奥古斯丁看来,只要一群人能就其自私之爱达成共识,即可成为populus。下面我将奥古斯丁的populus直接表述为“人民”,希望不至于引发歧义,让人误以为这一概念具有“自然正义”。
那么与正义无关的“集体性自私之爱”岂不是注定会藏污纳垢吗?是的,但奥古斯丁对政治、对社会生活的态度是很现实的,在他看来,“政治社会的现实不能建立在绝对的或自然的正义概念基础之上,而毋宁说是一种建立在集体性自私基础之上的社会契约。尽管‘统治欲’的事实依然是政治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现实,至少它可以被‘提升’到集体性自利或自我中心的高度,也就是说将某种民主理念运用于政治。不是由少数人来决定公共生活的目标,而是考虑到大众的自私追求。对于特定的某一人民而言,这当然是比独裁政治更好的一种社会模式,尽管它并不一定有利于不同人民之间的关系;对自私之爱的对象作集体性裁决,并不能减弱征服外邦的贪欲。”(《奥》,P175)
有必要说明的是,上述引文中提到的“统治欲”是奥古斯丁分析社会生活的核心概念。它是最可鄙的恶,因为它“表现了罪的本质:它是‘骄傲’,人因它而企图仿效上帝,贪爱自身的权力和荣耀胜过爱造物主……在‘统治欲’的状态中,基于魔鬼的骄傲,人用一种悖乱的方式企图仿效上帝,把自己的统治强加于同胞之上,从而败坏了人人平等的自然秩序。”(《奥》P128-129)但奥古斯丁强调“统治欲”在社会生活中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就是堕落状态中的人类之“罪”的本质体现。相比之下,“集体性自私之爱”是一种程度较轻的恶,不妨用它来制约“统治欲”的大恶。
不过,奥古斯丁认为,在尘世中尚有一片净土是不受“统治欲”污染的,那就是“客旅的上帝之城”中的家人之爱。奥古斯丁与母亲莫尼卡感情极笃,因此他对家人之爱深具信心。但一旦迈出家的门槛进入社会生活,更不用说涉足政治,“统治欲”的邪恶力量便无所不在,而能够对之构成一定制约的“集体性自私之爱”也绝对不能和家人之间充满责任感的仁爱相提并论。这也就是我在上文提到的,“齐家”与“治国”两歧。
还有必要指出,“集体性自私之爱”和古典哲学家经常强调的“友爱”也是无关的。“友爱”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核心概念,但拉丁教父奥古斯丁似乎没怎么读过用希腊语写作的亚里士多德,“友爱”对他来说无足轻重。我们先前讨论过,“友爱”是构建传统帝国价值系统的关键要素。而奥古斯丁大约是倾向于反帝国的,他似乎相信,“统治欲”在小国中比在帝国中更容易受到制约。
正是从“集体性自私之爱”中导出了对社会契约的诉求。这是因为,首先,人最根本的自私之爱无非就是爱惜自己的生命,为了保全生命,所有人,无论是地上之城的子民还是上帝之城的子民,都至少会追求某种最低限度的社会秩序,追求“必要的和平”;其次,尽管人类因为“意志与爱之重”深陷于罪,但上帝创造的自然本性是善的,这些善的自然本性即使在罪的深渊中也还不乏残存的片断,构成某种自然德性——奥古斯丁经常暗示,异教徒罗马人之所以能够建立一个强大的帝国,就是因为他们拥有并奉行自然德性——这些自然德性也使得两座城之间可以获致某种某种最低限度的“和谐”(concordia)。“在意志与爱的领域内,‘和谐’概念包含着两座敌对之城的民之间的某种社会契约。这时的和谐是他们为了维续地上生命而有的共识。”(《奥》,P197)
似乎可以把奥古斯丁视为倡导“和谐社会”的先驱,但他对“和谐社会”的倡导其实离不开对国家强制力的倚重。这可以从他与多纳特派的斗争中得到证明。多纳特派就是上文提到的十分强调教会纯洁性的北非基督教派,它扎根于较为边缘贫困的努米比亚和毛里塔尼亚地区,其信徒惯于为信仰而施暴,随时准备殉教,甚至不惜以自杀的方式博取烈士的美名。从390年开始,多纳特派与北非公教会之间的长期矛盾演变为剧烈的流血冲突,公教会表面强大但实际上处于弱势,直到412年罗马帝国颁布强制法令镇压多纳特派才扭转局势。奥古斯丁身为北非希波城的公教会大主教,坚决支持这一强制政策,乃至在书信中以救人多于杀人的算法来为之辩护。
不过,奥古斯丁对现实政治中的国家建构保持缄默。“关于哪种国家形式对社会生活而言即便不是最多的善、至少也是最少的恶的问题,他不予置评。在君主制、寡头政治或任何一种形式的民主制之间,他毫无偏好。”(《奥》,P178)然而,在他身后,中世纪罗马教廷正是以《上帝之城》为依据,在“西方”世界确立了国家依赖于教会的神权政治。当然这是后话了。
書訊 | 2023亞洲圖書獎 圖書四種
編者按:2023亞洲圖書獎揭曉,來自中國、台灣、韓國、日本的四本圖書獲獎: 中國:Cowrie Shells and Cowrie Money by Bin Yang 台灣:Diaspora and Return by Hsu Hsueh-chi 韓國:Money Free Life by Park Jeongmi 日本:The birth of same-sex marriage law in Taiwan by Suzuki Ken 《波士頓書評》推出《Cowrie Shells and Cowrie Money 》的作者楊斌的專輯,並就《Cowrie Shells and Cowrie Money 》這本書做了專訪。此外,《波士頓書評》還特別介紹
关山越 | 前近代西方政治思想札记(二)
編者按:《前近代西方政治思想札记》一共七篇,此為第二篇。 严格地说“犹太”一词只能追述到公元前四世纪后期,但为了行文简洁起见,下文我将古代希伯来人、以色列人和后来的犹太人统称犹太人。 马丁·布伯在《论犹太教》中说过,犹太人的时间感远胜空间感,希伯来《圣经》中的描述性形容词都不谈“形式”“颜色”,只谈“声音”“运动”。可以想象,占卜对犹太人来说是陌生的,因为占卜就是化时间为空间,在“形式”和“颜色”中辨认征兆。犹太人的先祖亚伯拉罕不是通过占卜测知神意,而是直接聆听神谕。于是便有了那个著名的故事:上帝命亚伯拉罕带上他疼爱的独子以撒去摩利亚,在一座指定的山上将以撒献为燔祭。亚伯拉罕带着以撒走了三天来到指定地点,造好祭坛,就在举刀杀子前的一刻,上帝阻止了他,让他以一只公羊替代以撒作为祭品。克尔凯郭尔在《恐惧与颤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