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图 | 弗格森与苏格兰启蒙运动:“自由是每个人都必须随时自我维护的权利”
編者按:发生在 18 世纪欧洲的“启蒙”不仅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运动,更是在思想观念上创制了现代性内涵。正是那些熠熠生辉的启蒙思想家,描绘出现代世界的图景。复旦大学李宏图教授的《新启蒙札记》以苏格兰启蒙运动和法国启蒙运动两种样式为重点,揭示启蒙运动的普遍性特质以及在不同空间的多样化呈现。本文为苏格兰启蒙运动专辑中《奴役与自由:亚当·弗格森的思考》一节。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1723-1816)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作为道德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他以《文明社会史论》(1767)闻名。该书从经验主义视角剖析人类社会演进,强调自由并非天赋权利,而是通过公民参与与道德自律实现的动态过程。弗格森区分“政治奴役”与“个人奴役”:前者源于专制统治,剥夺公民自主;后者则指帝国扩张中的奴隶贸易,他理论上斥为“不自然”,违背人类本性与社会和谐。在苏格兰启蒙的理性光芒下,弗格森将“奴役”与“自由”置于历史与伦理张力中,视奴役为社会腐败的产物,而非单纯的经济制度。 他主张,真正自由源于“公共精神”,通过教育与制度防范奢侈腐蚀,避免从自由滑向奴役,“自由是每个人都必须随时自我维护的权利”。弗格森的思想桥接休谟与斯密的经济学,启发后代对奴役的反思。而李宏图教授教授的解读,更是提醒我们:奴役并非遥远历史。
本文为出版社授权刊发。
一
英国历史学家罗伊·波特认为:“启蒙纲领的中心准则是自由。”他引用了英国历史学家、社会主义者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1924—1993)在其名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的总结并详加说明:“免于绝对主义(君主立宪制),免于遭到任意逮捕,由陪审团审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免于任意闯入及搜查的在家中的自由;思想、言论与信仰的在某些方面受限的自由;由议会的反对权,选举以及选举造成的喧哗所提供的对自由的间接参与(或表面上如此)……还有旅行自由、贸易自由,出卖自身劳动力的自由。”
对此,美国学者彼得·盖伊也有相近的结论。他认为:“启蒙人士统一在一个雄心勃勃的纲领之下。这是一个提倡世俗主义、人道、世界主义,尤其是自由的纲领。这里说的自由包括许多具体形式:免于专横权力、言论自由、贸易自由、发挥自己才能的自由、审美的自由,总之,一个有道德的人在世界上自行其是的自由。”
英国牧师约翰·泰勒(John Taylor,1694—1761)认为,1688年光荣革命之前的特征是知识上的神秘与天主教的控制,之后则是“革命中的自由,噢,那光芒万丈的日子!以她优美的身影巍然耸立,对着我们的乐土微笑。人们从暴政与迫害的恐惧中解脱出来,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解力”。英国哲学家沙夫茨伯里伯爵三世(Anthony Ashley Cooper,3rd Earl of Shaftesbury,1671—1713)也认为,自由带来了文明。“一切儒雅都归功于自由。我们通过一种温和友善的碰撞交往,相互改进,磨掉我们的棱角。”爱尔兰哲学家约翰·托兰德(John Toland,1670—1722)最早以思想自由者自诩,英国哲学家安东尼·科林斯(Anthony Collins,1676—1729)在1713年出版了《论思想自由,写于所谓思想自由者派别问世和成长之际》(A Discourse of Free Thinking, Occasioned by the Rise and Growth of a Sect called Free Thinkers)一书,认为思想自由的权利是理性的基本准则。
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亚当·斯密将自由视为商业社会的重要内容,在斯密看来,自由主要涉及如下内容:第一,自由是指参与市场交换的每一个人都是独立自主的个体,是一个自由人,其个人自由的身份与“奴隶”或者受到“奴役”对立。而与农业社会相比,商业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实现人的自由。恰如另外一位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家詹姆斯·斯图亚特(James Stuart,1688—1766)所说:“在现代社会里,工业发展,服务业也惠及千家万户,这些都会帮助底层人民摆脱对他人的依附,实现自由。”
第二,每个人能够自由支配本人的财产权和劳动权,参与到市场交换活动中去,因此所有权问题非常重要。在这里,所有权不只是指物本身,还包括每个个体所拥有的“劳动”。斯密说:“劳动所有权是一切其他所有权的主要基础,所以这种所有权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个穷人所有的世袭财产,就是他的体力与技巧。不让他以他认为正当的方式,在不侵害他邻人的条件下,使用他们的体力与技巧,那明显地是侵犯这最神圣的财产。显然,那不但侵害这劳动者的正当自由,而且还侵害劳动雇用者的正当自由。妨害一个人,使不能在自己认为适当的用途上劳动,也就妨害另一个人,使不能雇用自己认为适当的人。”因此,他提出劳动权概念,以之批评政府制定的“学徒法”,其认为一个人必须当满7年的学徒之后才能满师,才可以自由流动和寻找工作。这显然违反了商业社会的自由原则。
同样,斯密也反对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济贫法”,因为,在“济贫法”的规定下,“贫民除了在所属的教区内,就不易取得居住权,甚至不易找到工作的机会”。 所以斯密才说,要建立起“在各事物都听任其自然发展的社会,即在一切都听其自由,各个人都能自由选择自己认为适当的职业,并能随时自由改业的社会”。
第三,法治的社会。法治不仅是文明的标志,更重要的是,只有在法治的条件下才能保障每一个人的自由。
第四,就市场本身来说,它是自由的,受着“看不见的手的支配”,打破了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种垄断。斯密自陈,他对不列颠整个商业体系做出了非常猛烈的攻击。这种批评体现在,他主张自由,反对垄断。例如,他反对土地贵族对粮食价格的垄断,要求实现产品交换、劳动力自由迁徙等。
总之,在斯密那里,自由,就是要捍卫人的财产、能力、工作等权利,实现自由竞争与自由交换。同样,在斯密关于自由的内容清单中,还包括劳动的时间、报酬、工作环境,劳动者的身份,个人的安全和契约受保护等方面的内容。从这些自由的内容清单来看,以斯密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不仅关注政治自由,还关注社会性的公民自由。同样,自由也不只局限于英国,这是社会发展到商业社会阶段的特性。 意思是说,任何社会只要历经到这一阶段,就需要有充分的自由,以及实现这些自由。
二
如果说斯密主要侧重于市场经济自由的话,那么,这些思想家在讨论自由的时候同样没有忽视政治与自由之间的关系。且不说斯密关注政府如何不对市场交换干预太多,主张建立起自由的市场交换体制,很多思想家也都从政治的维度思考自由和奴役的问题。可以说,追求自由是整个18世纪启蒙运动思想家的一致追求,他们的相关论述也十分丰富。当然在讨论自由时,这些思想家也同样在讨论自由的反义即奴役,以及如何保障自由。
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家亚当·弗格森在其《文明社会史论》中有一章论及“政治奴役”问题。在笔者看来,弗格森对自由的思考不应被遗忘,而需加以重视。这里就以弗格森为个案加以论述。
弗格森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由似乎是文明国家所独有的。” 并且,“自由来自法制。我们倾向于这么认为:法令不仅仅是一个决心争取自由的民族的决心和信条,也不仅仅是他们的权利的成文记载,而且是一个用于捍卫他们的权威,是人类的变化无常无法侵越的障碍”。纵观历史,和考虑到当时的历史语境,这里的“人类的变化无常”可以理解为,在专制君主的个人专断统治下,由于君主的意志变化无常,因此对自由的侵害也就越大。
弗格森举例说:在亚洲,当一位帕夏(Basha,即奥斯曼帝国的高级官员)试图依据自然衡平法裁决每种纠纷时,我们承认他拥有可以随意支配的权力。由此,就不会有法律的公正裁决,人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如果诉讼程序、成文法令或其他法律构成部分不再靠产生它们的那种精神来推行,那么它们只会包庇滥用权力,而不会限制滥用权力。当它们迎合腐败官员的意愿时,它们甚至可能得到腐败官吏的尊重。”
和孟德斯鸠一样,弗格森认为,为了要避免奴役,获得自由,仅仅讨论法律还不够,政治体制的建设非常重要。他说:“人们告诫我们,无论在哪一种政体中,我们都应当警惕滥用或扩大行政权所造成的篡权行为。” 因为对权力的渴望和控制似乎是人类的本性,“在任何一级,掌权的人都非常讨厌约束,他们随时准备消除对立”。弗格森重点讨论了专制政体的特性和建立的原因。他说:“压迫和残酷并非总是专制政体的必要组成部分。而且,即使这些都已存在,它们也只不过是它的部分弊病而已。专制政体是建立在腐化堕落和压抑所有社会美德和政治美德的基础上的。它要求臣民以恐惧为行为动机。它会以牺牲人类的利益为代价来平息少数人的情绪。而且,社会安定本身建立在产生人类精神享受、精神力量和精神升华的唯一基础——自由和信心的废墟上。”
弗格森比较了自由政体和专制政体的区别:“在任何自由政体存在的时期,并且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等级、基本权利和个人权利意识时,每个群体的成员相互间都是值得关心和尊敬的对象。文明社会中每个权利要求的实现都需要运用能力、智慧、劝诫、魅力以及权力。但是,专制政体最大的进步在于用简单的命令进行统治,在于排斥强制手段以外的任何手段。所以,在这一政策影响下,能利用和培养人们的理解力,能唤醒人们的情感、激发人们想象力的时刻渐渐消失了。人们本着一种自由的精神在社会中从事各种活动而给人性增光的进程和他们沦为这一不幸境地的进程一样都不是始终如一的,或者说,也是那样断断续续的。”
弗格森还指出,专制政体造成了人人沉默、万马齐喑的局面,任何言语都是多余的,也会招致灾难,甚至是杀身之祸。“在这样一副沉默、沮丧的场面中,任何地位都不能赋予思想上的自由。”“在专制宫廷中,所有阶层的人们同样都是以这种愚昧和野蛮为特征的,或者说,正是这种愚昧和野蛮使不同的等级趋于一致,并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
在比较中,弗格森准确地指出了专制君主的另外一个特性:“专制君主管理政府的准则是任性和随心所欲。每个权力代表同样也是按这一指导性准则办事。被激怒时,他会出击;高兴时,他会施予恩惠。在与税收、司法或警察相关的事务中,每个省长就好比是身处敌国的将领。他来时全副武装,以杀人放火相要挟。与其说他在征税,不如说他是使用武力敛集贡品。他或是进行破坏或是慈悲为怀,这得看哪一种方式合他的意。当受压迫者的呼声或者他以牺牲整个省份为代价为己敛财这一消息传到君主耳中时,强取豪夺者要么拿出一部分赃物,要么让人把所有赃物都取走以免受罚。但是,受害人并没有得到任何赔偿。更有甚者,首先是大臣犯罪、搜刮民财,而后是大臣受到惩罚,君主中饱私囊。”弗格森这里的描写入骨三分,惟妙惟肖。时隔多年之后,这样的情景在有些地方还是经常再现。
所以,弗格森一再提醒人们:“一个道德败坏的野心家恣意肆虐会给人类带来奴役。”据此,弗格森认为,维护自由、反对奴役,不仅取决于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所说的“三权分立”,也取决于人的“美德”,即捍卫自由,勇于承担作为公民的责任。用今天的术语说,就是要成为一个“积极公民”,而不是消极被动,甚至主动放弃自己的公民责任。秉持这一理念,人们必须精诚团结,勇敢反对和抵抗奴役。在这里,弗格森的观点非常清晰,即每一个人都需要履行公民的责任,但履行公民责任不是一定要做出多么轰轰烈烈的壮举,而是可以在日常行动中像维护自己的生命一样维护自由,像沐浴阳光和呼吸空气那样,将反抗暴政作为一种本能。试想,如果每一个人都能秉持这一理念,并将其化为日常行动,那么,每天点滴的进步就会汇聚成坚实的基础,何愁自由不能确保?暴政也无法降临,因为每个人都能捍卫自由,守护自由。
从公民的美德和责任出发,也是弗格森在全力批评专制体制之后找到的不同于其他思想家的实现自由的路径。弗格森说:“自由是每个人都必须随时自我维护的权利。试图将自由权利作为恩惠施予他人的人,事实上,恰恰会因此而丧失了自由权利。甚至政治制度也容不得轻信。尽管它们看上去不为人们的意志所左右,也无须接受人们的仲裁,但是,我们仍然不能依赖它们来保存自由。它们可以助长自由,但是它们无法超越那种坚定不移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自由人总能和不光彩的行为作斗争,并依靠自己来维护自身的安全。”
事实上,弗格森有很多这样的论述,其主旨是要回答一个尖锐的问题:人们总是向往自由,不愿受到奴役,但“我们应该把自由的丧失归咎于谁呢”?弗格森质问:“是归咎于放弃了自己地位的臣民,还是归咎于仅仅是留在自己的位子上,或者只要政府附属或下属官员不再对他的权利提出质疑就可以继续随心所欲地进行统治的君主呢?”
在弗格森看来,应该从每个个体来考察,或者说,每个个体都重任在肩,都肩负着反抗暴政、维护自由的重任。弗格森指出:“人们是否有资格享有这一福祉(指“自由权利”——引者按)只是取决于能否使他们理解自己的权利,能否使他们尊重人类正当的权利要求;取决于他们本身是否愿意承担管理国家和国防的重任,是否更愿意投身于自由人的事业,而不耽于怠惰或者耽于用屈从和恐惧换取安全感的虚妄的希望。”这令人想到了英国革命时期“新模范军”在反抗国王查理一世个人专横统治时所发出的誓言:“我战斗是为了我国的自由和法制,它们正处于被人颠覆的危境;这些人长期以来费尽心机地要使这个王国陷于暴戾恣睢的统治之中。我战斗是为了维护我们的国会。”从这里也分明可以看到,自由是要每个人来维护,甚至是用生命来维护的。
三
弗格森的这些论述,还令人想起当代英国思想史家昆廷·斯金纳对“共和主义自由”的挖掘和阐释。在斯金纳看来,自由并非如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所说的那样,只有“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这两种类型,而是还存在着像英国17世纪一批共和主义者所论述的那种“第三种自由”。这一自由观认为,如果你生活在允许在法律之外运用任何形式特权或专断权力的政府之下,那么你很容易处于被你的政府用暴力或其他强制性手段剥夺你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这种危险的状态,你也就将变得不自由了。当然,你的统治者也许不会选择运用上述的那些强制权力,或可能十分亲切地运用这些权力来关心你的个人自由。这样,也许你实际上依然还充分享有你的公民权利。但在事实上,你的统治者拥有如此专断的权力就已经意味着,你持续享有的公民权在任何时候都仅仅存在于对他们善良意志的依赖(政治权威的恩赐)上。换言之,你仍旧是臣民,你的行动权利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被剥夺掉,这无异于生活在一种被奴役的状态。不仅具体的阻碍行为可以让人丧失自由,实际上,专断权力的存在,以及统治与依附关系的存在就足以将人们从“自由人”(liberi homines) 身份贬至奴隶身份。
这样对自由的理解即是,如果你希望保有你的自由,你就必须确保你生活在没有任何专断权力成分的一种政治体制下。这样你的公民自由才不可能仅仅依赖于某个统治者、统治集团或任何其他国家管理机构的善良意志。换言之,你必须生活在这样的一种体制下,制定法律的唯一权力要保存在人民或由他们所委托的代表手中,政治体的每一个成员——统治者和公民都一样——服从于他们所选择的加之于他们自身的法律(任何人都不拥有超越法律之上的权力) 。如果你生活在这样的一种自治体制下,你的统治者将被剥夺了任何能强制别人的专断权力,其结果也就剥夺了迫使你和你的同胞处于屈从于别人的善良意志的状态下,及奴役状态下的任何专制的可能性。
政府与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是服从法律的,不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一旦这些统治者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存在着专断权力的话,那么就意味着不自由。因此,统治者和人民共同服从法律的统治成为自由的基础。共和主义的自由强调“被依从”或“不依从”,在一种关系中理解自由与奴役。
再有法律的制定问题。在斯金纳看来,法律是基于作为整体的全体人民的意志而制定的,这就意味着你必须参与政治。如果你在一个代议制政府下作为一个积极公民而生存,你才能摆脱个人处于被奴役的状态。如果你生活在一种依从的状态,你的自由的保障不仅要被缩减,而且自由本身也要被消减,甚至不存在。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必须要有公共道德性,意识到并履行作为一个公民的责任。这样才能确保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免受任何外在的奴役。
关于奴役与自由的关系,早于弗格森一个多世纪的英国思想家约翰·洛克在其《政府论(下篇)》“论奴役”一章中已有论及。他写道:“处在社会中的人的自由,就是除经人们同意在国家内所建立的立法权以外,不受其他任何立法权的支配;除了立法机关根据对它的委托所制定的法律以外,不受任何意志的统辖或任何法律的约束。……处在政府之下的人们的自由,应有长期有效的规则作为生活的准绳,这种规则为社会一切成员所共同遵守,并为社会所建立的立法机关所制定。这是在规则未加规定的一切事情上能按照我自己的意志去做的自由,而不受另一人的反复无常的、事前不知道的和武断的意志的支配。”非如此,那就意味着,人们处于一种受奴役的奴隶般的地位和状况。
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爱尔维修也认为,自由就是不受妨碍。他说:“自由的人,就是未受桎梏、未被囚禁、不像奴隶那样由于恐惧刑罚而畏首畏尾的人。在这种意思内,人的自由即是他的权能之自由的行使。我说他的权能,因为若以无权能做的事——如要我们像飞鹰之穿云、鲸鱼之潜海和把我们变成国王、教皇或皇帝——为非自由,那就觉得滑稽了。”
当代共和主义思想家佩蒂特(Philip Noel Pettit)认为,人的独立、自主和保有尊严不仅是免于干涉的公民自由的一种产物,而且这反过来也有助于自由的实现。当你享有这一地位的时候,就意味着你不必过分地恭维任何人,也不必充满奴性地趋附任何人。同样,别人也正是因为对你的地位的承认,他们随意侵犯你的冲动才会被斩断。因此,不自由意味着服从专断的支配——服从他人潜在的、反复无常的意志或乖戾的判断。自由便意味着从这种屈从地位中解放,从这种依附关系中解脱。它要求你能够在其他公民面前昂首挺胸,并产生这样一种共同意识,即你们当中没有谁可以拥有专断地干涉另一个人的权力。
对照这一理解自由的思路,将视线转向当下的现实时,我们会发现,很多人都忘记了维护自由、反抗暴政的那些基本原则,甚至常识,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混淆是非的作为比比皆是。这可以反证,耕耘出一片维护自由的肥沃土壤当是多么重要。没有这一沃土,又如何能长出自由这棵参天大树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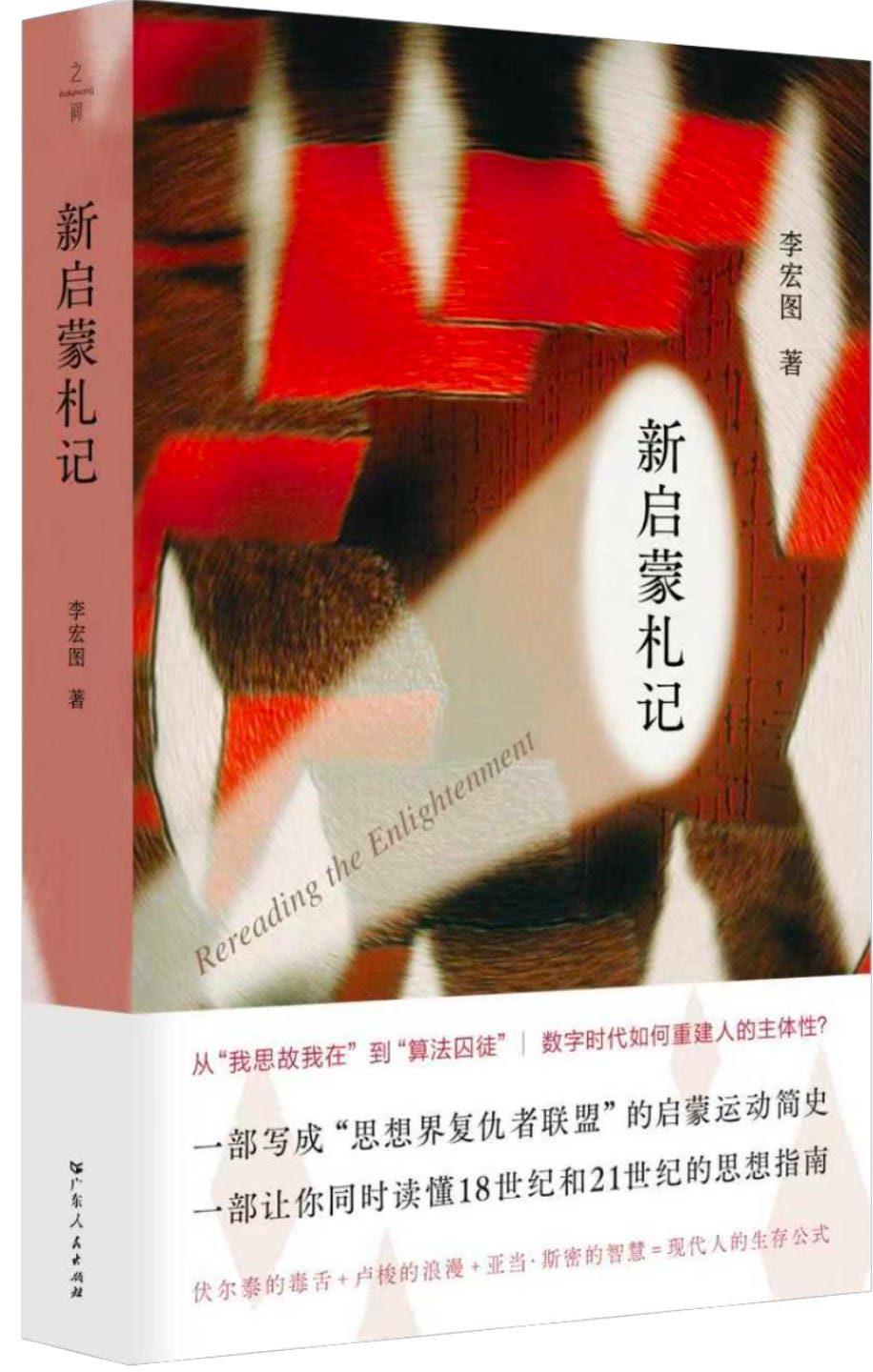
英文书名没有歧义,中文一看会想起张申府1939年写的那本《什么是新启蒙运动》。所以还不如搬用英文书名:重读启蒙
是的,我们也需要一场启蒙,如果一个个人没有权力为自己辩护,那么普遍攻击就会成为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