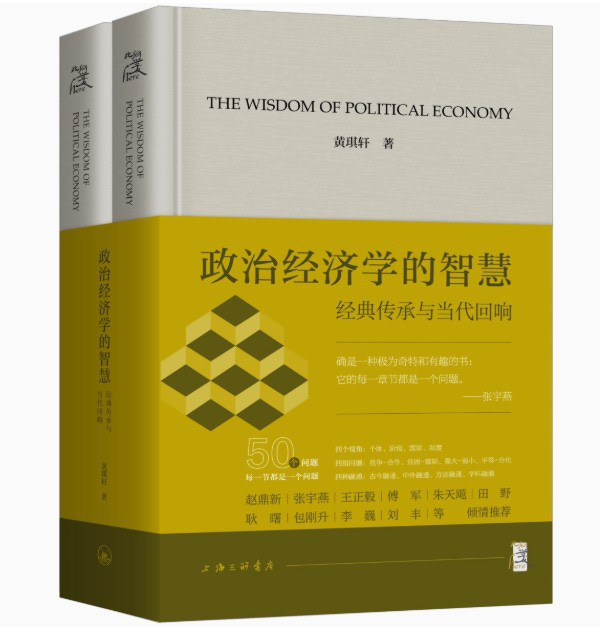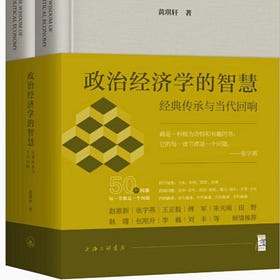黄琪轩 | 马克思的警钟:为什么福利制度与工会也无法消除经济危机?
编者按:特朗普的“大而美”法案(英语: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通过之后,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的地基似乎发出了一声断裂的声音。无论是与中国对于供应链的争夺,还是国内左支右绌的税收、福利与医保问题,抑或是可怕的美债问题,还是跨国公司在地缘政治中越来越暧昧的角色,或是无法抑制的通话膨胀,都让人感觉到似乎一场巨大的经济危机和政治秩序的颠覆正在到来。尽管我们对照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一场的金融危机,有太多让我们来不及理解的经济现象和未知的力量;虽然特朗普和万斯都希望让美国回到二战后那个一边向全世界输出民主秩序,一边以民主兵工厂和原子弹引以为豪的时代,但是我们都明白,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而经济危机与民主秩序衰落的连锁反应却依旧存在,这种震动和变化,也许会在未来改变我们每一个人,和我们对于政治和经济的认知。
也许,是时候让我们了解什么是金融危机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危机源于买卖分离、平均利润率下降及生产相对过剩等因素,根源在于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他预测这些危机将引发无产阶级革命。然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技术工人增加、福利制度、国家干预(如罗斯福新政和劳工法案)及工会作用,延缓了革命的发生。尽管如此,近年工会影响力下降导致贫富差距扩大。马克思以阶级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视角,揭示了资本主义结构性缺陷,但其预测的革命在发达国家却未实现,为什么?
本文选自《政治经济学的智慧》一书,出版社授权刊发。
免費訂閱《波士頓書評》及相关事宜发送邮件:boshidunshuping@gmail.com,隨意打賞:Zelle,PayPal:boshidunshuping@gmail.com 用戶名:Boston Review of Books;長期支持請點擊下面訂閱,升級為付費訂閱。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的《1929年大崩盘》是对那一时期美国经济危机的绝妙记录。在这次危机爆发之前与之后,资本主义不断被经济危机困扰。1825年危机被马克思确认为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开始。1825年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间歇性地爆发。例如,1836年、1847年、1857年、1866年、1873年、1882年、1890年、1900年、1907年、1914年、1921年、1929—1933年、1937—1938年等年份都爆发了经济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历了战后初期的快速增长,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又再度陷入危机,经济停滞同时伴随严重的通货膨胀,因此当时危机被称为“滞涨”。20世纪80年代初,拉美国家经历了严重债务危机;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经历了储贷危机(S&L Crisis),全美3000多家储贷机构中,有上千家无法兑付储户存款;1987年,以美国纽约股市暴跌为开端,美国金融地震引发全球股灾;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也经历了股票市场萧条与经济停滞;1992年,欧洲货币体系出现问题,爆发货币危机;1994年,墨西哥比索汇率狂跌,股票价格大幅度下跌,墨西哥和土耳其爆发危机;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从泰国开始,波及印度尼西亚、韩国,1998年,危机扩散到俄罗斯等国家;2000年,由于互联网泡沫破裂,美国与欧洲股市大跌,遭遇危机;2001年,土耳其以及阿根廷又爆发危机,阿根廷危机期间,两周之内五易总统;从2007年开始,次贷危机席卷美国,2008年美国的危机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危机。这次危机波及了欧盟、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也引发了全球企业破产浪潮。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经济指标急剧下降,全球经济经历了一次严重冲击。以上危机的原因和形式各不相同,但却印证了马克思的预言:危机将始终和资本主义相伴随。
经济思想史学家亨利·威廉·斯皮格尔(Henry William Spiegel)认为马克思从未提出一个独立的、内容充实的经济波动理论。有学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危机受到无穷多因素影响,所以不可能在任何一个抽象层面得到一个完整解释。邱海平:《经济危机理论》,载《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十五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5页。马克思关于危机的论述散见在他《资本论》以及《剩余价值理论》中多个章节。马克思对危机的论述有重要价值,海尔布隆纳指出,马克思的预言被不断验证,尤其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学者都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具有内在的危机倾向。
马克思对危机的关注点有好几个,包括平均利润率下降导致危机、生产部门比例失调导致危机等,这里无法一一展开。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 Baptiste Say)等人认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一种产品,生产得越多,那么对要素需求就越大。买的过程就是卖的过程,供给与需求相联系、相适应。因此,资本主义不会出现普遍性危机。在前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认为不会有经济危机。“在人们为自己而生产的状态下,确实没有危机,但是也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古代人在他们的奴隶生产中知道有危机这一回事,虽然在古代人中,曾经有个别的生产者破产。”资本主义之所以会有危机,是因为人们不再为自己生产产品,“没有一个资本家是为了消费自己的产品而进行生产的”。马克思注意到,如果为他人生产产品,就可能存在买和卖的脱节:“危机的可能性在于卖和买的彼此分离。”因为出卖商品的人会遇到困难。“已经卖掉了商品而现在持有货币形式的商品的人并不是非要立刻重新买进、重新把货币转化为个人劳动的特殊产品不可。”
如果手里面有货币的人并不着急买进产品,而是把货币储存起来,延缓使用。这就给下一步支付带来了压力。“卖者——假定他的商品具有使用价值——的困难仅仅来自于买者可以轻易地推迟货币再转化为商品的时间。”同上,第581页。一旦他推迟了消费的时间,就可能引发连锁效应。因为“不仅是因为商品卖不出去,而且是因为商品不能在一定期限内卖出去,在这里危机所以发生,危机所以具有这样的性质,不仅由于商品卖不出去,而且由于以这一定商品在这一定期限内卖出为基础的一系列支付都不能实现”。同上,第587页。一系列支付不能实现,债务链条被干扰,就会引发信用危机,进而出现经济危机。因此,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流通包含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买和卖的分离以及支付连锁关系的破坏。但是这是资本主义爆发危机的可能性。
马克思也提到资本主义企业平均利润率下降也会导致危机。因为如果企业获得的利润率呈下降趋势,这会给资本家带来负面影响。利润减少抑制了资本积累,进而导致投资不足。投资不足会引发经济低迷,最后导致危机。
跟投资相关的是产业后备军的变动,当资本主义在经济活跃期,企业规模扩大,对劳动力需求增长。资本家吸纳了产业后备军,失业者减少,这会导致工资提高。而工资提高会减少资本家利润,进而抑制积累,并导致投资不足,投资不足也会导致危机。马克思指出:“现代工业特有的生活过程,由中等活跃、生产高度繁忙、危机和停滞这几个时期构成的、穿插着较小波动的十年一次的周期形式,就是建立在产业后备军或过剩人口的不断形成、或多或少地被吸收、然后再形成这样的基础之上的。”
马克思还关注到资本主义危机的一个结构性原因,这个原因被后来的学者所不断地、反复地强调,就是“生产相对过剩”。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伴随着两个过剩,第一是产能过剩;第二是人口过剩。事实上,在马克思看来,正如人口是相对过剩,产能也是“相对过剩”,因为贫困的民众没有购买能力。在经济危机期间,你会发现企业家将卖不出去的产品销毁,这让人感觉出现了“生产过剩”。“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经济增长悖论”不仅表现为经济增长同时,相对贫困和社会分化加剧;同时也表现为巨额物质财富增长同时,社会购买力却在相对减少。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竞逐剩余价值,在生产过程中,需要降低工人工资以降低成本;但在消费过程中,高工资却有助于剩余价值的实现,因为高工资意味着更多的购买力。从个体资本家角度来看,理想解决方案是:压低自己雇佣工人工资,但鼓励其他资本家支付高工资,让自身生产的产品有旺盛市场需求。然而,如果所有资本家都试图耍这样的小聪明,结果就不妙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资具有双重作用——工资既是生产成本,也是需求来源。资本主义剥削形式,就其本质来说,其强度会超过以往剥削社会。高强度剥削导致民众生活贫困化,资本主义产能过剩会格外严重。
马克思则认为:“生产过剩”这个词有误解。“只要社会上相当大一部分人的最迫切的需要,或者哪怕只是他们最直接的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自然绝对谈不上产品的生产过剩。”2008年11月,美国经济危机爆发初期,科罗拉多州一对农场主夫妇宣布:任何人都可以来农场拿走他们采收之后的剩余蔬菜。让他们意外的是,超过4万人来到农场,把地里剩余蔬菜摘得一干二净。马克思强调,看似过剩其实是工人买不起这些产品。“生产能力的过剩同支付能力的需要有关。这里涉及的不是绝对生产过剩。”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无产者没有支付能力,缺乏消费能力。由于资本家尽最大限度地榨取工人剩余价值,工人所得的经济份额太低,难以形成有效购买力。马克思指出:“发生生产过剩的时候尤其令人奇怪的是,正是充斥市场的那些商品的真正生产者——工人——缺乏这些商品。”
而获得利润,有消费能力的资本家会大肆消费吗?不会!“只有在越来越多地占有抽象财富成为他的活动的唯一动机时,他才作为资本家或作为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执行职能。因此,绝不能把使用价值看作资本家的直接目的,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在这场谋取利润的无休止运动中,资本家不是好的消费者。按马克思的理解,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不仅最大限度地榨取工人剩余价值,他自己也会尽最大可能积累资本,扩大生产规模,以期在竞争中获胜。因此,资本家是为他人生产,自己却不怎么消费。从长期来看,资本家会把他们结余下来的剩余价值全部用于投资。在资本主义经济里,投资是资本家的功能,为了积累而积累,为了生产而生产。资本主义制度迫使资本家积累。资本家为了在竞争中生存下来必须积累。资本家会不断扩大生产,“按照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也就是按照用一定量资本剥削最大量劳动的可能性)进行生产,而不考虑市场的现有界限或有支付能力的需要的现有界限”。因此,这里就出现了“生产相对过剩”。“它们的生产过剩之所以成为生产过剩,仅仅因为会出现相对的,或者说,被动的生产过剩的那些物品存在着生产过剩。”
资本家不断扩大生产规模,而工人的购买力却在缩减,资本家自身又不是好的消费者。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资本愈增殖,它就必然更加盲目地为市场生产,生产愈益超过了消费,供应愈益力图扩大需求,由于这一切,危机的发生也就愈益频繁而且愈益猛烈”。“生产相对过剩”的一个表现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不断攀升的家庭负债率。在1964年到1984年间,美国家庭负债占税后薪资比例稳定在66%左右;在2008年经济危机前夕,这一数据上升到134%。2013年的第一季度仍然有112%。低储蓄、高负债导致家庭难以形成有效购买力。而危机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不顾民众支付能力,无限扩大生产;单个企业管理得井井有条,而整个社会生产则陷入无政府状态。
按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不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力,因此,经济危机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体现。“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重复中越来越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资本主义不仅是剥削的、异化的,还是自我毁灭的。资本主义周期性的危机将触发革命。
在危机中无产者深受苦难,他们会组织起来反抗资本家,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不仅如此,不少资本家破产,沦为无产者,憎恶资本主义的人会越来越多。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无产者会日益壮大。“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反抗也不断增长。”最终,人类社会会拾级而上,走向共产主义。在19世纪中期的欧洲,马克思与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就指出: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事实上,马克思预言的革命在俄国、中国等国家爆发了,而在他寄予厚望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要么迟迟没有爆发,要么没有取得足够成功。如果要解答这一现象,需要看当代资本主义有哪些变化,延缓了革命爆发。
我们知道,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已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有较大差别。当代资本主义技术工人增多,工人主体已不再是蓝领工人。技术工人获得的工资更高,工作更有保障。在20世纪70年代,“新阶级”开始出现了。部分美国劳工变成白领工人,成为“专业管理阶层”“受教育阶层”“知识阶层”“创意阶层”。他们居住在纽约郊区、费城、波士顿、芝加哥、西雅图、洛杉矶、硅谷等地,大部分居住在城市郊区。这些人成为科学家、工程师、科技企业的高管、律师、学者。他们积极支持平权运动,关注环境问题,重视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他们的需求和传统蓝领工人显著不同。此外,“经理革命”的出现,让那些不是资本家,而有卓越管理才能的经理人在掌控公司,领取高薪。资本主义社会阶层或许不是单单的无产者与有产者,社会阶层在变得多元化。此外,有两个方面的政治变化也值得我们注意:资本主义国家“国家自主性”的变化和工会作为政治力量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首先,国家是否能调节资本主义矛盾?马克思告诉我们,要让政府来纠正资本主义体系的错误是根本不可能的。国家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代理人,不可能成为社会不同成员之间冲突利益的仲裁者。因此资本主义根本无可救药。而有学者注意到,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获得了“相对自主性”。他们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短期利益的代理人,而成为长期与全局利益的代理人。为维护资产阶级长远统治,资本主义国家需要调和矛盾。美国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在麦金利遇刺后意外就任美国总统。他运用国家力量,积极限制资本集团影响政治的权力。1902年,宾夕法尼亚煤矿工人举行罢工。罗斯福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调解劳资矛盾。强大的煤矿主坚持动用军队来对付矿工。罗斯福的做法与以往总统大相径庭。他考虑派遣军队从矿主那里夺取矿山,重新开矿。此前没有任何一位总统威胁使用军队来反对大公司。而西奥多·罗斯福有效运用国家权力,抑制了资本集团强大力量。
在20世纪30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第二次就职演说常被称为“三分之一演说”。他指出:我看到国家三分之一的人口住得很差、穿得很差、营养很差。他传递出这样的信息,要帮助美国穷人与工人。罗斯福“新政联盟”(New Deal coalition)的核心成员是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集团、投资银行和面向海外的商业银行。由于这个资本集团的用工成本低,他们积极团结崛起的劳工以赢得政治竞争。1935年,纽约州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Robert Wagner)倡导的《全国劳工关系法案》(National Labor Relation Act,即《瓦格纳法案》)通过。虽然罗斯福对该法案并不满意,但他最终还是在法案上签字。这主要是因为在1935年,美国劳工已成为一股强大力量,罗斯福意识到自己的政治前途有赖于劳工支持。该法案承认工会享有集体谈判等权力,保障工人结社自由,宣布罢工不受干扰,要求雇主承认工会。在美国历史上,劳工第一次获得了联邦政府实质性的支持。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案》获得了罗斯福的公开支持。该法案第一次为全国老年人建立退休金,对残疾人及幼童予以救助,为失业者提供救济。该法案在“二战”结束后仍发挥影响,美国对贫穷人口及社会福利的支出从1950年的350亿美元上升至1964年的1080亿美元。
在不少时候,资本主义国家具有“相对自主性”,不再被资本家俘获,起码不是完全俘获。马克思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改造了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在面临挑战的时候开始积极行动,推动建立社会福利制度,缓和阶级矛盾。资本主义国家也纷纷采用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尝试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也是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相对过剩”问题。北欧国家“统合主义”(corporatism)资本主义模式,更是让国家发挥更为重要的协调作用,把资本家与工人的利益进行统合,促成阶级矛盾缓和,实现经济长远发展。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在调和阶级矛盾上,开始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其次,工会等工人组织开始积极发挥政治作用。马克思在早年即指出工人阶级会走向贫困化。作为无产阶级贫困化的一个后果,就是福利开支减少,工人平均身高下降。在19世纪,资本主义国家福利支出有所下降。在1820年,福利支出占资本主义国家GDP的2%,达到峰值。在这个世纪的剩余时间里,资本主义国家福利支出日益下降,占GDP比重降至不足1%。不过步入20世纪以后,社会福利在资本主义各国以不同形式逐步普及推进。此外,从1830年到1860年,英国工人平均身高的确下降了,这是当时工人生活水平下降的一个体现。但随后,英国工人的身高却开始增高了。这是因为1850年到1865年,英国工人阶级实际薪酬涨了17%,全职工人平均工作时间也在逐渐减少,1856年为65小时,到1873年缩减为56小时。在马克思撰写《资本论》期间,英国工业生活水平提高了,1865年到1895年,英国工人生活水平提高了50%。因此可以说,马克思选择英国作为其研究资本主义的对象是选取了典型案例,但是在选取工资变动的产业时,却可能选取了非典型案例。那一时期,英国典型产业的工资在缓慢上升,而不是下降。马克思指出:“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而工会作为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在日益崛起。因为工会出现,工人工资开始上升,工人健康水平和寿命得到提高。的确,工人阶级所得到的相对份额减少,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差距扩大。但是工人获得的绝对份额在逐步增加。相对份额是否如此重要?贫富差距的扩大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相对剥夺感”,但是正如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在她的著作中展示的,这样的“相对剥夺感”却未必带来革命。
不过就美国而言,社会福利、工会作用在近几十年又有新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有三分之一的美国工人加入工会,而现在的工会会员只占工人总数的九分之一。在美国私营部门,20世纪70年代,工会会员占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一;而到了2010年,这一数字为7%。美国劳动者加入工会的比重在1960年的时候为30%;到1984年变为20%;到2014年,降至11.1%。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历“去工业化”转型,工会受到削弱。由于缺乏工会制约,美国近几十年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社会矛盾加剧。
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平均利润率下降、资本集中、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周期性的经济危机——马克思所展示的这些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是否存在,在多大程度存在本身就存在争议。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其他阵营的学者都可以找到支持与反对证据。即便使用“科学”手段,在研究社会问题时,不同视角常常会找出不同证据,得出不同答案。
总的说来,以往的政治经济学是以“个体”为中心,而马克思引领了政治经济学一个新视角,即以“阶级”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