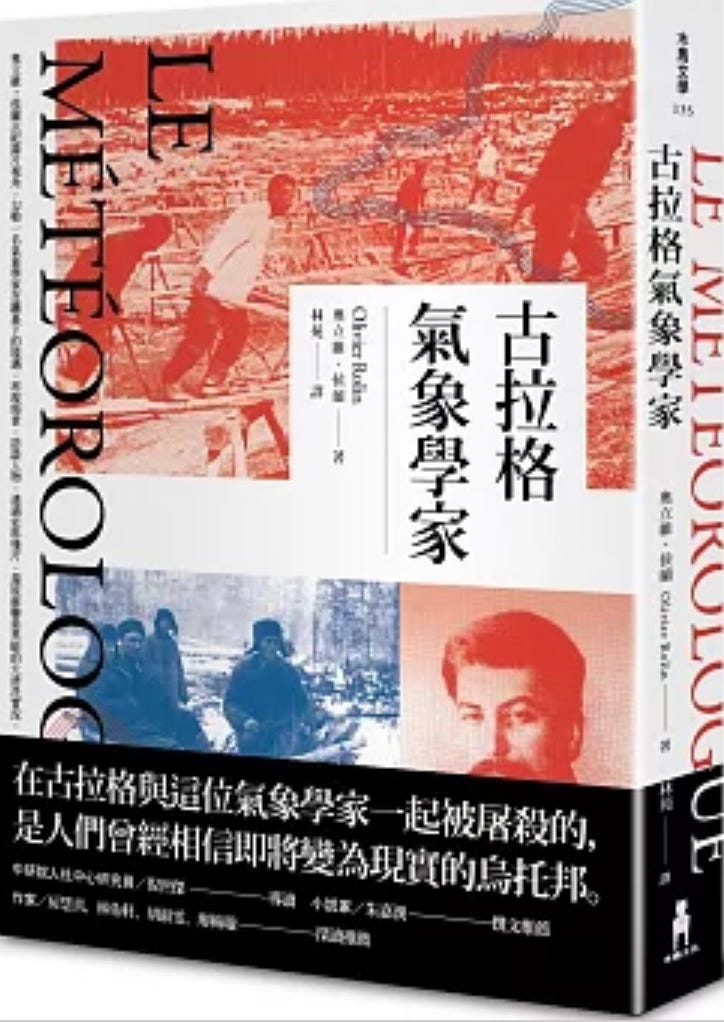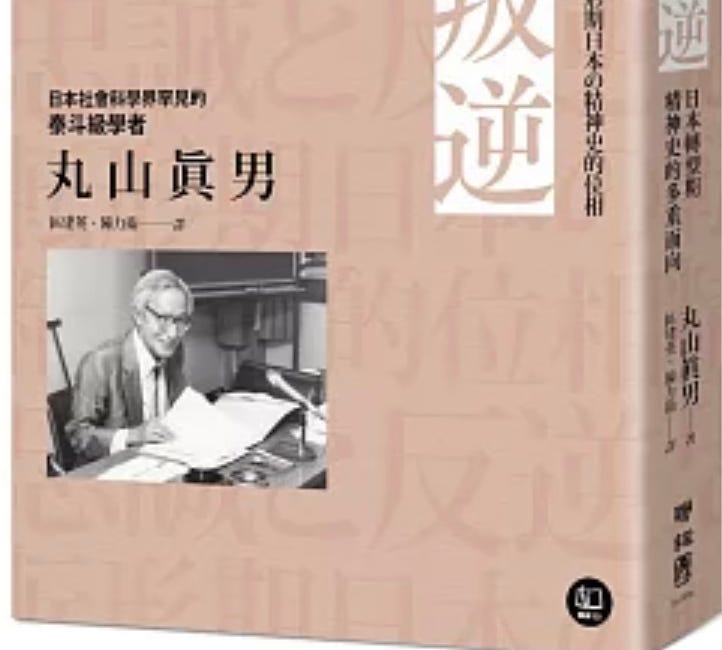倪世傑 | 見證紅色恐怖――屬於全人類的古拉格記憶
編者按:史達林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那段相對平和的日子所進行的「大清洗」,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歷程,這些受難者在勞改營中,又是如何度過人生的最後歲月。本文為《古拉格氣象學家》導讀,作者倪世傑授權刊發。
對當前中壯年以上的台灣民眾而言,「古拉格」並不是一個陌生的名稱。榮獲一九七○年諾貝爾文學獎桂冠、知名的蘇聯政治異議作家索忍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於一九八二年訪台並於中山堂發表公開演講,其大作《古拉格群島》一書中譯本(聯經)同時於台灣出版,蔣氏統治集團的「反共大業」在台灣又獲得新的能量。極其弔詭的是,在後美麗島時期的台灣,「古拉格」反倒給予主張「反共復國」的國民黨政權新的正當化基礎,而當時有「台灣古拉格」之稱的火燒島,仍長期關押著一群分別支持台灣獨立自決以及回歸紅色祖國的政治犯。無獨有偶的是,當時執政黨已落入遲暮的蔣經國總統之手,他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三七年間曾留學蘇聯並在當時成為堅定的共產主義者,也是史達林時期「大清洗」的親身見證人,卻也操刀戰後台灣社會的大清洗。二十世紀上半葉是帶著血腥味的意識形態恣流的年代,杜聰明、郭琇琮、呂赫若這一代知識分子的不幸遭遇與運命,與《古拉格的氣象學家》一書中的主人翁范根格安姆(Alexei Feodosievich Wangenheim,1881—1937)的最後遭遇竟是相當雷同的:皆堅信社會主義為人類前途之所繫,但前者被白色恐怖連根拔起,後者則是命喪於史達林的紅色恐怖。
《古拉格的氣象學家》這本書是由獲得多次文學獎的法蘭西作家侯蘭(Olivier Rolin),根據范根格安姆在集中營三年中寫給妻子瓦爾瓦拉(Varvara Ivanovna Kurguzova)與女兒艾萊奧諾拉(Eleonora Wagenheim)的信件為基礎,進行多次的社會調查後,從紅色恐怖被害者的角度,認識史達林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那段相對平和的日子所進行的「大清洗」,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歷程,這些受難者在勞改營中,又是如何度過人生的最後歲月。
誰是范根格安姆?
范根格安姆,出生於一八八一年沙俄時期烏克蘭的富農家庭,曾經擔任過沙皇時代的軍人,但同情列寧發動的十月革命。他是蘇聯首位水文氣象局局長暨蘇維埃人民委員會水文氣象委員會主席,著手建立蘇聯的水文、日照與風力等氣象檔案,為這片覆蓋世界陸地面積六分之一的大國建立氣象情報網,一個終身信奉蘇共以及社會主義的先進性的共產黨員,一生的志業是將社會主義建設搞到天空上去。
對蘇聯而言,范根格安姆對氣象的研究應用範圍相當廣泛,從明天衣服該怎麼穿的天氣預報、挑選適合撒種耕種的日期、引導飛機起降,從民生到軍事無一不包。一九三二年他組織了一個探討氣候對人類影響的會議,探討氣候對健康與城市規劃,在當時絕對是舉世創舉;一九三三年九月底,也就是他遭到逮捕的前一年,蘇聯的USSR-1(書中作URSS-1,為法文)平流層高空氣球成功升到了近十九公里高空的全球創舉中,也有賴臨危授命的范根格安姆調教偵測儀器,完成這一項絕對「超英超美」的任務。
這麼一位忠誠於蘇共與勞動群眾利益的科技文官,卻於一九三四年底遭到逮捕,與眾多貴族、大主教、知識分子以及其他來自世界各國卻不服從史達林的共產黨人,在臨近北極圈的索洛維茨基(Solovki Island)的古拉格共度人生中最後一千個日子。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的槍響中,1110位當時的社會菁英,一齊劃下人生的終點。在索洛維茨基強制勞動的期間,范根格安姆,這位在艾萊奧諾拉生命中缺席的父親,孜孜勤勞地通過天象與小動植物為內容的插畫,以及一些讀來無甚有趣的小謎語,「遠距」教育著千里之外女兒。其後成為生物學者的艾萊奧諾拉終身未嫁,並於二○一二年自盡。在她走向生命盡頭前,終身無法釋懷的是遭遇如此待遇的父親,在生命即將逝去之際,為何還能繼續忠誠於這個殘酷無情的史達林以及社會主義建設?
史達林的大清洗
侯蘭指出,范根格安姆之所以被殺害,遠因是其富農家庭的背景以及一個曾經投身「白軍」而流亡的兄弟,終因是為一九三二年的大饑荒充作「氣候預測失誤」的替罪羊,近因則是在其上級的單位「人民土地委員會」中查獲「反革命分子」而受牽連招致其禍。這段歷史,眼尖的讀者不難與「延安整風」、「文化大革命」聯繫起來。的的確確,史達林時期對國內的高壓統治絕對可以「國家恐怖主義」加以定性。
回到後列寧時代的蘇聯政治發展,吾人就比較能夠理解這個宛如「溫水煮青蛙」的政治過程。自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三年間,俄羅斯內部發生紅軍與白軍爭奪國家政權的內戰,白軍為農村與西方國家所支持,范根格安姆的身分,相當程度種下了他不被蘇聯高層信任的因子。再來是一九二八至二九年強調發展重工業的第一個五年計畫,這就需要從農村榨取經濟剩餘,政府用低價向農民購買農產品,一方面供應城市無產階級需要,另一方面出口賺取外匯購買工業器材。去富農化運動(Dekulakization)與農業集體化同時進行,那些被指為國家敵人的富農――其實大多為不支持農業集體化的小農――人數高達二百餘萬人,直接強制遷移到西伯利亞、烏拉山、中亞的加盟共和國等荒地進行五年計畫中的「大墾荒」工程。但也因為生活艱困,逃跑者所在多有,在都市中行乞或幹起盜匪的勾當,形成嚴重的社會問題。同時,農村勞動力一方面陷於短缺,另一方面農民抵制集體化,導致農業生產效率低落,因而造成了一九三二年的大饑荒。造成這場大饑荒的原因與一九六○年代中國「大躍進」下的三年饑荒異曲同工,並不是如莫斯科與北京宣稱的「三年自然災害」。
自一九二七年開始,蘇共當局開始界定「有害社會成分」,並將因此被界定為「壞分子」的民眾送往各地的古拉格從事強迫勞動。隨著農業集體化觸礁,有害社會成分的內容益發擴大化,這包括不服從農業集體化政策的農民,都市中的流浪者與罪犯、政治上的不同意見者,而最惡名昭彰的是擴大到其他國內少數族裔群體,投射出蘇共擔憂國外資本主義勢力滲透而引發的仇外情緒。蘇聯境內的吉普賽人、庫班—哥薩克人、德裔、波蘭裔、芬蘭裔以及朝鮮裔都在發配中亞與西伯利亞的行列,甚至到了一九三七年夏,將近七十萬名德裔與波蘭裔民眾直接被處決。
國家恐怖主義下的政治文化
國家恐怖主義的受害者究竟還能夠做些什麼?侯蘭本人其實相當期待在范根格安姆與其妻來往的信件中發現他批判黨或領導人的蛛絲馬跡,但是每次都讓他失望了。即便他也知道他寫給史達林等黨高層的陳情信皆石沉大海,似乎亦無損於范根格安姆對黨領導人以及社會主義的未來所抱持的強大信心。有鑒於他明確地表明「在最初幾個月他們拿家庭安全威脅我的時候」,我們可以推測他不斷對黨表忠,可能是出於保護家庭安全的需求,但我們也不能否認,野心勃勃的蘇聯相較於過去的帝制,確實給予像是范根格安姆等科技菁英一展長才的機會,而他也確實獲得了這個機會。
然而,那個時代的范根格安姆們可能更專注於如何建設這個偉大的新國家而忽略了政治局勢。在一九二○年代內戰後到農業集體化前的短短幾年,史達林政權確實還未達成中央集權,但從以上提到的大規模且有目的性的人口移動中不難看出這個政權的殘酷性格,除非,范根格安姆們對這些大規模的人口移動以及伴隨而來的污名化均視而不見,直到黨/國家機器直接找上門,才知大禍臨頭?於一九一八年逝世的俄羅斯革命家普列漢諾夫(Georgi Valentinovich Plekhanov)生前雖未能目睹史達林上台,但他卻早已預見了史達林主義的橫空出世。即便缺乏經驗證據,但他判斷在經濟不發達地區的社會主義政權為了組織生產,往往變質為父權制與威權制的共產主義,在這底下,則是羸弱的工人階級以及對政治冷漠的民眾。由於計畫經濟需要方方面面的專家與科技人員的估算與預測,使得專家與科技人員在之後蘇聯內政治地位與權力大幅提升,甚至形成「新階級」,但這終究是後話,范根格安姆們其時或是出於對政治的冷漠,或是無視於新形成的壓迫結構,又抑或是更等而下之的,服膺黨的領導下的忠誠,最後都讓自己成為獨裁政權的俎上肉。馬丁.尼莫勒牧師(Martin Niemöller)在波士頓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碑所提的銘文,不偏不倚地為范根格安姆們的命運下了最佳的註腳。
身繫鐵幕的氣象研究者,通過沒有國界的大氣與水文,在包覆以恐懼的極權政治鐵蹄下想像著某種從未真正擁有的自由,然而,在當年的史達林統治期間,所謂的資產階級自由與人權觀念在這片廣袤的土地上是相當稀缺的,所存在的僅僅是隨著農業集體化而來黨國權力的恣意擴張,而史達林的暴力統治,隨著他於一九五三年三月亡故後暫時劃下句點,繼任的赫魯雪夫同樣殘暴地處決了貝利亞,但因為貝利亞作為史達林鷹犬的惡行劣跡為人深惡痛絕,赫魯雪夫此舉反而獲得民眾支持,與史達林大相徑庭,「修正主義者」赫魯雪夫以開明的形象贏回蘇聯民心。范根格安姆的案子在赫魯雪夫批判史達林的蘇共二十大後獲得平反,而古拉格的殘虐暴政,卻直到一九九一年民主化之後政府祕密檔案公開,方得以有機會重建天日。
古拉格的現在進行式
過去歷史留下的傷口,在二○一九年的今天看來卻格外諷刺。在二○○四年「顏色革命」漸次發生之後,同樣以防範西方國家為由,普丁總統展開恢復俄羅斯大國光榮為內涵的國族再締造工程,威權主義的作風取代了一九九○年代曇花一現的自由民主。當前的俄羅斯甚至出現了一股懷念史達林的風潮,位於莫斯科的列瓦達民調中心(Levada Center)二○一九年四月的民調指出,高達70%的受訪者表示「史達林的統治對國家是好的」,對史達林任內的壓迫,持正面與負面態度者分別為46%與45%。俄羅斯社會學者琵琵雅(Karina Pipiya)認為這個現象反映的是經濟表現不佳、民眾生活水準倒退的當今俄羅斯,在「偉大的護國戰爭」中獲勝的史達林是一個能夠喚起大國光榮感的對象,而且愈來愈多的青年人對史達林抱持好感,即便他們出生的時候紅色政權就已經倒台了。
史達林並未真正的死去,他極度擴張國家權力、踐踏少數族裔群體與基本人權的極權主義政策風格在諸多國家都仍持續進行著。當前一股反自由主義的威權主義――無論其名為極右派、極端民族主義還是民粹主義――在世界各地都出現復甦的跡象。在歐洲,極右派政黨在許多國家都站穩了腳跟,傳統的保守派政黨言論與政策往極右派挪移的跡象甚明。當前世界兩大強國更是毋須多說,美國川普總統將非法移民的子女集中化管理,而中國的新疆更活脫是維吾爾族的大型集中營。
「古拉格」看似殷鑑不遠,但卻又已明目張膽地捲土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