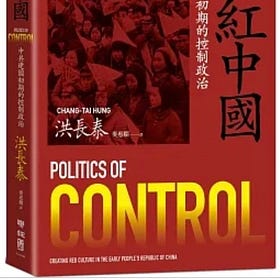羽戈 | 用鲁迅杀人
編者按:“过分在气节上求全生活在那个苦难时代的知识分子,都不免是为那个残暴的政权在作开脱。”
《鲁迅的最后十年》,林贤治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10月第一版
为鲁迅先生立传的人数以百千计,最得我心者,除了竹内好,便数林贤治。他人写鲁迅,将其当作客体,作者是作者,鲁迅是鲁迅,两者之间泾渭分明;林贤治写鲁迅,则将其当作主体,作者与鲁迅,简直要不分彼此,合二为一,甚至只见鲁迅,不见作者。林著《人间鲁迅》,上下两册,将近千页,虽是第三人称,却可作鲁迅的自述来读。能使鲁迅在纸上复活,不仅需要思想的相通,更需要风骨的相通。画虎画皮难画骨,写鲁迅,若无风骨支撑,便难以临摹其俯首背后的横眉、绝望背后的悲悯。这一点,恰是林贤治的擅长。他们相通到什么程度呢,我看林贤治近年来的肖像,竟有了一些晚年鲁迅的气质。
说林贤治酷肖鲁迅,于他而言,无疑是最大的赞美。他对鲁迅的传承,不止传承了鲁迅的优点,还传承了鲁迅的缺点。因此有人讥讽他是鲁迅的“凡是派”:“凡是鲁迅赞成的他都赞成,凡是鲁迅反对的他都反对,凡是赞成鲁迅的他都赞成,凡是反对鲁迅的他都反对。”对此他的态度十分坦然:“朋友告诉我,说有一位海上批评家说我是鲁迅的‘凡是派’,问我意下为何?我回答说荣幸之至,只是愧不敢当。”
“凡是派”的立场,之于林贤治的鲁迅写作,可谓利弊参半。像《人间鲁迅》这样的文学创作,“凡是派”的爱憎分明、一往情深,正有助于林贤治进入并呈现鲁迅的精神世界;如《鲁迅的最后十年》这样的学术研究,“凡是派”的偏执与狭隘,则阻碍了林贤治认知并解剖鲁迅生命最后十年的政治与文化生态。质言之,文学需要激情,学术需要客观,“凡是派”得之于前而失之于后。林贤治是优秀的作家,却未必是优秀的学者(当然林贤治从不以学者自命,而对学者的称号颇为鄙夷,对学院的生态相当厌恶)。
《鲁迅的最后十年》一再重印,足见风靡。从初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03年)到最新一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这十八年来中国的变迁,固然不比“鲁迅的最后十年”(1927-1936年)那般波澜壮阔,天翻地覆,却也是暗流汹涌,于无声之中酝酿惊雷。林贤治写此书,立意不止在历史,还有影射现实之意,连书中的留白都充满了反讽的气息(不妨说,此书诸多论调,相比历史,毋宁更适用现实)。不过,而今蓦然回首,只怕他要失望了:此书谈论的主题,如“书报审查制度”、“自由与人权”、“专制与改革”,十八年来现实并无显著进步;作为主角的鲁迅,所受冷遇、贬损、废黜更甚往日……
“凡是派”的教条主义僵化了历史,影射史学的实用主义扭曲了历史,这二者,决定了《鲁迅的最后十年》必将陷入重重争议。在我看来,此书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出在鲁迅身上(林贤治试图以一个自由的鲁迅,来对抗被权力禁锢的鲁迅,然而鲁迅始终被供在高不可攀的神龛之上,不曾回归人间,自由趋向极端,同样是一种神化),而出在了鲁迅的批判对象身上:一是国民党,二是胡适。
此书第一章名曰“国民党‘一党专政’”。林贤治竭力论证国民党反自由、反民主,是一个极权主义政党,蒋介石是一个大独裁者等,以环境的险恶、敌人的凶残,反衬鲁迅战斗的无畏、风骨的嶙峋。他的论据都是什么呢,如“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口号。拿口号来立论,正折射了林贤治的颟顸。因为口号之为口号,尤其政治口号,一在欺人,二在自欺,无足为凭,何以为证。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林贤治竟混淆了口号与行动、理论与现实,或者说应然与实然。纵使国民党企图成为一个极权主义政党,事实则是,从其诞生,至今百年,它从不曾具备极权主义一半以上的特征;纵使蒋介石企图成为大独裁者,事实则是,如其对手所嘲讽的那样:“民主无量,独裁无胆”(需要注意,独裁并非胆量的问题,而是能力的问题),哪怕在其权力巅峰,却不过是“弱势独裁”。反观历史,在“鲁迅的最后十年”,中国四分五裂,国民党内忧外患,谈何一党专政,谈何极权,谈何独裁?要知道当时国民党最大的问题,不是独裁,而是不能独裁。更不难想见一点,假如那十年的国民党诚如林贤治所论,鲁迅的命运必遭改写,在真正的极权之下,怎么可能容忍鲁迅式的写作呢,他的归宿,不是沉默,就是入狱,生于1948年的林贤治可谓过来人,对此应有明鉴。一言以蔽之,倘若国民党极权,蒋介石独裁,就不会出现“鲁迅的最后十年”;恰因存在“鲁迅的最后十年”,则可反证国民党不够极权,蒋介石不够独裁。所以说此书自打开篇,便陷入一种自相矛盾、自我解构。
如果说林贤治对国民党的误判,可以归结于现实的焦虑,那么他对胡适的贬斥,只能归结于自身的狭隘。此书第三章“自由与人权”,以胡适观照鲁迅,把二人强行对立,诸如这样的结论:“承认还是不承认现存的政府和法律,承认还是不承认奴隶——政府称之为‘公民’——反抗专制压迫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是鲁迅和胡适们的分歧的根本所在。”此言貌似深刻,可惜只说对了一半。胡适的确承认“现存的政府和法律”,主张在体制之下、现状之上渐进改良,然而他什么时候否决了公民“反抗专制压迫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呢,须知反抗者不止鲁迅一人,反抗的方式,不止鲁迅一条,胡适何尝不在反抗,而且极具杀伤力,否则就不会导致《新月》六七号合刊和《人权论集》被查禁,中国公学校长一职被迫辞去。鲁迅的朋友(鲁迅书信集中,有二十五封半致曹聚仁)、写过《鲁迅评传》的曹聚仁说:“胡适的处境在那时期,并不比鲁迅更自由些。”可为注脚。
以胡适衬托鲁迅也好,以鲁迅鄙薄胡适也罢,林贤治的思维,还是二元论,使鲁迅与胡适构成了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关系。我早说过,二元思维作为一大病毒,十分流行,看来连林贤治都不能幸免;一旦感染,其论点便无足观。因为鲁迅与胡适之间,绝非针锋相对,势不两立,若譬之为两条线,他们不是平行的直线,反而时有重合;况且那十年间中国的反抗者,不止鲁、胡二人,就像这世间的颜色不止黑白,人心不止善恶,倘你眼里只有二元,则只能看见一个一元的世界。从思维上讲,一元的终点是专制,多元的终点才是自由。
林贤治心中的一元,便是鲁迅,他的一元论,便是唯鲁迅论,把鲁迅塑为几近完美的标杆,藉此横扫天下,推倒一世豪杰。在鲁迅的辉光之下,胡适沦为奴才,乞求政府施与自由;陈寅恪沦为“文化遗民”,其气节仅在于守旧,而无关开新,所张扬的是“一种没落的士大夫情调”,所演奏的是一首“唱给旧文化的深情挽歌”……这样的道德批判,遍布林著,诚可谓鲁迅遗风。
鲁迅的风骨,怎么弘扬都不过分。然而风骨,以及气节、道义等,用途在于劝勉,而非责难。所谓不以大义责人,你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成为伯夷叔齐,成为文天祥、方孝孺,成为鲁迅、胡适。道德批判的意义,不在抬高上限,而在维护下限,捍卫人之为人的良知与尊严,使人类不至沦为奴隶、禽兽;换言之,成为一个人,并不意味着要成为圣贤,成为英雄,成为斗士。倘把上限降格为下限,道德批判便可杀人。
这不是危言耸听。可以史为鉴。1949年后,留守大陆的冯友兰备受政治批判,屡作“自残、自践、自辱式”的检讨和自我批评。1950年8月,在印度讲学的张君劢读到冯友兰《学习与错误》,遂撰《一封不寄信——责冯芝生》,刊于香港《再生杂志》,信中责备冯友兰“不识人间尚有羞耻事乎”,“足下读书数十年,著书数十万言,即令被迫而死,亦不失为英魂,奈何将自己前说一朝推翻,而向人认罪?”虽倡以大义,却满纸杀气腾腾,不啻用名节杀人,逼冯友兰舍生取义。
同理,林贤治批判陈寅恪,对于1949年后陈寅恪的一些表态,以及“晚年唯剩颂红妆”等,非但不予体谅,反而横加苛责,以“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的名义,以鲁迅所云“战斗者”的名义。他却不去想,假如将鲁迅置于晚年陈寅恪的语境,该当如何?只要坚持战斗,不管怎样深沉、韧性,结局终不免一死,而且极有可能是横死。就此而言,以三十年前的鲁迅批判三十年后的陈寅恪,可谓杀人之举。痛斥“文化移民陈寅恪”的林贤治,最该倾听周质平的告诫:“过分在气节上求全生活在那个苦难时代的知识分子,都不免是为那个残暴的政权在作开脱。”(周质平《气节与学术——论冯友兰的道术变迁》)
書訊:
染紅中國:中共建國初期的控制政治
染紅中國:中共建國初期的控制政治 Politics of Control: Creating Red Culture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作者: 洪長泰 譯者: 麥惠嫻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23/07/13 語言:繁體中文 內容簡介 深度解密「紅色文化」管控系統 全面剖析中共精心布局的控制手法 榮獲美國圖書館協會期刊《Choice》評選為 ★ 2022年傑出學術書籍 ★ 要鞏固政權,先操縱文化! 全面洞悉中共染紅人民的文化控制大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