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特朗普就任之後,和哈佛大學的關係越來越緊張。先是凍結哈佛近40億美元聯邦研究資金,並計劃終止約1億美元聯邦合同,理由包括反猶太主義、校園暴力及與中國共產黨的合作。此後發文要求哈佛8月前進行學術項目審計、改變招生和招聘政策,否則面臨進一步制裁。哈佛校長Alan Garber拒絕,稱此為對學術自由的攻擊。而最近,5月22日,國土安全部(DHS)宣布終止哈佛的「學生與交流訪問者計劃」(SEVP)認證,禁止哈佛招收國際學生,影響約7,000名學生(佔學生總數27%),包括超過1,000名中國學生。哈佛提起訴訟,5月29日波士頓聯邦法院法官Allison Burroughs發出初步禁制令,暫時阻止禁令。然而,同一天,DHS再次施壓,理由包括持續的反猶太主義行為和與CCP的合作。在哈佛許多師生看來,哈佛的管理、招生和言論自由等方面確實存在問題,而且也需要改革。但是,無差別針對所有國際留學生,哈佛會變好嗎?美國會更偉大嗎?然而在這敏感時刻,哈佛卻在有著”中共海外黨校“之稱的肯尼迪學院,找一位學鍍金專業的”紅二代“來做畢業生演講呢?穿著珠光寶氣的刺繡雲肩學士服,空洞談著”人類命運共同體“,這真是讓人想為國際留學生說一句話,卻欲辯無能。
5月29日週四,哈佛大學舉行了第374屆畢業典禮,慶祝2025屆畢業生的成就。典禮於上午9:30在哈佛園(Harvard Yard)的Tercentenary Theatre舉行,由校長艾倫·加伯(Alan M. Garber)主持,醫生兼作家亞伯拉罕·維爾蓋斯(Abraham Verghese)發表主旨演講。在典禮期間,約24人在哈佛廣場抗議川普政府對哈佛的行動(如資金凍結和國際學生禁令)。一幅寫有“Harvard Divest from Genocide in Gaza”的橫幅在Sever Hall短暫展示,隨後被警方移除。校外有卡車展示標籤“哈佛主要反猶分子”的照片,反映校園內部關於反猶太主義的爭議。
幾乎同時,距離校園8公里的波士頓聯邦法院正在舉行聽證會,法官Allison Burroughs延長臨時命令,阻止川普政府禁止哈佛招收國際學生,典禮現場對此消息爆發歡呼。
根據Reuters報導,此案源自川普政府對哈佛的壓力,包括凍結近40億美元聯邦資金和限制國際學生招生。聽證會的焦點是川普政府試圖立即撤銷哈佛招收國際學生的權利,影響超過7,000名學生,其中哈佛肯尼迪政府學院近60%的研究生為國際學生。Burroughs法官於6天前(5月23日)發出臨時限制令,阻止川普政府的行動,29日的聽證會則決定是否延長此命令。
最近,哈佛一直處於風口浪尖之上,哈佛的師生如何看哈佛和川普之間的爭鬥呢?在過去一個月(2025年4月29日至5月29日),哈佛教授在媒體上發表了多篇有關哈佛的評論,特別是針對與川普政府的衝突和校園政策,這些評論主要出現在《紐約時報》、德國《法蘭克福匯報》和X平台,涉及哈佛的學術自由、內部治理和外部壓力。
1 Steven Pinker的評論:Harvard Derangement Syndrome (《紐約時報》2025年5月23日。
Pinker作為哈佛心理學教授,擁有22年教職經驗,批評對哈佛的批評過於激烈,缺乏根據。他提到自己在2014年和2023年的文章中已呼籲哈佛改革,如透明的錄取政策和自由言論承諾,顯示其對大學治理的長期關注。但Pinker認為,對哈佛的批評已演變成一種過激的「錯亂症候群」,特別是來自川普政府和保守派的攻擊,試圖以資金凍結和招生限制削弱哈佛。他承認哈佛存在問題,如錄取不透明和言論自由爭議,但強調這些批評被誇大,忽視了哈佛的學術價值。他呼籲哈佛進行內部改革(如透明招生政策),同時警告外部政治壓力對學術自由的威脅。但在文章最後,他指出:“令人不安的事实是,许多这些改革是在特朗普先生就职后进行的,与他的要求重叠。但如果你站在倾盆大雨中,特朗普先生告诉你要打伞,你不应该仅仅为了刁难他而拒绝。”
2 Boaz Barak的評論:I Teach Computer Science, and That Is All)(我只教計算機科學)(《紐約時報》5月2日)。
Boaz Barak是哈佛大學計算機科學教授,是一位以色列裔美國人,擁有終身教職。 文章探討了大學教授應避免將個人政治立場帶入課堂,強調學術自由與政治中立的重要性。作者回憶2023年10月8日參加哈佛悼念活動,呼籲保護猶太和以色列學生,同時批評政治化對學術環境的干擾。他主張,教授應專注於教學,而非政治活動。
3 Alan Dershowitz的評論:發表於2025年5月5日(NEWSMAX X Post)的貼文。
Dershowitz作為哈佛法學院榮譽教授,在"Wake Up America"節目中討論哈佛可能失去免稅地位,評論道:"They have to be focused on the evils of the campus, and there are enough of them to be focused on." 他指出校園內部問題需關注,特別是在川普政府施壓的背景下。此評論是對哈佛與川普政府衝突的回應,涉及資金凍結和調查,Dershowitz表示對哈佛內部治理的擔憂。
4 Omar Haque的評論:《城市期刊》的X貼文和訪問(City Journal X Post,5月20日)。
Omar Haque 是一名精神病學家、哲學家和社會科學家,Haque擁有布朗大學神經科學(學士)、醫學(哈佛大學,榮譽博士)、宗教與哲學(布朗大學博士、耶魯神學院碩士、哈佛神學院碩士)等多學科背景,並在哈佛與Steven Pinker教授和Arthur Kleinman教授進行博士後研究。2024年,他因不滿哈佛的意識形態偏見和多元化政策(D.E.I.)離職,公開批評哈佛放棄追求真相,轉向左翼種族主義。
Haque作為前哈佛教授,在訪問中描述哈佛被多元化政策(DEI)和左翼意識形態腐蝕,評論道:"Today, Harvard resembles an aging billionaire secluded in his mansion, consumed by narrow moral obsessions, clutching his treasures, disconnected from a world he scorns." 他批評哈佛偏離傳統學術使命,成為意識形態的象徵。Haque的評論是對哈佛內部政策的批評,特別是在川普政府行動的背景下,反映了對大學方向的長期擔憂。
5 Michael Bronski的評論:"Harvard-Professor Bronski über Trump: „Man darf einem Bully nicht nachgeben”,德國《法蘭克福匯報》訪問(FAZ Article 4月23日)。
Bronski作為哈佛性別與性研究教授,提到川普行動的不可預測性,評論道:"One simply does not know what Trump will say or demand next."
6 David Bernstein(@ProfDBernstein):"I think Harvard's top leaders understand the mess they are in. I don't think the lower-level bureaucracy has. They are so used to ignoring the law and acting with impunity that they really haven't been able to assimilate that being Harvard is a liability right now, not a defense."
此外,喬治梅森大學法學院教授 David Bernstein在X平台上評論道(5月9日):「我認為哈佛的高層領導明白他們目前的困境。但我認為低層官僚尚未意識到這一點。他們習慣於無視法律並肆意行事,以至於他們無法接受當前「哈佛」的身份是一個負擔,而非保護。」
這些評論主要聚焦於哈佛與特朗普政府的緊張關係,包括資金凍結、法律訴訟和國際學生招生的限制,但教授們更多討論的是哈佛校園內部問題,如多元化政策、學術自由和反猶太主義、管理不力、招生不公不透明、言論自由等等。
《哈佛深紅報》(The Harvard Crimson)是哈佛大學的學生報紙,創立於1873年,社論通常代表編輯委員會的多數觀點。也是在5月29日,《哈佛深紅報》發表了兩篇社論:《哈佛欠下了什麼?》( What Does Harvard Owe?)《哈佛欠誰的?》( Who Does Harvard Owe?)
《哈佛欠下了什麼?》分為學術、招生和言論環境三部分,指出哈佛學生學術表現優秀,但數位干擾和職業主義文化影響專注力;招生偏向特權背景,需提升公平性;言論環境需平衡自由與包容。比如對招生公平性的分析:文章回應外界對哈佛高昂學費和DEI政策的批評,指出真正的問題在於招生過於偏向特權背景。文章提到,哈佛缺乏公開的社經背景數據,導致招生公平性難以評估。2024年9月的社論呼籲公開種族數據,強調透明度的重要性。儘管哈佛改善了財務援助政策,例如2025年3月的社論提到降低免費學費的家庭收入門檻,但文章認為,問題不在於學費負擔,而在於招生策略。遺產招生和對精英預科學校的偏好被視為加劇精英主義的因素,2024年11月的社論批評對「送生學校」的依賴,呼籲改變招生模式。
文章還討論哈佛的言論環境,指出外界認為哈佛言論極端,但實際問題是學生在敏感話題(如以色列-巴勒斯坦)上感到不適。文章引用調查數據,顯示學生在公開表達意見時存在不適感,特別是在政治和社會議題上。
文章結論強調,哈佛的批評者應超越簡單化觀點,認清問題的複雜性。哈佛應承擔以下責任:建立重視學習的文化、改革招生以減少精英主義、鼓勵學生在困難討論中表現勇氣。這些目標需要社群共同努力,而非僅靠行政措施,如新聞稿或工作組報告。
《哈佛欠誰的?》探討了哈佛在面對國會、捐贈者、媒體和內部利益相關者壓力下的治理危機問題。它質疑誰有權影響哈佛的決策,特別是在特朗普政府削減資金、監控國際學生等政策下。文章批評哈佛解決兩起反猶太主義訴訟並採用IHRA定義,可能威脅言論自由。它還提到哈佛針對巴勒斯坦相關項目(如解雇中東研究中心主任)的行動,這些被視為屈服於外部壓力,引發爭議。文章指出,哈佛被國會、捐贈者、媒體和內部利益相關者拉扯,考驗其是否能真正自治。文章建議哈佛應通過與教師和學生對話,建立更民主的治理機制,抵抗外部干預,維護其核心價值。
哈佛師生關注的核心問題是外部政治壓力(特朗普普政府的行動)、校園內部治理(反猶太主義與D.E.I.政策)以及加沙問題的投資爭議。觀點分歧顯示了校園的緊張氛圍,支持者捍衛學術自由,批評者要求內部改革,抗議者聚焦全球正義。
在這場哈佛與特朗普普政府之間緊張關係中,神秘的哈佛公司和其背後掌門人Penny S. Pritzker出現在公眾視野中。Penny Pritzker,1959年出生,哈佛1981年畢業,經濟學學士)是哈佛公司(Harvard Corporation)高級研究員(Senior Fellow)。
哈佛師生對 Penny S. Pritzker(哈佛公司高級研究員)的批評主要集中在以下幾方面:
Claudine Gay校長遴選爭議:Pritzker領導2022年校長遴選委員會,選擇Claudine Gay為哈佛首位黑人校長,但Gay因反猶太主義處理不當和學術抄襲指控於2024年1月辭職,師生批評Pritzker未充分審查Gay的學術背景。
多元化政策(D.E.I.)與意識形態:部分師生(如Omar Haque、Bill Ackman)指責Pritzker推動的D.E.I.政策導致校園意識形態偏見,壓制學術自由,特別是在反猶太主義和巴勒斯坦相關爭議中。
與特朗普政府的衝突:Pritzker支持哈佛對抗特朗普政府(凍結40億美元資金、國際學生禁令),但校友Bill Ackman等批評其領導下的哈佛策略「管理不善」,引發不必要的法律爭端。
透明度不足:哈佛公司以決策不透明著稱,師生(如David Bernstein)批評Pritzker領導的治理缺乏公開性,尤其在校長遴選和危機處理中。
同時,Penny Pritzker與特朗普之間的私人恩怨,也引起許多背後討論。
Penny Pritzker 家族是美國最富有的家族之一。其家族與特朗普之間的私人恩怨源於1970年代的商業糾紛。1975年Pritzker家族與特朗普合作翻新紐約大中央車站旁的Commodore酒店(後更名為Grand Hyatt)。初期合作成功,但隨後因財務問題惡化。特朗普依賴高風險債券,資金短缺,無法支付酒店升級費用。普利茲克家族要求他承擔應有份額,導致爭執。1993年,特朗普提起5億美元訴訟,指控普利茲克家族「詐欺、敲詐和洗錢」,試圖迫使他出售酒店股份。普利茲克家族反訴,指特朗普未支付裝修費用。最終,1996年買斷特朗普股份,結束合作。1993年,特朗普公開表示「普利茲克家族在我低谷時攻擊我,一旦我東山再起,他們將是我第一個報復的對象」(Daily Beast, 4/17/2025)。《波士頓環球報》認為特朗普對哈佛的強硬態度部分源於對Pritzker的個人報復,延續了數十年的家族恩怨(Boston Globe, 5/22/2025)。
雖然哈佛已經暫時獲得成功延長臨時命令,阻止特朗普政府立即撤銷哈佛招收國際學生的權利,但依然面臨許多財務和訴訟問題。此外,特朗普政府於2025年4月11日發函,要求哈佛在8月前進行治理改革,包括審計學術項目、改變治理結構和招聘政策,否則將面臨進一步制裁(Harvard Gazette)。根據Harvard Magazine,政府的治理改革要求被視為對學術事務的史無前例干預,可能威脅學術自由和創新。哈佛校長艾倫·加伯明確表示,哈佛不會屈服,強調學術自由和憲法權利。5月28日,美國國務卿Marco Rubio宣布,美國將「積極撤銷」具有中國共產黨關係或在「關鍵領域」(如物理科學)就讀的中國學生的簽證。也同樣在5月29日,DHS發布聲明,國土安全部長Kristi Noem加劇對哈佛的行動,理由包括持續的反猶太主義行為和與CCP的合作(DHS Secretary Noem Doubles Down and Escalates Action Against Harvard)。這一政策旨在應對中國政府招募美國訓練科學家的擔憂,但缺乏證據顯示大量學生為中國工作。這項政策影響約275,000名在美的中國學生,可能對哈佛上千名中國學生構成額外風險。
可見,雖然DHS的SEVP認證撤銷行動被法院暫時阻擋,但其壓力可能進一步升級,雙方的法律戰爭將持續進行。哈佛已提起多起訴訟,挑戰政府的資金凍結和國際學生禁令決定(The New York Times)。再加上Penny Pritzker 家族與特朗普的私人恩怨,不少評論認為哈佛和特朗普政府的關係在短期內會進一步緊張。
不管是出於政治、還是意識形態或是個人恩怨,針對國際留學生的行為是否就可以讓哈佛變得更好,讓美國變得更偉大呢?
就在特朗普政府撤銷哈佛大學學生與交流訪問者計劃(SEVP)認證、禁止招收國際學生的第二天,5月23日《哈佛深紅報》(The Harvard Crimson)發表社論《哈佛國際留學生是人——不是棋子(Harvard’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re People — Not Pawns)》(作者Frank S. Zhou),社論強調國際學生是哈佛社群的寶貴成員,而非政治操縱的棋子。文章譴責特朗普政府的行動,認為其以國際學生為靶子,試圖迫使哈佛改變其招生政策和學術立場,特別是在反猶太主義和「觀點多元化」等議題上。社論指出,這項禁令不僅威脅國際學生的未來,也損害哈佛的學術使命和美國高等教育的全球聲譽。
然而也是同一天,一個叫蔣雨融(Luanna Yurong Jiang)的中国留學生,身披一件珠光寶氣的刺繡雲肩學士服,在哈佛大學畢業禮上致詞,題為「Our Humanity(我們的人性)」,大談多元文化與共同命運。她是哈佛歷史上第一位代表畢業生演講的女性。在演講中,蔣雨融說到:
Because if we still believe in a shared future, let us not forget those whom we label as enemies. They too are human. In seeing their humanity, we find our own.
(因為如果我們仍然相信共同命運,就不要忘記那些我們標籤為敵人的,也是人啊。在他們身上看見人性時,我們也找到自己的人性。)
習近平致力推廣、2017年寫入中共黨章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官方英譯正是「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蔣雨融口中的「shared future」,是不是就是中共黨章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在哈佛畢業典禮上閃光呢?(參見馮睎乾在其FB公共網頁)
隨後,中國網民很快挖出她的父親:父親蔣志明曾任遂寧市政協黨組副書記、副主席兼市委統戰部部長,2018年以副廳級幹部退休,2019年起擔任綠色發展基金會「綠色未來專案基金」執行長。蔣雨融從小留學英國,得到綠發會副理事長周晉峰的推薦,上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國際發展公共管理碩士」。
對於蔣雨融的演講,作家馮睎乾在其FB公共網頁評論:
我不知道多少人看過蔣雨融的演講影片,它其實很適合正在減肥的人觀賞——在飯前播放,保證十秒內反胃;若想事半功倍,只要反覆觀看以下一段蔣雨融「忍淚」兼以「哭腔」唸的台詞,應該連隔夜飯也嘔得出來:
If there's a woman anywhere in the world who cannot afford a period pad, it makes me poor. If a girl who skips school out of fear of harassment, that threatens my dignity. If a little boy dies in a war that he didn't start and never understood, part of me dies with him.
(如果世上任何地方有一個女人買不起衛生巾,那會使我感到貧困。如果有一個女孩因害怕騷擾而不敢上學,那會危及我的尊嚴。如果一個小男孩死於一場他沒發動也從未理解的戰爭,那我的一部分也會隨之死去。)
片段在此:
生硬的表情動作、刻意顫抖的聲音、造作的深呼吸聲,再配上十級矯情的台詞,根本是一場完美爛戲。望着這個蔣雨融,披着珠光閃閃的土豪級雲肩學士袍,時而為買不起衛生巾的女性長嗟,時而為死於戰亂的小孩短歎,可一兩分鐘後又若無其事眉飛色舞,如果這樣也不作嘔,我會懷疑自己的人性。
在這異常敏感時刻,為什麼哈佛會在有著”中共海外黨校“之稱的肯尼迪學院,找一位學鍍金專業的”紅二代“來演講呢?這真是讓人想為國際留學生說一句話,卻欲辯無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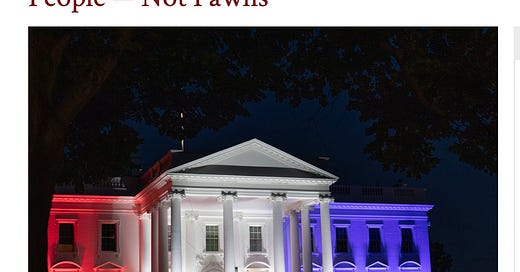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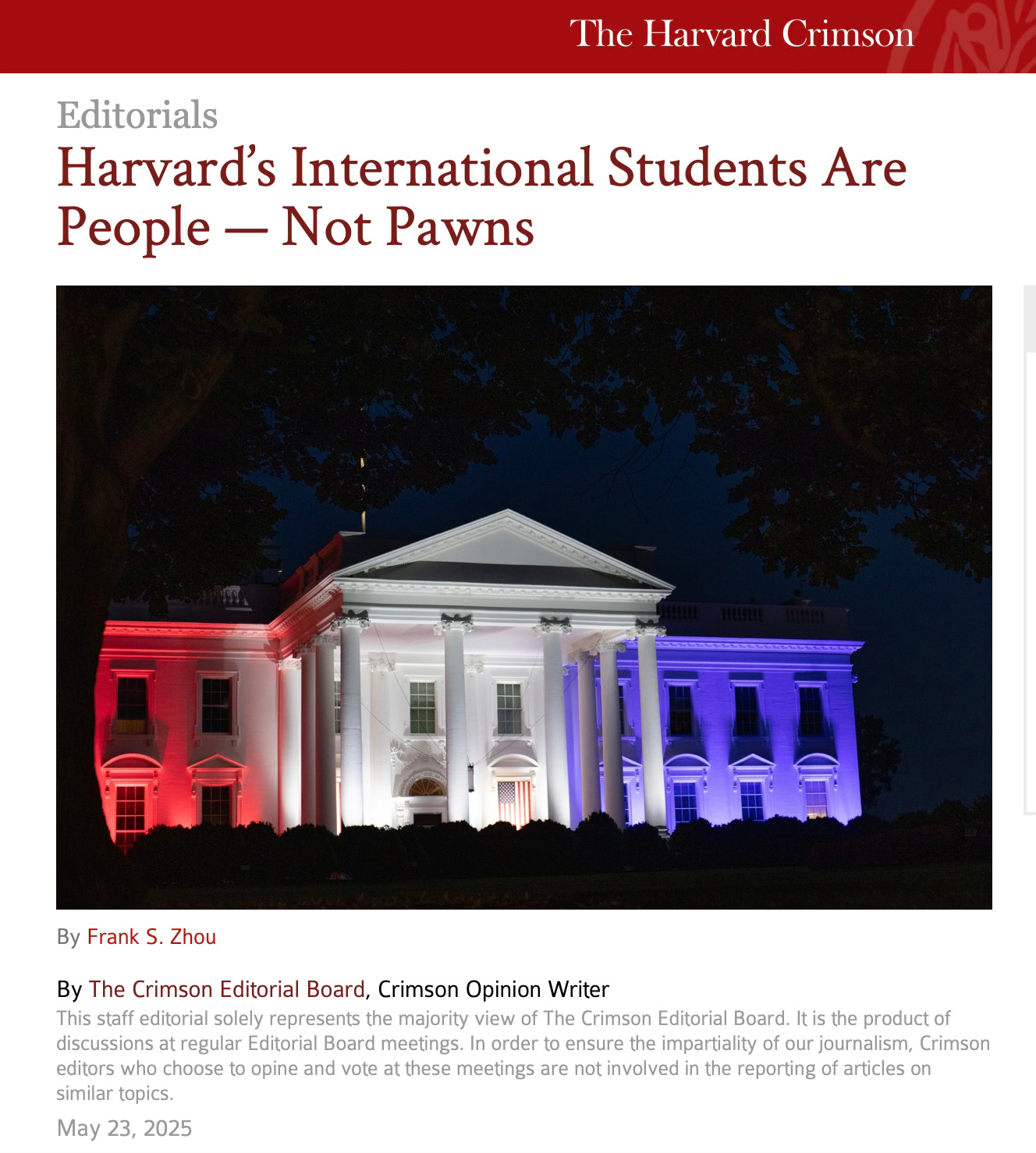


很有趣的短评,包含好多有趣的问题和话题,其中有Steven Pinker教授的有趣的评论:“令人不安的事实是,许多(哈佛的)这些改革是在特朗普先生就职后进行的,与他的要求重叠。但如果你站在倾盆大雨中,特朗普先生告诉你要打伞,你不应该仅仅为了刁难他而拒绝。”
Pinker的类比说法犹如伊索寓言,让我不禁也想用寓言来回应——鳄鱼对在河边走的小男孩说:瞧你呀,这么清凉的河水你不享受,非要穿着鞋在河边走?傻不傻呀?…又,鸡窝鼠患严重,投喂的饲料大半成了鼠饲料,黄鼠狼毛遂自荐要求看守鸡窝,声言自己是鼠类的天敌…。
不错,河水确实是清凉的,应当享受;黄鼠狼确实是鼠类的天敌。但人们在想问题、看问题的时候,不能只是凭直观,直觉。Pinker所说的“如果你站在倾盆大雨中,特朗普先生告诉你要打伞,你不应该仅仅为了刁难他而拒绝”,这话从直觉/直观的角度看貌似很有道理,但也可能实际上很没有道理。
将近四百年的老店哈佛确实问题很多,病症很多,然而,假如治疗对健康状况造成的损害比疾病还厉害,假如施治的人怀有敌意,用”下大雨有人要你打伞”的思路来考虑治疗问题就有了不可承受的风险/危险。理智正常的人都可以看到,特朗普跟哈佛的关系绝非前者要后者在大雨打伞免得被淋湿那么简单,那么无害。
以上所言的意思并不是说哈佛的问题不存在或不应当解决,病症不应当治,而是说眼下的问题就像是一个人明显有病,一个丝毫不掩饰其强烈敌意的人强行给他开药,要他服药,声言药对他有好处,不服药就要予以毫不留情的惩处。
在一个正常的国家,人们遇到这样的事情,会劝说甚至呵斥那个强行开药的人。呜呼,今日美国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人们要么对那个强行开药的人不敢批评或谴责,要么跟着他的曲调起舞,为他喝彩。
啊 好奇怪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