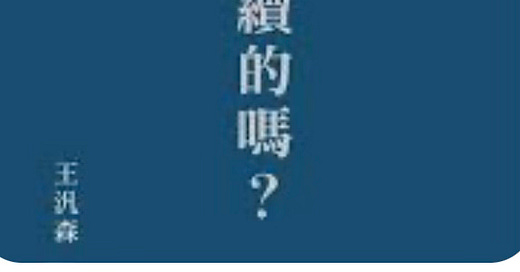王汎森 | 觀念的勢力:以1911年前後史事為例的討論
編者按:台灣《思想》復刊近20年,2024年5月推出五十期《思想的力量:俯仰50》。經《思想》與作者授權,波士頓書評特選發其中三篇,此為第二篇。作者按: 辛亥革命百年時,我受邀在若干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香港城市大學等)演講「觀念的勢力」,但始終未曾寫成定稿發表。這次撰寫重點與原先的講述略有不同:為了呼應《思想》的主題「思想的力量」,我儘量扣緊「思想」如何成為「力量」的實際機轉這個問題進行發揮。另外,本文中的部分內容曾見於〈啟蒙是連續的嗎?——從晚清到五四〉,收於拙著《啟蒙是連續的嗎?》(香港:香港城市大學,2020),敬請鑑察。
21世紀西方史學有一種傾向,好像研究的題目離思想愈遠愈好。史學界對於物質史、器械史的愛好,便是其中一個例子。但是,人們仍然不能不承認,歷史中許多重大的發展與思想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本文之所以以「觀念的勢力」為名,是想強調思想和觀念塑造、改變現實的力量。往往在最初只是幾個人物的想法,後來卻成為燎原之勢。譬如《明夷待訪錄》〈學校〉篇中一句「學宮以外,凡在城在野寺觀庵堂,大者改為書院,經師領之,小者改為小學,蒙師領之,以分處諸生受業。」1引發晚清康有為(1858-1927)、張之洞(1837-1909)分別提倡「毀廟興學」運動,結果全國寺、觀由七百餘萬家劇減為萬餘家,大量寺院財產被沒收,影響之大、紛端之多,真是筆墨所難以形容。晚清以來,共和、民主、議院、立憲等政治思想,在此之前罕為人知,可是一旦它們透過各種傳播形成「觀念的勢力」,便硬拉著人們非緊跟著走不可,不跟著走便是「反動」,而「反動」是錯的。
在這裡我想強調:生活在21世紀的我們深受「後見之明」的影響,每每誤以為古往今來歷史中新思想的提出是很容易的,是理所當然的。但是仔細觀察歷史,便會發現在思想或理念上轉開一扇門,說不定需要五十或一百年之久。而新「思想」一旦產生,它在現實生活中發生實際作用的「機轉」相當複雜。有時候新思想的提出,是像打開一瓶濃郁的香水,人們馬上聞到它的香氣並受其影響。正如柏格森(1859-1941)在《道德與宗教的兩個來源》中所說的「由於基督教浸潤了整個西方文明,人們像吸進香氣一樣吸受這一文明所帶來的每種東西」。2「思想」確實有風行草偃、不一定需要太多助緣便可成為力量的時候。但是從歷史上看,也有很多時候在「思想」產生「力量」的過程中,它與現實有種種複雜的交涉。即以「宗教改革」為例,顯然不全像柏格森所說的如花香一般,聞到香氣的人都要受其影響,依據昆丁.史金納(1940-)的研究,路德發起宗教改革的過程,如果不是若干王侯的保護與支持,新教不可能立足傳播。而諸王侯之所以保護、支持他,跟他們與羅馬教廷的緊張對立是分不開關係的。3從這一點看,「思想」與現實政治格局之間又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一
本文的關心延續著去年10月,我在中研院史語所95週年的主題演講「由下而上的思想史」中的旨趣。4在該演講中我提到,如果要從歷史的角度來考量「思想」成為「勢力」的過程,應該要注意三種可能的陷阱。
我當時藉著反思將近四十年前入所之初的一篇未刊稿,討論以戴震(1724-1777)為中心所形成的一種寬容、寬讓的哲學,檢討我對思想史看法的改變。在四十年前,我深受胡適(1891-1962)、錢穆(1895-1990)等先輩的影響,隱隱然以為思想一旦生發,即如射出的箭自然飛向遠方,成為歷史「實際」的一部分。但事實不然,人們關心戴震的主要還是他考證學方面的著作,至於「欲當即理」的思想,在當時並沒有引起很大的反響。所以它並不像柏格森所說的人們像吸進香氛一樣,立即受這個突破性思想影響。
因此在那篇演講中,我主張如果要從歷史的角度來考量思想的力量,應該把思想世界視為充滿張力、不停地循環上下、往復周流、來回激盪的世界。所以不只「由上而下」地看其影響如何擴散,也要「由下而上」地歷覽不同層次的思想狀態。故在「由下而上」這個口號下有幾層意義。一、思想由下而上擴散的情形。二、由下而上歷觀某時代不同層次的思想狀態。三、在看出不同層次的思想狀態時,可以發現有時表層上雖仍然是儒家正統意識形態,但下層早已蝕空、早已被各種秘密宗教席捲而去。四、從不同層次看,則事物的性質也可能有所不同。如日本的神道,當年美國占領軍由上而下將之定義為「宗教」,但由下而上看,人們卻認為它是一種「祭政一體」的體制。
諸層次並不是一個物理的,或簡單的空間概念,而只是一個大致的區分。我以為在歷史書寫或進行歷史判斷時,應對此問題有相當的關照,並隨時放在心中。此外,歷史工作者還應辨別不同史料的層次性,盡量發掘較具公約數性質,較能反映日常性的概念思想文本,以方便了解一個時期中思想或概念的主色調,並瞭解到某一種新思想的提出到某種程度,以某種方式落實到日常生活世界時的種種「機轉」。如果不是以前述的角度入手,則常常會出現三種謬誤:「混淆不同層次的謬誤」、「時代錯置的謬誤」、「數目計算的謬誤」。我認為思想、概念與它們時代的社會往往存在層次之別,而且「理想的」與「實際的」這兩個層次之間往往存在著「時間差」。
有許多思想,從開始生發到站在歷史舞台上成為主流思想之一往往需要經過幾百年的時間,而史家通常忽略了這一個問題,將提出某種思想的時間與成為主流的時間錯置,誤以前者為後者。譬如王夫之(1619-1692)的《黃書》、《讀通鑑論》等激烈種族思想的文本以及黃宗羲(1610-1695)《明夷待訪錄》等,雖然成書於十七世紀,但真正發揮重大影響則要到19世紀末。那麼,如果把它們當成17世紀歷史的主幹,而忽略了它們在當時的真正地位,便犯了「時代錯置的謬誤」。
歷史中的思想/概念不一定要下及草根才能左右世運。事實上有許多時候,一般人民或者什麼多不關心,或者是「新舊未定家」(傅斯年),故新思想往往影響了在當時的政經或文化環境中能起作用的「歷史團體」——如五四初期北京幾十個新人物,逐漸掀起旋風,即能逐漸轉動一世。所以,歷史上雖然有許多時候,思潮確實能下及草根層次,但也有許多時候,它們是透過「歷史團體」而轉動一世,或透過「歷史團體」漸次以各種方式(包括成為制度或影響立法),而漸漸擴及街頭層次。因此,簡單地計算數目並不一定能解釋歷史的變動。
一旦我們的研究是涉及思想或其他學問對日常生活的影響時,則必須考慮到其影響的方式與學院中學理的探討方式有所不同。在日常生活層次中,思想文本往往像一瓶打開的香水,聞到了便可能受到某種薰陶,所以不一定是從特定思想文本的授受之中才能找出影響的痕跡。不過香氣還是有一個範圍,譬如說一公里外,就可能聞不到這個香氣了。就像一個人含著糖果,或是把兩杯溶液倒在一起,總之,思想史書寫應考慮「歷史的不同層次」(layers of history),以免犯了「混淆不同層次的謬誤」、「時代錯置的謬誤」、「數目計算的繆誤」。
在那篇講稿中,我談到「思想」或「概念」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時,提到兩種型式,一是在平常時候,思想、概念往往是透過逐漸醞染而擴散開來。第二種形式則是在大變革時期,概念/思想強拉著人走,不跟著它們走的人甚至可能無法立足於社會中。在本文中我還將提到「思想」與「社會」之間的另一種「機轉」。
本文即想以1911年革命前後「思想」與「政治體制」之間的動態關係為例,探討「思想」成為「勢力」的各種「機轉」中的一種,即「思想」與「政治體制」之間如何形成一種「互緣」或「轉轍器」的關係。佛經《攝大乘論》中有一段話:「如是二識,更互為緣」。它的大意是說,有阿賴耶識才有受用識,有受用識才有阿賴耶識,兩者相互為緣。而這種思想與現實「互緣」的關係,形式非常之多。
本文是藉1911年辛亥革命前後的思潮與政制之間的關係,說明一種「轉轍器」般的關係。韋伯(1864-1920)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曾經提到「轉轍器」的觀念,就是火車在跑的時候,將轉轍器一拉,火車本來要往革命方向跑的就變往另一方向跑了。
在這裡我是取動態的「相互為緣」的意思。也就是說「思想」產生「力量」的過程中有一種現象:往往是藉由一群人的鼓吹,引起社會各界的觀瞻,形成一種震動,而這種震動在積累到相當程度之後,往往打開一道閘口,由思想落實為制度,以國家的力量來保證它的實行。譬如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新文化運動的許多主張在後來成為制度,以白話文為國語,形成政策頒行全國。而每個制度又回過頭帶出更廣闊或不同性質的思想改變。有兩個重點值得在這裡特別提到,我們因為受線性歷史觀的暗示,所以每每以為只有一種思想力量在左右著時局,其實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往往有幾股勢力在競逐,而其中有較強而具說服力的,它可能具有壓倒性優勢,也可能只是比其他幾條競爭的線索高出一點而已。但是,就這極小的一點差異,也可能因為衝向前打開水庫的閘門,建立新政治體制,又好像是一股相對較高伏特的電流,將電燈點亮,而一旦點亮,整個暗室便頓時光亮起來,但另外幾股相差較大的力量,卻成為了「反動派」。也就是說互相競逐的幾種思想勢力之間,不管是勢力懸殊或可能只有極小的差距,但因為得到勝利,便牽動整個制度格局的改變,正如威靈頓公爵(1814-1852)在回憶錄中說的,滑鐵盧戰役中,拿破崙(1769-1821)部隊與聯軍的力量相差其實是非常微小的,可是從這個微小的差異逐漸擴大,最後導致法方失敗,拿破崙退位、放逐,全歐洲新的政治格局形成,徹底改變歐洲的命運。
如果我們考慮思想的現實影響,則“scale”本身便是一個重要的主題。5一個思想力量的“scale”如果大到了撥動「轉轍器」,而「轉轍器」決定了火車的方向之後,便帶著全部的馬力往前衝。而因為思想勢力的增大,可能扭開了另一個轉轍器。當然這並不是一個始終不停的「轆轤劫」,往往在某些情勢、條件下,一個新思想勢力的出現形構了另一個新思想格局。前面提到,在本文中,我想探討1911年前後的重大思想動盪與政治體制之間的「更互為緣」或互為「轉轍器」的現象。
二
晚清以來,思想界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不過對於這個變化的時間序列必須要區辨清楚。為此,我曾經將1820年代以來成書的政論,排出一個時間序列,發現1850-60年之前的政書,其基本方向是一方面阻擋西方新式思潮的進入,另一方面是「眼前無路想回頭」,不斷回到所謂更純粹的古代並加以改造以適應現實變局。譬如道光年間畢子筠的《衡論》,便用盡力氣倡導一種「宗法烏托邦」。6
但從1860年左右開始,新思想開始不很系統地出現在《校邠廬抗議》、《資政新編》,薛福成(1838-1894)的《籌洋芻議》等書。一路下來,我們所比較熟悉的近代啟蒙的思路逐漸成為各種政書中重要的部分。但是整個轉換的過程還是比較緩慢的,整個思想歷程的「年輪」相當清楚。大體而言, 1880-90年代的政書又有一次大變,出現《弢園文錄外編》(1882)、《佐治芻言》(1885)、《盛世危言》(1893)等書。至於戊戌前後,則批判封建,提倡民權、自由的思想開始流行。但時人主張將「民權」與「民主」加以區分,認同「民權」,卻拒絕「民主」。大體而言,此時變法,民權、自由等方面的思想開始擴散。接著辛亥革命前十年是重要的轉變期。在1900年之後不久,國家思想、國民觀念勃興,鼓吹國家與朝廷的對立,又如「帝國主義」的觀念取代「列強」等。此外,民族主義高張,尤其是漢族種族主義之熾烈,對社會主義的謳歌、無政府主義的宣傳等等,成為一個待爆的火藥庫。7我們可以說清末最後十年,是另一個思想變局,是醞釀革命思想的重要時刻。1960年代編輯的《辛亥革命前十年時論選輯》,想來在時間序列上是經過一番斟酌的。大抵而言,1890年之前,人們是慢慢地忖度著是不是跟著新思潮走,但從1890年代開始,尤其是甲午戰爭(1895)之後,便進入「觀念」強拉著時代走,而且到了後來是不緊跟著走不行的地步。
細釋1860年代以來二、三十種發揮重大影響的政書(至於單篇文章當然不在此限),看書中思想元素的變化,可以發現許多新元素是從各種翻譯或介紹的西文材料而來。不管是清末的立憲派還是革命派都是如此,《革命史譚》的作者陸丹林(1896-1972)(引馮自由之說):「廣州雙門底……聖教書樓,即以販賣廣學會出版書報為營業,孫總理及康有為之倡導維新,大都得力於是。」8正如康有為在《康南海自編年譜》中所說的,他的思想啟蒙得力於「大購西書」。9
從1860年代以來的各種新思維,有的從本土傳統中滋生,但也有不少是輸入西學的。這些新思潮每每由零碎、邊緣而慢慢積累、發酵,最後變成沛然莫之能禦的力量,在這裡我用「觀念的勢力」一詞來加以形容。
「觀念的勢力」 (power of ideas)一詞來自梁啓超(1873-1929)的〈論時代之思潮〉,他說:「此種觀念之勢力,初時本甚微弱,愈運動則欲擴大,久之則成為一種權威。」10「勢力」二字有其時代 意 味 , 我 認 為 梁 啓 超 選 用 它 , 也 不 是 偶 然 的 。 1920年 杜 威(1859-1952)在華演講〈新人生觀〉時,根據中文的紀錄,他還特地解釋了「勢力」二字說:「勢力的觀念是由科學方法中發生出來的,是一種活動的、主動的、發展的、開闢未來的觀念」,11足見「勢力」是主觀的、能動的,有一特定的意思。我覺得「觀念的勢力」一詞很能告訴我們,在特殊的時空裡面,某些不一定是從本地土壤所生出的、漂浮在空中的觀念的勢力,可以由星星之火到形成燎原之勢。
托克維爾(1805-1859)的《舊制度與法國大革命》,指出法國大革命時期,寫書、編書、抄書,出版各種小冊子或宣傳品的人,幾乎都是一些出身不高、從不捲入日常政治、沒有絲毫權力,也不擔任公職的人。他們靠著一些想法,一些原來被認為不切實際的普遍抽象的觀念,最後構成了一套新的政治思想。每種公眾激情都喬裝成哲學,政治生活被強烈地推入文學之中,作家控制了輿論的領導,一時間占據了在自由國家裡通常由政黨領袖占有的位置,進而對法國大革命產生如此深遠的影響。當時有些人可能認為這些觀念不過是一些無聊的發想,卻沒想到它們攫住青年,並且強而有力地改變了歷史的命運。對法國大革命來說,文人以及他們的觀念是多麼重要。所以托克維爾不禁要問:到18世紀中葉,文人何以變為國家首要政治家?12
我用「觀念的勢力」,一方面也是受到托克維爾著作的啟發,就像梁啓超在《戊戌政變記》所說,晚清出現了一大批年齡在二、三十歲之間,既無官職,也沒有功名的人(「無科第、無官階」),13這些人形成了自由流動的資源(free floating resources)。他們中間一些人基於時代的局勢,寫了各式各樣的小冊子。14這些書的作者,有些原來有低階的功名,但後來就不再追求了,有些根本就沒有功名,或許有些許功名但沒有任何官職,他們的想法、觀念成為辛亥革命的重要資源。
辛亥之前這些書冊大約可歸納為幾類。第一類是反滿的,反滿是 晚 清 的 「 觀念 的 勢 力」 裡 最 大的 一 個 課題 。 譬如 , 李 六 如(1887-1973)以自傳式寫成的歷史小說《六十年變遷》中的一個角色葉得勝,你跟他講亡國,他不在乎,他說:「亡國,亡不到我們頭上,一個月不寄錢回家就會餓死」,可是你跟他說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說到滿人以前大殺漢人,他整個人就振奮起來了。15亡國已經夠嚴重了吧,但對有些人來說亡國還不夠刺激,反而是種族仇恨才能激勵他們。由此可見,像《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略》這類的書籍在清末是有很大影響力的。這類書其實大多在17世紀中葉,滿清入關後就已經寫成,但後來因為忌諱,只有少許抄本在文人手上偷偷流傳,到了道光年間才被印出,但真正產生重大的影響力,都已經又過了六、七十年。
其實,這類書很早就已有人在讀了,清朝末期的若干讀書筆記中都提到過《揚州十日記》等書 ,但是當時人讀後往往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人可以被屠戮得這麼慘,天卻毫不憐惜,讀書筆記裡面並沒有強烈的種族的聯想。當然對屠戮之慘的感慨,在內心中也可能產生了很大的震撼,但這種震撼未必即與「種族」、「革命」聯在一起。甚至於很多在明末清初清楚記載漢人如何對抗清朝、如何遭到屠戮的書,在清朝後期也被拿來做為提倡「忠義」精神的文獻,希望人們模仿幾百年前忠義的精神來對抗流寇與西方帝國主義的入侵。
這些文獻與排滿革命連在一起的想法,大部分都出現在清末最後的十幾、二十年間。清朝後期的對外的屈辱和內政的弊病使得它跟種族思想之間形成一個很特殊微妙的關係,很多人認為如果不再反滿的話就會成為亡國奴,所以必須要反滿。於是發生在17世紀的悲慘屠戮,以及那些英勇對抗外族入侵的忠臣義士,到了清朝最後一、二十年,慢慢由甜變酸,由補藥變成毒藥,成為反滿、反清的重要材料。曾有一位滿族學者寫文章說《揚州十日記》是假造的,是辛亥革命之後所虛構出來的書,16但是我個人發現日本圖書館中收藏著寬政或其他年間的《揚州十日記》翻印本,可見它們不可能是偽造的。由於這些書長期處於敏感的環境,在不斷抄錄、移寫的過程中,內容可能出現很多變動,所以有人會誤以為是後人偽造的。
晚清新的「讀者社群」與時代環境,使得人們閱讀這些文獻時產生了極為不同的意義。這類書籍的讀法及它們所產生的意義,必須配合著晚清的時代屈辱感去了解。近代中國的屈辱感,不是其他革命國家能形容的,俄國雖然也產生大革命,但俄國沒有失去過領事裁判權,也沒有租界;日本有明治維新,可是日本不論是明治維新之前,還是之後,國家的力量始終都還是控制在日本人自己手裡。所以中國跟其他很多近代革命國家所產生的屈辱是不太一樣的,。這種屈辱感才會使得這些17世紀的帶有民族仇恨的文獻,突然像火柴點燃火藥庫一樣爆炸開來。所以「觀念的勢力」還需要與時代的政治、社會現實配搭,正如火柴丟入火藥庫,才可能產生爆炸性的影響。
晚清批判傳統、批判君權的思想非常厲害,在清朝最後十幾二十年已經出現,其中譚嗣同(1865-1898)的《仁學》提倡一種「衝決網羅」的思想。這個世界就像被蜘蛛絲網住了,動彈不得,我們要衝破這些蜘蛛絲,如家庭、政府、君王、國家等等各式各樣的束縛所結成的網子。清朝最後十年,即1900到1911年這段時間,影響時代變動最大的不是考證學家或桐城派的文章,而是各式各樣的小冊子。這些小冊子往往宣傳衝決網羅、推翻君權的傳統,指責「兩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仁學》的下半卷裡面,由批判君權進而批判滿清王朝,譚嗣同的這些言論對後來反滿革命有很大的影響。17
對反滿有重大影響的,還有幾個重要人物的著作及重要刊物,如章太炎(1869-1936)的《訄書》,以及《民報》等刊物,這些著述及刊物很多都是推動反滿思潮非常重要的媒介。章太炎《訄書》中的「訄」字,是緊急的意思,《訄書》即緊急的書,為甚麼緊急?因為一切都不行了,再不把這個政權推翻,國家都沒有了。「共和」是18世紀西方最流行的理論,可是誰也說不清楚「共和」究竟是甚麼,「共和」主要是指立憲、議院等,當時的人除了立憲、議院之外,還常把它與君主制相反的東西,譬如反對等級制、家長制、從屬制、效忠君王等不平等關係,把關於個人、家庭、國家等一系列新思想觀念都統統塞進「共和」這個乾坤袋裡。這種情形恐怕也不是獨一無二的,便有史學家指出美國革命時期人們對「共和」想法一樣莫衷一是。18不過晚清士人的「共和」思想中有一點是很清楚的,他們大多傾向於組成代議議會和立憲,並反對當時的君權,這是一股很重要的思想力量。
另外一股觀念的力量是社會主義,談及社會主義在中國的流播,Martin Bernal(1937-2013)的《1907年以前中國的社會主義思潮》,19告訴我們1907年之前的中國知識分子,尤其是指在日本的留學生充斥著各種社會主義的思想。當時留學生的刊物,包括《民報》和《新民叢報》等,都是以日本東京為總部。雖然在中國,有一些人偷偷的讀,也有人在偷偷的翻印。當時上海更有一位外號叫「野雞大王」的人,專門兜售革命刊物,20當時這些刊物裡面的社會主義思想已經非常興盛。國民黨裡面最左翼的部分即是吸收了馬克思的思想,所以《民報》經常鼓吹社會主義思想,這對1911年建立的中華民國也有一些影響,孫中山(1866-1925)的「平均地權」就反映了這一點。
此外,無政府主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東亞很有影響力,後來隨著革命成功而慢慢退位。當時在日本的革命分子與日本的無政府主義者互相激盪,產生非常大的影響。事實上中國共產黨早期的建立者,有一些人認為最理想的不是建立共產主義世界,而是無政府主義世界,但是希望先到達共產主義世界,然後再達到無政府主義 世 界 。 周 恩來 有 一 首詩 整 個 想法 都 是 無政 府 主義 , 毛 澤 東(1893-1976)早期也有這個想法,無政府主義對當時的革命產生很大影響:全部破壞,全部政府都不要,貨幣也不要,警察也不要,軍隊全部都不要,滿清政府當然也不要了。清末的思想界充斥著各種不同的想法與觀念,如社會契約論、女權論等等,不一而足,有很多是歪打正著,有很多是直接的針對。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理念雖然在1905年左右便已確定,但在1920年代才進行公開系統的演講,事實上也還沒有講完,陳炯明(1878-1933)叛變時,許多材料都因戰爭而銷毀了。辛亥革命之前,孫中山雖曾在《民報》或演講中談到「三民主義」,但當時並未系統成文。《民報》上由孫中山本人執筆的文章也很少,很多都是演講稿,還有很多人傳揚他的想法。雖然當時「三民主義」尚未成書,但是民族、民權、民生對當時人已經產生很大的影響,尤其是「民族主義」。民國成立以後,「民生主義」,尤其裡面的社會主義的層面,產生很大的影響。三民主義反對極端的社會主義,《三民主義》中有一段大意是你不能為了能有機會穿上漂亮的皮大衣而天天祈禱老天下雪。我們不能要求整個社會改變去附和共產主義,正如不能為了穿皮大衣而希望廣東下雪一般。21但它吸收社會主義中的某些成分 ,以致於民國建立之後,經常有人得要出面寫文章論證「民生主義不是共產主義」。
誠如比利時史學家亨利.皮雷納(Henri Pirenne, 1862-1935)的比喻,他說,歷史發展像海洋的波浪,先是一滴一滴匯成波浪,波浪愈堆愈高,然後到了最高的浪頭,再逐步退去,在這中間,又隨岸邊地形的不同而拍打出不同的浪花。在大略交代了1911年之前的種種思想潮流之後,我要再回到「互緣」或「轉轍器」上來。也就是說我們在考慮這一段思想歷史時,絕不能輕易放過實際的政治、社會狀況,觀念、思想可以說是騎在這樣的浪頭上而步步拔高。單單只有「觀念的勢力」還不足以自行,這些思想觀念像海洋的波浪打在黑暗惡劣的政治、風俗、社會,形成了各式各樣的浪花。也就是說晚清觀念的勢力與黑暗的社會互相激盪,才導致了重大革命。
李伯元(1867-1906)描寫晚清縣府衙門黑暗面的譴責小說——《活地獄》,被阿英稱之為「一部非常重要的社會史料書,中國監獄史」,22觸目所及,全是悲苦世界。當時內外政治的失敗、官場的昏濁、習俗的窳陋,以及人民流離失所,或許人們不一定注意到,在宣統年間,已經有許多官員放棄他們的官職回鄉。名畫家黃賓虹在晚清時是積極的革命分子,他後來即曾回憶說:「前清末造,風俗頹敗,局賭窩娼之事,到處有之。舉世滔滔,恬不為怪,沈迷莫返,振作無由,伊戚自貽,而惟都會之地為尤甚」。23
三
在這裡我要對辛亥後思想與政治體制的關係,提出三點觀察。第一是清末流行的政治思想,往往成為民初各種大小政黨政綱中的元素。即使它們只是為了妝點門面,但是一旦成為政綱,它就多少起了規範的作用。
清末最後十年,主宰時局的一套概念,如「立憲帝國」、「軍國民教育」、「地方自治能力」、「振興實業」、「整理財政」,很快地風行各方。24到了辛亥前後,從一些帶有綜覽性或調查性的文本中可以看出,當時居「大數」的「概念層」,如《革命史譚》中所列出的,「平等、民主、自由、民權、共和、國民、中華」、「國民之公意、團體」等思想概念,25成了隨處可見的思想概念。民國初建時,一位日本特務調查了當時旋起旋滅的百餘個政黨, 26從各政黨的政綱中可以看出前述那一批概念已經不只是「理想的」,而是「實際上」落實到政黨政綱的概念:「民主、自由、共和、民意、國家、國民、自治、競爭、進步」,或是「統一、共和、自治、種族、社會政策」。27除了上述之外,如「富強」、「鞏固共和國體」、「全國統一」、「完全共和政治」、「永遠泯除私見」、「組織一大團體」、「國家應以民為本」,甚至「天民」一詞亦常出現。人們在構想政黨的政綱時,好像隨便可以任意拿這些「奶粉」泡一杯牛奶,譬如當時一個稱為「自由黨」的,政綱是「維護社會自由,驅除共和之障礙,故鼓吹絕對之自由。」 28宗方小太郎(1864-1923)說,民初那一百多個政黨大多很快的消失了。政綱就像食譜,人們不一定完全照著食譜烹調,但是政綱這些「理想」往往微妙地牽動「實際上」,使得人們不管是不是真心信從,但至少表面上仍要像魚兒們般向著餌移動,長期下來便可能產生一些「假作真時假亦真」的效應。
民主憲政的調子一旦定了,就很難回到舊的帝制時代,雖然日後不斷有人說以前的時代比較好,應該回到君主制度,但如果仔細看後來張勳復辟時的相關文獻,就會發現復辟這件事是連許多軍閥都反對的。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最後的比喻,資本主義一開始像一件輕紗罩上,後來則變成了鐵籠,它一旦罩上去,你就不能輕輕的把它移開了。
第二,是因為共和體制的確立,頒布了許多法令,在當時或許只是一些門面,實際上也面臨許多反對的聲浪,但是這些法令規章把「轉轍器」轉到另一個方向,使得西方民主政治的思潮——不管是否當真,正式成為官方要求人民遵守的條文,必要時還有國家的力量撐腰。
辛亥革命成功以後,民國政府在南京雖然只有九十天,但它用體制性力量在民元的最初一個月間公布了許多符合西方潮流的政策,三十幾通除舊布新的文告,原是晚清革命宣傳之思想,現在以法令、政策頒行全國,那麼它們的影響力最初也宛如一件輕紗罩在身上,最後是有可能性變成鐵籠的。
舉例而言,《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等於當時的憲法),將天賦人權、自由、博愛、平等的思想條文化、法典化。這個憲法體現了晚清民主共和、啟蒙、改革、平等的思想,並用法條確定下來。譬如:第一,中華民國爲中華人民組織之。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還有如:「第五條 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第六條 人民得享有左列各項之自由權。一人民之身體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罰。 二人民之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三人民有保有財產及營業之自由。四人民有言論、著作、刊行及集會結社之自由。五人民有書信秘密之自由。六人民有居住遷徙之自由。七人民有信敎之自由。」這些條文將思想文化上的主張得以藉建制性的(institutional)力量推行下去。
又如中華民國第一任教育部長蔡元培(1868-1940),在1912年1月頒布《普通教育暫行辦法》,其中有幾點如:改學堂爲學校、小學可男女同校、小學廢止讀經科、各種教科書必須符合共和國國民的宗旨等。蔡元培又在別的地方宣布廢止尊孔,所以晚清以來所風起雲湧的思想多在教育法規等命令中落實了。29此外,教育部還命令廢跪拜之禮,改三鞠躬,祭服改爲便服等,課本裡面有任何與共和國抵觸的通通要刪掉。
在此類法令規章之後,同一件事的意義亦有所不同。就像講美國總統湯瑪斯.傑弗遜(1743-1826)本來就蓄黑奴,還跟其中一個黑奴生了小孩,革命之後他一樣蓄黑奴,但革命前與革命之後意義不一樣,革命之前蓄黑奴是天經地義的,革命之後卻被認爲是不義的。
第三,在文化領域,因為革命將「轉轍器」轉向「新」的一方,便出現了民國政府以官方力量打擊或壓制舊傳統的現象。周作人(1885-1967)在他的《知堂回想錄》裡講,辛亥革命以後有兩件事情,一件是停止祭孔,另一件是北大廢經科為文科,「這兩件事在中國的影響極大,是絕不可估計得太低的」。30這兩件事代表整個傳統文化從此以後頓失所依,這是以制度力量推行全國,跟晚清時零零星星作宣傳是不一樣的。劉大鵬(1857-1942)在他的日記中記載了他對省視學視察學校的觀察,他說:「省視學到縣一日,今日來晉祠查學校,僅許辦理新學,不許誦讀經書」31。過去主張不讀四書五經的是異端邪說,但原來天經地義的現在變成異端;又如民初安徽都督柏文蔚(1876-1947)下令將城隍廟充公,撤毀偶像,是派警察廳長負責執行的。以上兩個例子說明了,革命前不容於當道的狂舉,革命後都是由官方動手執行。
鄭超麟(1901-1998)在他的回憶錄裡有句話說:「皇帝的城牆怎麼可以拆去呢?」,32王權、傳統就像一道原本矗立的城牆,辛亥革命的成功象徵著那道原本的牆被拆了、推垮了,但這並不是說舊的、專制的東西從此都消失了,而是新的和舊的全部都衝過去了,但它們所居的相對地位產生了劇烈變化。晚清時宣傳這些東西在當時的體制下是大逆不道,可是現在它跟原來最正統的東西都衝過這道牆,成為可以被感受到的,甚至慢慢成為領導性的思維。
這造成了法國洪席耶(Jacques Ranciere,1940-) 所說的 “regime of aesthetics”的變化,有些東西在某一時代才會被感知,在很多時代它只是邊緣,或被人民視而不見。正如梁巨川(1858-1918)所說:「今人為新說所震,喪失自己權威。自光宣之末,新說謂敬君戀主為奴性,一般吃俸祿者靡然從之,望其自己生平主義」,以前稱頌忠君愛國,如今同樣的行為變成是奴性不改;他又說:「昔所目為不肖者,今或以為當行」,33以前的叛徒,現在成為革命英雄,這就是革命。革命不單是消滅那些不相容的東西,而是重新排列它們之間的價值,原來核心的變為邊緣,如劉大鵬說:「自變亂以後,學堂之內禁讀經書,只令學生讀教科書,則聖賢之道將由世而泯焉」,新式學堂不再念四書五經,改念教科書。34這是一個大的翻轉變化,如果沒有辛亥革命這個變化,許多事情都不會發生。
在社會菁英的鑑別與篩選上,「轉輒器」把從前基本上以科舉為主的「仕學合一」體制扳到新的方向。革命消滅了王權以後,與王權相關的很多機構也都消失了,這些機構所蘊含的思想或其他意義也隨著消失了。鄭超麟認為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的地方社會,有種「紳士大換班」的現象。35
「轉轍器」的作用發生在各個角落,以1905年的廢科考來說,過去熟讀四書五經、擅長八股的舊菁英突然被掃到邊緣,而在舊軌道中不被看好的邊緣人,有的卻翻身一變成為新菁英。蔣夢麟(1886-1964)《西潮》裡說,小時候在私塾裡那些成績最好,老師認為他將來是最有成就的學生,後來卻因為無法適應日新月異的環境而落伍了。反而像他這種四書五經念不好的,後來反而因禍得福。36科舉廢除後,八股文沒有了市場,四書五經也不用再考了,37從此以後晉身社會精英的渠道完全改變了,如同胡適所說,假使科舉制度至今還在、八股文依然當令,白話文學的運動絕不會有這樣容易的勝利,可見廢除科舉的影響是非常深遠而且關鍵的。另一方面,原來那些阻撓新思想的一些地方士紳也被推到一邊,地方上所謂的「道德鎮守使」也失去了權威。《六十年的變遷》裡面有一段說男主角參加革命成功以後,原來壓迫他們的叔叔伯伯,也要到他家來巴結他,因為他已成為新的精英了。38辛亥革命以後,紳士換成別人做了,到北伐時,紳士又換成奉行主義的黨人做。葉聖陶有一本小說叫《倪煥之》,北伐勢起時,有辦法的人要填一張申請表,弄一張中國國民黨黨證,有這張黨證就變成新的地方紳士。39「紳士
大換班」使得地方菁英換了一批人。
林毓生(1934-2022)先生說,中國傳統的王權是政治、文化、道德、宗教、心靈的一個叢聚(cluster),40而辛亥革命使得政治、宇宙論跟倫理秩序、道德、政治,這些原來綁在一起的叢聚體散開,就像木桶散開一樣,不再能裝水了。皇帝一方面是以治國安民為奉祀神明的要道,一方面祭祀神祇及教導道德為統帥國民之要義,這種思想一直維持至清代。所以當王權消失,這個凝合所有東西的力量就散掉了。
《呂氏春秋》說:「亂莫大於無天子」,董仲舒(179B.C.-104B.C.)在《春秋繁露》的〈原道〉中說:「道之大原出於天」,王權作為「天」在地上的代表,既是政治的,也是道德倫常的。回到秦漢時代的政治思想,儒家文獻中像《春秋繁露》以及《白虎通》,對「普遍王權」 (universal kingship)的特殊地位都有很好的描述。《白虎通》裡面按照宇宙秩序,連飛鳥走獸都列入王權的範圍裡面,所有動物的名字都有原因,譬如飛禽走獸的「禽」,是指可以擒來為用的意思,每一個字音都可以變成有意義的道德解釋,整個宇宙都屬於一個無所不包的系統,而這個系統在人間的中心就是皇帝。王權的消失像是一面牆倒了,但不表示原來舊的事物都消滅了,而是像前面所說的,新的和舊的事物全部衝過去,只是它們的主從位置顛倒了。
過去,我們在思考王權崩潰時,大部分想的都是經書、先秦諸子或者其他文獻中對王權 (kingship)的看法。事實上在1911年之前,人們對於王權的想像,有很大一部分是來自於小說戲曲、通俗文學,或是胡亂的猜測。譬如小說《乾隆皇帝下江南》裡,皇帝幾乎就是天地鬼神的總主宰者,譬如乾隆有難的時候,城隍神會出現,然後調兵幫他解圍。皇帝不是我們一般想像中的「王權」而已,它是包含一切的整體。所有東西都假皇帝之名來宣稱,甚麼東西都要加一個「王」字,皇帝是一切事物的最終統領者。中國人一談到皇帝,就有一種莫名奇妙的感動,「皇帝」、「王權」這兩個詞語是很難用言語去表達清楚的。
日本即不如此,日本天皇仍在,隨時可以發布《教育敕語》之類的文件。《教育敕語》是對於明治以來過度崇拜歐美新潮,忽略日本固有之道德的一個大反逆。《教育敕語》說:「爾臣民,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婦相和,朋友相信,恭儉持己,博愛及眾」、「一旦緩急,則義勇奉公,以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
「王權」在1911年的突然消失、崩潰,它所產生的影響絕對不只在政治層面,而是非常廣泛的。中國的王權制度維持了兩千多年的歷史,中間沒有中斷過,多少改朝換代,也都沒有要取消皇帝的想法。清末劉大鵬說︰「草野人民皆謂上既無君,吾等皆可橫行矣。」 41這句話顯示出王權就是最大的統領者,總管所有的事情,人們都按照風俗習慣而不為非行事,萬事萬物當中都假設上有天,下有皇帝,皇帝統領一切事情,這都是普遍王權所帶來的變化。
在這裡我要再引《鄭超麟回憶錄》中有關下層社會中的幾段觀察:「皇帝沒有了這一點,漳平縣老百姓無論如何想不通。世界怎麼可以沒有皇帝呢?自從盤古開天地就有皇帝」、「但『老爹』背後沒有皇帝,畢竟減損了威風」,42當王權突然在1911年消滅掉,就好像人們突然從銀行或自動提款機中領不到錢了。
四
概括地說,這是一個來回往復的過程。先是觀念的力量打開了政治的水龍頭,然後政治的水龍頭(如辛亥革命)一旦打開,思想的大潮往前衝,可能又打開了別的水龍頭。
先是觀念的力量使得政治朝向種族革命,朝向推倒王權追求憲政共和的方向邁進;接著辛亥革命成了一個思潮的轉轍器,它使得原來最核心的變成邊緣,原來邊緣的變成核心,清朝末年在日本東京等地,以一群「離經叛道」的留學生為主的文章,此後變成全國性的制度,而且要以政府的力量推行下去。原來只是文人腦內所思考的東西,現在變成是日常生活裡的實際,而且制定成為國家的政策。
這個「轉轍器」的變化非常重要,所以我想多引一些材料佐證。梁巨川說:「今開國時大倡反道敗德之事」、「想像從前中國,本係仁禮德義最為著名之國。自民國肇興,特開奢淫縱恣之惡風」、「信以為共和之國,但取人生行樂,無須檢束準繩,於是舉國若狂,小人無復忌憚」、「昔所目為不肖者,今或以為當行」。43或如劉大鵬日記中所說:「叛逆多居要津」、「辛亥大變以來,倫常全行破壞,風氣亦更奢靡。禮義廉恥望誰講究,孝悌忠信,何人實行,世變日亟,岌岌乎其可危」、「學變為新,吾道非特不行,而且為之大晦耳。親聞有毀謗勝人者,謂聖人毒害世人,歷久遠近,乃不以聖人為準則方為大幸事」,44使得新思想價值被定在最核心的位置,舊東西或者消失了,或者退到邊緣。
辛亥革命那一年胡適剛好在美國念書,當時大部分美國留學生是反對辛亥革命的,尤其是學理工科的人,稍微贊成的大多是學文科的,胡適是其中很少數的一位,而且很快就看出辛亥革命的重要意義。45甚至稍後袁世凱當政的時候,美國有很多後來成為民國時期重要人物的留學生也是支持袁世凱的,他們都認為中國需要一個實力的政府,不然會大亂,而胡適依然反對他們。胡適有一篇講辛亥革命的文章說,連皇帝都得走了,哪麼還有什麼事情可以再安然地被認為是神聖的呢?46所有東西都要拿出來掂一掂才放下去。胡適後來在新文化運動時期引用了尼采(1844-1900)的「重估一切價值」作為口號,他並未主張打倒所有舊的東西,但提出要「重估」,這個口號與他先前所說的,既然兩千多年的皇帝制度都打倒了,還有什麼可以視為當然、視為神聖是一脈相承的,假以時日,這個改變的影響可以無孔不入。
以學術方面的影響為例,辛亥革命前後流行「國粹主義」、「國學」等觀念,「國學」這個詞從沒有人能定義得非常清楚,因為它的內容一直在變,晚清的許多刊物如《國粹學報》、《民報》等,裡面都有一個重要主題:討論「國學」跟「君學」的差別。這個討論徹底重整了甚麼是有價值的學術這個問題,它重整了傳統學術的系譜,這個重整運動一直影響到今天。現在我們讀近三百年學術史這方面的書籍會發現,清朝人所編的《國史儒林傳》裡面有二分之一以上的人,現在的學術史都不重視了。也就是說經過清末革命的大變動,經過清末提倡「國學」跟「君學」相對抗之後,學術傳統被大幅翻修了,尤其是對中國傳統學問中涉及專制政治的,幾乎整個清洗和重整。因為對抗專制或正統思想而長期被壓抑的思想與學術,亦在「國學」的大帽子下得到重估,這個重整國學或重整國故的運動產生了異常深遠的影響。
中華民國作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這個新的「國體」一旦確定下來,與後來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是有密切關係的。如前所述,我們從復辟時代很多相關文獻可以看出當時不少軍閥都反對回到原來的君主制,表示民主共和這頂帽子已經戴上了,所以即使後來有無數的來回動盪,但是一個大致方向已隱然在那裡。因為這頂帽子已經戴定了,但北京的官場風氣依舊,尤其是受了張勳復辟的刺激,使很多人覺得文化上並沒有相應的改變,於是人們呼籲在這樣的國體之下,思想文化上要有一個相應的變化。我曾經撰寫一篇題為〈思潮與社會條件〉的論文,47當中就談及五四新文化運動與辛亥革命的關係。在新文化運動的相關文獻中,可以一再看到許多人批評民國是一個掛了假的招牌的「民國」,名為民主共和,其實文化跟思想都還在君主時代。所以新文化運動時期人們才會說:「要想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革新的基礎」。48如果不從文化上徹底改變,永遠都會有另一個張勳、另一個復辟。所以新文化運動有一個很重要的源頭,來自於辛亥革命所定下的國體。兩者之間的關係是密切的,但不是簡單的因果關係。
思潮觀念與政治互相影響,辛亥革命前後形成的思潮與觀念,不僅支配了後來的政局,也反過來受到政治革命力量的衝擊與引導。到底是政治力量引導了觀念的形成,還是觀念促進中國的政治變革?我認為這是兩個界面之間不斷地互為關係、互為決定。
最後我想以魯迅的話作結。魯迅(1881-1936)在《阿Q正傳》裡講到,「(阿Q)知道革命黨雖然進了城,倒還沒有什麼大異樣」,49在經歷了辛亥革命之後,實際上阿Q生活的「未莊」似乎沒什麼改變。我在前面提到過,革命把「牆」推倒之後,新的舊的都衝過去了。舊的力量仍以其原狀或各種變體存在著,雖然表面上「未莊」沒有什麼改變,但很多東西事實上已經悄悄改變了,總統都已經是選出來,人們心裡雖然都不想這個東西,但口裡都說要民主自由。
袁世凱當選總統時的誓詞:「世凱深願竭其能力,發揚共和之精神,滌蕩專治之瑕穢」。當籌安會大起時,許多輿論痛斥它是與原來國體相反,實屬大逆不道。袁世凱宣誓時口口聲聲說要維護共和憲制,軍閥曹錕想當總統也得要透過賄選,證明表面上沒有變,但事實上已經變了。成為哲學家奧斯汀 (1911-1960)所謂的 “Illocutionary act”(「做言」或「話語施事行為」),革命所定下的種種形成一個又一個「施事話語」(performative utterance),50人們奮力向它們趨近。所以即使一時之間是假革命,一時之間沒有什麼實質改變,但變化的可能性存在著,它有造成一次又一次微妙變化的可能性。雖然這些變化歸根結底不可能是徹底的,而且這些變化也可能與原初的方向不同。且讓我們看一下鄭超麟在回憶錄中是怎麼說的:「以後徹底的革命,就是從那次不徹底的革命發展下來的。形式上、稱謂上的改變,孕育著後來實質上的改變」。51如果讓我們參考John Dunn(1940-)的《近代革命》(ModernRevolution)一書,可以發現並不是所有的革命都是邁向激進、開放的。墨西哥的革命是邁向保守、內向的(inward、backward);相對而言中國革命所追求的方向與美國革命比較接近。美國革命帶有濃厚的以羅馬共和為師的色彩,52美國首任總統華盛頓在功成之後退隱到農莊,就是師法古羅馬大將功成之後退職莊園的精神。53美國革命之後,在思想、文化及社會方面的影響非常廣泛:如敵視任何階級,不願屬於任何人之下,不願為僕人,社會看重自己成材之人;不再為固定人生產,主人變成雇傭人,教育大興,人們努力使得思想與舉止符合共和政府之理想;各種學會、刊物興起、印刷氾濫等等。54
辛亥革命儘管曾經假途於一種返古的熱情,故錢玄同在辛亥革命成功後,穿著古代的深衣去政府上班,但很快地發現其不合時宜。因為整個時代的思潮是朝向共和憲政、自由、民主、平等、開放的方向。
辛亥之後,另一次思想變化是五四。以五四後的思想圖景為例,在五四前後還只是一群又一群青年學生的理想主張,到了1930年代,居然成了各階層共享的思想質素。在這裡我仍想以一份民調性質的文件為例。1933年的《東方雜誌》向全國各階層發出兩百多份調查,從140份回函發表了244個夢想,便可看到十多年前「理想的」主張已經成為十多年後思想界的主流,甚至建立新中國的政綱。 55雖然當時《東方雜誌》的主編胡愈之(1896-1986)是左傾人士,但回答的人士基本上包括各種政治色彩,我以為從中可以看出當時各層人士大致的政治思想圖像。其中較常出現的「夢想」,有高度交集性,譬如希望「辯證唯物主義」勝利。而上述夢想,其實是從五四前後開駛的各種新思想,過了十多年,便在1930年駛在一起,成為當時政治思想的公約數,並進而在1940年代後期決定了中國的命運,此後原先與馬列並駛的其他火車被曳入廢棄廠了。
以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為例,北伐前的基金會組織一直都是由親北洋政府的學者主理其事,直到北伐之後胡適才有機會成為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董事,所以基金會後來跟近代新學術的發展變得非常密切。56如果不是北伐,它的董事組成結構可能不會改變,這個基金會也就不大可能與新學術的建立如此相關。所以「政治」作為一個介面,它的轉動會改變很多思想和文化的現象。辛亥革命、北伐、五卅慘案、九一八事變、1949年國共政權輪替等都是如此,不只在政治上重要,在思想上也都具有重要的意涵。反過來說,「觀念的勢力」有時也對政治事件產生了樞紐性作用。
結論
本文強調思潮與革命、革命與思潮,在時代的發展過程中交互成為對方的轉轍器。清代最後幾十年,新思想愈堆愈高,好像水箱積貯了愈來愈多的水,終於有人轉開水龍頭,思想的大潮遂造成政治上重大的改變——變法、革命都是。過去我們之所以忽略了上述重大政治體制革命在思想上的重要性,主要是因為一種「後見之明」,認為清末以來,許多思想元素是一氣相連的,它們在清季已經出現苗頭並慢慢擴張,在民國初年接續發展。所以認為一切都是線性積累的成果,而忽略了政治體制與思想運動兩個介面互相轉接的現象;忽略了同一脈絡的新思想在「轉轍」之前可能是零星的、邊緣的,甚至是「大逆不道」的,經過新政治體制的「轉軌」,藉著官方的制度和機制去落實、 擴散、顛倒正面,成為領導性的論述。
從 另 一 方 面 看 , 思 想 運 動 如 果 沒 有 產 生 「 建 制 性 遺 產 」(institutional legacy)(不管是形成社團或政制),那麼某種思潮也可能因為沒有制度性的保證而旋起倏滅。上述幾個方面,都是我們從史學的角度討論思想如何產生現實力量時所不能忽視的。
本文注釋:
1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黎洲遺著稾刊》(台北:隆言出版社,1969)(下),頁6。
2 柏格森,王作虹、成窮譯,《道德與宗教的兩個來源》(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頁169。
3 Quentin Skinner,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Vol. 2, pp. 20-113.
4 〈由下而上的思想史〉將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
5 《美國歷史評論》曾經專門為歷史中的“scale”問題做了一個專號。Sebouh David Aslanian, Joyce E. Chaplin, Ann McGrath, Kristin Mann,“AHR Conversation How Size Matters: The Question of Scale in Histo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ume 118, Issue 5, December 2013, pp. 1431-1472.
6 王汎森,〈嘉道咸的政論〉,2021年政大「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中國思想的新傳統時代》第三章,書稿出版中。
7 有關這方面簡要的論述可參考:劉志琴主編,《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遷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第三卷,頁167-172、212-214、278-279。
8 陸丹林、丁士源,《革命史譚. 梅楞章京筆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150。
9 康有為,《康南海自編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11。
10 梁啟超,〈論時代思潮〉,《清代學術概論》(台北:臺灣中華書局,1978),頁1。
11 杜威,〈新人生觀〉,收於袁剛、孫家祥、任丙強編,《民治主義與現代社會:杜威在華講演集》(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頁266。
12 Alexis de Tocqueville, The Old Ré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Stuart Gilbert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1955),pp. 138-148.
13 見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頁289。
14 《十種影響中華民國建立的書刊》由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黃克武所長與潘光哲副研究員主編,這十種書分別是:譚嗣同《仁學》、梁啟超《新民說》、孫中山《三民主義》、《《民報》《新民叢報》論戰選編》、鄒容與陳天華的《《革命軍》《猛回頭》《獅子吼》合輯》、章太炎《太炎革命政論選》、嚴復的《天演論》、劉光漢(師培)與林獬合作完成的《中國民約精義》、金松岑《女界鐘》、宮崎滔天原著,章士釗「譯錄」的《大革命家孫逸仙》。
15 李六如,《六十年來的變遷》第一卷(北京: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頁164-165。
16 金寶森,〈《揚州十日記》證訛〉中引謝國禎《清稗類鈔》第一冊的前言說:「又因史料尚未大量發現,但憑個人信筆出之,這也難怪」,《滿族研究》第四期,1989,頁29。
17 參見拙著〈「心力」與「破對待」〉,收於王汎森,《執拗的低音: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台北:允晨實業出版公司,2014)。
18 Gordan Wood著,傅國英譯,《美國革命的激進主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頁95。
19 Martin Bernal, Chinese Socialism to 1907 (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6).
20 蔣夢麟,《西潮》(台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1994),頁86;馮自由《革命逸史》特別記述了這位「野雞大王」徐敬吾的故事,馮自由,《革命逸史》,集1 (台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1969 〔台1版〕),頁179-180。
21 孫文,〈民生主義第二講〉(民國十三年八月十日),《三民主義》 ,收於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訂:《國父全集》(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3),第一冊,頁 190。
22 阿英,《晚清小說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146。
23 浙江省博物館編,《黃賓虹文集.雜著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30。
24 參見宗方小太郎著,馮正寶譯,《壬申日記 一九一二年中國之政黨結社》(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127。
25 陸丹林、丁士源,《革命史譚 梅楞章京筆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45、49。
26 宗方小太郎的《一九一二年中國之政黨結社》中提到,大體而言它們以傾向同盟會居多,但舊官員多同情共和黨。但在1920、30年代幾本我們比較熟知的政黨史中,這些小黨派便消失得無影無蹤了。宗方小太郎著,馮正寶譯,《一九一二年中國之政黨結社》,頁247。
27 其中當然也有反對民國、反對革命,如由道學派所組的「政益會」等。宗方小太郎著,馮正寶譯,《一九一二年中國之政黨結社》,頁176。
28 宗方小太郎著,馮正寶譯,《一九一二年中國之政黨結社》,頁165。
29 見王世儒編纂,《蔡元培先生年譜》(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8)上冊,頁116-117。
30 周作人,《知堂回想錄 .中》(台北:龍文出版社,1989),頁424。
31 劉大鵬著,喬志強標注,《退想齋日記》(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頁184。
32 鄭超麟,《鄭超麟回憶錄》(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頁22。
33 梁濟,《梁巨川遺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2008),頁55、66。
34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頁179。
35 鄭超麟,《鄭超麟回憶錄》,頁115、119。
36 蔣夢麟,《西潮》,頁43。
37 這裡應該稍加說明的是新舊制度之變,並不一定立即造成完全的影響,譬如戊戌變法、廢除科舉,推廣新式學校,但學校與科舉有一段重疊並行的日子。但當時很多人是買雙重保險的,一方面上新學堂,另一方面還準備科舉,因為在1905年廢掉科舉之前曾有過一次動盪,宣稱要廢了又沒有廢,使很多人產生買雙重保險的心理。很多人以為科舉還會回來,但辛亥革命成功則明示它永遠不會再恢復了。那些以前白天要上學堂,晚上要去書塾補習的人,從此完全死心。
38 李六如,《六十年的變遷》,頁333。
39 葉聖陶,《倪煥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頁220。
40 詳見林毓生,〈「五四」式反傳統思想與中國意識的危機——兼論「五四」精神、「五四」目標與「五四」思想〉,《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增訂本)》(北京: 生活 . 讀書 . 新知三聯書店, 2011) ,頁178-179。
41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頁179。
42 鄭超麟,《鄭超麟回憶錄》,頁7。
43 梁巨川,《梁巨川遺書》,頁66、71、75-76。
44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頁177、182。
45 參考:周質平,〈胡適論辛亥革命與孫中山〉,《現代中文學刊》,
2011年期6(上海:2011年12月),頁14-17。
46 Hu Shih, “The Memory of October Tenth”,收入周質平主編,《胡適英文文存》(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5)第二卷,頁786。
47 王汎森,〈思潮與社會條件——新文化運動中的兩個例子〉,收入余英時等著,《五四新論:既非文藝復興,亦非啓蒙運動》(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9),頁103-144。
48 胡適,〈我的歧路〉,《我們的政治主張》原收於《胡適文存》第二集卷三(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頁65。
49 魯迅,〈阿Q正傳〉,《魯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頁517。
50 J. L.奧斯汀(J. L. Austin),《如何以言行事:1955年哈佛大學威廉.詹姆斯講座》(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尤其是第一、八、九講。
51 鄭超麟,《鄭超麟回憶錄》,頁6。
52 John Dunn, Modern Revolution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nalysis of a Political Phenomenon (Cambridge: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47-71.
53 Gordon Wood, “The Legacy of Rome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The Idea of America: Reflections on the Birth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1), pp. 71-73.
54 Gordoan Woo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2002), pp. 117-129與劉志琴主編的《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遷錄》第三冊中所描述的辛亥革命之後的各種文化現象相比,可以看出兩者之間的相似性。劉志琴主編,《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遷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55 1932年11月1日,上海《東方雜誌》策畫了一次徵求「新年的夢想」,向全國各階層人士發出徵稿函四百份,最後140餘位人士發表了244個夢想。這份調查是受九一八、一二八、淞滬戰役的刺激而起的。
56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資金,總數約達總計約美金1250萬元,相當於一個銀行的規模,近代很多高等學術機構、大學都曾接受過它的資助。
王汎森,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現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研究領域以十五世紀以降到近代中國的思想、文化史為主,近年來將研究觸角延伸到中國的「新傳統時代」,包括宋代以下理學思想的政治意涵等問題。著有《權力的毛細管作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