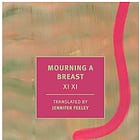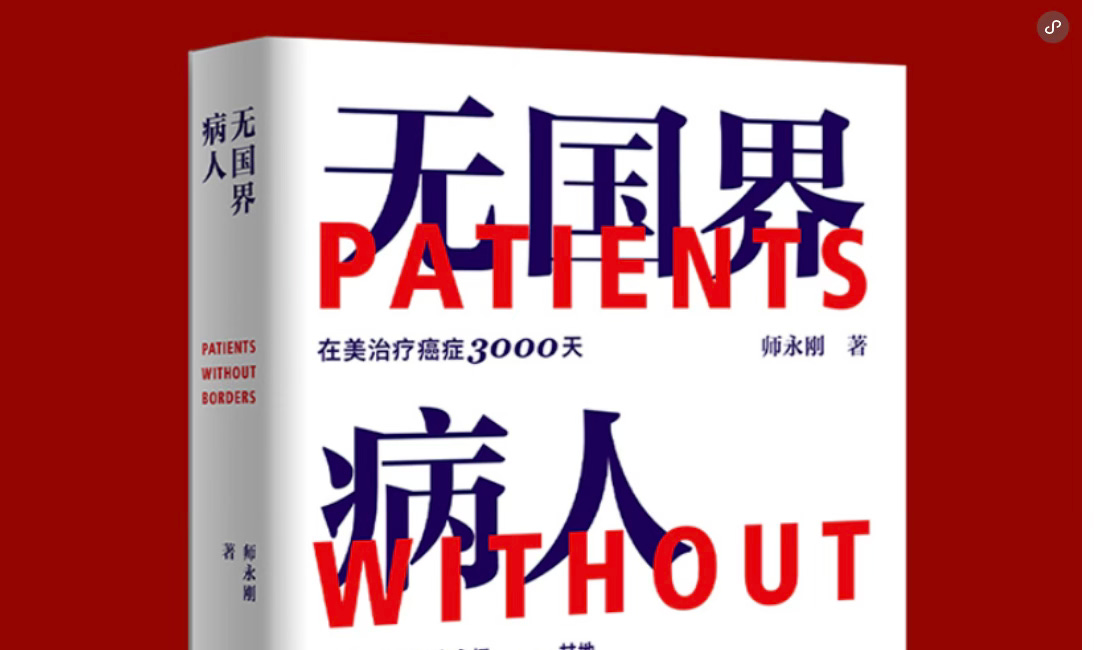Mimi Cheng | 《哀悼乳房》書評(A Brave—But Oddly Endearing—Memoir about Surviving Breast Cancer)
In “Mourning a Breast,” the Hong Kong writer Xi Xi tells a story that defies all expectations.
編者按:2022年12月18日香港作家西西去世。她的自傳《哀悼乳房》英文版於2024年7月9日由紐約書評出版。學者Mimi Cheng為英文版《Mourning a Breast》撰寫書評。書評原文為英文“A Brave—But Oddly Endearing—Memoir about Surviving Breast Cancer——In “Mourning a Breast,” the Hong Kong writer Xi Xi tells a story that defies all expectations.”,發表於The Washington Post online version, July 7, 2024。經作者授權,波士頓書評翻譯為中文,譯者程映虹教授。
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乳房部位發現一個惡性的、異己的、不斷擴張的組織,何嘗不是借用身體語言的一種隱喻。— Mimi Cheng
今天還推薦張小蛇為師永剛《無國界病人:我在美国医院治疗癌症3000天》一書所寫書評。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写道,癌症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疾病,更是一种巨大的、社会的和政治范畴的疾病,一种充满惩罚意味的疾病。
香港作家、詩人西西在介紹她的書《哀悼乳房》時,直白地說:“這是一本關於乳房的書。”1989年,52歲的西西被診斷出患有乳腺癌。此後的幾個月裡,她不但經歷了乳房切除手術,術後的放射線和激素治療,同時還在照料年邁患病的母親。在這本1992年初出版於台灣的書裡,她超越各種文學流派,對自身的這些遭遇做了獨特的探索性表達。Jennifer Feeley將它忠實地翻譯成英文,今年由New York Review Books出版。
這本書結合了內省和智慧,對經受創傷的身體和轉型中的社會做了多棱鏡式的富有情感的描述。出版社將她的書介紹為半自傳小說,但西西可能不屑這種基於文學體裁的定位。她很可能會告訴讀者:不要理會那些將文學作品在閱讀之前先將其分門別類的建議。在序言中她說:“我想,尊貴的讀者,您想怎樣分類就怎樣分類吧,這次,隨你的意”。她甚至告誡讀者,“花太多的時間通讀全書也許得不償失。最好是隨便翻幾段,選自己認為有趣的就行”。
我們可以把這些話當作西西的謙遜。雖然每一章的標題都很奇特突兀,讓人好奇,例如“三打白骨精”和“蔬果傳奇”,它們的內容也都可以做為獨立故事來看,但我們還是值得花時間讀一下全書,讓自己沈浸在她完整的世界裡。
故事始於一個公共泳池的女更衣室。西西自稱熱愛游泳但動作笨拙。此刻站在其他女人旁邊,自己生命將盡的想法和充斥四周的感性的活力在她心裡交替。 「嘩啦啦的水流聲在我耳邊迴響,彷彿我能聽到肥皂擦在女人皮膚上的聲音。肉質柔軟,水分充盈,還有肥皂的甜香。我什麼時候可以再去游泳?我不知道。我無法猜測、理解、探索或預測我的命運。”
在接下來的章節中,某一天,我們和她一起進入檢查室和外科病房,穿越病區改造中的浴室,陪伴她散步。在活檢當天,我們看到她帶了四本法文、中文和英文版的《包法利夫人》,在醫生進來前對比閱讀不同的版本。另一天,她又是一個都市文化漫遊的嚮導,帶領我們穿越香港鼎鼎大名或者名聲稍遜的地標和景點。她會在拱廊裡停下來,凝視一家內衣店閃閃發光的櫥窗,不由得好奇:“有沒有一家出售單只胸罩的內衣店呢?”但轉念一想,那種貨品即使有的話也不會陳列在這種地方,於是便掉頭而去。
《哀悼乳房》拒絕癌症回憶錄的常見套路。西西沒有在活檢診斷結果和病情初步緩解之間安排一段與病情英勇搏鬥的單一情節,使用陳舊的、似乎避免不了的隱喻描繪一場與身體的戰爭。她描寫的是在這個階段自己學會如何傾聽,而不是如何堅持鬥爭。以前“我對自己的身體一無所知,” 而現在,「我的身體開始越來越頻繁地說話,抗議因罹患絕症而遭遇的一系列的不公,好像我內心發生了一場革命。」她也坦承是對語言和文學的熱愛以及朋友和社區的關心支撐了她。
西西的寫作最感人的是她採用了意識流風格,用生動的、零碎的片段反映了這種疾病的複雜病因和災難性影響。乳房切除術後的第二天早上,她被切除的乳房被裝在塑膠袋裡放在她的床邊。她稱之為「我的標本」。當她試圖描繪眼前這個物事時,她的句子卻變得嘈雜而刺耳。十七世紀志怪小說《聊齋誌異》和佛學經典《心經》裡互不相關的情節忽然來到眼前,然後她的文字又跳躍到住在以前她家附近的一個連環殺手,新聞裡說他將受害者的乳房保存在罐子裡。她試圖在自己的身體和思維之間找到和諧,然而寫出來的一段話卻變成了各種想法和念頭交錯混雜的漩渦。
西西的智性和坦承與蘇珊·桑塔格和奧德麗·洛德的癌症敘事如出一脈,但她的文學風格卻最接近安妮·博耶,後者在獲得2019年普立茲獎的《不死之身》中描繪了一種特別具有侵害性的乳腺癌。和《哀悼乳房》類似,博耶的故事由一系列零碎的意識片段組成,違背通常的敘事範式。但二者的區別是,博耶的故事充滿了對癌症給患者帶來的不公和喪失尊嚴的憤怒,而西西的描寫卻往往是輕鬆的。在“不是故事”一篇裡,她羅列了一系列從新聞裡得知的有關癌症的趣聞,雖然它們之間毫無關聯。最後一則花絮是一種形狀像癌細胞的胖乎乎的兩棲動物,看上去“又扁又圓,就像一隻紅豆沙餅。”有些人戲稱之為“癌細胞青蛙”。西西困惑不解地說:“這個名字很奇怪,但青蛙聽起來卻迷人又可愛。”。
西西是一位被讀者喜愛的作家。她的作品包括短篇和長篇小說、詩歌和散文,在香港文學中佔有重要一席。《哀悼乳房》是中文世界裡從女性視角敘述癌症最早的作品之一,所以在她的作品中非常特別。她在序言中說,在文化上,“中國人從來就是一個諱疾忌醫的民族。總把疾病,尤其是這種病隱瞞起來,當成一種禁忌。到頭來,有病的不單是肉體,還是靈魂。”九十年代初正逢香港的乳腺癌高發期,西西這本書的問世幫助大眾打破了對這種疾病的禁忌。
西西寫作此書時,香港也正處於歷史上一個關鍵時刻。面對1997年就要到來的主權移交(從英國回歸中國),很多香港人準備移民,其中包括西西的家庭醫生。更多的人則表達了對這座城市未來的焦慮和擔憂。此前香港學生已經走上街頭,表達了對1989年中國學生要求民主的運動的支持。西西書中對這些政治事件做了隱晦的暗示。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乳房部位發現一個惡性的、異己的、不斷擴張的組織,何嘗不是借用身體語言的一種隱喻。
那麼,我們最終能從西西的故事裡得到什麼啟發呢?可能最有意義的是她的一個簡潔明瞭的想法:善待自己,珍惜親友。“和別人相比我有什麼呢?財富、美貌、知識、健康?這些我都沒有,可是我有朋友。” 2022年,八十五歲的西西在平靜中因心臟病離世,臨走時身邊環繞著親友。今天我們得以傾聽她那依然如舊的聲音,就像一位慷慨而善良的老朋友。
Mimi Cheng is a cultural historian and writer. She is at work on her first book.
張小蛇 | 疾病与命运之间,藏有无法洞悉的秘密
作者: 师永刚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副标题: 我在美国医院治疗癌症3000天 原作名: PATIENTS WITHOUT BORDERS 出版年: 2022-8 “疾病就像旅途,必须在路岔口做出决定。” 01苦难来临 40岁,正值壮年。 事业有成,有一连串带有光环的Title:知名作家、媒体主编、畅销书制造者……身体健康,每天保持游泳锻炼的习惯,能适应高强度的工作;家庭和睦,可爱的孩子刚刚出生。新生和希望,一切都奔向美好。 然而,一次常规的体检,将上述一切美好击得粉碎。——身体里发现一个大肿瘤,且确证是恶性的。“为什么我会得这种病?这种病是什么?我还能活多久?孩子与妻子怎么办?……”“苦难的来临总是静默的、迅疾的、锋利的、倾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