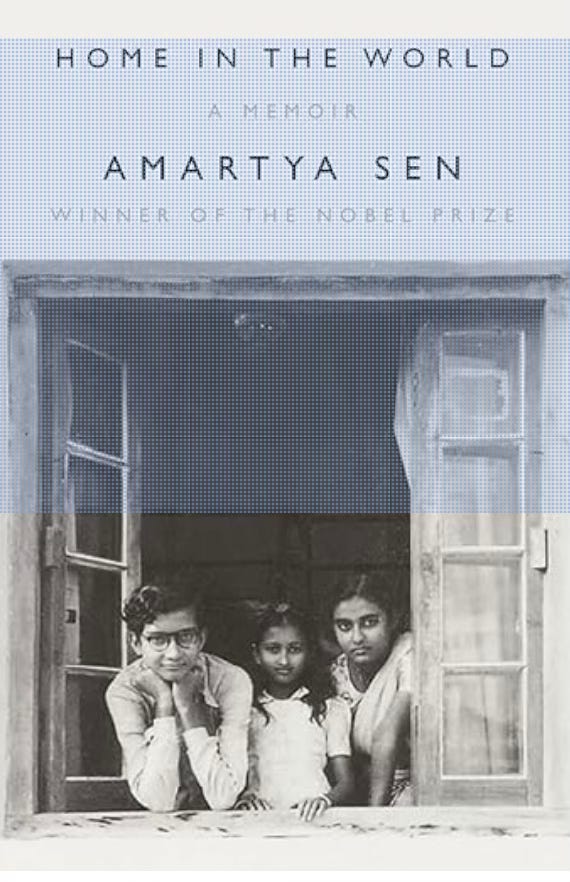Amartya Sen,Home in the World: A Memoir,2021,Penguin Books Ltd
許多國際化的知名學者在漂泊一生後,都會在晚年回憶錄裡對自己身分認同進行探索。 例如薩義德回憶錄《格格不入》,又如這兩年很火爆的王贗武回憶錄《家園何處是》。 而諾貝爾獎得主、印裔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在2021年出版的回憶錄《世界為家》(Home in the world)也是如此。
於我而言,阿馬蒂亞.森的形象既熟悉又陌生。 因為我曾經讀過他的十多本書,不計其數的論文,內容涵蓋社會選擇、理性選擇、發展經濟學、政治哲學、認同研究、印度文化等,似乎跨越了各個領域。 他的思想與經濟學家哈耶克、斯拉法、阿羅、索洛、巴格瓦蒂、斯蒂格利茨,哲學家以賽亞.伯林、羅爾斯、納斯鮑姆等的 研究都構成了深刻對話。 經濟系學生可能是在社會選擇這門課上讀到他,而哲學系學生會在研究羅爾斯《正義論》時讀到他,發展專業的學生則會在「能力方法」這個主題下讀到 他。
阿馬蒂亞.森簡直無所不在,但我又不知道如何界定阿馬蒂亞.森。 把他說成「諾貝爾獎得主、印裔經濟學家」似乎是個簡單又討巧的方法,而他真正的關涉不止於此。 當我訪問印度時,曾造訪森的故裡聖地尼克坦(Santiniketan)。 當地人指給我看他的房子,「阿馬蒂亞.森小時候就住在這裡」。 但我跟一些印度學者聊起他的時候,大家都紛紛搖頭,「他不能算是印度經濟學家,也許應該算英國經濟學家或美國經濟學家,反正他在劍橋和哈佛都有教職, 但他不能算印度經濟學家」。
所以我看到《世界為家》這本400多頁的回憶錄出版,深感興奮。 似乎以前讀到、聽到的無數關於阿馬蒂亞.森的碎片在逐漸融合,成為一個更豐富更立體的森。 對我而言,這是一本令人著迷的傳記,不過它也許會讓另一些讀者失望。 因為森在整本書裡都在寫自己30歲以前的經歷和故事,最多延續到1960年代初,當時他只是個剛畢業的青年學者。 森沒有在書裡介紹那一系列讓他獲得諾貝爾獎的論文,也不關心那些以他名字命名的經濟學定理,甚至森不想多談自己後來的研究經歷,反正論文和書都已擺在 圖書館。
我們讀了這本書會發現,後來的一切,原來早就隱藏在他的童年和青年時代。
一 青年時代
阿馬蒂亞.森是哪裡人? 把這本書反覆讀了幾遍,我才建立一些概念。 1933年,森出生在距離加爾各答不遠的孟加拉小城聖地尼克坦,這也是印度思想泰斗泰戈爾長期生活的地方,字面上意義就是「和平鄉」。 森的父親在也不遠的大城市達卡的大學裡教化學,所以森出生後兩個月後又回到達卡,今天的孟加拉國首都。
在森很小的時候,父親就帶著他去緬甸工作。 森童年最早記憶之一就是被一艘船的巨大鳴笛聲驚醒。 父母安慰他,他們坐的船正在離開印度,駛向緬甸。 在緬甸的曼德勒待了兩年後,1939年,森又跟著父母回到達卡。 當時無論達卡、加爾各答、仰光、曼德勒或聖地尼克坦,在地理上都是英屬印度(British Raj)的領土,所以他的父母並沒有離開自己的國家。
森回到達卡生活不久,國際情勢又發生突變。 1941年,日軍佔領緬甸,逼近孟加拉。 森的父母趕緊把8歲的森送回聖地尼克坦,要他和外公外婆住在一起。 森的父母相信堅信,日軍有可能轟炸達卡或加爾各答這樣的大城市,但不會有心思去轟炸聖地尼克坦。
事實確實如此。 聖地尼克坦不但保護了森,也對森的思想產生了深遠影響。 他自己回憶,「我認為在聖地尼克坦度過的三年是我一生中最富有成效的三年...聖地尼克坦讓我第一次看到了印度和遠東藝術的輝煌。在此之前, 我完全被西方的藝術、音樂和文學所左右。聖地尼克坦使我成為東方和西方的綜合產物。”
森在聖地尼克坦經歷了可怕的「孟加拉大饑荒」。 這與日軍入侵孟加拉有關,同時也是森後來關注飢荒問題的起點。 二戰結束後,森與父母從達卡搬回了加爾各答,隨後是1947年的印巴分治,從此加爾各答與達卡分別屬於了兩個國家。
1951年,森前往加爾各答的總統學院(Presidency College)求學,專業是梵文和數學,似乎這才是森真正感興趣的學問。 但是森也對現實問題感興趣,就在朋友的推薦下接觸了經濟學。 正是這一年,肯尼斯·阿羅的代表作《社會選擇與個人價值》在美國出版。 和森一同研讀經濟學的友人從書店借到這本新書,借給森讀了幾個小時。 森被阿羅的「不可能定理」完全迷住了,從此明白自己以後該做什麼。
1952年,森被診斷出患有口腔癌,他不得不接受非常高劑量的輻射來治療。 但是一年之後,他的口腔癌奇蹟般地被控制住。 第二年,森就抓住一個機會離開印度,前往英國劍橋的三一學院,這是他心目中唯一適合研究經濟學的地方。 在那裡,森很快就成長為一個有能力獨立進行研究的經濟學家,並且做出一系列重要工作。 1956年,森返回印度,此時他已是個成熟的經濟學家。
傳記差不多就在這裡結束。 森後來的經歷,學界已經比較熟悉。 他從1960年代開始,在許多國家工作和訪問,在印度也有教職;1970年代,森回到英國,先後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和牛津大學擔任教授;1980年代,他又前往哈佛教書,此後就 在美國生活。 到了1998年,森當選為三一學院院長,同年獲得了諾貝爾獎。 有人說他半年生活在英國,半年生活在美國,不時回印度,或偶爾出現在世界其他角落。
但是這些經歷都沒有出現在森的回憶錄裡。 對森而言,這些不太重要,重要的還是一切的源頭,是他童年時的那一連串經驗。
二 思想的源頭
聖地尼克坦對所有孟加拉人似乎都有特別的意義,對森也不例外。 因為這裡是泰戈爾的故鄉。 森的父母兩系家族都與泰戈爾家族有深刻的聯繫,稱得上是世交。 泰戈爾家族是孟加拉豪門之一,他的祖先從十七世紀末就成了東印度公司的代理經紀人,家族財富隨著東印度公司的成長而增長。 到十九世紀,整個家族已經堪稱是加爾各答週邊地區的美第奇家族。
泰戈爾是父母的第十四個孩子,從小接受極佳的國際教育,最後成為一個通才,寫作、繪畫、音樂無一不精。 泰戈爾尤其喜歡導演戲劇,並且帶領團隊在加爾各答等各個城市演出。 森的母親阿米塔不僅在泰戈爾位於聖地尼克坦的學校學習舞蹈,而且經常在泰戈爾的舞劇中擔任主角。
泰戈爾一直聖地尼克坦搞教育。 除了捐出所有家族土地以外,他也把一切國際資源導向這座小城。 1913年,當地的委員會當時正在討論,如何為學校所需的一套新的排水系統尋找資金。 泰戈爾突然收到一份來自斯德哥爾摩的電報,告知他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泰戈爾用一種古怪的形式公佈了這個消息,他對委員會說,"我們剛剛找到了建造排水溝的資金"。 在這些錢的支持下,1921年,泰戈爾正式創辦了國際大學。
森很小就認識泰戈爾,甚至他的名字都是泰戈爾起的。 每次他在聖地尼克坦時,都會跟隨祖父母或母親一起去探望那個可愛的大鬍子男人。 泰戈爾於1941年8月去世。 當時森還在達卡的學校裡讀書。 校長匆忙召開了學校大會,向全體學生宣布了這一不幸的消息,並宣布當天暫停教學。 森很詫異,他趕回家裡,就想從父母那裡了解,為什麼這個熟悉的老人對世界竟如此重要。
幾個月後,森回到聖地尼克坦,開始在泰戈爾創辦的學校就讀。 這所學校有一個突出的特點,沒有教室。 泰戈爾特別反對四面有牆壁的教室,認為那會禁錮學生的精神。 只要不下雨,泰戈爾就願意與學生在田野裡散步,或是在樹下圍坐,一邊探討學問。 校園裡有很多幾人合抱的大樹,周圍修了一圈水泥座椅,這就是大家的教室。 當然有些教室更考究些,上面修了遮雨蓬,師生總是在這種開放空間裡自然地學習和討論。
國際大學的傳統是,老師坐在一棵樹下不動,學生們圍著這個老師聽完課後,換一棵樹,再去聽其他老師講課;而又有一批剛來的學生跑到這 棵樹下聽課。 所有的學習都在一棵棵不同的树下完成。直至今天还有一些老师保持着泰戈尔的作风,坚持在大树教室里讲课。这幅场景被做成画像,如今展示在圣地尼克坦火车站里。
自由是圣地尼克坦的核心精神。泰戈尔不喜欢学生的思想被禁锢在自己的社群。他认为,无论宗教还是国籍或是其他方面,都不应该束缚住学生。国际大学是一所进步的、共同教育的学校,必须拥有最广泛和最包容的课程,包括接受亚洲、非洲、欧洲不同地区文化的浸润。泰戈尔力邀中国学者谭云山长期在此执教,把这里变成中印文化的交汇点。此外,这里也陆续培养出如印度前总理、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奥斯卡奖获得者、大导演罗伊(Satyajit Ray)等各界名人。
圣地尼克坦虽是一个偏远小镇,但却是在思想上足以与伦敦、纽约抗衡的文化中心,汇聚大批拥有国际视野的孟加拉思想者。森在这里能随时读到欧美最新的学术著作,与伙伴讨论重大学术难题,也在这里见到过来访的蒋介石、甘地、罗斯福夫人等世界政要。从那时开始,森已经做好走向世界的准备。
事后来看,很多影响世界的思想都源于圣地尼克坦。后来森在英美各国与其他学者交流,介绍自己在圣地尼克坦与伙伴们讨论过的问题时,很多人都大吃了一惊。比如森在书中提到前辈学者马哈兰诺比斯(P. C. Mahalanobis)。他们两人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对森而言,马哈兰诺比斯不仅是一个亲密的家庭朋友,也是一个伟大的圣地尼克坦人。他曾作为泰戈尔的学术秘书工作过几年,对于一个处于创造力高峰期的独立学者而言,这是一个相当特别的就业选择。
泰戈尔过世后,马哈兰诺比斯回到自己的专业研究方向,统计学。马哈兰诺比斯很快在加尔各答创办了一所重要的学术机构:印度统计研究所。他把该研究所建成为世界领先的统计研究中心之一,并且为印度独立后的经济发展制定了“五年计划”,堪称印度计划经济之父。1950年代,马哈兰诺比斯曾经访华,介绍印度的“五年计划”,这也是中国采用“五年计划”的开端。
三 从经济学到伦理学
阿马蒂亚.森如何真正走上经济学的道路,我对此非常好奇,始终抱着这个问题来读这本书。根据森的回忆,他是在加尔各答的河边,看着恒河浑浊的颜色,开始萌生想法。正是在加尔各答,森读到了亚当-斯密关于河流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的分析文章。斯密认为十八世纪的孟加拉在经济上非常繁荣,他认为这不仅与当地训练有素的工人的技能有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与河流和航运带来的机会有关。
"那些伟大的海湾,如欧洲的波罗的海和亚得里亚海,欧洲和亚洲的地中海和欧新海,以及亚洲的阿拉伯、波斯、印度、孟加拉和暹罗的海湾,将海上贸易带入那个伟大大陆的内陆地区。”森意识到,孟加拉地区相较于整个印度次大陆,也处于类似的位置之上,使得孟加拉成为印度经济和文化中心。
但是进一步思考印度现状,森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触到一些重要问题。森没有想过回避,而是用整个人生来解答童年时的诸多困惑。他在反复研读“阿罗不可能定理”的时候,就必须思考它对于民主政治的致命打击。新独立的印度正努力成为一个成功的民主国家,民主政治的一致性和可行性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到底能不能有民主的一致性,还是说民主只是一个虚幻的东西,在实践中难以完全实现?
在当时加尔各答的许多学术讨论中,阿罗的观点得到了很好的宣传。但是阿罗的论述极为复杂,需要在数学上加以提炼和推广。这就是森后来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他不但系统化地归纳了阿罗的研究,也推出了自己版本的“不可能定理”,从而奠定了社会选择理论的基本框架。
而森必须面对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马克思。不管圣地尼克坦还是加尔各答,都是印度左翼思想圣地,拥有无数非常了不起的马克思主义者,至今仍然如此。森回忆说,“马克思在我晚上在基督教青年会吃完饭后的时间里占有相当大的份额,尽管他不得不与其他人竞争,包括亚里士多德、亚当.斯密、玛丽.沃斯顿克拉夫特以及约翰.斯图尔特.密尔”。
马克思主义虽极大地影响了森,也使得森在一生中都对左翼思想抱有深刻的同情,但是森最终没有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他来说,实在还有太多的其他思想来源,并非都与马克思主义的信条相一致。他之所以选择剑桥,就因为那里有数量最多同情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经济学家。
森在加尔各答学习期间,已经熟读对于马克思正反两面进行评价的经济学著作。萨缪尔森就是其中森非常喜欢的一位。日后,他们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虽然学术立场并不一致。萨缪尔森不赞成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他承认,劳动价值论当然可以作为价格理论的一种近似,但它并不是一种好的近似,并不准确,也不容易操作,--那为什么要使用它呢?
而另一位剑桥经济学家多布(Maurice Dobb)则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回应了萨缪尔森的批评。多布提出了一种辩解,"现代科学和经济学中有很多简化后的最优近似值,但人们经常觉得它们还不如次优近似值,因为它们没有更系统的理论基础,对现实也很难有更多启发。所以人们在实践受到挑战时,往往放弃最优近似值。
多布认为,只有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得到强调时,劳动价值论才能发挥作用。我们当然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看待劳动价值论。它确实也是一种价格理论,但它不是最优的价值理论,甚至我们不能确定它是否是一种次优的价值理论。但是劳动价值论除了作为价值理论以外,还是一个具有道德内容的规范性理论。劳动价值论可以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不平等和贫穷的劳动者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如何得到不公平的待遇。
多布的这个回应深深打动了森。这也是他选择剑桥、选择经济学的根本理由。他抱着对左翼思想的炽热感情和冷静反思,登上了前往英国的轮船。漫漫旅途中,他与伙伴仍在畅谈对于社会主义的思考。到了剑桥,他终于见到了心目中的一众偶像,多布,斯拉法,罗宾逊夫人等等。其实很多人都与森的设想不一样,甚至每个人的方法论和价值观都不一样,对森的期待也不一样,但是乐观的森总能从他们身上获得鼓舞人心的人力量。
森很快就在正统经济理论上获得了突破,奠定了自己在经济学界的地位,同时开始把注意力延伸向各个领域,尤其是伦理相关的领域。他源源不断地开始写作贫困、饥荒、自由、正义、能力、族群冲突、身份认同、中印关系、孟加拉传统文化,圣地尼克坦对他童年的影响,源源不断地从他笔下涌现。
数年前,我曾精读森的晚年力作《正义的理念》。这本书源自他对罗尔斯《正义论》的解读,也包含了他与罗尔斯数十年不间断的学术讨论和思想碰撞。可直到读了这本书我才明白,森关于“正义”的问题意识远比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来得早,一直可以追溯到他在圣地尼克坦看过的古典梵语戏剧“小泥车”。原来圣地尼克坦才是读懂森的思想的那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