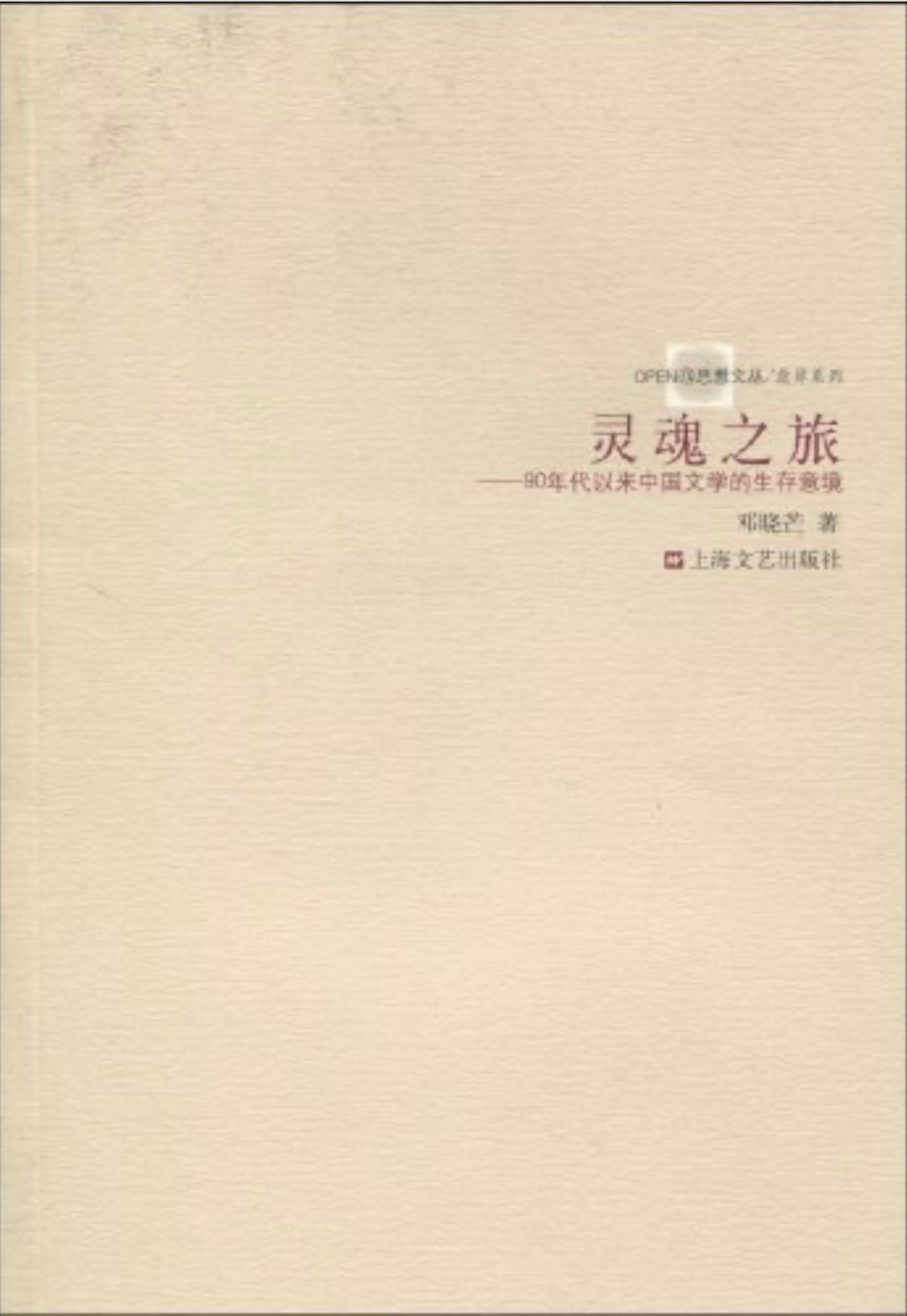王加勉 | 文有“病”,天知否?——殘雪之後是東西?
在容易被不少哲人視作“生產實踐”的文學創作上,殘雪,作為哲學家鄧曉芒的胞妹,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享有名氣,近年“被候選”諾貝爾文學獎更是讓其頻頻“出圈”。在試圖“重建當代形而上學”的鄧曉芒先生筆下、認知下,殘雪作品大受評論界低估,如在其享有聲譽的文學評論集《靈魂之旅——中國當代文學的生存意境》中,鄧曉芒甚至將殘雪之作視為“一種哲學,一種用細膩的女性直覺寫出來的高深的哲學。這在中國文學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文學史上也是罕見的。”如以兄妹之系來妄議背後的“吹捧”,固然屬於無稽之談。然而,面對殘雪作品的莫衷一是之時,如看到殘雪之言(“我在期待更為高明的讀者”)後,讀者在喟歎自己少智之時,也難免生出一絲疑竇:“有那麼高級麼?”讀不懂的情況下,打開殘雪的方式似乎只剩下了所謂的“信仰之躍”,即在一籌莫展時,放下無力解讀的焦慮,硬著頭皮讀下去,讀不清楚則再讀一遍。而這一過程,頗似在處理宗教經典。甚至在某以殘雪研究為主題的公眾號上,我們可以看到“諾獎將頒,我們為殘雪祈禱”這樣的宣傳文案,雖然這多少讓少許殘雪讀者感到有些“欠高明”。
從“方法論熱”的八十年代到被冠之以“去政治化的政治”(汪暉)“漫長的晚期風格”(陳曉明)的九十年代再到千禧年後,殘雪作品在“文學+哲學”之路上走到了如今。當時間的鐘表指向2024年,十年前聲稱要創作的哲學新作《物質的崛起》已經被殘雪放棄良久。而在2023年8月,東西以小說《回響》摘得茅盾文學獎。在落筆布滿濃鬱的欲望、性、死亡等元素的《回響》之前,東西做夠了心理學知識儲備(在此書的自述後記可知)。隨著心理學遊戲在當下的興起,當MOBI測試、星座占蔔、“殺人”遊戲等早已經取代紙本文學成為相當數量青年的思索遊戲之時,對小說的心理遊戲化處理或許也顯得“和乎時宜”。東西走著的“文學+心理學”路徑和殘雪的路徑內容不同,形式卻有些相似,即“1+1>2”的樸素願望。
誠然,作家都有虛構的天賦權力,但“曆史+文學”這種中文老派做法在兩位作家的小說創作中似乎有些乏善可陳:殘雪的“新經典主義寫作”試圖“引領人類”;東西先生則迷戀著人心的黑洞。在淡化史料後,“哲思跑馬場”和“心理遊樂園”固然是安全的,足夠“活”一輩子,然而那不是所有寫作者們的使命。一如名諺:船在港灣是安全的,但這不是船被造的初衷。從“二本學生”到“外賣詩人”,無論是創作對象還是寫作主體,我們都可以看到非虛構元素在當下的倔強之姿。對於大部分讀者而言,哪怕文本生成時遭遇的刪減無從知曉,非虛構的“本事”在現實接受度上是要容易些的——這當然不是懷疑純文學的合法性,而是呼喚更深刻的審美發生。作家不必幹曆史學人的活,然而,在文學史語境中定義尚有分歧的“當代”,中國先鋒文學行走至今,“新又新”的先鋒性背後真有那麼“新”嗎?而概念性寫作的背後或許也藏有一個尷尬的問題意識:作家的史觀幾何?而順此思路可帶出的另一個尷尬之問是:概念化、跨學科化地處理文本能不能成為獲得中國文學“沖擊‘最高獎’諾獎”的呼聲的底層邏輯?
可以肯定的是,殘雪、東西兩位作家的寫作初衷當然不會是為了獲獎而寫作。但在影像、讀圖、玩梗時代的語言浪潮下,受益於影視改編和心理學遊戲之熱,東西是有可能成為“下一個殘雪”、下一個即“被候選”的陪跑者的。寫作者在拿起“麥克風”之前,淡化玄秘的哲論和不離“下半身”的心理學說,瀏覽些史料檔案,重思片刻所處精神原鄉的背後之文化機制,或許有可能獲得走出原鄉的鑰匙——至少,韓江女士這麼做過,且“成功”了。
當然,得“西方”獎本身沒那麼重要。更為重要的“東西”在等待中國當代文學“驀然回首”。當下“文壇”,文學研究已經在史料化上越走越細,而文學作品則在去曆史化上越走越深。如借魯迅先生話,批評者們當然“無權去勸誘人做犧牲”,但,如文有“病”,天知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