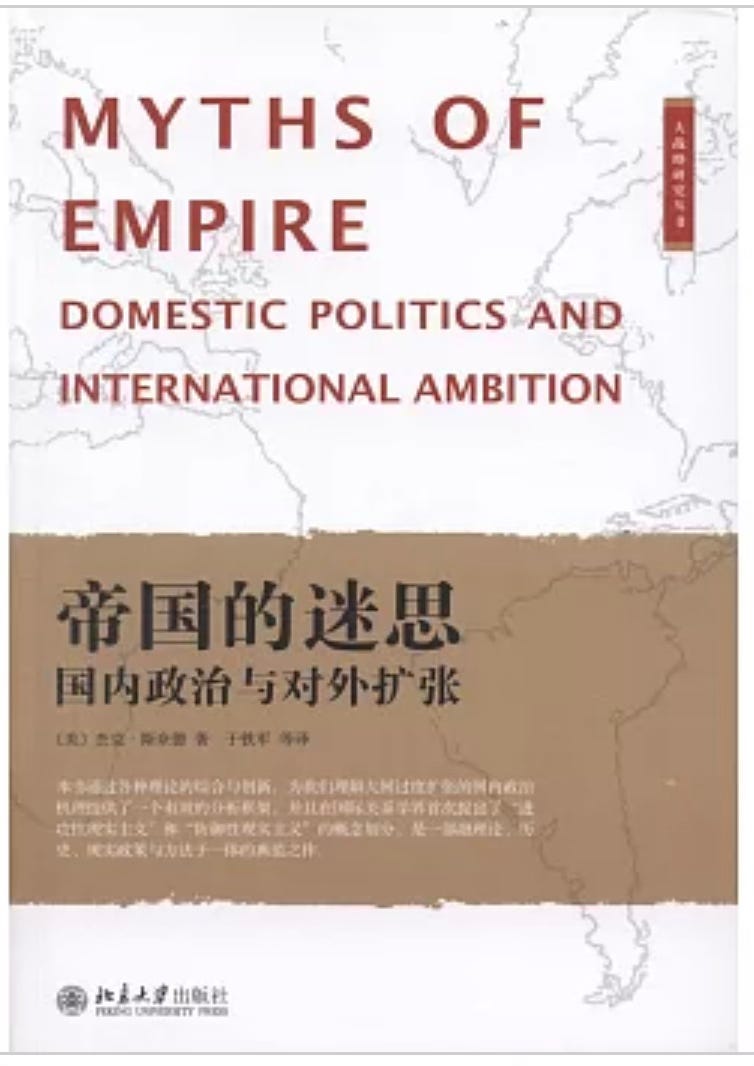倪世傑 | 特朗普,外交上的短視商人?
編者按:本文2016年4月6日首發端傳媒,作者授權刊發。
當特朗普(Donald Trump,台譯川普)被扣上「孤立主義者」(isolationist)的大帽子時,特朗普或許也感到不適,轉而強調他是主張「美國優先」(American First)。
生活在台灣許久的人都知道,「台灣優先」從來就不是保護主義、不遵守國際規範的同義詞;相反,「台灣優先」在意味着強調台灣主體性的同時,仍抱着進入國際社會的期待。同理,「美國優先」也必有其內在的意涵,它可能指的是華府應更關懷國內,更甚於國際事務。
如同前民主黨籍參議員 William S. Symington, Jr 提到越戰時說,吾人應該多關心位於美國南方的聖路易市,而不是在亞洲南部;「美國優先」也可指的是一種單邊主義(unilateralism),在2001年3月之後出台的布殊主義(Bush Doctrine,布希主義)就是一例,無論是退出《京都議定書》以及其後入侵阿富汗及伊拉克,都是以「美國優先」為號召的單邊主義例證。
當然,「美國優先」也有可能是孤立主義的替代用語。美國共和黨籍參議員 Craig Thomas 就表示,「右派、美國優先,以及反聯合國的共和黨人」,往往是迴避「孤立主義者」標籤的替代用詞;其骨子裏就是孤立主義。
美國從無真正的「孤立主義」
不過,證諸歷史,美國罕見徹頭徹尾的孤立主義者。
美國參議員Robert Taft反對美國在二戰後對歐洲駐軍,反對美國提供經濟援助,廣為人知。然而,就像美國國際關係學者 Jack Snyder 在《帝國的迷思》一書指出,當這些老衛士(old guard,共和黨內的保守勢力)面對遠東的共產主義力量蔓延時,基於其堅定反共的立場,就主張美國應建立空中核威攝,並以原子彈結束韓戰。從而,孤立主義者「失去了思想上的完整性。」
美國政治學教授 Robert Tucker 也曾主張「新孤立主義」,他認為美國應建立自給自足的經濟體系,利用核武保衛自己。但當1973年石油危機發生時,他立刻主張美國應介入中東事務,保衛原油供應無虞。
John Dumbrell 教授無疑是清醒的,他在《美國外交政策的形成》(The Making of US Foreign Policy)一書中表示:美國的外交政策,其實並非擺盪在國際主義以及孤立主義之間,而是美國要「如何」參與這個世界的問題。
特朗普的言論中也反映,他也不是什麼真正的孤立主義者。誠然,他認為美國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以下簡稱北約)關係日漸淡薄,歐洲的北約國家應擔負起更多經費;他也提過,在東北亞的日韓若需美國更多軍事援助,自己也該多捐獻一些。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也表示美國不會坐視北京在南海的擴張行徑,並不排除對伊斯蘭國使用核武。如果因為特朗普部份發言,就認為他在搞孤立主義,也實在言過其實。
特朗普的葫蘆裏究竟在賣什麼藥?吾人不妨從「單邊主義論」以及「社會認知論」這兩個角度理解。
「美國說了算」的單邊主義
其一,他的美國優先論更多是單邊主義。華府過去的外交行動,不乏以犧牲盟國利益為代價──尤其在國家領導人認知到,美國國力處於衰落的時候。像是在1969-71年之間,美國總統尼克遜(Richard Nixon,尼克森)不僅斷然解除金本位制,同時也「鼓勵」東北亞國家分擔軍費和防務責任,最後則是背着日本去找北京和解,日本因此稱之為「尼克遜衝擊」。
類似的劇碼在1985年又再上演一次,列根(Ronald Reagan,雷根)政府為改善美國巨大貿易逆差問題,在《廣場協議》(Plaza Accord)中等同強行逼迫日元與德國馬克迅速增值,強行貶值的美元,使日本商社在美資產以及所持的美國國債大幅縮水。
特朗普在接受《紐約時報》記者 David Sanger 與 Maggie Haberman 訪問時,就用了二次「不可預期」(unpredictability),顯示他對戰爭的態度。不僅如此,他在伊拉克油田問題上亦顯示出相當程度的反覆,或是「不可預期」。去年十月,川普在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訪問中表示,美國應該「取得」伊拉克的石油,因為伊拉克的石油不僅被中國買走,還轉向伊朗及伊斯蘭遜尼派恐怖組織伊斯蘭國。但在這次紐時的訪問中,他又改口認為美國應該「摧毀」伊拉克的油田,因為他們就要被伊斯蘭國搶走了。這就是「不可預期」下美國的單邊主義。
令人發噱的是,美國慣常以「不可預期」來形容朝鮮的金式王朝與伊朗政權,這可以說是「流氓國家」或是「麻煩製造者」的特徵。若說特朗普要將美國帶往流氓國家,或許言過其實;但「美國說了算」的單邊主義,應該就是特朗普式「美國優先論」的實質內涵。
用「交易」思考外交
其二,特朗普在以生意人的身份理解國際政治。心理學家皮亞傑(Jean Piaget)認為,當個體面臨刺激或問題情境時,會將所遇到的新經驗,納入其從舊有經驗累積的認知基模(schema)內,形成理解。特朗普是一個知名的投機房地產商,在紐時訪問中他表示「相對於政客,我一直是個非常成功的企業家」。企業家所認識的世界,最主要的活動無非是買與賣,着重成本與利潤之間的對應關係。
特朗普在紐時專訪中大量使用「交易」(deal)這個字眼來概念化的他外交政策。他不僅用「過時的」(obsolete)來比喻北約,並認為北約在經濟上對美國而言不公平──美國人花費太多經費在北約上;對比之下,其它位於歐洲的北約成員國獲益較多。他主張,美國的盟國欲維持當前的軍事配置,就必須出更多的錢。
外交,在特朗普眼中就是一筆直接涉及金錢的交易。不僅如此,金錢同時也是一種外交工具。在談到南海問題時,特朗普表示他會用貿易手段,像是讓中國商品難以進入美國市場的措施,使中國退出南海。
計較短期利益的商人
凡事都計較損益的外交政策觀,顯示特朗普既不了解國際政治,更不了解經濟運作。美國在今天國際還具有領導權的基礎,在於其「為世界訂規則」的權力。二戰後美國國家菁英反對孤立主義,建立了新的國際組織、制度與規範;這一切都反映了美國的利益。然而,特朗普傾向把「國家」視為國際體系下的交易方,並把其它國家看成利用美國的「搭便車者」(free-riders)。他用買賣方式決定國際制度的存續,忽略了美國主導的制度,在維持區域穩定與和平的效用。
美國的投資確保了他在國際政經領域的話事地位,這是世界超強國家維持國際秩序必須付出的代價。美國與盟國間的關係,更是維繫美國國家安全與權力伸展的保障。而當前美國就具有這種制訂國際規則的地位,而不是在規則下找尋活動空間的其它國家;其是市場交易的定價者,而不是市場價格的接受者。
政治評論人費雪(Max Fisher)表示,特朗普其實就是一個計較短期利益的生意人,他出賣美國自二戰後建立的制度以及權力基礎,以及最重要的,美國對盟國的信譽與承諾,只為從盟國中抽取蠅頭小利。
隨着特朗普代表共和黨競選美國總統的聲勢看漲,他的國際政治觀,自然也引發了盟國的緊張。對東北亞而言,特朗普先前表示日本與韓國必須多負擔些軍費,甚至可以自行發展核武的言論,已引起日、韓兩國的緊張。3月29日,當CNN主持人庫柏(Anderson Cooper)表示,因為二戰後的日、德兩國被剝奪了裝備攻擊性武器、發動戰爭,以及發展核武的權力,因此德國與日本才需要美國駐軍;特朗普卻表示因為對這維持盟邦的費用太高,美國應該要考慮更換盟國。
面對特朗普的發言,韓國外交部發言人趙俊赫(Cho June-hyuck)表示:韓國致力維持朝鮮半島非核化的目標。但令人質疑的是,一旦特朗普當選,面對「不可預測」的金正恩,韓國能夠維持非核化的目標嗎?這又是否意味着東北亞將開始下一輪的軍備競賽?當北約規模被迫縮減時,對歐洲的政治力量分配又意味着什麼?
普京的新「雅爾達體系」
如同國際關係學者Robert Cox在《生產、權力與世界秩序》一書中所提到的,二戰後在美國強權下的世界和平,創造了一個由華府所領導的世界秩序。在後冷戰時代,過去冷戰時代的制度並未終結,反而更得到強化;像是北約不僅持續東擴,也搖身一變成為以國際反恐為主要任務的組織。
隨着蘇聯分崩離析,美國也成為「一超多強」世界格局中唯一的超級大國。然而,在美國霸權下仍懷抱大國夢者,除了習近平以外,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台譯普丁)胸中亦懷抱着,重建過去蘇聯時代歐亞大帝國的俄羅斯民族復興之夢。
普京於2015年9月在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說時,譴責美國在東歐與亞洲推動的「民主化」,反而導致更多混亂;此外他也提到,世界大國應該建立類似於當年反希特勒的聯盟,共同對抗恐怖主義。瑞典前外交部長可利瓦(Aaron Korewa)認為,普京將伊斯蘭國比作納粹,顯示俄羅斯與西方國家共同站在反恐的一邊;同時,如同當年對抗希特勒,西方國家也需要俄羅斯。
普京所盼望的,是建立一個新的「雅爾達體系」(Yalta system)。1945年的雅爾達會議中,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以及蘇聯共黨總書記斯大林三巨頭,在彼此同意的基礎下劃分國際勢力範圍。普京在聯合國演說中盛讚,雅爾達會議建立了一個穩定的、可預期性高的戰後國際秩序,表現出對建立某種類似體系的企圖心。
特朗普對北約,乃至對俄羅斯在敘利亞戰爭中的態度,都恰恰正中普京下懷。倘若北約中的美國角色下降,只靠法國、英國以及德國武力支撐,應有助於克里姆林宮確定(甚至擴大)勢力影響範圍,更能使普京遂行新雅爾達體系。那麼,自1989年後甫脫離莫斯科掌握的東歐國家,豈能不緊張?歐洲各國未來是否要建立更強大的國防,以求自保?歐洲是否又將陷入另一種安全困境?
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洛娃(Maria Zakharova)於3月22日表示,他們支持特朗普關於「北約組織已陷入危機」的看法。這顯示克里姆林宮已經開始面對,特朗普若是上任,華府可能採取孤立主義的國際情勢。更不消說,早在這之前,特朗普與普京早已相互恭維──特朗普說希望與俄國建立更深層、緊密的雙邊關係;普京則表示「特朗普非常傑出、愛炫,毫無疑問相當能幹」。
特朗普若執政,北京如何應對?
如果特朗普執政,美國與俄羅斯關係可能改善,北京又該如何應對?畢竟,特朗普已經數次對中國表示不友善的態度,包括「我們不能繼續每年做生意丟五千億美元給中國人了,我們賠不起了」、「對中國出口到美國的產品開徵45%的關稅」、「經濟制裁中國以解決南海問題」。
相對於莫斯科,北京還在察言觀色。《環球時報》發動了激烈批評。其於3月14日的社評中將特朗普比為小丑,以及共和黨的最大夢魘,其並把特朗普跟墨索里尼與希特勒相比,提醒美國「或許需要嚴防自己對世界和平的破壞性力量輸出」。
照理說,北京應該對特朗普執政後,對所謂美軍縮減在東北亞的部署額手稱慶。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的報告中顯示:隨着中國航母數目的增加,到2030年,從東海到南海都將成為中國的「內湖」。特朗普在接受《華盛頓郵報》訪問時表示,他不會為了南海問題發動世界大戰,且會運用貿易戰來解決南海紛爭。可以預期,當特朗普執政下的美國,有可能鬆弛在西太平洋的防務,使得東亞(甚至南亞)開始邁向武器競賽的新高峰。
這些年來,因為海權爭議升高,東亞與南亞國家展開令人矚目的軍備競賽。越南與馬來西亞在前些年皆購入潛艦;菲律賓也於日前計畫購買潛艦。印度分別與日本、俄羅斯展開更緊密的軍事採購合作,當前印度向俄羅斯購入的T50戰鬥機,就已傳言是中國航母的殺手。更不消說,台灣的蔡英文總統當選人,早已將國防工業當作重點發展產業;由中船、中鋼支援下的國造潛艦計畫,也已箭在弦上。
一旦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之後,這種趨勢恐怕只會更為嚴重。
「大美和平」(Pax Americana)的終結?
如同國際政治經濟學者彼得‧卡岑斯坦(Peter Katzenstein)在《地區構成的世界:美國帝權中的亞洲與歐洲》一書中所表明:亞洲的地區安全秩序,在很大程度上,仍建立在大國均勢、追隨強國和威脅的邏輯上,是由美國、中國、俄國和本地區一些較小國家的政治與軍事菁英塑造而成。
倘使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美國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或許將隨着華府的戰略收縮而一去不復返,這無疑增添北京決策時不確定性。而「不可預期性」正是特朗普自我標榜的特點。
諷刺的是,特朗普推動的美國軍力收縮政策,其實一直是各國左派勢力希望達到的目標。像是當前英國工黨黨魁James Corbyn在2015年角逐工黨黨魁時,就表示他希望英國能夠退出北約,以及不再部署三叉戟核彈防衛體系(Trident nuclear deterrent);德國的左派黨則主張以新的區域安全體系替代北約。在亞洲,菲律賓左傾的人民運動Bayan近月以來,反對美軍重回菲律賓;韓國人民運動中的左翼與自由派,對於美軍持續駐紮韓國亦抱持否定的態度。
當華府認為,擔任世界警察吃力不討好,又耗費國家財政,區域權力結構不免將面對重組。屆時是會導向新的區域性的安全困境?還是新雅爾達體系?善變的特朗普使世界更大困惑的同時,恐怕已經使各國嚴重懷疑,美國維繫世界和平的承諾。
(倪世傑,政治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兼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