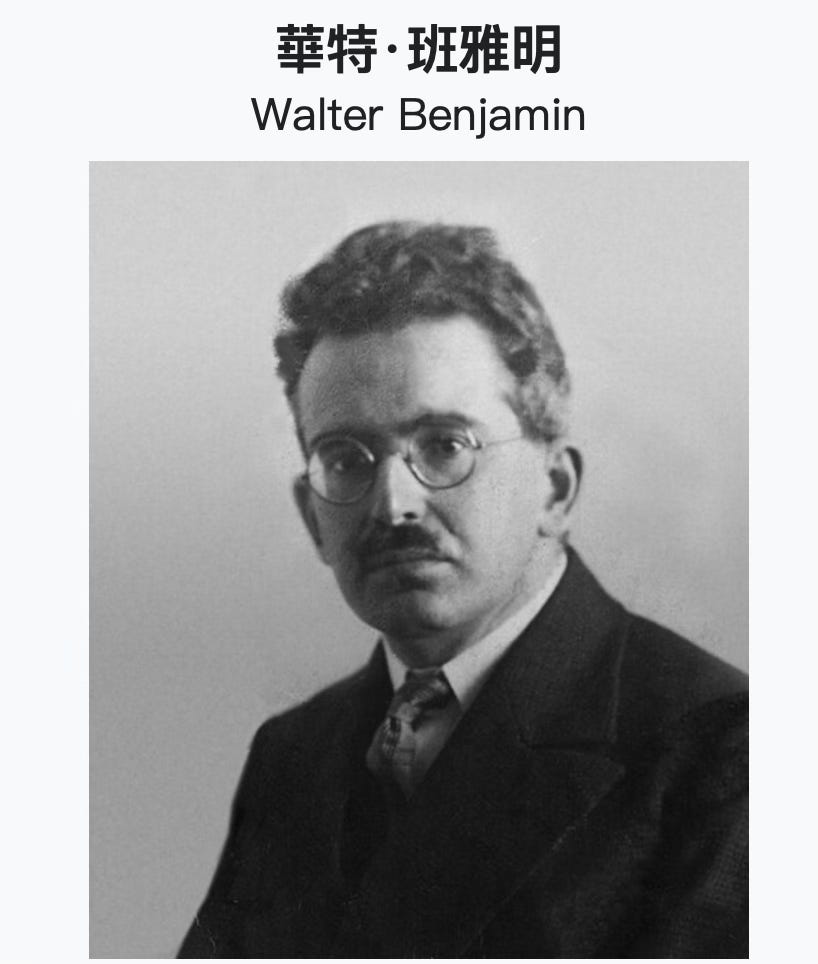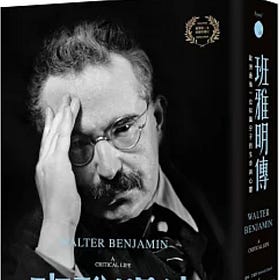还学文 | 本杰明和他的思想:党外马克思主义者
编者按:“二十世纪之初面对战争、革命、社会的动荡,对科学、理性和人性的深刻不信任滋养着对神秘主义和非理性的渴望,本杰明的神学——唯物论的历史哲学迎合了这种末日感,并且似乎是在正统马克思主义之外独辟蹊径指示了一条解救之途。”作者还学文1982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1983年赴德留学,现居德国。
引子
中文喜欢和喜欢标榜的德国人名首屈阿伦特(Hahna Arendt,1906-1975),一个语焉不详的“平庸恶”留下随兴穿凿附会的无限空间。阿多诺(Theodor Adorno,1903-1969)次之,也是借标签文化之便,因“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那句他后来收回了的昏话知名,收回这一段慕名者就不管了、也不想知道。三个人当中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殿后,他思想丰富且复杂,顺手“拿来”不方便。但三个人里更有有意思和启发性的,无疑当属本雅明。
三个人都是同化了的富裕犹太人家庭出身,都是左倾而显然非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哲学上都深浸于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辩证法。今天看来,比阿伦特和阿多诺年长十几岁的本雅明在那个世纪之交的生活和思想,堪称他们的前驱。
二十世纪之初面对战争、革命、社会的动荡,对科学、理性和人性的深刻不信任滋养着对神秘主义和非理性的渴望,本杰明的神学——唯物论的历史哲学迎合了这种末日感,并且似乎是在正统马克思主义之外独辟蹊径指示了一条解救之途。
时过半个世纪,共产主义制度解体之后,人们期待着一个立即的复兴。然而,事情的发展却非如此。于是东方和西方的左派说,现实表现为历史预兆的颠倒,它要求我们修正取消共产主义的要求。在德国著名的《时代周报》上,有人撰文主张,马克思主义价值批判的历史正确性并没有随着共产主义制度及其经济和道德意识形态的解体而过时。由此,对边缘马克思主义理论———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各种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对本杰明理论的需求也再次应运而生。
有人说,本杰明的神学人道主义思想的现实性是显然的。他们说,虽然本杰明谈革命,也使用阶级斗争的字眼,但他是在这个词最好的意义上发展出一种人权的理论;他们说,本杰明之所以谈神的“救赎”,是因为他拒绝人类历史必然进步这种危险而有害的思想;……
不仅在他的国家,而且在东方,在大陆、台湾和韩国这样不同形态的社会中,本杰明被当作西方思想的杰出代表而有相当的影响。我们希望通过对于他的时代与他思想发展的陈述,发现他在当代思想历史中的位置。
一 简短的生平:生命中的几个重要时期
一八九二年本杰明出生于一个殷实的德国犹太中产阶级家庭,他是长子,有一个弟弟和妹妹。关于童年生活,他在三十年后写有《十九世纪的柏林童年》和《柏林记事》(死后发表的)。这些文字与其说是童年生活的记录,毋宁说是一个成年人对于童年生活经验的分析与重构/重塑,以成年的我“提升”童年的我,力图从中显示一个成熟的唯物主义历史学家的精神发展。例如在对一次家庭晚宴的记述中,本杰明写道,“这儿是深渊、我从属的那个阶级的深渊,在那个晚上我就是这样认识了它”,似乎孩提的他就已具有明确的阶级意识了。对个人生活本杰明终生保持缄默,收在《柏林记事》中有一篇文章题目就是“绝对不用‘我’这个词”。二十岁年那一年本杰明从文科中学毕业,同年考入弗赖堡大学哲学系。一九一二年后的两年间本杰明差不多全身心投身了当时德国的青年运动,从他我们看到整整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缩影,甚至立刻联想起中国“五四”的一代青年。一九一四年始他逐渐脱离政治社会活动,专心于文学与哲学研究。其间本杰明结识了G·肖勒姆(Gershom Scholem),并成为终生的亲密朋友。对犹太人在德国的前途肖勒姆老早就不报幻想了,一九二三年移居巴勒斯坦。一九一七本杰明与多拉(Dora)结婚,第二年他唯一的儿子斯特凡出世。一九一八年在瑞士本杰明结识了布洛赫和卢卡奇这样一群出身上层社会、激烈地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敏感的青年知识分子。
一九一九年完成了博士论文之后本杰明马上开始撰写教授资格论文,希望能尽快完成,以此作为继续要求父母经济资助的资本,过一种自由学者的生活。一九二四年五至十月本杰明在意大利卡普里岛(Capri)五个月,完成了教授资格论文。此间他结识了俄国女革命家阿斯亚(Asja Lacis),对他日后的思想和生活发生了重大影响。
一九二六至二九年间本杰明达到其生活与创作的高峰。这一期间他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文章,成为文坛知名的批评家,经济上也第一次独立而有保障。一九三〇、三一年间本杰明还曾在医生监护之下吸大麻,有时是和在布洛赫等人一起,有时是在其它朋友那里。在给医生的记录中他写道:这种感觉是无法言喻的,吸毒后,成长与自立的意志就全然消失了。“成长与自立”对本杰明具有特殊的意义。他一直希望能够依赖家庭的经济支持过一种自由学者的生活,而父亲却要求他自立,长时间以来他处于一种经济上依附与内心困扰的状态。他感叹,到了四十岁他才第一次有了成人的感觉,不是因为已经不再年轻,而是感觉到自我开始得到实现。
一九三三年三月由于盖世太保1的骚扰本杰明终于离开了德国。流亡到法国后,他一直在社会研究所工作。巴黎的社会研究所隶属于纽约,在那里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主持。流亡的生活非常痛苦,除去经济上的困窘,他在研究和创作上也不得志。由于学术意见上的分歧,本杰明的文章常常被霍克海默大段删改,他《论波德莱尔》一书有三章因为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不能接受他的哲学观点与方法论而被断然退回,以至他不得不重写。这常使他感到屈辱和无奈。
一九三九年在法国被纳粹关进集中营,经朋友营救而获释,一九四〇年在逃亡中自杀。
二 青年革命家的本杰明
本世纪初德国曾有过一场从教育改革要求开始的社会改革与文化革命运动,称之为“青年运动”。当时,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思潮弥漫了整个世界,征服了一代青年。许多文科中学高年级学生和大学生积极参与了这个运动,他们大都出身于社会中上阶层,根深蒂固地有一种菁英意识,自诩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和文化的传播者、是天才,因此是教育改革的当然领袖。本杰明中学毕业后立即投入青年运动激烈派的活动。激烈派首脑古斯塔夫•维内肯(Gustav Wyneken)是本杰明维就读两年的豪宾达(Haubinda)寄宿学校校长,当时他在校内推行教育改革,给本杰明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到弗赖堡大学后,本杰明立即投入了当地的自由学生运动,这个运动旨在实现洪堡(Wilhelm Humboldt)2的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理念,争取学生对学校事务的参与权。在这个松散的学生社团中,维内肯组织了自己的激烈派派别。这个派别认为政治讨论毫无意义,宣传坚决反对现实社会,要求实现一个只有尚未堕落的青年一代才可能具有的纯粹精神领导的新社会。这一时期本杰明大力投入社会组织活动:他主持弗赖堡大学教育改革分部工作,吸引学生加入这一运动;在柏林组织“论坛”(Sprechsaal),为要求摆脱家庭束缚、反抗资本主义社会的青年朋友提供一个自由的空间;同时还定期为青年运动的《青年杂志》(《Zeitschrift fuer die Jugend》)、《开端》(《Der Anfang》)撰稿。在一九一三年的不少文章中他系统发挥了青年运动激烈派的观点:抗议家庭和学校对青年的压迫,抨击小市民道德,反对怀疑主义,并以一种菁英的政治使命感提出他的社会改革纲领。在一篇题为《教学与评估》(《Unterricht und Wertung》)的文章中他激烈抨击文科中学中的古典教育─古希腊与拉丁文化教育─,说现行的古典教育并不传授体现和谐与理想主义的古希腊文化,而是宣扬白里克里斯时代3、寡头政治、歧视妇女崇尚男性的古希腊,还有它的奴隶制,……呼吁取消这种反现代、反民主、傲慢的教育体制。难怪S•伯恩菲尔德(Siegfried Bernfeld)─当年维也纳教育改革学术委员会的创建者和主席─在后来的回忆中指出,激烈派的这种态度引起了中学教师、校长乃至社会中自由主义分子的广泛不满。到了一九一三、一四年之际本杰明的态度发生了一个大转弯,在这个冬季学期柏林自由学生会主席就职讲演中他转而反对学生从事社会活动,理由是青年个人的精神生活与他关心劳动者后代的活动并没有必然联系,谴责靠社会活动满足精神上的需要是一种相对主义。一九一四年两个最亲近朋友的自杀对本杰明标志着青年运动的结束。一九一五年之后,他甚至完全厌倦了关于战争和时事政治的讨论。
不论在哪一个时代,年轻人总激烈和极端的,但是激烈与极端的内容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个人却各不相同。本杰明青年革命家的形象作为时代的缩影生动地显示了二十世纪初席卷整个世界的社会思潮的一般特征,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思想的广泛影响,在不同的层次上、以不同的方式它把年轻人反叛的心理与激进的改革诉求纳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现实社会的危机与弊端提供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温床;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激烈的资本主义批判在年轻人反对社会不公的愤怒中引起强烈共鸣,它的乌托邦社会理想以及彻底革命纲领正好迎合年轻人的激烈与极端,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所确认的那种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先锋的政治使命感与青年知识分子的贵族菁英意识一拍即合。相信这种分析对于今天也仍然适合。例如,当年大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许多人是报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腔热情,怀着一种夹杂着牺牲自我与拯救世界的悲壮情怀而去的,他们以这种精神上的自我嘉许作为对在现实社会中损失的补偿。而今天西方社会中左派知识分子对诸如萨特、阿尔都塞这样一些准马克思主义思想贵族的认同,也是潜在地作为对于民主社会平等原则不能赋予知识分子特殊的菁英地位的失落感的一种心理补偿。
三 非常德国人的本杰明
本杰明是一个犹太人─仅就其出身而言─,在自由主义的家庭气氛中成长,并无所谓对于犹太文化与宗教的认同,一直到“青年运动”时期,他才从与志同道合的犹太朋友的接触中第一次认真了解与思考犹太精神。后来他发展出一种独特的犹太文化认同,即以犹太精神为精神生活的灵魂。
本杰明其实是非常德国人的,─就其精神上与德国的内在联系而言。一九七七年P·von·哈塞尔贝格(Peter von Haselberg)在本杰明研究中就提出了“作为德国人的本杰明”的问题4。文中援引本杰明通信,“对于我来说,彼此区别的民族性一直是十分重要的,例如德国人的,法国人的。关于这一点以及自己与前者不可分割的联系,绝不会从我的自我意识中消失”。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致友人的信中,本杰明写道,“不管在什么地方,我都不会忘记德国。”这里他用的是名词化的形容词“das Deutsche”,即“德国的”,指德国文化、德国精神、德国气质等等。一周之后致同一人的信中他又谈起自己的德国情怀、德国“根”,“对德国民族、它的语言以及它的思想的热爱,在于我是合而为一的;即使是逃亡也不能改变这种爱。我的生活经历告诉我,我不能失去对它的爱。当然我也不愿成为它的牺牲品。”他一生都深深地执著于成为他创造性的生命源泉的德国精神。
早年移居巴勒斯坦的好友肖勒姆,在二十年代本杰明事业与生活都不景气之时就曾劝他移居巴勒斯坦,而他一直迟疑着。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后,事业与生命受到严重威胁,他再次面临抉择:留在德国还是移居巴勒斯坦。六月份他在给肖勒姆的信中写道,“那里对于我─就我的知识与能力而言─有比在欧洲更大的空间吗?……不必说,在去留问题上我必须考虑不必放弃我已经拥有的而能够继续发展。”肖勒姆坦诚相告,“只有从感情上完全认同这个国家、犹太文化和这里的一切,人们才能面对所有的问题、困扰,战胜内心的压抑;而且对那些新来乍到的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要在社会中找到适当的位置,常常并不容易,……”。除开经济与社会生活的现实考虑外,本杰明也不具备对犹太文化的内心认同,他那种德国式的犹太情怀绝不会帮助他克服真实的犹太生活将带给他的困扰与压抑。
谈到德国与犹太人之间的关系,本杰明认为犹太人之所以能够抛弃他们参与形成的德国文化,是因为他们对德国的态度是可收买的。“可收买”是指犹太人期望以对德国的公开认同换取德国人对他们的容忍与承认。而他自己,他希望通过从扭曲与遗忘中拯救德国思想精华积极地代表和维护德国。5
关于德国精神与犹太精神之间的密切关系,本杰明是一个例子,但不是唯一的。本杰明以犹太精神作为精神世界的灵魂,黑格尔以德国为绝对精神的历史化身;很难说是犹太人体现了德国精神,还是德国人发扬了犹太精神。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中曾经十分精采地分析过马克思主义中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旧约中先知与救赎的结合。犹太德国人当然还有另一种类型,例如著名诗人海涅、自由的歌者,因为无法忍受德国思想文化界的气氛移居法国而遭到国人的非议。又如被非常德国人的德国著名物理学家施塔克攻击的爱因斯坦。他们常常被认为很不德国人。爱因斯坦十分平静地说过,“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同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联系在一起,更别说德国了,我同德国仅有的唯一联系只不过是我担任了普鲁士科学院的院士,还有我从小学会的德语。”6对于思想研究而言,德国思想与犹太精神的联系,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一个重要的课题。
四. 走向无产阶级革命:与俄国女布尔什维克阿西娅的爱情
对本杰明一生发生过影响的有三个女人,一个是他的妻子多拉,另外两个是他的情人:尤拉(Jula Cohn)和阿西娅。本杰明与多拉一九一五年定婚,一九一七年结婚,次年生有一子,一九三〇年离婚。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五日,本杰明死后一年之际,多拉从英国写信给肖勒姆,谈到他们的分手、他们以往的幸福时光,谈到她早已为本杰明准备好了到英国的逃亡,谈本杰明的死对她的沉重打击。十月六日多拉再次致信肖勒姆,告诉他,本杰明死亡使她与生命的联系危如游丝,恳求他给她讲讲他们分手后本杰明的一切。尽管如此,她远非本杰明生命中重要的女人。
博士论文完成后,一九二一年本杰明一家从瑞士迁回柏林,与雕刻家、他中学时代的朋友尤拉重逢。他们早在一二年就认识了,一九一七年本杰明结婚后中断了联系,因为,本杰明自己讲,“尽管我们(尤拉、我和多拉)的一切努力,彼此之间还是无法达成一种和谐的关系,三个人共同生活没有可能。”四年后,本杰明重又燃起对尤拉的热情,有很长一段时间尤拉又住到了他和多拉那里。这一次毁坏了他与多拉的婚姻,他们断续地开始分居。一九二六年本杰明事业上开始上升,个人生活上却极不愉快,他一直深爱的尤拉和别人结婚了,婚后似乎又不幸福。
本杰明命运中最重要的女人是阿西娅,一个女布尔什维克,她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思想发展,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干预了他的生与死。一九二四年他们在意大利的卡普里相识。当时本杰明正在考虑肖勒姆移居巴勒斯坦的建议,为此阿西娅与他发生激烈的争吵,她认为对一个进步人士来说,希望在莫斯科,而不在巴勒斯坦。结果是阿西娅胜利了,“我可以平静地告诉你们,我终于达到了目的,本杰明不去巴勒斯坦”。 7
和从里加来的激烈的女共产党员阿西娅的相识与相爱,使本杰明生动而直观地了解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者,并确立了对它们的认同。从那时刚刚出版的卢卡奇著名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他印证了自己对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衰亡的分析,并且试图把它提升为一个与认识论相结合的历史哲学体系。卢卡奇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社会的扭曲归结到它思想中的矛盾对立,并把这种精神危机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普遍瓦解的指示计;另一方面又指出,如果把这种思想文化改造为社会进步的杠杆,则可以扬弃它的内在矛盾从而升华它,在这种哲学和历史的矛盾混合中本杰明找到了自己政治观点的表达,在其后期重要文学评论《论技术再生产时代的艺术》一文中,人们可以清楚辨认出同样的论证。同年十二月本杰明告诉好友肖勒姆,“……共产主义是一个信号……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它激励我阐发那迄今为止一直伏在法兰克人面具下的我对于现实政治的思想。……(你会看到我)对彻底的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解在许多地方都有更新”。一九二四年标志着本杰明明确地认同马克思主义思想。
二五年罗沃特(Rowohlt)8出版社和他签了合同,答应陆续出版他的《论德国悲剧的起源》、《论哥德的心灵的亲睦》,并约他翻译布鲁斯特9的作品,为他今后一段时间的生活提供了可靠的经济保障。秋季开始,他从汉堡出发到西班牙、葡萄牙和南意大利旅行。从拿波里回到德国后,十一月份又专程去里加看望阿西娅。然而,对于这位共产党员来说,知识分子如果不积极参与革命,和他们打交道就毫无意义;因此对本杰明的来访,阿西娅相当冷淡,“他(本杰明)总喜欢给人意外,这一次他的意外可一点不和我的口味。他完全是从另一个星球上来的,我没有时间给他”。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本杰明再次来到苏联。十二月六日在他莫斯科见到了阿西娅,和他的伴侣、导演兼评论家B•莱希(Bernhard Reich)一起。关于阿西娅以及她与他们两个男人之间的关系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出现在一个无法攻克的堡垒面前。尽管如此,我对自己说,仅仅是我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胜利”。本杰明不会一句俄文,在采访和社交上他都离不开莱希,于是三个人持续处于嫉妒与争执的紧张关系之中,逗留莫斯科两个月的日记中充满这些纠缠不清的争执与感觉屈辱的记载。一九二八年随苏联商务代表团阿西娅来到柏林。在柏林的一年半时间中他们时常同居在一起,导致多拉与本杰明最后分手。同年,本杰明出版了政论文集《单行道》,题献给阿西娅。《单行道》一书集中体现了本杰明评论文章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特征,它们试图通过对各种社会现象的分析批评建构一个革命历史理论,说明现代社会为理想社会的没落,为历史暗示自己本来目的否定的、破坏性的征兆。
通过阿西娅,本杰明实现了其哲学、社会学思想和文学批评的马克思主义化和直接政治化。
五 本杰明创作生命的高潮:杂文时期(1926─1929)
根据和罗沃特出版社的合同,一九二六年本杰明开始为翻译布鲁斯特做准备,并同时为《法兰克福报》和《文学杂志》撰写评论。这一期间本杰明创作十分旺盛。二六至二九年间,他平均每年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三十篇评论。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日益激化,本杰明觉得不能继续认同它的宗旨,一九三○年之后便退出了《文学杂志》。《法兰克福报》是一份左派民主主义的报纸,一九二六年四月本杰明在该报发表了第一篇文章“一个小的启发”(“Kleine Illumination”),其后陆续在该报发表的文章于二八年集成《单行道》一书出版。部分地由于与《文学杂志》竞争的缘故,本杰明一直没有能够成为《法兰克福报》的正式撰稿人,尽管如此他每年平均为该报撰稿也在十五篇以上。
本杰明定期为当时德国两个最著名的文学刊物撰稿,以多产的创作奠定了文坛知名批评家的地位,自认成功地扮演了批评家之为文学战场上战略家的角色。这一时期的文章明显地表现出苏联之行为他观察与分析社会析渗入了新观点和新方法。在“批评家技巧十三则”(“Die Technik des Kritikers in dreizehn Thesen”)一文中他主张,如果斗争需要的话,客观求实性应让位于党性,在这一时期的评论中他明确地以唯物主义历史学家和政治家自居。一九三〇年罗沃特出版社答应将他几年间在两刊发表的重要文章汇集出版,本杰明非常希望能够由此向公众强调表明他之为德国新批评理论奠基人的地位,但是后来由于出版社的财政危机这个计划未能实现。
在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到希特勒上台前的这几年间,本杰明达到了自己事业的高峰。不仅有了稳定的职业与社会地位,而且作为领衔的批评家在同行和公众那里也获得充分的承认。
六 党外布尔什维克与战斗的党文学批评
由于出版业的产生与发展,以文为生者的经济生活因此纳入市场经济的体系。在经济上尚未自立之时,本杰明曾抱怨,谁要是认真从事精神劳动,他就必须面对饥饿与贫困的威胁。当时在知识分子、尤其是左派知识分子中间发展出一种阶级意识,认为由于出版商,他们不得不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他们的精神产品被迫异化为消费品。二十年代左派知识分子们致力于一种社会主义文学,鼓吹通过阶级斗争改变现存的生产关系,以消除资本主义对精神生产的异化。马尼克出版社(Manik─Verlag)的创办人W.赫兹菲尔德(Wieland Herzfelde)与版画家兼作家乔治•格罗兹(George Grosz)于一九二五年发表宣言:“今天,一个艺术家如果不愿意做一个无能的臭皮囊、一件过时的古董的话,那么他必须在匠人还是阶级斗争的宣传家中作出选择;然而不管在哪种情况下,他都必须放弃‘纯艺术’。” 10
一九二五年法兰克福大学拒绝接受本杰明的教授资格论文《论德国悲剧的起源》,本杰明收回了论文。他认为提出和坚持自己独立的、批评性的思考比教授的头衔更重要。在谈到未来的计划时他写信告诉肖勒姆,“事情完全取决于和出版商的关系。如果在这方面没有运气,我就准备全力投入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研究,……并且入党,这一步我是迟早要走的。我的研究领域也将有所改变,人不能人为地把自己局限起来”。但后来本杰明并没有加入共产党。在一九二六年的莫斯科日记中我们发现了其中的缘尾,“我放弃入党的意愿完全是由于一些外在的原因,……因为当初要入党的冲动也不过是我生活中的一个插曲。……我自问,在现实中和经济上是不是做一个左派党外人士更好,能为继续发展自己已在进行中的精神生产提供更好机遇与保证?”11。“左派党外人士”不仅对本杰明,而且对其它许多左派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及其思想活动都是一个十分准确的刻画,本杰明和共产党以及他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对于那一代左派知识分子是典型而具有普遍意义的。
本杰明一九二六年的莫斯科之行是受命《世界文学》杂志采访社会主义苏联。他的文章广泛报导和分析了俄国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从新经济政策到教堂、剧场、交通、招贴画乃至街头摊贩,当然更多的是谈知识分子。在“论德国悲剧起源”一文中他提出,现代社会中文学地位的改变使知识分子的传统社会角色成为过时,而在苏联对知识分子任务的规定中,他发现了知识分子新的社会定位。在《文学世界》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一日“俄国作家的政治流派”一文中他提出,在新的社会中不是美学上而是政治上的亲和性决定作家们的分野。文章介绍了当时苏联作家的三个主要派别:左派无产阶级作家(Linke Prolekult),右派流行作家(Rechte Poputschki)和全苏无产阶级作家协会(WAPP),认为他们代表了当时俄国三股主要的社会力量:英雄的战时共产主义者、新经济政策下复活的资产阶级和党领导之下的无产阶级专政。他赞扬苏维埃新文学突破了资产阶级上层的自我表现,成为大众政治启蒙的有效工具。
一九二九年以后本杰明集中于批评保守的、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和社会理论,同时也激烈地批评左派知识分子,虽然─就社会和文化背景而言─他自己也属于那些对这个社会绝望的、激烈的布尔乔亚左派。但本杰明认为,自己与这些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贩卖自己的思想为了取悦颓废堕落的社会和读者,而他却是致力于改造社会。这种批评在“左派的感伤”(“Linke Melancholie”)一文中登峰造极,以致由于它挑衅性口气《法兰克福报》拒绝刊登,后来在社会民主党刊物《社会》杂志上发表,“论知识分子政治化”(“Die Politisierung der Intelligenz”)一文也是在这个杂志上发表的,
本杰明这种意识形态的、党性化态度不仅主导了他的大部分评论文章,而且也渗透了他的“纯”学术著作,例如他的《巴黎片段》(《Pariser Passagen》)。《巴黎片段》是二七年开始、三○年中断、三四年复始、三七到三九年集中精力完成的。据他说,该书研究十九世纪的历史与艺术在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如何被歪曲,希望在辨证法的历史重建中扬弃现代社会对它的扭曲,恢复它被遗忘的本来面貌。又如《论波德莱尔》。这本书是用辩证法三段论的方法写成的,作者将该书衬托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复辟时期”的背景之下以突出它的价值。─文学的价值?!书中有波拿巴与希特勒、波德莱尔与本杰明的对比,因为作者认为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法国与一九一八至一九三三德国的社会政治状况是类似的。本杰明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一旦进入商品生产时代,原则上就不再产生任何新东西,而只是无限重复同样的恶。唯一能够彻底打破这一历史恶性循环的就是“拯救”,通过“拯救”才可能重建新世界。而这种拯救,本杰明相信,是辨证唯物论的“拯救”,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拯救”。
七. 本杰明的哲学思想和文学批评
大体上,说本杰明的思想为神秘主义的语言哲学与经过犹太教神秘主义诠释的辨证唯物主义的历史哲学和文学批评的综合体,是不错的。但正如阿多诺所说,他的思想产生于他的时代,然而又无法归之于同时代任何一种思想主潮;他的思想具有某种独特的色彩,这种颜色又不存在于当代思想的光谱之中。今天,本杰明主要地被了解为文学批评家。然而作为文学批评家,他评论的价值常常不是纯粹文学的,而是哲学和社会政治的,是从特定历史背景的分析出发对文学现象的哲学、社会学诠释。而他对作品局部与细节分析的隐喻式与启示性的风格,阿多诺认为如同中世纪的圣经诠释者。本杰明文学批评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它们强烈的意识形态品格和党派性。肖勒姆曾经批评本杰明以马克思主义范畴曲解神学基本概念,本杰明反驳道:“要是文章已经是反革命的,─从党派的观点出发,你对我文字的定性非常正确─,难道还需要明说作者是反革命的吗?……明确地区别个人和他的意见、语言和运用语言的人是多余的吗?这种区分在我的文章中不是常常显得太不够了吗?作为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应该在其他方面强化这种区别吗?”肖勒姆批评本杰明“学术”的意识形态化,希望他把两者明确地区分开来。而本杰明自己显然是把这种意识形态化就认作是学术研究本身。直到今天,本杰明的追随者仍然在使用他上述的自我辩护,矫情地区别他之为共产主义同情者和他之为文学批评家,把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当作他在美学理论上的建树。
关于本杰明的党文学批评,前面已经谈过,下面我们来简要地追踪一下本杰明文学批评及其哲学基础的基本特点。
亚当的语言
本杰明的语言理论从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时间上讲,都构成了他日后哲学分析和美学理论的出发点,而且他的语言理论充分表现了历史神学解释的特征。“论语言自身和人类语言”完成于一九一六年。
本杰明把语言分成四个等级:一、创造性语言,在这个阶段词创造对象并通过命名识别它们。二、亚当的语言,这是一种在命名中的纯粹认识的语言。三、当代人类语言、判断性语言,这是一种败坏了的语言,是直接直观性的。四、无声的事物语言。他赋予语言以本质上的双重性:一方面它具有指称的功能,通过将无声的事物语言翻译成词而表达事物;另一方面它又是精神本质的表达,并且精神只有通过语言才能够传达。他提出语言中未被意识到的成分,称之为模拟或表演的功能(mimeticelement)。正是由于这种“通神的,即精神传达的直接性”品格,语言得以成为精神本质的表达。他批评,“一种抗议它的研究使用的语言的科学是胡闹。词是在数学符号以外科学的唯一表达中介,但它自己并不是符号。”在《论德国悲剧的起源》第一章“关于认识论批评的前言”中本杰明提出:哲学的对象观念(Idee)不能直接描述,要通过概念(Begriff)及其从属于它的物为中介表现自己,即“独一无二地在概念与物的对应体系中表现自己。”这类似于新柏拉图主义的观点,但是与柏拉图的理念说不同,在本杰明,观念与物的关系即非分有也非摹写。
根据本杰明,语言最初是作为上帝的话语,而后经过亚当而成为人类的语言,他把它作为人类成熟的标志,表示人类对于史前期神话阶段的创造性超越。本杰明用“神话”在这里指示一种人类未成熟形态,一种尚未达到语言意识的宿命状态。在一九三五年的一则日记中他写道:“在这种(语言与思维的)联系中发生了一种摹仿表现能力中心的转移,它从眼睛到嘴唇,同时环绕整个身体。这一过程就包含了对神话的超越。”本杰明用“环绕”表示变化过程,这一变化通过运动完成:从“眼睛”到“嘴唇”、到语言意识,超越神话通过回忆与复活上帝赋予的语言灵魂完成。并且他认为,超越宿命状态不可能通过启蒙─像现代技术世界中启蒙理性所做的那样─而完成。这种神秘主义的语言学以及由此衍生的认识论和历史学的解释与辨证唯物主义一起构成了本杰明文学、社会和历史批评的哲学基础。
说到本杰明的哲学,虽然本杰明的哲学教育是新康德主义的,但这绝不意味着他基本上接受了康德哲学。恰前相反,在“未来哲学纲领”(一九一八年)一文中他要求超越康德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有限的经验概念,取消它对于人类经验意识的限制,为一种更高的经验概念作出说明。他把哲学定义为致力于建构和确定绝对真理的科学,因此要在这个意义上从根本上修正康德哲学。他提出以语言作为纯粹认识的工具,因为它不仅扬弃了主客观的对立,而且确保了从最低级到最高级经验─包括宗教经验在内─之间的连续性。在同年的“实用主义哲学大纲”一文中他又提出,作为一个纯粹认识概念的等级体系,哲学应该而且必须是上帝能够思考的对象,自然科学的经验概念应该代之以植根于语言的起源之中的宗教经验。
接下来让我们来顺次通过本杰明生平三部主要学术著作─一九一九年的博士论文《论德国浪漫派时期的文学批评概念》,一九二五年准备作为教授资格论文提交的《论德国悲剧的起源》以及一九三三年的《论技术再生产时代的艺术》再现他的文学批评理论。
关于《论德国浪漫派时期的文艺批评概念》
该书分两章,第一章本杰明从费希特的“反思”概念出发,把文艺批评界定为反思。他提出,“反思”作为对思想的思想不是对自我的反思,也不能理解为自我意识。这种超越自我的“反思”就是文艺批评,是在“绝对”中对艺术作品的反思,或者说,是一种以艺术品为中介的反思。援引十八世纪浪漫派诗人和哲学家F·施雷格(Friedrich Schlegel)他指出,浪漫派很正确地把反思理解为作一种美学形式,确定为艺术的最基本概念。
第二章从对费希特的“绝对”观念出发,阐述了浪漫派以及他的文艺批评观。他反对哥德关于批评是对作品的评价的观点,认为“与其说批评是对作品的评价,不如说是完善作品的一种方法”,“批评的中心目的不在于评价作品,而是对它的补充、系统化和完善,是在绝对层次上对它的扬弃,批评即显现作品之为绝对的艺术理念的体现”。
关于《论德国悲剧的起源》
一九三一年谈到这部著作时,本杰明认为它表现了真正的科学研究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学术活动的区别,并且提出这个研究运用了辨证的方法,通过它的独特的语言哲学理论表现为向辨证唯物主义的过渡。
该书的内容结构为:认识论前言,第一章:悲剧与悲剧戏剧,第二章:讽喻理论,每章又分三节。他以辩证法的三段论处理材料,最后以讽喻理论的合题表现悲剧意图的实现。
本杰明首先特别区分了古典悲剧与巴洛克剧戏剧,然后论证现代悲剧之为悲剧戏剧。他的悲剧戏剧概念是由两个概念合成,即“悲哀”和“戏剧”,区别于古典悲剧概念。他认为,古典悲剧的对象“不是历史,而是神话”,“是跟神与命运的斗争,是远古的直接现实化”。古典悲剧表现英雄人物通过死亡战胜命运。而悲剧戏剧,并不表现为破解神话─指人类史前期状态,不自由状态,表示命运─,尽管它也是通过一种极端的存在境遇,即死亡来表现生命。在悲剧戏剧中生命始终充满罪恶,并且最终不可避免地沉沦于死亡。通过显现历史事件中的自然力,悲剧戏剧将对个人命运的判决映射到历史的整体。悲剧戏剧的对象是历史。
第二章讨论象征与隐喻,论证隐喻之为悲剧戏剧的方法:通过隐喻扬弃历史现状,回复到隐喻所暗示的太初理想境界。本杰明提出,古典主义的象征手法作为对观念的启示是与隐喻相对立的。隐喻的对象是被忘却者,因此具有历史的特征,区别于平庸的“解释”(见《论波德莱尔》)。在“反对被误解了的实在论”(“Wider den missverstandenen Realismus”)一文中卢卡奇分析了本杰明“论德国悲剧的起源”的“隐喻”特征。它在主题、方法和内容上都以隐喻为对象:作为文章主题的十七世纪德国巴洛克戏剧本身就是隐喻的对象,就其方法而言,本杰明的哲学技巧是隐喻,说到内容,整篇文章就是一个隐喻、一个在巴洛克假面之下的关于现代艺术的隐喻。本杰明为合适的内容找到了合适的方法:隐喻作为哲学的技巧与隐喻作为艺术手法。甚至本杰明对题材解释自始至终都体现了他关于隐喻的思想:通过回到浪漫派他发现了“批评”概念的真谛,巴洛克的悲剧戏剧作为“隐喻”展现了艺术的本质,指点了历史的迷津,预示了未来。回到古代,或者说回到德国神秘主义时代,是本杰明文学理论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特征。
在这种哲学─神学隐喻中,通过亚当这个形象本杰明传达了对自己角色的憧憬:亚当作为人类的始祖和新时代的哲学家,既是原罪者又是疗治者,作为批评家承担起讽喻的犯罪,是为了回归到世界的真实。
《论德国悲剧的起源》一书有些章节完全是由语录像马赛克一样拼起来的,本杰明称之为对语录的“神奇”运用。他先从原文中摘出句子或句子成分,然后根据讽喻的目的把它们重新组合起来,并加上作者自己的意思,而并不要求这些成分的连续性。
作为反古典美学的宣言,《论德国悲剧的起源》还提出了“自主自足的作品居主导地位的古典文学时代已经结束”的观点,这种观点在“技术再生产时代的艺术”一文中得到阐发和完成。
“论技术再生产时代的艺术”
这几乎是一篇文章无产阶级新文学宣言,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
文中,本杰明告别了传统美学理论,以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出发,规划了未来文学图景。从原始宗教崇拜的观点出发他提出,传统艺术品是某种自我满足的、静观的、被接受的对象,它拥有一种宗教的内涵,并且在审美关系中发生影响,这种宗教因素他称之为“圣光环”(Aura)。然而艺术的这种“神圣性”品格是前工业化时代的特征,只存在于即时的、直接的、单一的审美关系之中,工业革命最重要的结果之一就是结束了传统艺术的宗教神圣性可能存在的条件。现代社会中,工业化的生产与复制使艺术审美不再是一次性的个人的观照与接纳,而是复多的同时性和可重复的历时性给予与群体的接纳,因此取消了产生神圣性意境和理性批评的空间。这一次本杰明并不要求回到艺术昔日的神圣与辉煌,而是预言全新的艺术时代及其不同以往的社会功能─它的政治的和革命的功能。
一九三四年本杰明提出了“作家作为生产者”的命题12,并由此发展出“论技术再生产时代的艺术”一文。本杰明提出,现代社会中文学的功能以及作家的社会角色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从事精神生产的文学家是出版商的雇佣劳动者,出版商购买和销售他们的产品。在这种市场化过程中,精神产品蜕变为消费品,思想与文化的传播为市场原则所制约。文学的意向、甚至革命的信念由于它之为“物”的品格,都变成了可交换的东西。文学作为对大众的启蒙和革命宣传都被商业化了,以至于资产阶级可以大规模地、商业性地传播革命思想,却不构成对自身的威胁,“反对贫困的斗争化解为消费的对象”。另一方面,通过工业化的生产与复制,资产阶级可以把它的主义造成公众现象─集体造神与崇拜─,这就是政治的唯美化,法西斯主义的蔓延即是一例。只有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才能通过技术时代大规模生产与复制的可能性在新的审美关系中实现艺术的无产阶级政治功能。以电影作为现代艺术的典型,本杰明把现代艺术理解为纯粹世俗的媒介─政治革命的媒介─,以艺术作为改变世界的手段。本杰明认为,作为集体创作的产品和集体观照与接受的对象,观众在接受过程─看电影─中完成了自我组织、自我控制,从而实现了一种大规模的、直接的政治净化。
在苏联的共产主义文学中本杰明看到了未来社会文学生活的理想模式。在这个社会中文学为整个社会所共有,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区别只是相对而言。作为读者,每个劳动者都有场合需要写作和表达自己─例如告状、写报告─,在一定条件下都可以是作家,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差别从根本上消失了。在一切写作行业中,本杰明认为报纸是无产阶级文学最重要的阵地,首推新闻记者为文学的无产者。他的无产阶级文学纲领定位文学家为以精神生产为无产阶级服务的革命者,他甚至极端激进地提出:不论一种文学本身的政治倾向怎样革命,只要作家还是屈从于个人的意向,而不是作为一个生产者而感觉到他与无产者的团结一致,那么他的文学仍然可能是反革命的。
八 历史唯物论、无产阶级革命与救赎
本杰明的历史哲学表现为一种神学与马克思主义结盟的现代神话,它以神学的一元论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以神学的罪与罚、以上帝的救赎从道德上阐发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公正性。
与唯物史观一致,本杰明把历史类比为自然过程,视资本主义社会为现代社会的史前期。从神学出发,他把现代社会解释为神的否定,因此是必然毁灭的对象。在本杰明救赎的历史哲学中,现世的堕落对应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先知与拯救对应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革命,把当下世界理解为救世计划先定的瞬间对应唯物史观的历史决定论。在“论暴力”(一九二一年)一文中,本杰明把“无产阶级革命”誉为一种要求彻底消除暴力的、唯一能彻底打破暴力恶性循环的、纯粹的、非暴力的暴力。“属于拯救的”─他在“论‘历史’概念”(“Ueber den Begriff der Geschichte”)一文中告诉人们─,还有“坚决的、看起来好像血腥的干涉”。本杰明以上帝对历史的干预解释革命暴力的积极历史作用,宣告了救世主与无产者革命的直接结盟。显然,这并不像一些人解释的是一种神学的人道主义,这种神学或宗教关怀是直接现实政治的。这种神学的资本主义批判,这种“现代虚无主义”,或是用卢卡奇的话说,这种“宗教的无神论”具有强烈的历史与现实相关,它不像古典的非理性主义那样表现为对历史的反动,而是在历史的紧迫和直接的现实性之中重新发现超验与救世。
结束语
本杰明生活于世纪的上半叶,一个充满问题的时代。于是他追求神话,制造神话,在神话中应许救赎。今天是世纪末了,历史宣告了本杰明神话的破产。我们的时代依旧充满了问题。我们还要再经历一次神话的轮回吗?!
注释:
1. 盖世太保为第三帝国时期德国秘密警察的简称。
2. W·洪堡(Wilhelm Humboldt):1767─1835,外交官、语言学者和教育改革家,人道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教育改革中他强调人道主义与学术自由的精神,要求限制国家对教育的干预。
3. 白里克里斯时代指波(斯)希(腊)战争之后,公元前五世纪雅典民主政治盛期,白里克里斯(Perikles)为当时著名的将军和政治家。
4. 见哈塞尔贝格(Peter von Haselberg)同名文章“德国人W·本杰明”(“Der Deutsche Walter Benjamin”, in MERKUR,1978,p.592─600。
5. 见《书信集》(《Briefe》,hg. Von Th. Adorno und G..Scholem, Frankfurt 1966),p.374。
6. 《爱因斯坦谈人生》(《Albert Einstein,The Human Side》,ed. By H. Dukas and B. Hoffman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高志凯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
7. 见Asja Lacis:《职业革命家》(《Revolutionaer im Beruf》,Muenchen,1971),p.45)。
8. 罗沃特(Rowohlt)为德国著名出版社之一,尤以出版严肃的名人传记著称。
9. 布鲁斯特(Marcel Proust, 1871─1922),法国著名作家,一九一三至一九二十七年,以十四年时间完成了巨著《追忆似水流年》(《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这是一本回忆体小说,在回忆中重现整个世界。这本小说被认为是现代文学的开始,与一九二二年乔伊斯(James Joyce)的小说《尤利西斯》(《Ulysses》)齐名。
10. 见《Die Kunst ist in Gefahr》(艺术在危机中),p.131。
11. 《莫斯科日记》(《Moskauer Tagebuch》),p.106。
12. 见本杰明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七日报告“作家作为生产者”。
直接参考书目:
W. 本杰明:
1. “论语言自身与人类语言”(“Ueber Sprache ueberhaupt und ueber die Sprache des Menschen”),1916。
2. 《论德国浪漫派时期的艺术批评概念》(《Der Begriff der Kunstkritik in der deutschen Romantik》,1920,本文是本杰明的博士论文
3. “论暴力”(“Zur Kritik der Gewalt”),1921。
4. “论哥德的心灵的亲睦”(“Goethes Wahlverwandtschaften”),1922。
5. 《论德国悲剧的起源》(《Ursprung des deutschen Trauerspiels》),该文为本杰明的教授资格论文,1925年完成,但为法兰克福大学拒绝,1928年第一次发表。
6. 《莫斯科日记》(《Moskauer Tagebuch》)
7. 《单行道》(《Einbahnstrasse》,1928。
8. 《十九世纪的柏林童年》(《Berliner Kindheit um 19 Jahrhundert》),1931。
9. 《论技术再生产时代的艺术》,(“Das Kunstwerk im Zeitalter seiner technischen Reproduzierbarkeit”),1935年发表于《社会研究杂志》(in《Zeitschrift fuer Sozialforschung》,1935),1975年在德国第八次再版。
10. 《德国人民》(《Deutsche Menschen,Eine Folge von Briefen》),1937。
11. 《布莱希特研究》(《Versuche ueber Brecht》),1937。
12. 《查里•波德莱尔─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Charles Baudelaire – Ein Lyriker im Zeitalter des Hochkapitalismus》),1974。
13. 《布莱希特诗评》(《Kommentare zu Gedichten von Brecht》),
14. 《弗朗兹•卡夫卡逝世十周年纪念》(《Franz Kafka ,Zur Zehnten Wiederkehr seines Todestages》)。
15. 《瓦尔特•本杰明文集》(《Walter Benjamin,Gesamte Schriften》)三卷本,in 3Bdn.,1977/78。
16. 《瓦尔特•本杰明通信》(《Briefe》),两卷本,1978。
17. 《与G.·肖勒姆的通信》(《Briefwechsel mit G..Scholem》),1980。
间接参考书目:
1. Th· 阿多诺,E·布洛赫,G.·肖勒姆:《瓦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von Th.Adorno, E.Bloch, G.Scholem u.a.),1968。
2. J·哈贝马斯等:《瓦尔特•本杰明的现实性─本杰明八十诞辰纪念文集》(《Zur Aktualitaet Walter Benjamims, Festgabe zum 80.Geburtstag》,von A. Monnier, H. Schweppenhaeuser, J. Habermas u.a.),1972。
3. B·维特:《瓦尔特•本杰明─作为一个批评家的知识分子》(B. Witte:《Walter Benjamin, Der Intellektuelle als Kritiker》),1976。
4. “乌托邦是一种记忆─关于瓦尔特•本杰明”,《时代周报》,1991年12月6日第74版(“Utopie ist Erinnerung,ueber Walter Benjamin”,von Marleen Storessel,in《Die Zeit》,Nr.50,6.12.1991, p.74)。
5. “亲人与朋友眼中的本杰明─多拉•本杰明与肖勒姆的通信”,《时代周报》1991年7月17日第43版(“Walter Benjamin im Spiegel der ihm naechsten Menschen – Unveroeffentlichte Dokumente: Der Briefwechsel zwischen Dora Benjamin und Gershom Scholem”, von Klaus Garber, in《DIEZEIT》,1992.7.17p.43)。
6. “从柏林到卡普里”,摘自“Von Berlin nach Capri. Walter Benjamin in Italien”,von Momme Brodrsen, in《Benjamin auf Italienisch Aspekte einer Rezeption》, Frankfurt a.M., 1982, p.120─142。
7. “‘天使的创意’论文集导言”,摘自“Einleitung zum Angelus Novus”,von Renato Solmi,1962, in《Benjamin auf Italienisch Aspekte einer Rezeption》,Frankfurt a.M. 1980, p.7─46
德国·埃森,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五日, 原载 台北,《当代》,1993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