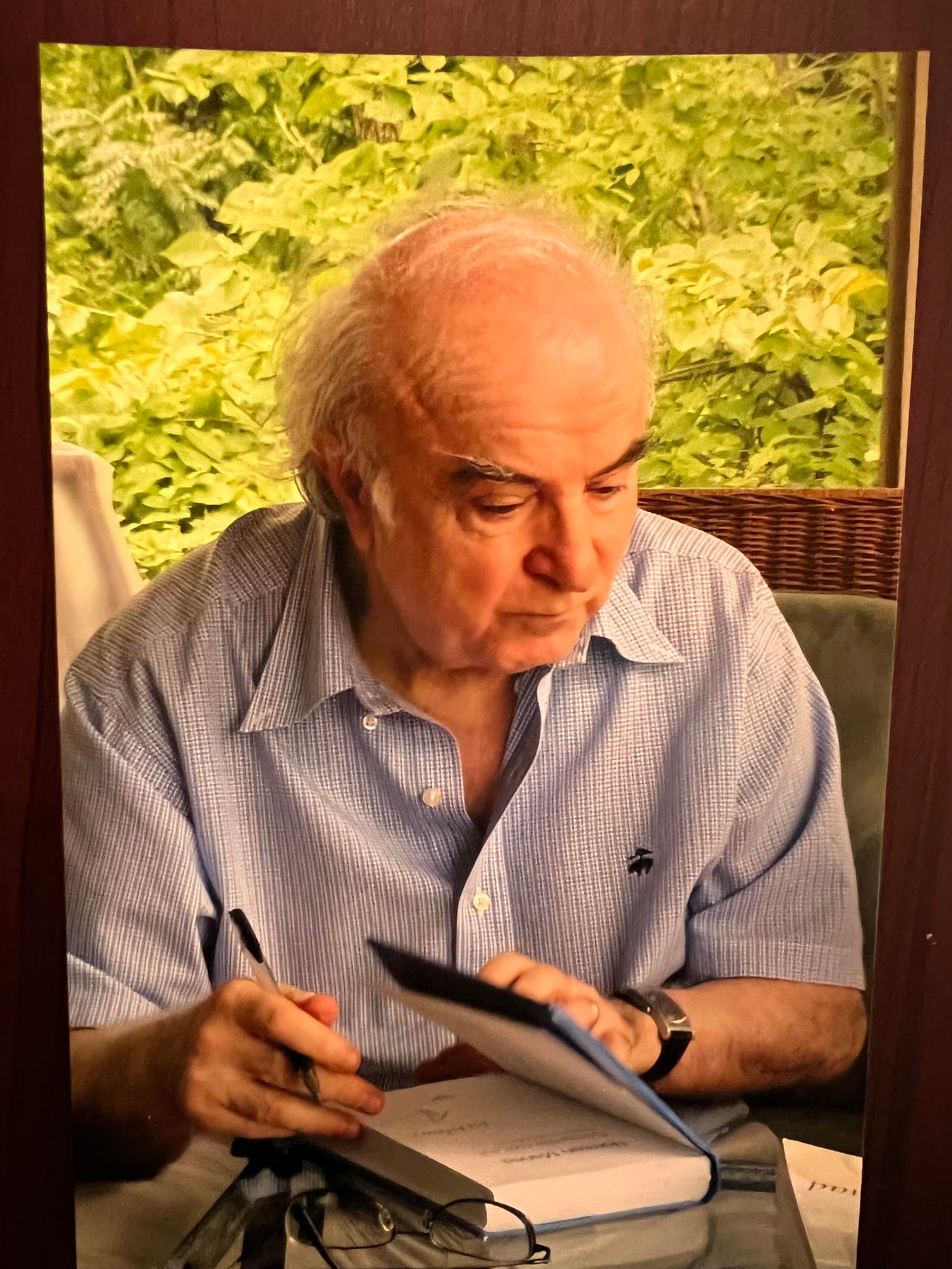諾曼·馬內阿:我想給世人留下一個警告
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對加薩走廊發動恐怖攻擊,哈馬斯與以色列戰爭爆發。
身為羅馬尼亞猶太人,諾曼·馬內阿一生經歷過三種集中營:納粹集中營、蘇聯集中營和羅馬尼亞集中營。加薩戰爭讓他感受到「30年代的鬼魂在美國追隨我」 。
同樣在本月,諾曼馬內亞的最新小說《流亡的影子》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 與他過去的所有小說一樣,這本小說首先用羅馬尼亞語寫成,並於 2021 年出版。
諾曼·馬內亞出生於1936年,現年87歲,大半生都是在流亡中度過的,他的寫作也圍繞著他在流亡中的生活和思考展開。
馬內亞的訪談通過電子郵件十多次完成,分為兩部分。 一部分為2017年完成的,另一部分為2023年12月完成的。對於他的寫作,馬內阿說,“我必須對未來的危險留下警告。”
第1部分:2023年12月
1 近期,哈馬斯襲擊加薩地區,以巴衝突再次成為世界焦點。 身為猶太人,你對此有何感想?
2023 年 10 月 7 日發生的事情是猶太人長期迫害和仇恨歷史的一部分。 這種血腥的仇恨讓我們想起野蠻的反猶太屠殺(大屠殺、宗教裁判所、納粹最終解決方案、大屠殺等),這是一種持久的痛苦。 這解釋了最近發生的事件與反猶太主義歷史記憶之間的聯繫,以及保護以色列國的存在和完整性的必要性。
哈馬斯是一個恐怖組織,其目標是從世界地圖上徹底摧毀和根除以色列和猶太人民。
以色列對大喊大叫、活活燒死、在父母面前殺害嬰兒和兒童、切割屍體以及劫持民眾的人質等野蠻事件的回應是任何國家為了保護其公民都會採取的正常防禦措施。 哈馬斯是一個納粹分子組織,不僅對以色列構成威脅,也對受害者和囚犯巴勒斯坦人民構成壓迫。 事實上,這對整個世界來說都是一個危險。
2 哈馬斯對加薩走廊發動恐怖攻擊後,哈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立即出現了親巴勒斯坦活動。 你怎麼看呢?
10月7日後,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和其他美國大學的學生示威活動並不是表達對巴勒斯坦事業的同情,考慮到他們所宣揚的口號是「從河流到海洋,巴勒斯坦將是自由的」。 這個口號是直接呼籲,煽動消滅以色列,正如哈馬斯憲章所規定的那樣。 人們認為,部分年輕一代學生的困惑源自於對歷史的共同認識,關注不準確的訊息,忽略了構成全球情勢的錯綜複雜的因素網。 「人權」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概念,但我們必須承認它的局限性,在戰爭時期,考慮到文化背景、政治背景、地理和軍事局勢等其他關鍵因素。 巴以衝突並不是簡單的善與惡的衝突。
3 以色列也對哈馬斯採取了軍事行動。 加薩地帶造成大量平民傷亡,其中包括許多兒童。 你怎麼認為?
以色列對其公民有權利和義務捍衛其完整性和未來。 加薩戰爭造成了包括兒童在內的大量受害者,這是一場巨大的悲劇,媒體每天都在報道,整個過程都充滿了恐怖。 我的傳記以法西斯種族滅絕為標誌,小時候,我發現自己正處於戰爭災難之中,處於滅絕的邊緣。 加薩的悲劇讓我想起了自己的經歷,我全神貫注地活在當下。 不幸的是,歷史重演,對我來說,由不明勢力維持的反猶太主義幽靈,作為對當前混亂局勢的回應,喚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氣氛。 在美國,我感覺到 30 年代的幽靈在追隨我。
4 能為我們介紹一下您的最新作品嗎? 在紐約流亡期間,您最強烈的感受是什麼?
是的,我剛剛出版了一本新書《流亡的影子》,重點關注我們這個混亂時代的知識/文化緊張。 這是一本關於流亡和疏遠的書,關於身份、孤獨、內疚和威脅我們日常生活的謊言。
我覺得,在我年老的時候,我必須對未來的危險發出警告,警告如果我們不照顧我們的星球和人類會發生什麼事。 這本書已經被翻譯成多種語言,我希望很快它也會引起中國讀者的興趣。
5 1997年您回過羅馬尼亞一次。之後您還回去嗎? 如果再回去,你的感情會改變嗎? 如果不是,那麼羅馬尼亞在您的心中或您的創作中佔據什麼位置?
羅馬尼亞對我來說,首先是羅馬尼亞語,我在流亡時帶著羅馬尼亞語,就像蝸牛照顧自己的房子一樣。
人類的處境、生命的本質是作家永恆的痴迷,當然還有語言、他用來建造他的作品和庇護所的神奇材料。
第2部分:2017
問:「1945年4月,我是個9歲的老男人。」在《流氓的歸來》中,你這麼形容自己的第一次歸來。 你還記得集中營的經驗嗎?
馬內阿:是的。 那正是當時我從集中營回來的感受。 時隔幾十年,我依然清楚地記得那時夢魘,那時的害怕,那時對未知的恐懼,那時的飢餓、那時的寒冷,那時的疾病,那時對壓迫我們的人的
仇恨。 我的祖父母便是在烏克蘭集中營裡時的第一個冬天去世的,那是納粹和他們同盟國在東歐的猶太人集中營之一。
問:你家中所有成員都被送到那個集中營了嗎? 他們後來都怎麼啦?
馬內阿:我們一家人是在1941年10月,和Bukovina(羅馬尼亞東北部的一個省)的所有猶太人一起被送往烏克蘭的Transnistria Camps 集中營的(我在《流氓的歸來》中稱它們是Trans -Tristia)。 其他省份的猶太人的情況不一樣:Moldavia和Muntenia這個兩個地方的猶太人有著苛刻的法律和大量的折磨,但沒有被送往集中營,被匈牙利佔領的Transylvania的一部分,猶太人被送往奧斯維辛 集中營。 我們家族被送往集中營的,除開我們全家和我的祖父母外,還有我的阿姨們、叔叔們,以及我的堂兄弟姊妹們。 在羅馬尼亞其他省份的親戚們都遭遇各自的災難,但各有不同的經驗。 我們所去的Transnistria Camps 集中營,由羅馬尼亞或德國人管理,目標是透過疾病、飢餓和寒冷,有時甚至是死刑來逐漸消滅被關押者。 這個集中營的死亡率是50%。
問:羅馬尼亞作家、《夜》的作者、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艾利‧維瑟爾(Elie Wiesel )當時是被送往了奧斯維辛集中營,他是來自特蘭西瓦尼亞(Transylvania)的嗎?
馬內阿:是的。 艾利·維瑟爾就是從羅馬尼亞這個地方被當時匈牙利當政者送往奧斯威辛集中營,在錫蓋特 (Sighet) 如今還有維瑟爾的紀念館。
問: 你第一次回羅馬尼亞是1945年對嗎? 當時什麼心情?
馬內阿:是的,我第一次「歸來」是1945年從集中營,第二次是1997年,從美國,我流亡的地方。 第一次回羅馬尼亞滿懷希望,在大屠殺後奇蹟般倖存。
問:你知道羅馬尼亞裔德國女作家赫塔·穆勒的《呼吸鞦韆》嗎? 這本小說是根據羅馬尼亞詩人奧斯卡· 帕斯塔爾的經歷寫的。 身為德裔羅馬尼亞人,帕斯塔爾在二戰勝利後,被關進了蘇聯人的勞動營,這個勞動營也在烏克蘭。
馬內阿:赫塔· 穆勒和奧斯卡·帕斯塔爾在羅馬尼亞屬於德國社團,他們用德語寫作。 帕斯塔爾在戰後所待的勞動營和我的是完全不同。
問:起初,你是贊成共產主義的?
馬內阿:身為年輕人,我當時被共產主義的偉大承諾所吸引,但不久我就明白其中的蠱惑人心與操縱,烏托邦在恐懼中變形了。
問:有沒有什麼特別事情讓你意識到共產主義是錯的?
馬內阿: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我為共產主義的神話,所有人都有一個幸福未來所深深吸引;後來我從這些幼稚的夢想中醒悟過來。 你只要睜眼去看每天的現實——充滿著謊言、恐怖、悲慘的事情和警察局裡的告密者——就已經足夠發現理論與現實之間的巨大的差別。
問:在您書中,您提到後來您的父親又去坐牢了,這是怎麼回事?
馬內阿:我父親被判5年,後來案件重審重判,他坐了一年牢。 雖然這是個小悲劇,但荒謬。 The Periprava 集中營是最野蠻的共產主義勞動營之一,我的父親被囚禁,對我們整個家庭來說都是可怕的災難。 在那個時候,很多家庭也有如此遭遇。
問:羅馬尼亞還有一個The Periprava 集中營?
馬內阿:佩日普拉瓦勞改營(The Periprava camp) (1956-1963)雖然命名是勞動營,但它實際上是一所滅絕營。 當時的共產黨當局不想公開承認這樣一所集中營的真正目的和情形。 這個地方靠近Danube河,被囚禁的人每天在炎日下工作很多個小時,修築早期的防堤壩。 因為缺乏食物和醫療,在極度嚴酷的氣候下長時間勞動,缺乏飲用水(犯人們使用Danube裡的被污染的水),看守們的野蠻行為、一些小事情招致的野蠻懲罰、殘酷的鞭打以及沒有人性的羞辱等等,在集中營裡似乎每三天就有一個人死去。 光是1960年,就有103位這樣的案例。 2013年的時候,羅馬尼亞共產主義罪行調查研究所以「種族滅絕罪」起訴了當年這所集中營的負責人loan Ficior上校(85歲)。
問:20世紀羅馬尼亞的歷史很特別,經歷了兩個極權: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 你自己親身經歷過,你是這麼看待這兩個極權主義的?
馬內阿: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還有今天的伊斯蘭血腥的原教旨主義——在製造可怕的恐怖和災難方面是相似的,但他們還是有不一樣的,經觀他們確實都有著極權體制 。 納粹主義有一個激進的傲慢的謀殺的意識形態;共產主義是建立在對於弱者的正義、共同體凝聚感、以及共同目標的理想之上的,這個理想被殘忍壓迫,欺騙和苦難出賣了。 此外,共產主義在許多國家傳播開來,它成為一種全球性的思想,儘管國家和民族之間存在著許多區別,比如說俄國和中國,人們是自己開始共產主義革命的;而在羅馬尼亞,共產 主義是二戰之後,共軍帶來強制執行的。 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有無數的受害者;在羅馬尼亞,這個政權雖然是東歐最殘忍的獨裁,野蠻與殺戮依然比中國和柬埔寨少。 波蘭、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國,與西歐在宗教信仰上有聯繫,情況更難說清楚。
問:極權主義對作家來說意味著什麼? 是否意味著作家會像一個“小丑”,如你在你的散文集《論小丑》的前言中所說?
馬內阿:對作家來說,極權主義不僅意味著他要和其他人一樣受到同樣的災難,同時還有審查、懷疑、不能隨心所欲地旅遊與閱讀,不能自由地創作和自由地表達你的觀點 和你的創作力。 一種被邊緣化的傻瓜,被一群警察跟蹤著,被這個國家的偉大的同志小丑嚴厲懲罰著。
問:你為什麼用小丑這個詞來形容?
馬內阿:我們的日常生活充滿了崇高、滑稽誇飾的巨大遊行和偉大撒謊的口號,浸染著一種苦澀的陰冷的幽默,這個詞剛好可以表現出這種怪誕氛圍。
問:為什麼用「流氓」來稱呼自己?
馬內阿:我在我的書中特意解釋了這個詞在羅馬尼亞文化背景中的意思。 在1930年代羅馬尼亞極度恐懼外國人的意識形態中,這個詞意思是一個好鬥的人或孤獨的知識分子。 在共產主義時代,它的意思是一個失業的嫌疑犯。
問:你在書中提到史達林和齊奧塞斯庫比提到希特勒和集中營頻率高多了?
馬內阿:極權主義者的意識形態和功能在本質上是相似的,但並非完全一樣。 共產主義靠著革命的啟蒙思想維持運作;納粹主義從一開始,就從民族主義立場對屠殺著迷。 我更多提到史達林和齊奧塞斯庫,因為他們佔據了我生命更長的時期。
問:在《論小丑》的序言中,你提到在極權體制下,一個作家如何做:諷刺。
馬內阿:沒有一個配方能告訴一位作家應該做什麼,該從事什麼藝術。
問:你提到西蒙娜‧韋伊的「大野獸」理論。 你也是這麼認為羅馬尼亞的共產主義社會嗎?
馬內阿:是的。
問:你是不是認為所有的極權社會都像「大野獸」?
馬內阿:是的。
問:你的《黑信封》第一次出版於1986年,當時你在羅馬尼亞。 在《論小丑》中,你有一篇文章談了這本小說出版和審查過程。 你甚至還附了一份審查報告。 是這樣的審查讓你決定離開羅馬尼亞的嗎?
馬內阿:在所謂的“社會主義”國家審查無所不在,因為國家是集體所有,集體所控制。 這是我離開羅馬尼亞的一個理由,恐怖和悲劇與一種新的令人厭惡的民族主義的結合是離開的其他理由。
問:你能介紹下當時的羅馬尼亞作家協會是如何運作的?
馬內阿:所有的出版社都是國營的,遵守黨的規定接受政府審查。 稿費是出版社付的,這意味著其實是國家付的。 羅馬尼亞作家協會是一種針對作家的職業協會,由黨領導和控制,它給會員職業身份和就業公民身份。
問:你在離開羅馬尼亞之前,已經出版了一些書。 你是如何保持自己寫作的獨立性呢? 不讓審查幹擾你的寫作呢?
馬內阿:我盡力。
問:什麼是新的討厭的民族主義?
馬內阿:新的民族主義如今到處成長,我聽說中國也有。 也許,它是也是對全球化和西方世界的所謂的「過度」自由的反應。
問:1986年,當你決定離開羅馬尼亞的時候,一位羅馬尼亞女詩人說:「不管發生什麼,我們都得生活在這裡,我們要在自己語言環境裡,堅持到最後。」你回答:「但是 為了寫作,我們首先得活著。墳地裡滿是不能再寫作的作家。他們留下來了,在墳墓裡,他們不再能寫了。」你似乎不同意她的觀點,寧願流亡?
馬內阿:我沒有也不願意流亡,我是被當時我在羅馬尼亞最後一段時間所面臨的危險被逼迫流亡的。
問:什麼樣的危險?
馬內阿:在我離開羅馬尼亞之前,我必須面臨的危險是恐懼、痛苦、腐敗、全面的審查和可疑的秘密警察的存在。
問:在《流氓的歸來》中,你寫了一場在美國的暗殺? 你是否也面臨這種危險?
馬內阿:被暗殺的人是芝加哥大學的一位年輕的羅馬尼亞學者Ioan Petru Culianu,這個暗殺發生在美國,那時我也已經在美國了。 這場謀殺引起了當時流亡的羅馬尼亞人的高度緊張,我收到的明信片就是類似某種死亡威脅。
問:這場謀殺是鐵衛軍做的。 可以把鐵衛軍看成是羅馬尼亞的納粹嗎?
馬內阿:鐵衛軍是一個極右翼、民主主義和反猶太組織,它大約興盛於1930年代晚期。 它有很深的原始正統基督教的宗教成分,它致力於一個「純潔」的國家,消滅所有外國人,有點類似於今天穆斯林的野蠻的狂熱主義。
問:鐵衛軍不是1941年就滅亡了嗎? 為什麼在1990年代的美國,還有他們的活動?
馬內阿:共產主義垮台後,右翼又復活,對極右派的懷念成為新的流行的反共產主義的一部分。
問:你是如何看待如今(20世紀和21世紀)新的民族主義思潮?
馬內阿:如今我們在俄羅斯、中國、匈牙利以及其他許多地方看到的民族主義是一個新的危險的演變,這可能會導致新的大的衝突。
問:1997年,十年流亡後,你決定第二次回羅馬尼亞,這次你是什麼心情?
馬內阿:第二次回去,我已經是另一個年紀了。 我為齊奧塞斯庫之後的羅馬尼亞的情況和第一次後共產主義時期羅馬尼亞國家媒體對待我的方式感到極度緊張和不安。 我拒絕公開露面,我只和我的朋友見面和去墓園。
問:第一次後共產主義時期是指什麼時候?
馬內阿:1989年12月,羅馬尼亞叛亂,殺死了獨裁者齊奧塞斯庫,第一個後共產主義時期就是從這時開始的,開始向一個民主國家轉變,如今依然在轉變。 不過,羅馬尼亞如今已經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歐共體的成員了,它必須遵守一些規則,開始以法治國。 不幸的是,因為腐敗、蠱惑宣傳和裙帶關係等,它的氛圍如今依然是沉重的,但它已經有了一個民主的初始的社會政治框架(即便是脆弱的和矛盾的)。
問:在網路上我看到有些羅馬尼亞人還很懷念齊奧塞斯庫事情,修他的墓地,到他墓地獻花,認為齊奧塞斯庫時期的經濟更好。 這是真的嗎?
馬內阿:資本主義和民主不是天堂,天堂般的樂園不是為我們塵世的生命預備的。 它是一個自由的社會,有自由競爭、自由市場、自由思考。 它也是一個有著失業的社會,有時候在財富上有著巨大困難。 你不能將它與極權國家的貧窮與精神上的奴役相比較,因為那決定了每一個的一切。
問:你最後為什麼選擇紐約作為你的庇護所?
馬內阿:我來美國是因為富布萊特獎學金,後來帶在紐約是因為我在紐約州巴德學院的工作。 不過,如今我依然認為這是最好的選擇,因為紐約是世界流亡之都。 紐約是一個非常混合的大都市,有著來自全世界的人。 這裡的氛圍非常世界性和全球化。
問:住在紐約,你人生最大的改變是什麼? 你似乎還是在用羅馬尼亞語寫你在羅馬尼亞的生活。
馬內阿:我住在紐約我的房子裡,我的寫字桌上,在那裡,我寫的是關於人類和他們的故事,這些故事可能來自羅馬尼亞或其他任何地方。
問:你是怎麼定義自由的呢? 紐約給了你自由嗎? 或是寫作上的自由?
馬內阿:自由是一頭由它的對立面所定義的野獸;它的缺乏所定義。 缺乏自由意味著沒有選舉的自由、選擇的自由、表達的自由、移動的自由、私有財產的自由和隱私,所有這些都與壓迫性的社會緊密相關。 紐約當然給了我自由,比較它不是共產主義統治下的布加勒斯特。 但是自由取決於人類;人類天生不是完美的,所以社會也不是完美的。 無論在哪裡,自由總是有它的限制。 它依賴於你將自由的「真實性」和誰比較。 說到底,關鍵在於在跟外在世界打交道的過程中,你能獲得多少自由。
問:索爾· 貝婁的作品為什麼會吸引你? 你們兩位都是猶太作家,你認為你們兩個的寫作有共同點嗎?
馬內阿:貝婁是一位「知識分子型」的作家,與美國其他作家相比,他更思考人類生命的一些本質問題。 我在他那裡也發現了歐洲人趣緻的痕跡。 此外,當然他始終在壓力之下保持著猶太人複雜命運的關注(甚至今天,他還因此在許多地方遭到敵視)。
問:“知識分子型”作家,非常準確形容貝婁。 你認為自己也是嗎?
馬內阿:可能我也是被認為是這樣的。
問:你在這本書的前言,談到了索爾 貝婁和羅馬尼亞文學的關係。
馬內阿:貝婁的五個妻子中的一位是羅馬尼亞人。 他的小說THE DEAN OF DECEMBER就發生在羅馬尼亞。
問:在書中,索爾 · 貝婁有一段對漢娜· 阿倫特的評價。 他說:“我其實在漢娜阿倫特的言論裡看不出任何東西,除了她招供了自己的反猶主義立場。對於一個哲學家來說,說出這樣的言論著實令人感到蹊蹺。 它還能意味著什麼? 它是她為自己對德國高端文化的忠誠所做的辯護,這種高端文化是她一直在思考的東西;而她認為,成為德國高端文化的代表,這是她此生 中的殊榮。為了某種高端的理由,成為一個猶太人不知怎的就要放棄某些東西。當然,既然我們有關於她與海德格爾戀愛的記錄,我們有明白了那個理由是什麼。我其實 壓根兒沒有想到這事,至少我沒有想到任何像此種性冒險一樣令人拍案驚奇的事情。但不管怎樣,我從來都不肯定我對她的立場。我是說,我不假裝理解她。 ”你同意他的看法嗎?
馬內阿:在有關對漢娜 ·阿倫特對東歐猶太人傲慢,有關她對納粹滅絕營的錯誤判斷和被監禁的猶太人與壓迫者之間的共謀的錯誤判斷方面,貝婁是對的。
問:貝婁曾經在巴德學院任教,漢娜· 阿倫特的丈夫也曾在那裡教書。 她的墳墓如今也在那裡。 貝婁是他們的朋友嗎?
馬內阿:這是從我和貝婁的對話錄裡一個評論。 索爾是對的,他認為她看低,蔑視歐洲的猶太人。 他也認為,她說的有關歐洲基督徒反猶太主義甚至滲透到了猶太人當中,然而這些話其實對她自己也是成立的。 她也過於輕率的對集中營裡囚禁的猶太人與納粹的合作下判決。 實際上,那是無可奈何的極端情況。
問:你自己是如何看到漢娜· 阿倫特和她的極權理論的呢?
馬內阿:她的關於極權主義理論的書是對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和極權主義國家的一個重要的心理和功能上的審查。
NM. New York 2022 photo 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