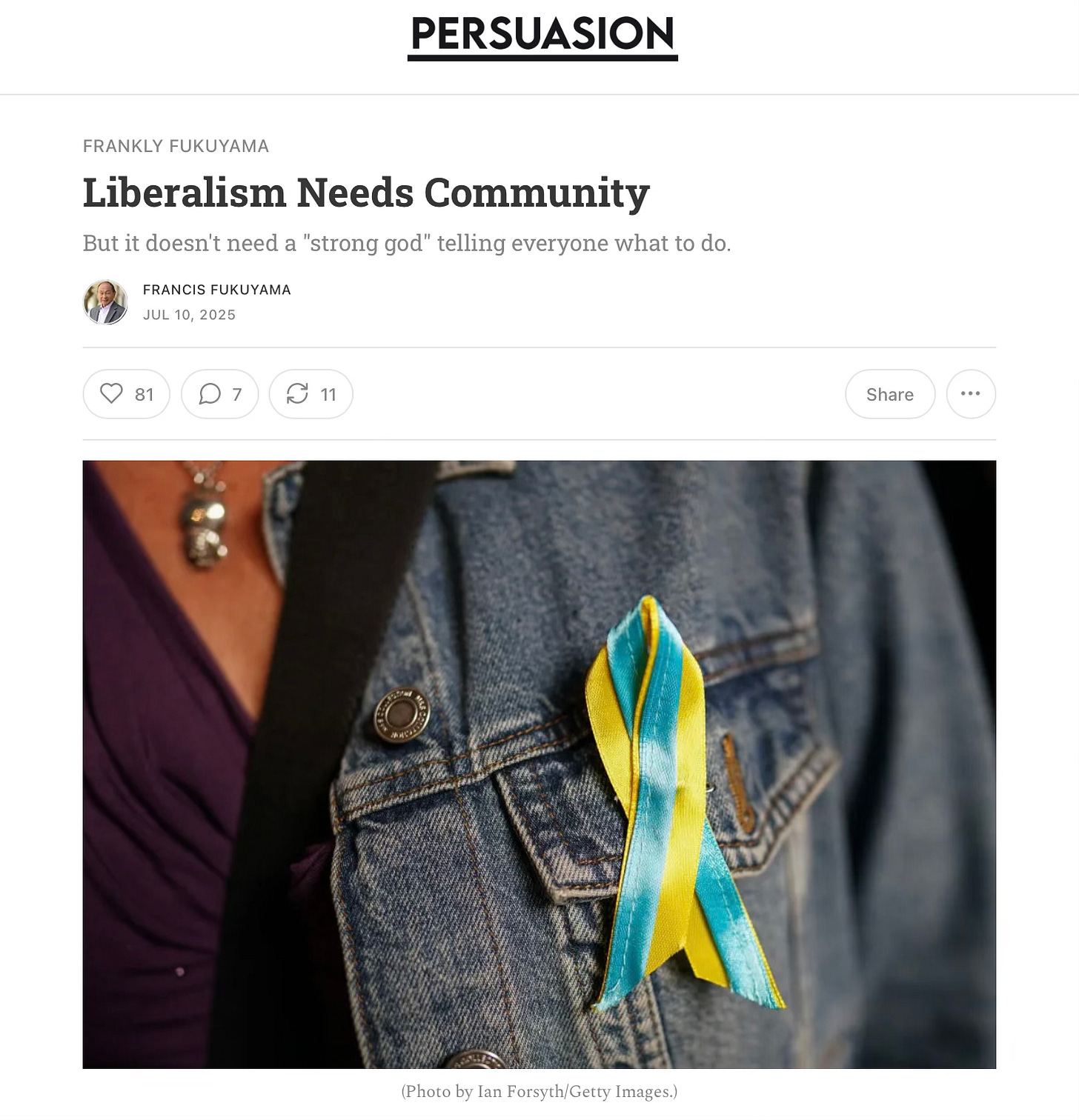編者按:自由主義誕生於17世紀,旨在調和多元社會中多個相互衝突的「強大之神」(如宗教、民族主義),強調個人自主與包容性。然而,社群主義者批評自由主義過分強調個人自主,忽視社群與道德判斷的重要性,認為真正的社群建立在共同信仰與美德之上,而非僅僅是利益結合。後自由主義者如R.R.雷諾認為自由主義否認形而上學真理,導致社群基礎薄弱。真的如此嗎?福山反駁,當代社會的多元性使得單一「強大之神」難以被普遍接受。健康的自由主義應以充滿活力的公民社會為基礎,允許個人自由追求信念,同時尊重社群價值。烏克蘭的例子顯示,自由主義需仰賴公民美德與犧牲精神才能存續,而非僅靠和平與安全。
本文原文為英文Liberalism Needs CommunityBut it doesn't need a "strong god" telling everyone what to do.(Persuasion:Francis Fukuyama專欄7月月10日)。經作者和雜誌授權,波士頓書評翻譯成中文,為書評福山專欄最新文章。
免費訂閱《波士頓書評》及相关事宜发送邮件:boshidunshuping@gmail.com,隨意打賞:Zelle,PayPal:boshidunshuping@gmail.com 用戶名:Boston Review of Books;長期支持請點擊下面訂閱,升級為付費訂閱。
上個月在本專欄重新刊發的列奧·史特勞斯 1941 年關於「德國虛無主義」演講的摘錄,指出了對二戰前自由主義的主要指控,這一指控導致許多德國年輕人支持納粹運動。其核心是:自由主義並非圍繞一個核心道德學說構建;相反,它主張容忍不同觀點,以此作為降低政治風險的手段。這就是為什麼在自由主義社會中,我們經常被勸誡要「非評判性」,因為對「更好」與「更糟」的評判意味著我們佔據了比批評對象更高的道德立場。自由主義社會對不同觀點持開放態度——它們尋求「包容性」。
但是,正如施特勞斯所指出的,道德判斷是人類本質的核心。我們是道德動物,擁有敏銳的頭腦,能夠對「更好」與「更糟」作出判斷。我們反抗一個由懶惰的自我利益驅動的社會,這樣的社會沒有更高的行為標準,也沒有對人類卓越的欣賞。
道德判斷實際上是創造人類社群的基礎。許多人並不希望對其他觀點無限開放,而是更願意生活在圍繞共同信仰和激情構建的封閉社會中。對自由主義最長期的批評之一是,它只為社群提供了最薄弱的基礎。人們可以圍繞共同利益建立社群——這就是營利性公司的本質——但最強大的社群是圍繞深層信念構建的。
1930年代驅使年輕德國人走向國家社會主義的對自由主義的憎恨,正是今日全球各地人們遠離1945年後自由主義共識、轉向各種反自由主義或後自由主義學說的動力。根據《First Things》雜誌編輯R.R.雷諾( R. R. Reno)的說法,過去三代的自由主義計畫試圖削弱被認為是20世紀初血腥衝突驅動力的「強大之神」——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宗教。如今,這些「神」正在回歸,並出現在進步左派和極右派的政治中——特別是右派,當今右派的特徵是要求強烈的民族認同或以宗教為基礎的國家社群。
然而,對於自由主義破壞社群的指控,存在一個有力的自由主義回應。問題在於,正如1930年代的情況一樣,自由主義的捍衛者尚未充分闡述這一回應。自由主義本質上並不反對社群;事實上,有一種自由主義版本鼓勵強大社群和人類美德的繁榮。這種社群通過發展強大且組織良好的公民社會而形成,在其中個人自由選擇與志同道合的人結合,追求共同的目標。人們可以自由追隨「強大之神」;唯一的條件是沒有一個單一的強大之神將整個社會綁繫在一起。
這些論點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由社群主義的自由個人主義批評者(the communitarian critics of liberal individualism)提出,像是阿拉斯代爾·麥金泰爾(Alasdair Macintyre)、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和麥可·桑德爾(Michael Sandel)等作家。他們的主要目標是自由主義理論家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他在許多方面定義了他那一代自由主義學說的主要基礎。
正如原型自由主義者( ur-liberal)約翰·斯圖爾特·密爾的情況,羅爾斯最關心的是保護個人自主性——那個受到社會壓力威脅、被迫順從的孤獨異議者或非主流聲音。對羅爾斯自由主義者而言,自由主義社會需要在所有領域最大化個人自主性,不僅通過保護個人權利免受國家權力的侵害,還要抵制社會對順從的壓力。
社群主義者則相反地主張,個人自主性往往表現為希望將自己置於社群約束之下的欲望。這在現代社會中人們持續的宗教信仰中尤為明顯:他們並不希望免受宗教的影響,而是希望擁有自由選擇追求宗教信仰的權利。這正是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中宗教自由的理解:其目的是保護宗教信仰的「自由行使」。美國及其他當代自由主義社會並不阻止其成員追求他們所選擇的任何強大之神。唯一的限制是,這種追求不能侵犯他人追隨自己「神」的權利。
後自由主義的批判在面對當代社會的事實多元性時顯得無力。當然,許多人希望將自己置於某個強大之神的約束之下。但現實是,存在許多強大之神,且人們對應該追隨哪一個並無共識。像阿德里安·弗繆爾(Adrian Vermeule)或帕特里克·迪寧(Patrick Deneen)這樣的整體主義者希望這個「神」是某種傳統天主教形式,但又有多少美國人會接受這種選擇?其他美國人偏好的印度教、自由派新教或異教之神又該如何處理?R.R.雷諾談論時似乎認為存在一種人類理性可以觸及的更大形而上學真理,而這種真理被自由主義否認。或許吧。有人可能會說,美國開國之父中的一些人相信某種基於人性理解的亞里士多德自然權利觀。但今天有多少人會接受這樣的形而上學?在達爾文主義和人工智慧等發展面前,自然權利又會變成什麼樣子?
那些渴望回歸強大之神及其所孕育的社群的人,必須面對一個事實:存在許多潛在的強大之神,而這些神彼此並不一致。這一點在後自由主義右派中尤為明顯。正如馬修·羅斯(Matthew Rose)在其著作《自由主義之後的世界:激進右派哲學家 A World after Liberalism: Philosophers of the Radical Right》中所示,保守派基督徒與可以稱為尼采式虛無主義者(Nietzschean nihilists)之間存在尖銳的意識形態分歧。後者包括當代另類右派的先驅,如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尤利烏斯·埃弗拉(Julius Evola)和阿蘭·德·伯努瓦(Alain de Benoist),他們將西方文明的衰落歸咎於基督教。他們直接引用尼采的觀點,針對基督教主張人類普遍尊嚴的觀念,認為這是現代性的根本錯誤。他們希望恢復一個等級制度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強者不再受到弱者的約束。這解釋了另類右派中一些人對異教神如奧丁(Odin)的迷戀,或他們對生命主義等學說的興趣。
自由主義在17世紀誕生,正是為了應對多個強大之神之間的衝突問題。當時,信奉同一神的不同教派——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在歐洲血腥戰爭中相互爭鬥。在我看來,自由主義的務實正當性至今仍然成立:它是一種調和多元社會中相互衝突的強大之神的方式。
一個健康的自由主義社會不僅僅是減少衝突的社會。一個健康的自由主義以強大的社群為特徵,人們的熱情和興趣促使他們在社群中團結起來,追求共同的目標。它圍繞一個充滿活力的公民社會而建。在某些情況下,這些社群的願望可能與其個別成員的權利相衝突。羅爾斯自由主義的社群主義批評者(The communitarian critics of Rawlsian liberalism)認為,最大化個人自主性並不一定是超越所有其他社會價值的最高善。例如,國家的權力不應被用來支持那些故意冒犯宗教信仰者情感的挑釁藝術。
此外,對自由主義中立性的信仰不應剝奪社會對美德與卓越的信念和尊重。事實上,小寫的共和主義(The small-r republican,意思是「非黨派共和主義者」)對自由主義的詮釋將公民美德置於現代綜合的核心。
批評現代自由主義的人認為,這一學說使世界變得平淡無奇,驅逐了所有的強大之神,他們應該睜開眼睛,看看現在烏克蘭正在發生的事情。那個國家已成為一種英雄式自由主義的典範 (a model of a heroic liberalism ),其公民為了捍衛國家和個人的自由,承受了難以想像的苦難。這是一個很好的提醒:沒有美德,自由主義無法存續,即便和平與安全已使當代自由主義社會的許多居民變得自滿,過分專注於自己的小小私人世界。
福山專欄 | 列奧·史特勞斯的令人毛骨悚然的預言
編者按:1941年利奧·施特勞斯在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發表關於“德國虛無主義”的講座。施特勞斯認為,德國虛無主義並非完全的破壞欲,而是針對現代文明道德意義的否定,特別反對自由主義所追求的開放社會、平等與舒適生活,認為這導致道德淪喪和“末人”的出現。這種虛無主義源於對現代文明的道德抗議,推崇封閉社會的嚴肅性和犧牲精神,深受尼采影響。施特勞斯指出,德國虛無主義缺乏清晰的替代願景,這使其危險,最終助長了納粹主義的興起。當下的美國讓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想起施特勞斯當年的預言。福山將當年的德國與當今美國的“後自由主義”思潮相比,指出當前極右派對自由主義的不滿同樣缺乏連貫替代方案,部分人嚮往宗教主導的道德秩序,部分人追求等級與強權政治。他警告,自由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