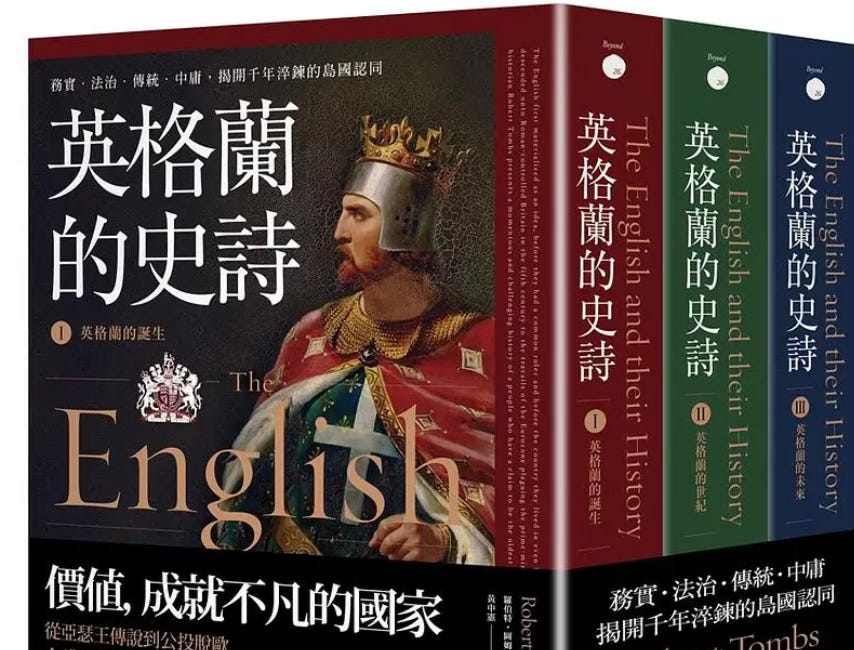编者按:抗战期间,除了大名鼎鼎的西南联大,其实还有西北联大和內地許多大學。《何去何从》便讲述了一所內地大學裡的知識分子和此后命运的故事。今年五月,壹嘉出版社(1 Plus Books)出版长篇小说《何去何从》,这是一部描写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长篇小说。以国立中夏大学为背景,故事横跨抗日战争至"文化大革命"中期,呈现出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在战乱与政治运动中的挣扎与沉浮,展现了三代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的不同选择:坚守、妥协,还是被动沉沦。他们的经历与心境,共同勾勒出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集体命运。
作者佘其(1922-2009),20世纪30年代末就读于女子师范,加入共产党地下组织,曾任地下党支部书记。女子师范毕业后,因地下组织被破坏失去组织关系,并一直寻求与组织重建联系。抗战时期任国立中学国文教师,其后在多所大学担任过图书馆员、研究员、教授和领导职务。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61年"摘帽",1984年平反,恢复党籍并追溯党龄。小说根据作者亲身经历及所见所闻撰写,为作者遗稿,由后辈整理出版。
本访谈为壹嘉出版社对作者后辈、整理者的访谈,壹嘉出版社授权刊发。
免費訂閱《波士頓書評》及相关事宜发送邮件:boshidunshuping@gmail.com,隨意打賞:Zelle,PayPal:boshidunshuping@gmail.com 用戶名:Boston Review of Books;長期支持請點擊下面訂閱,升級為付費訂閱。
问:Ning ,您是小说《何去何从》作者佘其的孙女和她手稿的整理人,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的来历吗?它是如何被写下,又是如何重见天日的?
Ning:我祖母是一位不平凡的人,经历了不平凡的时代。她一直有强烈的生存欲望和写作欲望。我记忆中,她一直都笔耕不辍,但是从来没写过长篇小说。这部作品大约是从七十岁开始动笔,一直陆陆续续写了有十年。到八十岁,这部书应该基本完成,可是阿兹海默症逐渐夺去她的记忆和写作能力。得到手稿以后,我所做的,就是按我个人对我们家和过去时代的记忆和理解,整理成一部书。
问:据说,佘其的原稿没有书名,为什么选择“何去何从”作为书名?
Ning:我的前辈几代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从我祖母出生的二十年代,中国一直经历着一轮又一轮的动荡。知识分子一直在艰难生存中纠结和挣扎,一次又一次陷入迷茫无助的境地,面临何去何从的困惑。 “何去何从”代表了三代知识分子的苦闷、彷徨与无助。
谈:小说主人公俞正堂是五四一代大学知识分子的代表,也是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群体的缩影。有意思的是,小说中写了他一段比较特殊的经历:他大学毕业后先是试图从政报国,被冯玉祥派到某个边远之地去当县长,差不多是被土匪连骗带吓唬地赶了回来,然后转向教育救国。这段经历是有所本的吗?
Ning: 这个情节确有其事,有曾祖父的影子。中国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中开始觉醒,很多人苦苦探寻各种救国之道,包括清正为官,救民于水火。上世纪二十年代北伐战争期间,冯玉祥主政河南,推行政治改革,开创县乡级民选,选拔出身平民的进步青年担任基层官员。俞正堂和黄敬齐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当上县长的。但是个人奋斗,终不敌动荡时局和土匪流寇。从政救国等各种救国梦想破灭以后,大批知识分子最终聚集在教育领域,这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又一个何去何从的选择。俞正堂的经历极具代表性。
问:我个人印象最深的,还有校长廖宗甫。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知识分子形象。他属于典型的“学者官僚”——重视组织、工于权谋,但他始终试图在政治夹缝中为大学守住一片空间。战后复员,因内战局势恶化,他带领师生先下江南,再远迁台湾。1949年逃往台湾后,他身陷困顿、山穷水尽之时,仍然尽力帮助追随他的师生与家眷安顿生活,以一名“尽责官僚”的姿态在学术与制度废墟中挣扎护持。这个人物形象的多面性,让他在众多知识分子写照中显得非常特别而真实。这个人物是否有原型?
Ning:书中的多数人物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原型,具体的原型都是谁,作为后人也只能猜测。第四章登场的廖宗甫这个人物确实比较特殊。他抗战复原后从另一所国立大学来做中夏大学校长。文人相轻,以黄敬齐为代表的一些教授对他有抵触,不买他的帐。但是,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反动校长”或“反动文人”。他既要在政治夹缝中尽校长之责为大学求生存,又要在知识分子堆里博人望。既想让师生都服从他,又害怕外界干涉将学潮闹大,自有一番苦衷。他带领部分师生逃到台湾后,晚景也很可怜。就连后来中夏大学的共产党领导干部,也是 “学术官僚”。曾先后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的江隆基和陆平,都是北大学生出身的“学术官僚”,又何尝不想把大学办好?但是前者因为反右不力被调离北大,文革期间被都活活斗死;后者被文革“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点名批判,受到诬陷和迫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在小说中,中夏大学党委书记邓梓华就是类似这样的人物。
问:已有的历史与文学作品中,对西南联大和沿海地区大学的内迁反映的比较多,而内地高校的内迁则似乎是一个被忽略的领域。相比大师名流云集,汇聚国家顶级资源,凝聚国人关注的西南联大和沿海名校,内地高校资源相对贫乏,关注的人较少,各类历史资料的留存也不多。您所写的“中夏大学”正是一所位于内地、命运颠沛的大学,可以说填补了这个空白。“中夏大学”是否有原型?您认为它的迁徙经历与西南联大相比,有哪些不同之处?
Ning:这是一段不幸被忽视的历史。抗战时期除了有西南联大,还有西北联大。西北联大的影响之所以不及西南联大,是因为存续的时间不长。 1937 年平津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国立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于 9 月迁至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1938 年 3 月,西安临时大学再次南迁城固,改国立西北联合大学。1939 年8月,当时的教育部指令西北联大改组为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农学院和西北医学院五所独立的国立大学。
其他内地的国立大学,也都历经颠沛周折。如国立山东大学,1937年11 月从青岛迁往安徽安庆,不久再迁四川万县。1938 年春在万县复课,师生后来转入国立中央大学。河南大学最是周折,在日寇占领河南省会开封后,即迁往豫西山区。1944 年5月,日寇突袭河南大学临时校址,造成惨案,人员伤亡,校产损失,还有教授被俘。河南大学师生被迫再向豫西南转移,然后入陕,先在汉中城固落脚,最后到了陕西宝鸡。
这些内地国立大学也都有许多著名的教授,如闻一多、梁实秋、洪深、老舍、游国恩、童第周、任之恭等曾就职山东大学,范文澜、冯友兰、董作宾、白寿彝、赵连芳、樊映川等曾就职河南大学。著名的新闻工作者、历史学家、诗人和杂文家邓拓,歌剧《白毛女》、歌曲《南泥湾》的创作者音乐家马可,军旅作家、长篇小说《红日》的作者吴强,作家姚雪垠等,都曾是那个时期河南大学的学生。这些内地的国立大学,在抗战时期都历经磨难,师生们毅然坚守,希望历史不要忘记他们。
问:谈起知识分子群像,人们都会想起钱钟书的《围城》。《围城》的时代背景与《何去何从》的前半部是一致的,止步于抗战胜利;反映的是知识分子的局限、虚伪、精神困境,作者对这个群体抱诙谐、嘲讽的态度。《何去何从》则从抗战一直写到文革,着重反映知识分子在严酷的政治高压下的挣扎,他们的自由、尊严乃至生命的被剥夺,反映他们的群体性幻灭与制度性压迫下的崩溃。虽然写作手法克制,读者能够感受到您对笔下的知识分子群体抱着深重的同情与悲悯,对他们所遭受命运的愤怒,对民族文化和精神未来的困惑或者说悲观。您怎么看待与《围城》的这种不同?
Ning:钱钟书先生曾经说过,《围城》是他的“游戏之作”,这或许是钱先生自谦。但是正如您所说,钱钟书是抱着诙谐和嘲讽的态度来写《围城》的。《何去何从》则与《围城》不同,佘其确实是抱着深重的同情和悲悯,以压抑的笔调写大学从苦难到苦难,知识分子由压抑到更压抑,直至崩溃。当我祖母把这些事和这些人写出来的时候,我想她的心情恐怕也一直是沉重的。
问:这本书从未打算出版,却最终成为一部极具分量的文学见证。您觉得它今天的出版,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历史、重新理解知识分子的角色,有哪些意义?
Ning:我们子女都知道祖母在生命的最后十年每天都写,她却不曾主动讲自己的写作。繁忙的工作和生活,也让我们忽略了祖母的写作。直到整理她的遗物时,才发现这部几近完篇的手稿。我们猜测,祖母生前之所以没有主动提过出书,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她一生受过很多不公平的待遇,不想在晚年再遭遇什么麻烦。二是因为她晚年渐渐老年痴呆(阿尔茨海默症),出版的事就无能为力了。所以,我们决计将手稿整理出来,然后争取出版。
问:在您心中,这部小说初稿最打动您的是什么?最让您感到沉重的是什么?
Ning:最打动我的是俞正堂。他不计个人得失,只为守护中夏大学。他恪守为师之道,既严格又慈爱;为保校产、救图书、育良种甘于幕后,不求名利。他敢讲真话,为真理与尊严宁愿得罪权威,最终却在校园被无端占领后,惨死于死于“白眼狼”之手。这种忠诚与悲剧,让人心痛。最沉重的,是那些被精神折磨至极的知识分子,一波又一波的打击最终让他们在文革中彻底崩塌。人格被践踏,尊严被剥夺,生不如死。读到黄怡欣走入湖中、又因孩子呼唤转身回岸的那一幕,我眼泪止不住地流。那种濒临崩溃中的母爱与牺牲,也让我想到祖母当年的委屈与坚韧。
问:您如何看待这本书在家族记忆与国家记忆之间的地位?
Ning:小说中的众多人物,确有我们后辈熟悉的众多身影,但是《何去何从》既不是校史,更不是家史,而是那个时代、那几代知识分子命运的综合写照。小说的故事截止于上世纪70年代初,至今已经过去50多年,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的巨变,大学早已经人非物非。但是,往事并不如烟。正如小说前言所说:《何去何从》将读者带回到那个年代,重温那段厚重的历史,意在不忘过去。因为,遗忘历史只能让悲剧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