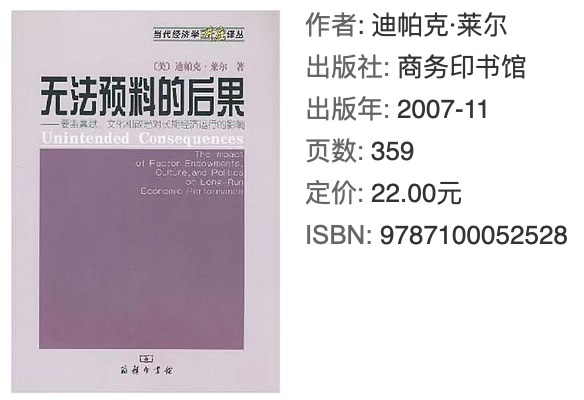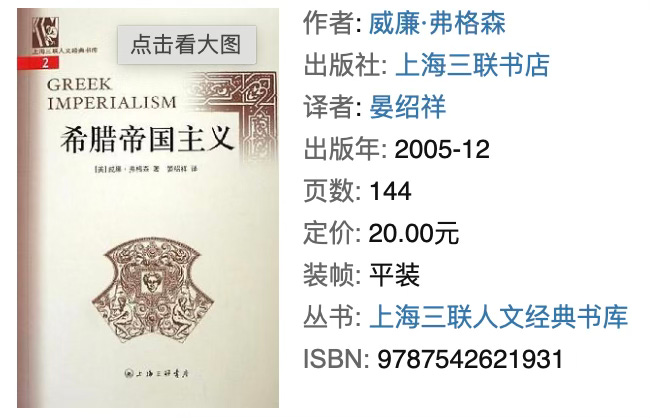关山越 | 前近代西方政治思想札记(一)
編者按:《前近代西方政治思想札记》一共七篇,此後會每週一篇。
早期国家由更为原始的族群政治实体演化而来,主要可分为以下四种稳定类型(不稳定的类型早就在历史长河中消失了,不在我们讨论之列):
古埃及型:
古埃及疆域为海洋和沙漠封闭,罕有外敌入侵,其居民以农耕为主,高度同质,尼罗河定期泛滥保证丰收繁荣。“法老不是凡人,而是神。这是埃及王权的基本观念,法老具有神的本性,是神的化身……说法老神化是错误的。他的神性不是在某一时刻以一种与罗马元老院宣布过世的皇帝为神的方式相似的方式来宣布成的。他的加冕典礼不是一次神化,而是一次神的显灵……在埃及,社会已通过把统治者设想为神而使自己从恐惧和怀疑中解放出来了。埃及社会为了永远保持社会与自然的结合而牺牲了所有自由。” (亨利·富兰克福特《王权与神祇》,上海三联2007年版,P3-4)传统日本“万世一系”的神格天皇制也属于这一类型。与古埃及类似,日本的疆域为海洋所封闭,丰富的降水量保证了它的农业繁荣。古埃及和日本都崇拜太阳神。不过,中世纪日本受唐代中华帝国文明深远影响,天皇王权从此长期隐而不彰。明治维新确立的现代天皇制是民族国家的一种形式,与传统意义上的王权无关。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型:
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没有明确的边界,经常受到边地山民和外来游牧民侵袭,其多数地区都是游牧生活,农牧业都依赖于不确定的降水量,并拥有一条虽然河水充足、但河流极为汹涌危险的底格里斯河。“与法老相似,美索不达米亚人的国王也是负责保持人类社会与超自然的神之间的协调关系;然而他绝对不是一个神而是一位社会成员……美索不达米亚国王领导着他的人民,但他并未被设想为与他的臣民有本质的区别。”“在美索不达米亚,社会保持着非常大的独立性,因为它的统治者只是一个人。美索不达米亚社会把永无休止的两种焦虑看作是相互关联的,它们是:神的愿望可能会被误解,灾难会扰乱人类与神两个阶层之间不稳定的协调关系。”(《王权与神祇》,P4-7)因此其国王虽然被认为是“君权神授”的,但却不得不通过仪式、梦和预兆来试探前行,以学会如何履行职责。这其实就是中国人熟悉的“天命”观。中国至迟从西周开始便属于这一类型。
王权退化型:
古希腊文明在迈锡尼时代曾经有过王权,后演变成为诸多城邦国家;古罗马早期也曾有过王政时代,公元前509年驱逐国王建立共和国;与之类似的还有位于喜马拉雅山麓的一些古代印度人共和国。盖因这些地方“土质贫瘠,从而农业只有相对较低的劳动力密集度,这使其不同于那类为古老农业文明提供经济基础的更为劳动力密集的农业,它不需要将社会分为阶层而进行严格的控制。再加上地理条件所决定的紧密的空间”(迪帕克·莱尔《无法预料的后果》,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P90)。正是从这些古代印度人共和国诞生了伟大宗教佛教和耆那教,而古希腊城邦则标志了一个政治上的创举和开端。首先,“城邦制度意味着话语具有压倒其他一切权力手段的特殊优势……所有那些原来由国王解决的属于最高领导权范围的涉及全体人利益的问题,现在都应提交给论辩的艺术,通过论战来解决。”其次,“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活动都被赋予了完全的公开性。”再者,那些组成城邦的公民,不论他们的出身、地位和职务有多么不同,在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同类人’。这种相同性是城邦统一的基础,因为对希腊人来讲,只有‘同类人’才能被‘友爱’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共同体。”(让-皮埃尔·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三联书店1996年版,P37-47)
希伯来型:
这一类型的代表是希伯来人或说犹太人,极为特殊却又影响深远。容我稍后详述。
前面我说过,帝国是在一片相对广袤的区域内统治多个族群、并凭借自身力量营建了其行政机构和经济组织的国家形态。在上述四种类型中,古埃及型因其边界的封闭性和民众的同质性无法发展出帝国;希伯来型在被穆罕默德“创造性转化”以后发展出了由伊斯兰“圣战”建立的阿拉伯帝国;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型和王权退化型都发展出了伟大的帝国,不同的是前者发展出“专断王权帝国”,后者发展出“民主帝国”,而“民主帝国”又要成为“民主王权帝国”才能取得成功。
我说“专断王权帝国”而不说“专制帝国”,因为近代以降的绝对主义国家才存在体制性的“专制”,传统帝国只是王权在敬畏天命、神意和习俗前提下的“专断”而已。居鲁士创立的波斯帝国无疑是一个“专断王权帝国”,但“与希腊公民相比,波斯臣民能够更加有效地躲避他或她的国家。在某种意义上,波斯人是‘更加自由的’。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在我们现今的时代,存在两个主要的自由概念:自由主义的概念和社会主义-保守主义的概念。自由主义的理想是不受国家干预,躲开其监视和权力。保守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共同理想坚持认为,自由只有通过国家,通过参与其生活才能实现。这两种概念都包含了明显的长处。如果我们做表面文章,回过头来把这些范畴硬搬到古代历史中,我们就会发现,希腊城邦很好地代表了保守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而令人惊讶的是,波斯在某种程度上反倒对应于自由主义理想。这后一个类推只是片面的,因为现代自由主义(自相矛盾地)得到了国家的宪政保证,而波斯的自由却是非宪政的和偷偷摸摸的。这种自由亦存在了较长时间。希腊人是屈服于后来的征服者,屈服于马其顿人和罗马人。波斯人则仅仅在形式上屈服于亚历山大。”(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上海人民2007年版,P307)
再看“民主帝国”和“民主王权帝国”,这里的“民主”和自由民主、人民民主都相去甚远,因为当时既无自由主义的“自由”亦无现代意义的“人民”。古代人的“民主”只是指每个拥有公民权的人都能平等地参与城邦的公共生活。完全的“民主”与“帝国”是冲突的。雅典依靠其海军实力几乎建立了一个海洋帝国,也出现了像伯里克利这样杰出的领导人,但却因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失败而一蹶不振。修昔底德告诉我们:“虽然雅典在名义上是民主政治,事实上权力正向第一公民(注:即伯里克利)手中集中。但是他的继承人,彼此都是平等的,而每个人都想要居于首要地位,所以他们采取笼络群众的手段,结果使他们丧失了对公共事务的实际领导权。在一个统治着帝国的大城市中,这样的政策自然会引起许多错误……最后打垮他们的,不是他们的敌人,而是他们自己以及他们内部的不和。”(威廉·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上海三联2005年版,P39-40)
在思想史上,从“民主帝国”到“民主王权帝国”的观念转型应当归功于亚里士多德。关于“民主”,他认为,城邦生活等于文明生活,如果缺少了城邦的公共空间和政治活动,那么人将与动物无异;关于“帝国”,他认为,为了弱者着想,强者应当统治弱者,而希腊人相对于亚细亚的蛮族是强者,因此他们应当统治亚细亚;关于“王权”,他认为,“如果事情碰巧,在任何一个城邦中,如果出现了一个家庭,或者一个个人在美德上如此地高于其他人,以致这个个人或者家庭的美德超过了该国所有其他人的美德,那么只有这个家庭享有王权或者最高统治权,或者这个人成为国王,才是公正的……当他在美德和政治能力上如此高于众人时,将他只作为平等的人对待,乃是错误。因为如此杰出的一个人,在世界上类似神灵了。”(《希腊帝国主义》,P65-66)——不难看出这已经何等接近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型的王权观念。命运让亚里士多德成为了亚历山大的老师,后者在所征服的领土上到处建立希腊城邦,传播希腊文化,目的就是“让世界上所有城邦有可能在一个单一的、庞大的领土国家中获得永久的联合。”(《希腊帝国主义》,P79)
但亚里士多德也有一些观点构成了对帝国的制约。他认为,任何希腊城邦都不能奴役其他希腊城邦的居民,这其实令帝国的集权变得不可能。亚历山大在马其顿和希腊本土的政治遗产安提柯帝国,就是因为希腊各城邦的内讧让罗马有机可乘。而罗马则因牢牢控制意大利半岛而保住了建立帝国的基础。至于罗马帝国不用多说了,它在强盛时期是伟大的“民主王权帝国”。
然而,在不存在经济增长率持久高于人口增长率的集约型增长的古代世界,古希腊罗马城邦有闲公民的公共生活是靠奴隶的劳动维持的,起先可以源源不断地将被征服的蛮族充作奴隶。但一旦罗马帝国抵达了所知世界的边界,成为一个世界帝国,城邦的理想就必然要求废除奴隶制,这反过来又剥夺了城邦的经济基础,并使平等变得黯然失色。如此看来,公元212-213年卡拉卡拉的皇帝敕令——“我授予全世界的外国人以罗马公民身份,授予各种保持不变的市政权利……因为这一大群人不仅应当分担我们的所有苦难,而且现在也应共享我们的胜利”——既是作为“民主王权帝国”的罗马荣耀的顶点,又是它衰落的开始。此后罗马逐渐转型追求一种非城邦的理想,成为一个基督教帝国,即使如此也未能避免它的灭亡。在不存在奴隶制的情况下,经济的集约型增长是城邦公共生活的前提,而集约型增长的体制基础是由中世纪的西欧人创建的,这导致了西方——即后罗马基督教世界的拉丁部分——的崛起和城邦的复兴,否则今人可能早已遗忘了城邦生活。
回到希伯来型国家,不同于古埃及型、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型,它否认王权具有任何神圣性;但也不同于王权退化型,它承认有必要设置王权以处理紧急状况,恰如《旧约·撒母耳记》所述:“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由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争战。”与另外三种类型的根本区别在于,采用这一国家类型的族群“承认他们的内在一致性源自一种分享性的游牧生活的过去,而非源自他们作为定居社会的成就。”(《王权与神祇》,P481)——大多数游牧族群一旦定居之后就被农耕文明同化了,既定居又拒绝同化的国家是很容易瓦解的。只是因为希伯来人独特的一神教信仰,这一国家类型才得以稳定下来并发扬光大。
希伯来一神教信仰的独特之处在于,早在无王时期,希伯来人已经作为一个整体被耶和华选出来,作为一个整体被西奈山的约捆绑在了一起。这其实等于开创了“人民”(people)这一重要的政治学概念。“人民”是作为整体被唯一的神选中的,“人民”与耶和华之间的约先于王权,也先于君王和耶和华之间的约。在古埃及型和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型国家,君主个人即为国家的象征;在王权退化型国家,有公民而无“人民”,领导人与神的关系远比普通公民和神的关系密切。自然,这里所说的“人民”只限于希伯来人内部,因此亦是族群的。可以说,二十世纪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对立,即是源自希伯来一神教信仰之“人民性”与“族群性”之间的张力,前者将“人民”概念世俗化普遍化,后者则是“选民”观念的拙劣翻版。
正是希伯来型的王权观念给人类带来了政治神学,这个留待下篇详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