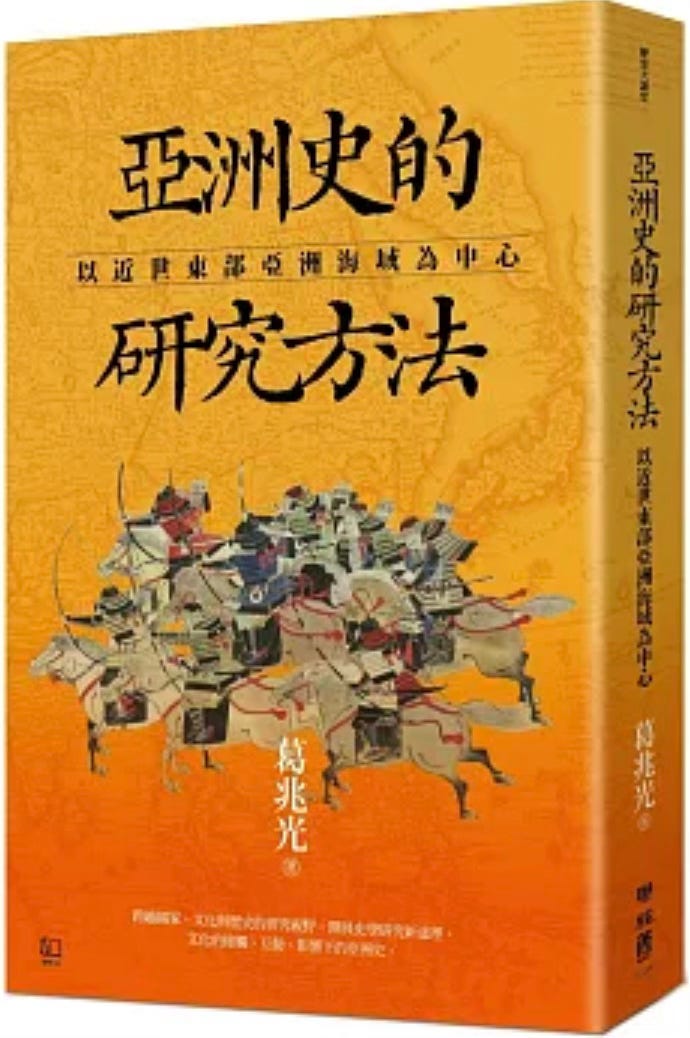編者按:“全球史並不一定要縱橫十萬里,上下五千年,其實它更是一種方法,試圖發掘各種微妙的全球性聯繫、交流和影響。”本文為葛兆光《亞洲史的研究方法:以近世東部亞洲海域為中心》作者自序,經作者授權,波士頓書評刊發,標題為編者所加。
這是近十幾年在復旦大學講“亞洲史的研究方法”這門課的講義。
之所以要講這門課,是因為2010年,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設立了“亞洲宗教、藝術與歷史研究”博士招生方向,必須要有一門和“亞洲史”有關的基礎課程。可是亞洲那麼大,沒有誰能包攬,沒有誰願意承攬這個活兒,我只能硬着頭皮自己來,於是開始準備講義。
講義的初稿是2011年的春天,我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客座時開始草擬的。胡適曾經任職的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亞圖書館(Gest Library),就在東亞系的Jones Hall隔壁Frist Campus Center的樓上。我真應該感謝這個圖書館!它收藏的東亞文獻給我提供了豐富的歷史資料,收藏的東亞論著也刺激了很多的研究思路。至今還記得,我當時在葛思德圖書館裏,攤開稿本開始撰寫課程大綱,想到甚麼就用筆在紙上寫下來,看到甚麼也用貼紙記下來貼在大綱上。就這樣,兩個月裏,漸漸積累了一大疊稿紙和五花八門的資料。五月中回到上海,就開始把大綱和資料,另外手寫,重新修改成講稿,那時的講稿很粗略,只是作為講課時的提示性內容。我歷來講課,都是一邊講一邊完善。這一年的九月開學,在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和歷史學系第一次講這門課,當時的自我感覺,好像還頗像模像樣。於是此後十一年裏,陸陸續續講了八九次,講了再改,改了又講。在十幾年裏,這份講義漸漸地從手寫的大綱和抄錄的貼紙,變成錄入電腦打印出來的講義,打印的講義天頭地腳上,陸陸續續又寫滿了新的內容,旁邊又貼上了好多寫滿字的貼紙,然後,再一次重新錄入打印。週而復始,到了2021年,終於成了現在這個樣子。
經過近十輪講述,2021年的秋冬學期,我最後一次上這門課,手中的講義也漸漸成型。正如成語所謂“敝帚自珍”,我決定把這份講義交給商務印書館,作為“葛兆光講義系列”中的一種出版。很多人都知道,多年來我的習慣是,一旦講義完成並交付出版,這門課便不會再講了,既是自信它已經完成使命,也是因為害怕再照本宣科讓聽眾笑話。可是,也許是因為這門課完全是一個嘗試吧,這回我還是感到了一點兒不自信,我總是在想,課雖然講完了,但不知道這門課的目的,是不是真的達到。
因此,我很想聽到讀者的反饋。
開場白
“亞洲史的研究方法”課程要旨
這是一門給博士生開的課,在進入本課程之前,我想首先說明“亞洲史的研究方法”這門課的目的和意義。
為甚麼要開這門課?為甚麼要把這門課的主題,確定為“亞洲史的研究方法”?為甚麼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要把宗教、藝術與文化交流史,作為亞洲/東亞史內容的重心?
簡單說起來,考慮的只有三點,很簡單的三點:
先說第一點。毫無疑問,“亞洲”不是一個。過去,明治、大正時代(1868—1926年)的日本學界往往以“東洋”代指“亞洲”,他們的“東洋史”,幾乎就等於是“亞洲史”,關於這一點,我們在後面的課程裏還會詳細說。比如日本著名學者桑原騭藏(くわばら じっぞう,1871—1931年)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影響很大的《東洋史要》裏就說,所謂“東洋”是以蔥嶺也就是帕米爾高原為中心的亞洲,包括:東亞(中、日、韓及俄國遠東地區),南亞(印度、阿富汗、巴基斯坦),中亞(興都庫什山以北,蔥嶺以西,錫爾河以南),西亞(阿姆河以西到咸海、里海以南,包括伊朗、土耳其、阿拉伯地區)和北亞(阿爾泰山及咸海、里海以北,俄屬西伯利亞)。當然,這裏還沒有說到環南海地區的東南亞呢。大家可以看到,很顯然,一個亞洲,各自不同。說到底,“亞洲”原本只是歐洲人給東方很大一塊地方命名的地理名詞,就像他們常說的“近東”“中東”“遠東”一樣,這是從歐洲看東方生出來的一個地理概念。雖然歐洲很早就有這個“亞洲”的說法,大家都知道早期歐洲以耶路撒冷為中心展開三個葉子形狀的世界地圖上,右上方的那片就是亞洲,不過,要到傳教士把歐洲的世界知識傳到明代中國,中國才逐漸有了這個叫作“亞洲”的地理概念。
所以我們說,這個亞洲,本來並不是一個在政治、文化、族群上有同一性的歷史世界。亞洲族群太複雜、空間太廣袤、文化太豐富、語言太多樣。桑原騭藏就說,東亞、西亞、南亞、北亞以及中亞,差異非常大,單單從族群或人種上說,亞洲就包括了蒙古人、波斯伊蘭人、印度雅利安人、馬來人等。就算你僅僅指我們這門課重點要說的“東部亞洲”,也就是環東海南海這個區域,也不那麼簡單,複雜得很。這門課之所以也採用“亞洲”這個概念,把它作為一個歷史世界來研究,主要是考慮到在歷史上,這個區域裏面,和中國之間曾經有過密切的互動、聯繫和激蕩,比如中古時期的“西域”,就把中國和突厥、粟特、回鶻、波斯、吐蕃、天竺、大食連成一片。近世以來的“東海南海”,就把東部亞洲海域周邊北到庫頁島,南到爪哇都連成一片。如果我們能把“中國”放在這個廣袤背景下去討論和分析,也許,我們可以看到更多的、單純在中國背景下看不到的歷史線索。當然,這並不意味着亞洲“自古以來”就有,日本人岡倉天心(おかくら てんしん,1863—1913年)在1903年寫的一本很有名的書《東洋的理想》裏開篇就說“亞洲是一個”。其實這話並不對。亞洲各地雖然互相有聯繫而且是密切聯繫,但無論從族群、信仰、歷史、文化、制度上看,並不是一個。而一個自我認同的“亞洲”,恰恰是在看似同一個“歐洲”的對照和刺激下,在近世才逐漸自我建構起來的地理、文化和歷史的“區域”。
亞洲實在太大,任何一個歷史學者在這種複雜、多樣、差異的歷史裏面,都會感到自己的知識欠缺。任何一個學者都不敢說,自己可以研究亞洲。更何況,要請大家原諒,我也是“趕鴨子上架”“半路出家”,我研究的主要領域,還是在中國史,特別是中國思想、宗教和文化史,只是現在,越來越希望年輕一代學者在亞洲/東部亞洲的語境或背景中,來重新研究中國史。所以,我的這門課,也許不可能討論如何研究整個亞洲/東亞,而更主要是討論以下三個問題:
第一,中國學界要不要超越國境,來重新研究中國史?
第二,對亞洲,特別是近世東部亞洲海域的歷史,怎樣有,或者能不能有一個整體認識?
第三,同時,我們又如何反過來,把“亞洲/東部亞洲海域”的歷史作為“中國史”(或者“日本史”“韓國史”“越南史”)研究的視野和背景?
近年來,歷史學變化很大,有人曾經預言,未來歷史學研究的趨勢,可能是“文化接觸”,也就是不同文化間的相互影響、接受與轉移,邊緣對中心的影響,以及從邊緣重思世界史,強調聯繫、互動、影響的全球史,也許就是這個趨勢的表現之一。這話說得很對,也很有預見性。過去,我們都習慣了所謂“就中國講中國”,只是在中國範圍內以中國史料談論中國,但這是不夠的,可能要大大改變。所以,儘管大家將來要做的,也許只是個別國家的宗教、藝術和歷史研究,但你一定要考慮,它與周邊——具體到中國,就是亞洲——的文化背景和互動可能。
如果我們能把這種超越個別國家的歷史背景和文化聯繫,作為自己的研究視野,我們一定會看到一些過去孤立地研究某個國家宗教、藝術和歷史的時候,可能發現不了的線索和被遮蓋了的現象。
再說第二點。研究亞洲或者東亞,為甚麼我們要把“藝術”“宗教”“歷史”這三者綜合在一起?也有人會問,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為甚麼要把“亞洲宗教、藝術與歷史研究”當作博士招生方向?這當然一方面是因為我的知識有限,不能不局限在幾個領域裏。像區域史裏面佔得比重很大的、資料很豐富的商品貿易、物質交流,我就不敢多說,因為涉及絲綢、茶葉、香料、瓷器、白銀還有鴉片,那些方面的知識我不具備。而另外一方面呢,我想,是因為藝術史、宗教史和文化交流史,在我看來恰好構成了“文化史”的主幹,而這三個領域的關係,恰恰又十分密切。
關於這方面的例證很多,大家都知道中古時期粟特墓葬中石棺牀的精美雕刻,就和中亞、族群、商貿、移民相關;又比如日本神道教所謂天皇象徵的三神器(八坂瓊曲玉、八咫鏡、草薙劍),就和中國道教的劍、印、鏡等法器信仰有關。這種例子太多了,這裏不妨再舉個非常小的例子。孫機先生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叫《從米芾〈蜀素帖〉說起》,裏面提到台灣故宮博物院收藏的米芾《蜀素帖》裏有一首《擬古詩》,講到烏龜和仙鶴合作渡河的故事,仙鶴叼着烏龜飛越河流,約定不可開口,因為一開口就掉下去了,但烏龜忍不住還是開口,於是就墮入河流。所以,米芾詩歌最後一句就是“報汝慎勿語,一語墮泥塗”。這個故事呢,周一良先生已經指出說,它來自印度佛教的“海禽啣龜”故事,“雙鶴御龜,龜咬竹竿,草薙劍一通渡河,但龜不可開口,否則墮入泥塗”,意思本來是佛教告誡信眾,不得“妄語”。大家知道,不得妄語是佛教很重要的一條戒律,因為人就是因為多嘴多舌,所以才陷入煩惱而不能解脫。這故事見於康僧會翻譯的《舊雜譬喻經》以及《法苑珠林》卷八十二。但是孫機指出,這個故事後來逐漸改變,在中國形成以“龜鶴”為主題的圖像,這個圖像又逐漸從中國影響到日本,一直到十五世紀。
你看,這麼一個小小的文學故事和繪畫主題,就影響到亞洲的三個區域,印度、中國、日本。所以,如果你是研究藝術史的學者,面對中古中國大量的磚雕石刻、墓室壁畫、石窟造像,你既不能忽略這些圖像和中亞、南亞的聯繫和淵源,也不能忽略它們和往來東西之間的各種異族、異國商人、宗教徒的關係,也不能忽略它們從中國到朝鮮和日本的流傳和分佈,更無法不掌握佛教、道教、回教以及三夷教(祆教、摩尼教、景教)的知識。歷史研究需要文字文獻,也需要圖像資料,藝術史研究需要歷史語境,也需要宗教知識。所以,如果我們能夠把這三個領域綜合起來,既可以使用所有的文字文獻、圖像資料和考古發現,也可以把它們看成是亞洲文化史領域,它兼容理性和感性、政治與信仰、歷史和藝術,也許可以對過去時代的歷史與文化有貫通的認識。
當然,還有第三點,那就是如今研究超越國境的區域史,不能不考慮全球史研究潮流的影響。現在“全球史”已經成為一個熱門,但是全球太大,誰能講一個包羅萬象的全球史呢?很難。現在有沒有真的可以籠罩全球的歷史著作呢?很少。有人告訴我,世界史和全球史,主要就有兩種:第一種是“滿天星斗式的世界史”,就是把各個國家、區域、族群的歷史相加,彷彿拼圖一樣。可這和過去的“世界史”區別不大,過去中國學界,無論是周一良、吳于廑的《世界通史》四卷本,還是吳于廑、齊世榮的《世界通史》六卷本,大體上就是這樣的。我們大學裏面的世界史也是這樣教的。這是西方的世界史被引進中國以來,無論是晚清、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直延續的史學傳統。還有第二種,是“檯球撞擊式的全球史”,就是重點描述各種事件、人物、現象之間的互動和聯繫,就好像古代禪宗詩歌說的,“一波才動萬波隨”,看看互相交錯的漣漪和波紋,一圈一圈怎樣互相波動互相影響,這當然才是理想的全球歷史。但是你要注意,這種全球史寫起來沒那麼容易,我建議,在全球史背景之下,先做區域史的研究。為甚麼?原因很簡單。
第一,全球史怎樣既超越國別史,又能夠容納國別史?這是一個難題,但是區域史則相對比較容易。
超越國家的歷史聯繫,主要是在經濟史、知識史、文化史、科學史上,也就是貿易、宗教、藝術和物質文化史上,可能比較容易找到很多證據,可以勾勒一個互相衝擊和彼此往來的圖像,可以寫出聯繫的全球或區域歷史。然而,在政治史研究上,做起來也許比較困難。我以前寫過一篇文章,大家可以去看看,叫作《在全球史潮流中國別史還有意義嗎》。為甚麼我一方面強調全球史、區域史的重要,一方面還要強調國別史必須存在?就是因為在傳統時代,政治常常被國家或王朝控制,不同國家或王朝的制度也常常有差異,而各個國家的政治,也會塑造各個國家的不同文化和環境,你不研究一個一個國家特別的社會、政治和制度,你就說不清楚這個國家和那個國家,在政治上、在文化上為甚麼不一樣。更何況有時候,你也不大容易找到古代各國在政治上和制度上彼此的影響和聯繫,也許,只有在東西方交通開始發達,在同屬一個文化系統的歐洲內部或東亞諸國之間,才比較容易找到政治史上某種彼此關聯。
可是,有時候一些相互聯繫比較緊密,彼此影響相對明顯的“區域”,倒是很容易看出它的互相撞擊、互相滲透。比如受到古希臘羅馬文明、基督教影響的歐洲,受到伊斯蘭教影響的西亞、中亞,以及我們後面會重點說的,由儒家文化、佛教文化和回教文化交錯,朝貢圈和貿易圈連接起來的“東部亞洲海域”。
第二,全球史並不是上下五千年,縱橫十萬里,其實,它更是一個觀察歷史的角度、視野和方法。
大家可能熟悉卜正民(Timothy Brook)的《維米爾的帽子》。卜正民是一個很棒的學者,這本書從荷蘭畫家維米爾(1632—1675年)的幾幅畫作開始說起,涉及了十六到十七世紀荷蘭的代爾夫特和全球貿易,這兩個世紀之交的明清交替,中國的寒冷和瘟疫,傳教士的來到東亞,還說到荷蘭東印度公司的亞洲經營,荷蘭人從海洋到達亞洲,甚至講到“全球性流動現象重新界定他們(荷蘭人)的世界觀,還拓展了他們的世界。”書裏面有一段話說得很好,我給大家唸一唸:“我們不妨再把17世紀的世界當做一面因陀羅網,有如蜘蛛網一般。這面網時時刻刻在變大。網上每個結都吐出新線,觸及新的點時,就附着在點上,這些線也往左右橫向連接,每條新出的線都不斷重複這個過程。隨着線的分佈愈來愈稠密,網愈來愈往外延伸,愈來愈複雜糾結,也愈來愈緊密相連……17世紀初的人就在做這樣的事,其速度之快、次數之頻,前所未見。”維米爾的繪畫,可能只是一個引子或者象徵,不過通過這個小小的繪畫,大大的世界歷史就漸漸凸顯了。
所以,我給牛津大學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教授新書《傳教士的詛咒》寫的推薦詞就說,“全球史並不一定要縱橫十萬里,上下五千年,其實它更是一種方法,試圖發掘各種微妙的全球性聯繫、交流和影響。”像沈艾娣的這本書,雖然寫的是微觀歷史,寫的是中國山西一個不起眼的村莊洞兒溝,居然會和遙遠的神聖羅馬教廷曾有過三百年的互動。當年傳教士來到這裏,影響了這裏的人一直信仰天主教,這個地方的宗教信仰,因為一代代村民們留下了歷史記憶,一個個傳教士們留下了文獻檔案,而且這些歷史記憶代代口耳相傳,這些文獻檔案保存在了羅馬教廷,所以,有關這個村莊的小歷史,就沒有湮滅在整個中國的大歷史中,還和羅馬教廷發生了關係,這就是全球史。所以,全球史不只是寫那些大的歷史,也可以寫小的歷史,過去中國所謂“草蛇灰線”和西方所謂“蝴蝶效應”,就可以通過這些小故事,成為全球史。更可以提出好些值得深思的問題,比如,歷史上天主教在中國傳教為甚麼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外來的傳教者和中國的信仰者之間,應該是怎樣的關係?政治性的國家認同和宗教性的普世信仰之間,應當怎樣處理?
我最近也寫過關於一個人物的隨筆,就是萬曆年間(1573—1620年)曾經當過福建巡撫的許孚遠。那時候正好是“壬辰之役(1592—1598年)”,中、日、朝打得不可開交,許孚遠到福建當官,就派間諜到日本偵察敵情,和呂宋的西班牙殖民者建立聯繫,建議拉攏琉球斬斷日本的左臂右膀,甚至主張開放海上貿易,孤立日本,而這一切的大背景,又與大明和日本之間的東部亞洲海上爭霸有關。你看,這是不是也是一種從微觀看宏觀,從一個人觀察全球變動的途徑?所以我說,“全球史”是一種角度、視野和方法。
第三,全球史早期資料不夠,這是一個難題。所以,我們不妨先從資料相對容易收集的區域史開始。
全球史有它自己的困難。為甚麼?因為它一方面受到時代的限制,一方面受到資料的限制。時代越早,這種全球或廣大區域之間聯繫的資料就越難找,因為古代交通條件有限,古人活動範圍也有限,就好像在桃花源裏,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小國寡民,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這時候你上哪兒去找“聯繫”“互動”和“影響”的資料?當然,越到後來,全球的聯繫就越多,不僅僅是絲綢之路出來了,航海技術也發達了,除了貿易之外,戰爭、宗教、移民越來越多了,疾病、物品、藝術也就彼此交錯,互相影響,這時候資料多了,聯繫和互動的全球史也就可以寫出來了。
因此,在聯繫還不充分的時代,是不是可以先敍述區域史?大航海時代以前,雖然全球聯繫也存在,比如法顯的故事,絲綢之路和粟特商隊,玄奘天竺取經,鄭和下西洋等等。像1984年發現的唐代《楊良瑤神道碑》,說明八世紀末唐朝官方使者楊良瑤(736—806年)就在貞元元年(785)十月從廣州出海,出使黑衣大食,很可能到過現在伊拉克的巴格達。後來《新唐書·地理志》中引用中唐賈耽編撰《皇華四達記》記載了廣州到縛達(巴格達)的“廣州通海夷道”,可能就是來自楊良瑤的報告。
但是,這樣的全球性聯繫資料畢竟不多,更容易看到和找到考古或文獻資料的,是區域之間的貿易、戰爭、傳教、藝術、移民等。而“區域”的聯繫很早就存在。我以前寫過一篇《從“西域”到“東海”》,你可以看布羅代爾(Femand Braudel,1902—1985年)關於“地中海”的研究,環地中海就是一個聯繫密切的區域;你也可以看敦煌文書發現之後的“西域”研究,西域也是東亞和西亞之間的一個“地中海”,它把整個亞洲連起來。當然,很多人認為“蒙古時代”以後,就進入“世界史”了,按照日本學者本田實信、岡田英弘、杉山正明等人的說法,“蒙古時代”終於把世界連在一起了,但這“世界”其實一方面主要還是歐亞大陸,而且另一方面,這種聯繫的世界也有曲折。我以後會說到,在十四世紀後半到十五世紀前半之後,由於蒙古在東部亞洲潰退,歐亞又形成“東是東,西是西”。
所以,中國學界不妨先從和自己相關的區域史開始,在這個區域史裏面,我覺得“東海”,現在我用“東部亞洲海域”這個詞兒,這個區域在十五世紀以後,成了一個有機的歷史世界。我最近正在寫一篇文章,就是想說明,在跛子帖木兒1405年去世之後,西亞(當然包括更遙遠的歐洲)和東亞又開始各自分離,宗教往來、商品貿易,雖然也不是沒有,但是,東部亞洲尤其是環東海南海區域,也就是我們說的東北亞和東南亞,聯繫非常密切,比較明顯地構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歷史世界。你從政治(朝貢圈),經濟(環東海南海貿易圈)和文化(東北亞儒家與大乘佛教,東南亞儒家、小乘佛教和伊斯蘭教)三方面,就可以看得比較清楚。英國學者約翰·達爾文(John Darwin)《全球帝國史:帖木兒之後帝國的興與衰(1400—2000)》也注意到,帖木兒去世是一個大事件,只是他沒有強調全球帝國史的另一面,也就是我說的“合而又分”。
所以,研究亞洲東部,也就是環東海南海這個區域的互動與聯繫,在現象上、理由上、資料上都很充足,如果把“東部亞洲”或者“東海/南海”作為一個區域,充分研究環東海南海地區的互動和聯繫,比如明清中國、朝鮮、日本、琉球、安南之間,加上東南亞的呂宋、暹羅、爪哇、滿剌加諸國,以及從南海過來的西班牙、葡萄牙、荷蘭和西洋諸國的互動。我覺得,這樣的“區域史”,也許是對未來理想全球史的貢獻。
所以,我們這門課雖然叫“亞洲史的研究方法”,實際上,會比較多地提及東部亞洲海域,也就是環東海/南海的東南亞和東北亞這一塊。
好了,“開場白”說完,下面我們就開始討論“亞洲史的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