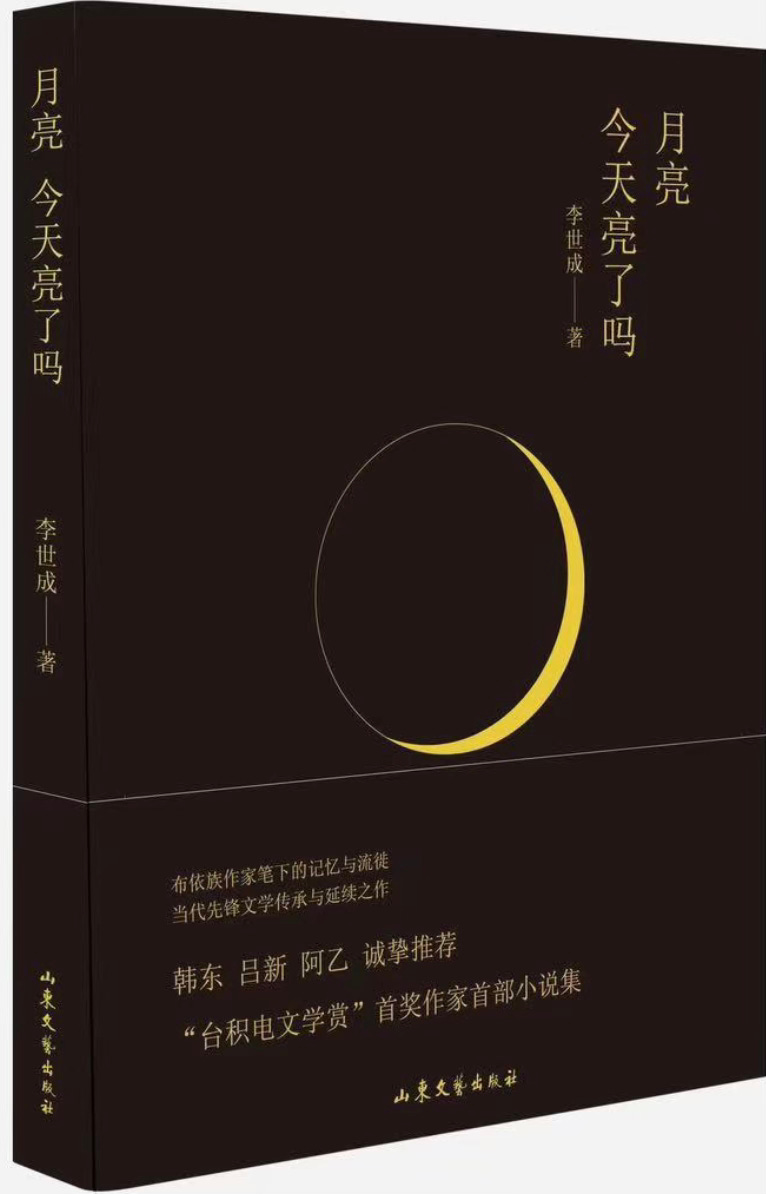李世成 | 庇隆灣(小說)
羊皮吃掉小筏艇,江河吃掉水流。
我在那裏種植玉樹,仍有貪婪的鄉人想要與我分掉全枝。本來他們安排我走過場,我卻將一首粵語歌唱翻了全場。你沒有來,沒能領略我的風姿。但這幾天他們都說遍了。“那真是一個瘋子,”人們誇我的聲音。流傳下來的,是他們遠距離錄下的劣質的音頻。人頭湧動,哪里像一個音樂會。
這兒沒有誰需要誰,只有自己想要去做某事,或者莫名被安排在某一境域裏大顯身手,或者行走於這一境地的我們乾脆是茫然無措的小孩。或許啊,我該提一提,一些別人沒有留意的事物,諸如顏色,形狀,大小,質地,輪廓,弧線,深淺,憂戚……以及飄忽不定的我們不曾把握住的回聲。可我還是抓到過什麼的啊,我右手繞過頭頂來摸摸我的左耳,稍事歇息,我左手輕輕摸下巴上幾日未除的鬍鬚,誰想要在意鬍鬚的情緒呢?我繼續捏自己的下巴,像捏塊纏繞傷口的膠布,或者一只剛出生不久的小狗脖子晃來晃去,你說是我的下巴晃還是手指晃呢,兩根手指就搞定了。
你看,你忘了我說過玉樹,我也忘了。我才不會重複去提它。我哪兒知道我要在達長種植玉樹呢,至於粵語歌,誰信啊,我才不會將一首粵語歌唱完。
我又在這兒遇到一些人。
為了規避某個辭彙,我不得不用一個模糊的概括性片語加以替換。關於這一場域以及人們對此的俗稱,我早就感到厭倦了。講述一個生厭的地方和遭際,意義也不大。可敘事這一行為,向來是誰都可以抱持決斷的意願的啊。
這是一個灰黑地帶。(哪怕在這兒我遇到了女孩的紅唇,甚至瞥見女孩明亮的門牙。)她像極了某個影星,又或者誰也不像,她就是與我初次面見交談的一個女孩。很難說誰先發現誰。但我事先在蘆笙家聽到她的聲音,這是肯定的。
我拿出從河邊撿拾到的石頭給蘆笙看。那是一張擁有魚臉模樣的石塊。我曾將魚頭置放於我的書架擱板上,問過一些朋友——嘿,看到我的魚了嗎?一位心細的朋友端詳出昏暗角落裏屬於我的那張魚臉,留下三個字——斑海豹。我差點動搖了,承認那就是一只斑海豹,它側對我張嘴巧笑的模樣可愛極了。另一位貼心的朋友對著我的照片數了數可見的幾十本書,說有三四十只魚。我隔空向她擊掌,退出我的網路空間。
瑉。蘆笙喊我。
我左眼皮跳動一下,左耳紅了起來,像是因為羞怯而警醒。“瑉”,水沖的一位長輩曾惠賜過我這一名字,它伴隨了我只懂哭泣的幼年時期。
那時我剛從且卯上完小學一年級上學期,回村踏進院子前,蘆笙用瘦小的肩膀靠著我家蘆葦柵欄在等我,“瑉”,他喊我。他知道他有一個弟弟叫“瑉”,我們有著共同的爺爺。媽媽喊蘆笙到家裏和我玩,並對蘆笙說,瑉不叫瑉了。接著對我說,朝陽,你和蘆笙說。
我走到蘆笙面前,將靠背木椅朝他轉了一面,雙手趴在椅背上對他笑。蘆笙也抽來一只椅子,將靠背的一面朝向我,趴在椅背上。我說我現在叫“朝陽”,水沖的外公有天來小王寨,聽到我的哭聲,問我親外公,小孩在哭呢。外公說,是瑉在哭,真煩人,只有吃奶的時候不哭。水沖外公是外公的姐夫,媽媽讓我也要喊他外公。煩人的愛哭鬼瑉被抱了出來。水沖外公隔著一張椅子的距離盯著他,良久不說話。最後水沖外公以懂陰陽的身份開口——我忽略了一件事,水沖、小王寨、達長,我們這地方還缺好玉嗎?一束陽光正照到瑉的側臉,陰影部分掛在他幼小的汗毛上晶瑩地拂動著,陰影吹拂著他幼小汗毛的幼小光亮。以後他叫“朝陽”吧,水沖外公說。從那以後“瑉”就沒再哭過了。
蘆笙說,有這麼神奇嗎,那你的書名叫什麼?
李向東。我說。
瑉。蘆笙喊我。
你對達長是什麼感……覺。蘆笙想問的是,我對達長的感情。
說不出來,每一次回來,除了我和蘆笙親近一些,其他外物與人事,我都是陌生的,熟悉的人和事物在變老,變遠。
我會記起我第一次學賭錢的經歷,以及小學時期裝模作樣寫情書的樣子,我說。你記得以前果園下有很多大石頭嗎?我問蘆笙。
石頭?
對啊,我現在還能看到我們父輩年輕時在這兒撬石頭的情景,偶爾能聽到炸藥爆破的聲音,看到引線著火時的煙絲與火星,看到他們揮動手臂錘打石頭的模樣……那時我們大概四五歲。
忘記了,我都不知道房子是靠什麼建起來的,馬,還有人力,它們離我們太遙遠了。蘆笙以一種模糊的腔調說。
我岔開話題,說,比結婚還遙遠嗎?
蘆笙看了看在門口拆玩具槍的三個孩子。指了指坐在地上的老么,說,也可以和他一樣近。
他還差一個開襠褲。我說。
蘆笙笑,說,小時候我們都不用吧?
也許一歲前穿過呢?
我們摸出橘子剝了起來。半小時前我們把一幫小夥喝倒了。看著他們相互攙扶著出門,我們眼裏開始現出輕鬆的光亮。那幫小夥太瘋狂。他們是蘆笙的妹妹的初中同學,大多初中沒上完便出去打工了。達長首次舉辦春節聯歡活動,他們一幫人從其他村寨騎摩托過來觀望,以看節目為名,瞅瞅女孩們充滿生氣的臉頰和飄動的過肩發。除了同學情誼,蘆笙的妹妹義芬傳承了布依族的好客精神,以前我們的長輩們相互遇到熟人,你不來串寨都要把你拉過來。
年輕氣盛啊。那一幫小夥。同我坐一張長條凳上的少年問我名字。我說我叫朝陽。他馬上喊我朝陽,來六拳。接著他自我介紹,眾小夥相繼找我和蘆笙劃拳。蘆笙對我笑了一下,他知道劃拳是我們的強項。純喝酒想必我們不是幾個小夥的對手。我們以前在地油坪上初中時,星期五下午要走路回家,三個小時的路程,馬路邊上的電線杆,一棵電線杆與另一棵電線杆的距離總是相等的,我和蘆笙剛學劃拳,誰輸了便背起另一個人的書包,到下一棵電線杆繼續論輸贏。
朝陽,我們以前的書包裏都有什麼呢?蘆笙問我。
嗯?那要看去程還是返程,回家裝書,去學校裝大米和書。
那時候的鋁飯盒堆起來真是壯觀。蘆笙感歎。
那時你就開始看課外書了。蘆笙繼續說,尤其武俠小說。
遺憾的是,當時到手的武俠小說往往有上冊沒下冊,除了喜歡看,我還有一個原因,逃避勞動。說著我笑了起來,彼時回到家,只要我手上有書本,哪怕我一目十行在看武俠小說,母親也不會喊我掃地或者洗碗。
我從兜裏拿出從河邊撿來的石頭,將桌面上的橘皮捏住,橘皮濺出的油霧給我的石頭渡上一層油亮的薄膜,將抽紙略擦我的小石頭後我遞給蘆笙。蘆笙轉動一下石塊,這是眼睛,他說,還有嘴巴,像一只小動物的頭部。再看看,我說。像一個魚頭,蘆笙說。
我還就運氣的成分與蘆笙傾倒個沒完。蘆笙看我話有些多,問我喝得沒事吧。我說恰到好處。
後來那件白衣你帶去築城放置在哪里呢?蘆笙知道我聽懂他指的是什麼,他也知道我的羞怯。其實那件白衣,更多是一份與信任和關愛有關的信物了。
那次我是回來參加大韞母親的葬禮的。
開堂前一天傍晚,蘆笙騎摩托帶我去河邊。天空浮著綿密的黑雲,我和蘆笙在賭我們的摩托騎到河邊會不會被雨淋。我說我們穿過黑雲,也許到河邊就變換模樣了,天氣,我說。我喜歡顛倒著說話。
我們在帕牆大韞家參加他母親的葬禮。本家中的幾個青年在相互開玩笑,不要和我站一塊,我們單身的不需要有對象的人陪。穿白衣戴孝是常見的喪禮儀式,白衣的來源在我們這邊的布依族卻有些規矩。前來祭奠的本家男子,結婚的或未婚的身上穿的白衣,要麼是自己結拜的義兄送來,要麼是媳婦那邊或是娃娃親那邊送來。穿上的白衣件數越多,則表明他至少有兩層以上的關係,未婚男子通常是穿兩件,即義兄家送來一件,娃娃親家送來一件,已婚男子所穿的件數則更多了,岳父岳母家那邊的兄弟家知曉,也要各送一件來。沒有義兄或娃娃親已先於他結婚的青年男子,則無人送來白衣了。我置身於雙無行列,心想是要和少數青年站末排等著跪拜的。但我們各自都在心裏打好了算盤,先是本家的幾個單身兄弟同他們的兄長借來白衣穿上,蘆笙自然也是早打算脫下一件給我穿,他拍了拍我肩膀,我跟著他繞大韞家的屋角走向他的摩托車。我們騎上摩托,向果園走去。
蘆笙在方向盤前開口,在大韞家不好脫下衣服給你,被外家看到不太好。我們在蘆笙家整理好白衣,喝了一口井水,繼續跨上摩托。
回到帕牆半小時,我接到母親電話。母親說芩的媽媽打電話和她說,要給我送來一件白衣。我頗為震驚,來不及多說,母親就在那邊說了,人家是好心關愛你,你從報話的總管手裏接上衣服後,帶阿姨回蘆笙家吃飯。母親在沿海某個小鎮打工,沒有回來。這次我來大韞家參加伯母的葬禮,她是知曉的。此前在葬禮上,我遇到了芩的父親。自然啊,我站在單身青年那一撮,離開堂時辰還有些時候,我們總不會著急穿白衣的,我們的娃娃親們倒是早已先於我們結婚了。
朝陽、朝陽……
報話的總管以渾厚的聲腔喊我的名字,我上前從總管手裏接過白衣,並請芩的母親到飯堂吃飯。其實我還應該多說一句,請阿姨到蘆笙家吃飯。母親不在家,我居然沒有開口提蘆笙家,實在是因為羞怯,哪怕我知道芩的母親不會同我去,只是這必要的禮儀,我都給省略了。母親後來與芩的母親通話,致謝時說了一句,都不知道朝陽懂不懂事,會不會請你去么娘家吃飯。芩的母親說,朝陽很懂事。
蘆笙不該提起白衣,說起白衣,事物就能飛起來了。你看,我們翻轉一下手掌,房屋將移到另一邊,消隱的不止是房屋了,連我們的語氣也被迴旋的敘事口吻取代。我們的眼睛或許看得更清,但語義只能更模糊。我們總不能恨眼睛,也不能對發燙的額頭感到恐懼。
小夥們還在蘆笙家的堂屋劃拳,他們明明已經離去了。他們還端坐在飯桌上,手指叢林,飛鳥走獸,飛簷走壁的武林高手……他們手指晃動著的光暈,我有意放緩,他們的手指不得不在鏡頭語言下更換敘事姿態,慢動作,劃拳,光線,手指出動的弧度,肌肉伸縮,皮膚變化……只有指紋無動於衷。
蘆笙不時向朝陽這邊看,朝陽大概是嫌右手上馬的頻率太多,他開始相信他的左手,果然,他左手五指翻飛的靈活度表現出讓右手羞愧的氣度。他自然是忽略了這邊的一個說法,右手為敬。劃拳最好不要用左手。但對於朝陽,一個左右手都可以打乒乓球的人,右手累了是應該出動左手的。明顯,蘆笙朝陽以二敵八,是該允許朝陽呼喚左手先生的。小夥們大概不以為意,他們忽略了一種與蔑視有關的小動作。我們上一輩的大人可是說過了,以常用手和人劃拳,賜人飲水水瓢不倒握予人,遞人剪刀務必將尖端朝己……很明顯,現在這些功課該是被人忽略了,故而朝陽的左手拳風與小夥們打成一片。
你知道,酒喝多了,劃拳總是會遲鈍的,酒量再大的人也要被放翻。雖然蘆笙已經替朝陽喝過幾盅了。大家興致高,朝陽也還面不改色。蘆笙那邊仍有兩個人保持戰鬥力。朝陽這邊也是兩個小夥在與他勾肩搭背。三人一副久別重逢模樣,就差抱頭而泣這道工序了。
朝陽說,我想起一個具有傳奇色彩的故事。他看了一眼坐他左邊的小夥,他是流水寨的。朝陽說,我給你們講述一個故事。旁邊的小夥舉起雙手遲鈍地拍掌。故事和流水寨、達長有關,據傳,我們的祖先來到這片土地時,有一只巨大的神鷹守護著,一直在流水寨、達長、紫塘、水沖、韋竹五個村寨上空盤旋,五個村寨是五個兄弟搬來生根發芽的,流水寨是長房,達長是二房,其餘我暫時分不清他們誰是老三老四老五。神鷹垂亡之際開口說話,說要留點東西給幾個兄弟,最後它不知道它有什麼是最珍貴的,它深深歎了一口氣,發出最後的悲鳴,望著老大點了點頭。最後神鷹消失了,老大捧著一只巨大的鷹腿立於眾人面前,骨髓已經隨著清晨的微風飄至遠方,鷹腿的骨髓飄散前變成一道彩虹架在流水寨與達長的山巔上,南北向跨越的弧線美得令人想哭,一些老人紛紛流下眼淚,少女們眼裏藏著彩虹背過身去,她們想忍住不哭泣,卻還是大聲哭了出來。男人們坐在家門口抽著旱煙,守著彩虹,沉默無話。流水寨那位最年長的前輩,沒有人知道他多少歲了,他捧著鷹腿來到他的兒孫面前,說以後清明就用鷹腿蒸糯米拜祭神鷹。老人找來鋸子,堅毅的面容使他的手勁更加有力,一副骨質的甑子就這麼做成了,人們遵從約定,每年的清明節輪流用它蒸糯米飯祭奠神鷹……
後來呢?流水寨的小夥擦著迷蒙的雙眼問。
朝陽喝了一口酒,說,甑子在古時的一場大火被毀。
流水寨的小夥舉著一碗酒,率先喝了下去,朝陽來不及倒酒,他是想同小夥碰上一碗的。
我們失去了什麼?小夥問。
如果我們失去一種語言和親情,我們大概還剩一條失蹤的開襠褲。朝陽說。
朝陽,困了就去床上睡吧。蘆笙拍我肩膀。
我聽到蘆笙的老么說,叔叔喝醉了。他舉起玩具手槍在遠處瞄著我,嘴裏說,piu piu piu……
我的背後,一雙鷹眼,用不該有的慈愛的目光敲擊我的脊柱。像是我的脊背因為不爭氣,委屈了應有的弧度。我突然想起來,我今天來蘆笙家沒有戴護腰。一些恥辱感開始浮現。
我仍對那天上午去醫院拍照心懷芥蒂,在做脊柱左右彎曲位檢查時,腰帶退至大腿,站在那兒像受難的耶穌掛在十字架上任人觀望,或許是考慮透明還是其他,但絕對不是為了藝術,擺放儀器的房間,牆上洞穿的牆壁鑲上玻璃,一排女生在等候拍照,她們或許因為哪里的骨頭或者組織不太好。
我打開音樂播放器,找到“Like Sunday, Like Rain”,點擊播放。
我對蘆笙說,慚愧啊,幾年沒鍛煉,運動過度,腰椎側彎了五度。
我說我還想將電影再看一遍,或者寫一個同名小說好了。
朝陽。蘆笙叫我。他說,坐久了不好,去床上躺一下吧。
考驗智商的東西還能持久嗎?我問。
得做點不需要智商的事。蘆笙說。
不不不,說點不需要智商的話。我說。
比如喝酒。蘆笙說。
比如夢話。我說。
我在蘆笙家路口遇到芩。芩看我笑了一下,說,你是不是喝醉了?我是不是該叫你哥?
就叫朝陽吧。
我也不喜歡叫人哥哥或姐姐。
說到喝酒,有次我做夢……我說。
你說做夢挺搞笑,你怎麼知道我們的相遇不是在夢裏呢?芩說。
咳,哪有這樣捉弄我的夢境。我繼續說,那場夢的內容,說有段時期,大概是我八個月大左右,我媽帶我去外公家。適逢缺水,男人們以酒代水,或者渴了就吃一把豌豆尖。你能想像吃花生下酒,或者吃一把生豌豆尖的樣子。我在外公家的院壩遇到很多人。我媽媽在臥房裏給我餵奶,畢竟她知道,我只有在喝奶時才不哭。親人們都頭疼,有個愛哭的小孩真是夠吵的,總不能打小孩吧。那時候我爸爸被叫去州府參演一個退伍軍人的活動,我爸槍法極准,被縣裏給喊去了。我媽媽說缺水的天氣,怎麼可能有奶呢,但總要哄一下我啊,明知沒有奶,我媽在故意逗我時對我說“吃飯啦吃飯啦”,如此,我聽到這三個字,就能條件反射咬母親大人的乳頭,能喝個一小口。母親後來與我說起另一件趣事。說我和長我一歲的兄長各分一只母乳,方言是“吃奶奶”。母親說,小時候我和哥哥各抱一只啃。幼時的我問,那我們家外公那麼多,太婆(外公母親)有很多個“奶奶”嗎?
你確定不是在說夢話?
我的母親那時也正是一個年輕的母親,我好像聽到我砸吧砸吧嘴的聲音了。
可我沒看到小孩啊。
我也沒看到小孩,只是通過我媽媽的敘述,隱約聽到小孩吸奶的聲音。
所以你只是借用一下敘述之聲,向我傾倒你的童趣?
童趣?若真是這樣,那我情願在夢裏不要醒來。剛剛我去參加了一場葬禮,通往水沖的路。看到惠賜我名字的外公停在通往水沖的那條馬路上,他站在路邊撒尿,我沒有喊他,我不確定我是否真的認識他。我倆擦身而過。我從一片黑雲下穿過,我感到口渴,向一個空房間走去,那裏有一塊活動門板,我將門板卸下來作畫。最後再把門板轉過來,灰黑色的門板開始有一點和其他顏色有關的東西,這一刻我想起一個詞,“體面”——我覺得,我們的世界相當體面。
你怎麼會路過蘆笙家院旁呢?我問芩。
我聽到你說我壞話啊。
算了吧,我幾時說過你壞話?
你當真不知道我們的父母想撮合我們?
可我們都沒見過是吧,我哪知道你會不會厭棄我的無趣……你看,此刻我剛從一場酒局中抽身。
在老家就是這樣,你不和大家喝酒顯得不好客,再說你也不差那二兩,二兩酒的量是多少,二兩能醉人嗎?
你一直在等我嗎?
聽說你還帶上我家給你的白衣去築城?
我不知道怎麼回答你。關乎禮儀的東西總能令我緘默。
實際上它的象徵意義並非只是禮儀。
我知道,是信物。於我於你,是一種牽強的信物。
所以呢?
所以我就算站在你面前,你也不認識我。我也未必真的遇見了你。
咳,真的是酒喝多了啊你。
沒有呢,我剛剛和蘆笙還去捉鳥了,我們穿過濃雲,在一處峭壁上追尋它的蹤跡。我們在抓一種叫“加娃”的鳥,它的聲音有些尖利,像孩子生氣時發出的喉音。事實上我們布依語沒有這種名字的鳥,漢語裏也沒有。後來我們還在一座山頭遇到一座古墓。
你倒是開始編故事了。
哈,是河岸正在受刑的女子的母親的墳。有人找來一個與該女子面貌一樣的女人,是她的孿生姐妹。但女人來到墓前就消失了。鏡頭換成我在古墓前評價墓的造價——電影成本也太高了吧,我說——繼而和蘆笙審視墓碑上的字。最後我在墓前挖到一顆火球,球體通紅,我一腳把它踢下山,我們村的左邊角落起火了,我們都在往另一邊的村道走。
所以,你們在去捉鳥的途中背對火光了。
是的,我們還將趕往山上的水庫,我們拼命向水庫趕,路面極滑,石料鋪就的斜面在坡上現出水澤和青苔的光亮。我知道我爬不上去了。我們遇到很多放棄的螞蟻,我是說,已經有人先於我們找過水庫了,他們憑倚螞蟻群體活動的姿態向我們滑過來,他們說路到頂了,根本沒有水庫。朝我說話的人,他的平衡能力超級好,一滑就滑到稍微平出幾步的邊緣上,沒有護欄,下邊是山崖,崖下是深湖。沒有成功滑到窄小平臺處的都掉下去了,但他們都會游泳。我也準備好有掉下去的可能,但我擔心水會襲擊我的鼻腔。
看你說得真累,就不能說點輕鬆的麼?
嗯,後來我們看到被我們灌醉的那幫小夥,他們長大了,有幾個去打工後回來上學的人也都畢業參加工作了。他們像是被誰將臉面粉刷過一番似的——我得想一個詞——體面——他們相當體面,酒桌上是一種瓶身奇特的酒,桌上的一個青年向同伴介紹這款酒,瓶身以古玉琮之形設計而成……我們隱約聽到“三百石”三個字,大概是酒名。其中兩個青年在討論象徵和擬真的意義。長條凳這邊的兩個人在玩對話藝術。青年A:只有肥肉一塊,你吃嗎。青年B:吃。A:掉地一塊。B:吃。A:肥肉斷腿了。B:吃。A:蟋蟀抱入懷中。B:吃。A:蟋蟀餓死,你還能吃蟋蟀嗎。B:吃。——這是一項沒完沒了的遊戲,參與者全憑耐心。
磕磕絆絆。
什麼?
你說的,就沒有一個故事是完整的。一個人物來了,又消失了。你所造就的不過是虛實的相互背對。
但他們總是有邏輯關聯的,我的某個辭彙,或者先前我提供的一個影像。你看,意義就是忽略意義,忽略意義就有意義。
我呸。
等你想清楚了就來找我。芩說。
這些日子,說過的話,做過的夢,正如我們清洗……或者乾脆換了被罩,回想起來我們使用過的語言將不那麼光滑了。
睡太晚或起太早,我都不敢看向鏡中的面容,只能眯著眼睛看一下腳上的人字拖或毛拖鞋辨認季節,我們理解,花朵何曾忍心觀望自己的焉塌與頃圮呢。
喝酒,我們以為我們贏了,其實我們輸了。蘆笙說。蘆笙遞給我一碗青椒肉末面,此前他調製了一鍋湯,他將整張青菜葉鋪到湯裏,並快速用筷尖壓青菜葉接近精心調製的油湯底層,複又抽出筷尖。
我翻了翻我的手指,說,其實我無法規避一個辭彙,哪怕我借用了灰黑這一色彩,跋山涉水的滋味不好受。最後我在四圍都掛著漂亮衣服的女生宿舍樓空地找出路,後來艱辛爬山,我不知道自己為何一直用指墊抓地而不用指甲,如果我像四肢動物一樣,我的指甲一定非常堅利。
滾蛋吧你。蘆笙嘲笑我。
我最後向蘆笙說了一個細節,我和他去抓“加娃”的地方叫庇隆灣。那只哀傷的鳥兒受困於一個門型籠子。它知悉人的行跡以及善用鳥類的智慧,我們之所以找尋不到加娃,是它率先隱匿了自身,它知曉神跡所有秘密,實的背面是虛,陰抱陽,可偏生有人缺失愛意和眼淚。加娃卸掉自己的一只右腿,並勸告骨髓,只能以彩虹的姿態出沒於人眼可視的行跡,一些與祭拜有關的辭彙,終會升騰,令人動容的不再是可視的美,可聞的美,或如犬乞尾,或如,噪鵑起聲。
最後呢?蘆笙不懷好意看我。
我果斷說,最後我吃完一碗我兄長精心製作的青椒肉末面後我就滾蛋了。
走出灰黑地帶,我像是一只崴腳的瘦狗,偶爾回看身後有沒有人攥著石塊。
我最後抱守的秘密是,我不過是個與年齡錯開的人,時間在走,自己變慢。可是人啊,必須把自己當回事,不是往頹喪陷進去,而是盡可能睡好。
我與芩在黑灰地帶的會面,從爆竹聲響起時我們就分別了。我回頭,煙火通明。我朝她離去的方向喊,芩,謝謝你的口紅,還有耀眼的門牙。芩話音漸弱式撤離,我們第一次見面,尺度就這麼大了嗎。
蘆笙家老么走過來拿他的小碗碰了一下我的大碗,他將青椒撥靠碗沿,心滿意足地喝了一口麵湯。我摸了摸老么的寸頭,看他掉頭擺下碗筷。
我略笑:“山頂的意義,不是蒲葦和高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