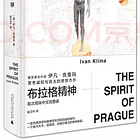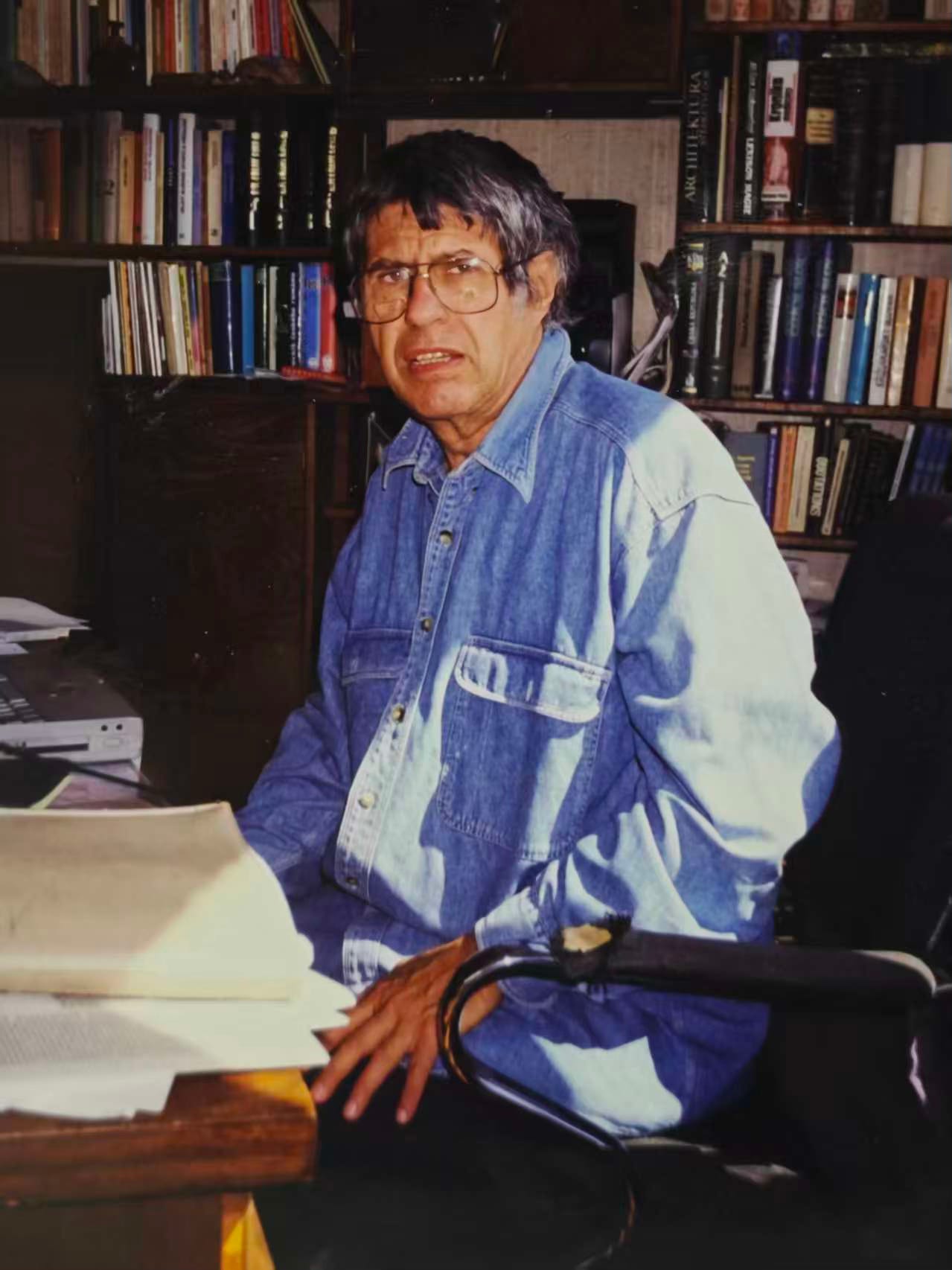崔卫平 | 我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个我:《布拉格精神》再版后记兼纪念伊凡·克里玛
编者按:2025年10月4日,伊凡·克里玛(Ivan Klíma)在布拉格寓所安详辞世,享年94岁。伊凡·克里玛1931年出生于布拉格。克里玛的父母并没有宗教信仰,却因其祖辈的犹太血统,全家人于1941年被送入泰里茨集中营。克里玛在集中营度过三年多时光,也初次尝试写作。1945年苏军解放集中营,克里玛及其家人均幸存。1956年,克里玛毕业于布拉格大学文学语言系,进入文学杂志社担任编辑,同时创作小说和剧本。1968年苏军进入捷克,克里玛应邀至密西根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后,他决定返回到捷克,随即失去了工作。他的作品在捷克被禁止出版长达二十年,只能以“萨米兹达特”的形式流传。他为谋生而从事救护员、清洁员等工作,同时更积极写作。他的作品在其他国家受到欢迎,被翻译成近三十种语言。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使他的作品在其国内再次获得出版机会。克里玛与赫拉巴尔、米兰·昆德拉齐名,且因其“始终在场”,被捷克读者视为20世纪90年代捷克文学的代表。克里玛著有二十多部小说、戏剧、评论集。主要作品有《我快乐的早晨》《我的初恋》《爱情与垃圾》《被审判的法官》《我的前途光明的职业》《等待黑暗,等待光明》,以及《布拉格精神》等。
中文译本《布拉格精神》1998年 由作家出版社首次推出,译者为东欧异议思想研究学者崔卫平。该译本因当时审查原因,删减了两篇文章、一篇改名,克里玛本人特地写的中文版序言也没有刊出(序言由中国捷克文专家刘星灿老师翻译)。2016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完整版。此文为当时全译本的译后记,以克里玛的自传《我的疯狂世纪》为引,探讨他如何通过记录观察与反思,重建被极权主义虚耗的人生格局。在得知克里玛去世消息后,略有改动。作者崔卫平授权刊发。
免費訂閱《波士頓書評》及相关事宜发送邮件:boshidunshuping@gmail.com,隨意打賞:Zelle,PayPal:boshidunshuping@gmail.com 用戶名:Boston Review of Books;長期支持請點擊下面訂閱,升級為付費訂閱。
一
捷克小说家伊凡·克里玛的随笔《布拉格精神》,1998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当时删除了两篇文章,另有一篇文章被改了名字。不知为什么,克里玛本人特地写的中文版序言也没有刊出,由中国捷克文专家刘星灿老师翻译。这回终于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一次完整面世,于2016年1月出版。然而,我的这篇新“后记”没有跟得上该书再版的节奏,真是十分遗憾。
伊万·克里玛1931年生人,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为疯狂的20世纪,他把自传直接命名为《我的疯狂世纪》。他声称自己活过了两次极权主义的寿命,看到了它们的崩塌,这在他有些不可思议,因为他身处其中时,并没有想到自己活得比它们长久。在大时代的变动中,他个人命运经历了两次重大灾难及转折:第一次是跟随父母在纳粹集中营当了两年多的小囚犯,1945年被苏联军队解放;第二次是1968年苏军入侵之后因自由思想被剥夺作家资格,做过土地测量助理员等多种体力劳动,直到1990年他才再度公开回到了自己的作家身份,迎来了另一个创作高峰。
一个人在灾难中度过了大部分岁月,很多时光都被虚耗了,他如何重新赢回自己的人生?如何扳回自己的人生格局?克里玛的办法是——记下它们,记下自己的观察尤其是思考,以语言所建立的秩序,来保存在实际世界中迅速流失的东西。“超越我们自身死亡的斗争是人类的精华。”而所谓记忆包含了理解在内,对一件事情的理解意味着步上一个新的台阶。这本随笔《布拉格精神》,释放了他对这两个极权主义的认识及反思,思想的不同阶段与他在现实中的经历正好相平行和匹配。当他能够再三穿透自身处境,超越自己过去的想法,他就获得了超越厄运的视野,能够战胜死亡带来的虚无。
二
战争结束时,他是一个14岁的孩子,既被一种狂喜所充斥,也被一种强烈的复仇情绪所压倒,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他形容自己如何紧张屏息地聆听广播中宣布的审判,审判纳粹首犯和捷克卖国贼,欣喜地扳算着纽伦堡被判处死刑的人数。这种感情和大多数周围人没有什么不同,与这个世界上其他地区有着相同经历的人们,也没有什么不同。
然而,他后来获得了另外一种视野。到目前为止,这种新视野对于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还是陌生的。那就是:“想要从我们的受苦经历中得出结论,会被导向致命的错误,那不是把我们引向想得到的自由和正义的境地,而是把我们引向相反的方向。对这些人来说,极端的经历并不打开通向智慧的道路。和自身的经验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们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换句话说,苦难并不直接等于正义,一个人仅仅是被放到某个处境之中,他不会因此而自动取得道德身份。
极端被迫害的经历容易产生复仇意识,产生将对方置于死地的幻觉和快感。然而,如此却进一步深化了受害者的危机:它让受害者处于一种迷狂的或狂热状态,对这个世界上其他的东西置之罔闻,对自己与他人的生活麻木不仁,概括地说,倾向于冷漠无情:“他们倾向于将任何人看作一个敌人,或哪怕是一个潜在的对手。”曾经落到他头上来的悲惨情景,他一方面认为不合理,但另一方面却认为不妨让他的敌人尝尝,因而在这个世界上制造出新的人间地狱。如果没有自觉意识去消化、化解他曾经遭遇的残酷无情,他将是这个世界上最为残酷无情的新人之一。
从受害者的处境中还容易产生那种道德优越感,认为施害者是邪恶的,受害者在道德上则是纯洁的。伊万·克里玛回顾了少年时在集中营遇到的情景。显然,集中营并不是一个培养道德的场所,相反,它只负责摧毁。在食物和其他物资十分匮乏的地方,偷窃的行为或者多吃多占的行为随处可见,人们可以宽慰自己说,这是拿回纳粹从我们这里拿走的东西,但实际上这种被压倒的处境,抽取了人类最基本的道德界限,模糊了人们头脑中是非善恶的概念,是对于一个人道德身份的剥夺。
在克里玛接下来要应付的后极权主义环境中,也同样存在这种道德模糊的状态。当某人得着了一些好处,这不是他可以洋洋自得的理由,而是他的人格遭受贬低和自我贬低的结果。“原本是正常人性需要的东西,因为极权主义,就变成一个稀罕珍奇之物。它们被用来贿赂人民……每件东西也就成了腐蚀人民的一项特权,这种政权摧垮了人们的公民意识和他们的自信。”(《极权主义始末》)每个人都面临道德上的困境危机,危机的程度随着他们的身份地位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那是一个广泛的境地,人们在接受现实中种种不合理限制的同时,也经受着道德上被摧毁和被攻陷。
这样一种批评极权主义思路,在东欧反对派思想家中有着普遍认同。哈维尔始终强调,大多数人虽然没有去作恶,但是“接受和处于伴随谎言的生活便已足够。由于这个突出的事实,个人巩固了这个制度,实现了这个制度,创造了这个制度,是这个制度”。这样说完全不是要为施害者解脱(像某些故意扭曲的人说的那样),而是激发受害者本人站起来,看清自己的处境,争取自己的合法权利和合法的道德身份。
不管是改变社会风气还是社会制度,事情总要从某个地方开始,从某些人开始,拥有一些手边的起点或开端。既然个人曾经“是这个制度”,那么也可以尝试让自己成为令这个制度掉链子的那个“开端”。
三
伊万·克里玛的另外一个思考,看上去不是十分引人注目,但是含义深刻。克里玛是加入了共产党的,后被开除党籍。书中涉及了二战结束之时,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整个向左转,选择共产党是在特定条件下人民自己做出的决定,而不仅仅是外部强加的(当然人民不应当只有一次选择的权利)。经历了许多失望和绝望之后,人们在寻找可能的新希望。克里玛的父亲是一位有着左倾思想的工程师,这是当时社会总体气氛使然,不是仅仅贴上“邪恶”的标签所能够说明的,也不是极少数人制造“阴谋”的结果,而是某种较为普遍的思维方式的结果。到底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在哪里?
《论世俗信仰的文学》一文,解释了为什么人们集体被一种幻象所压倒。因为有着死亡的大限,人们恐惧生活的无意义,恐惧空白和虚无,于是有了信仰和拯救的需要、对于不朽的渴望以及对于超出自己力量的崇拜。所有这些向往,本来是架设在“此岸”和“彼岸”之间,架设在“有限与无限、人性与神性、永久的无与不朽、灵魂和肉体”之间,它们之间的距离是永恒的。神性赋予人性以尺度,赋予人性希望和期待,但是人永远不可以将自己看作神,不能认为自身已经抵达神性。彼岸的天堂永远是一个憧憬,而不是脚下站立的地方。
错误正是从这里开始——一夜之间,人们“发现”自己正好置身于人间天堂,或正在一手制造人间天堂,遥远的东西变得唾手可得。原本来崇拜的对象消失了,人们开始崇拜自己,崇拜自己提交的蓝图和永不衰竭的精力,他们正好是地上的神,一切距离将要在他们这里消失,所有藩篱将要在他们手中破除。
那些预言家们(文学家也参加了这种准巫术活动)试图让人们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难题,没有攻克不了的对象,因为他们是一批得到豁免的天兵天将。对于经历了长期看不到希望的地狱般生活的人们来说,这无疑具有巨大吸引力。而这种世俗信仰(建立地上的天堂),对于任何年代及任何遭受过挫折的人们,会永远魅力不减,没有比将自己居于世界变动的中心且一劳永逸的图景更加吸引人的了。
四
这本随笔中有一篇关于卡夫卡的长文,本人以为这是该文集中写得最为深入漂亮的一篇。对卡夫卡创作的思考,提供了与极权主义正好相反的那一极。卡夫卡在时代潮流、重大事件面前,能够始终坚持个人经验的独特性,坚持自己的真实动机、欲求和立场。在他那些被解读为各种隐喻的小说中,蹲伏着一双忧郁的眼睛,那仅仅是他个人的和有关个人的。
通过对于卡夫卡作品的详尽分析,提供如同证词般缜密的细节,克里玛证实了——始终视为时代的寓言及对于时代深刻批判的作品《在流放地》、《审判》,然而实际上却与卡夫卡本人最私密的个人经验相关。1914年6月1日,卡夫卡与费丽思·鲍尔在女方家中订婚。六周之后卡夫卡提出退婚,接下来在阿斯肯纳什饭店中有过一场“奇怪的会谈”,在场的还有其他几个人。未婚妻表达了她对于婚姻前景的想法、恐惧和对未来新郎的指责。卡夫卡在日记中将这次会谈称之为“审判”。
“审判期间”,卡夫卡始终保持沉默,对费丽思和陪送她前来的家人感到惊恐。他后来形容自己“像囚犯”,他在当天日记中描述囚犯的语言,与《在流放地》十分接近。订婚所用时间十二个小时,也被用在《在流放地》里。《审判》的叙事时间为十二个月。实际上,小说中的那些行刑机器、审判场面也很难与任何一种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很难将此等同于当时社会“不合理的社会秩序”,它们是那么古怪离奇,其中的角色从根本上是含混模糊的,军官和旅行家之间的立场是可以互相转移的,审判的地点居然发生在私人公寓里,而不是在公共法庭上,其中的许多细节是自相矛盾的,事件和议论是令人费解的,恐怕只有卡夫卡一个人能懂(《刀剑在逼近》)。
什么叫写作中的天才?应该不是什么天马行空,两眼放电的人物,而是能够尽可能接近自身,抵达自身,穿透自身晦涩的私密经验,将此提升为可以观照的形式。获得形式是一种转化,是对于自身的超越,因而也有可能成为时代的。在这个意义上,克里玛认为昆德拉去到法国之后提供的写作图景,不超出一个外国记者在布拉格住上一阵子能够得到的,其中失去了对于个人命运深沉的承担。
克利玛这样评价卡夫卡:他描绘和捍卫了人类空间中最个人和内部的东西。当另外一些人认为建立人间天堂是理所当然的时候,卡夫卡表达了这样的担忧:人可能会失去他个人的最后凭借,失去安宁和他自己一张安静的床。
五
1998年《布拉格精神》译本出版之后,我多年看到人们引用其中最多的话是这句:卡夫卡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1914年8月2日)的日记中只有两句话:“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游泳。”
将重要的世界崩溃的事件和无关紧要的细节联系在一起,这种做法在旁人看来突兀奇特,然而它扎根于这个城市的命运之中:一方面,欧洲的战争很少有不影响到布拉格这个地区的,欧洲的危机和风暴尤其会造成这个地区的灾难或沦丧,而另一方面,处于危机中的人们仍然过着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他们视日常生活和私人性领域为最后的藏身之地和避难处,这是他们自我保护和蔑视强权的一种方式。
这意味向世界无声地宣告:我有权不加入你们这些侵犯者的行列,不以任何一种方式增添耀武扬威者的威仪,我也用不着学你们那种腔调和语言说话。用卡夫卡字里行间无处不在的潜台词来说:“我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个我。”
看重个人和注重个人般不大不小的比例,让世界成为由个人能够面对和消化的,布拉格因而成了一个堆满细节、不事夸张的城市。克利玛形容道,某种比例感也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来。布拉格生活从不追求夸张卖弄、胡诌乱吹、烟花爆竹、让人眼花缭乱的社会性狂欢、娱乐场或大型军事游行。这个地区的人们更倾向于日常生活、市场、季节性节日和简朴的舞蹈。对那些扎眼的、耀武扬威的东西他们本能地抱有厌恶。
这就是伊万·克利玛对于我的意义。他帮助我调整了眼前世界的比例和光线,帮助我在这个世界上找到来自自身的力量。即使参与公共生活,也要作为一个成色更足的个人来加入,给公共生活添加丰富色彩而不是淹没于其中。
2009年春天,在布拉格我两次见到了克利玛先生。一次是在与“七七宪章”成员的见面会上,显然他不喜夸夸其谈,只说了几句话还字斟句酌的,决不是一泻千里那种人。两天之后,我此行的邀请方安排了去布拉格郊外森林边上克利玛先生的寓所,与他静静地谈了一个下午,从文学到政治。他问起警察有没有找过我。他教我,面对警察问询时,什么也不要说。他们会假装自己已经掌握了一切,以此来解除你的提防警惕,接下来从你自己嘴里套出一切。但实际上他们比他们说的要知道得少的多,他们知道得可怜,所以你千万不要说什么。看来布拉格的持异见者们在这个问题上是统一的,我曾读到哈维尔的妻子说,什么也别说,连狗的名字也不要告诉他们。这个经验我后来用上了。
(2016,2025年10月5日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