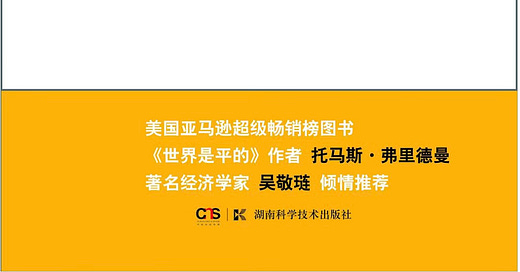郭锐 | 公司和国家
编者按:“方流芳先生对晚清商业和政治体制关联的分析,与刚获诺奖的两位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的洞见殊途同归。”本文为《波士顿书评》专栏作者郭锐最新文章。
如何理解公司?流行的看法是将其渊源追溯到古罗马,再罗列历史上各种商业组织形式,最后给出现代公司的特征。但在《公司词义考》一文中,方流芳先生给了我们一个更深入理解公司的机会。方先生引入“语言游戏”的哲学利刃,在“从1757年实行广州“一口通商”到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行商、通事、官员、学者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大班之间在冲突中的对话”的丰富历史语境中剖析了公司概念在中国的用法和所指。语言游戏,强调一种理解公司的全新视角:当不存在一个现成的公司概念时,在那些第一次遇到西方“公司”的中国人眼中,它到底是什么?对第一次见到公司的清朝官员而言,英国东印度公司不同于他们所知的任何机构。如何将其植入一个既有的世界秩序中,是中国人面临的第一个问题。面对一个异质的文明和未知的世界,清朝官员、行商和通事在回应英国东印度公司大班、外国官员提出的问题和挑战中,共同定义了公司的内涵。
将公司一词,放入到1757年至1840年这一历史时期的具体语境中,方先生发现当时公司最显著的特征是“官设”和“独占”。“官设”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需要得到国王的特许状,独占则是由其独占英国对华贸易权。正是基于这种先入为主的印象,在19世纪70年代的洋务运动中,中国兴办的第一批新式企业,无不是官府主导设立且在某一领域或者地域具有“专利”(垄断)权的企业,比如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平矿务局、北京电报局等。此后,清政府主导、参与企业经营的执着有增无减。这是因为中国首次学习西方公司制度时的模版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公司并不与私营企业天然契合,反而成为清政府直接介入商业公司的制度依据。
今天,很多学者对晚清公司的观察和公司制度移植困境的解释是:中国企业大多是家族企业,而家族企业所依托的宗族制度对现代公司赖以产生的财产法和契约法制度的发展造成阻碍,故此公司无法在中国产生,相应地现代市场也难以在中国发展;必须经由法律移植,中国才能发展现代公司。 这些说法,或多或少支持了立法者执着于对比中国与“国际标准”有何差异、在如何更让它像西方制度。如1993年颁布的公司法,就有类似的情况:学者和立法者均真诚相信,与从已有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的建议相比,与西方公司法更为相像的立法更能带来进步。进入二十一世纪初,“与国际接轨”的论调同样在中国股票交易所制度改革的讨论中风行一时。众多中外学者对中国公司制度的研究,往往将读者引向“缺乏投资者保护-公司制度不兴”或“公司制度不兴-缺乏投资者保护”的观点,结论就是需要更好地移植西方公司制度。
这种“自我殖民”的套路,让中国公司法陷入模仿-不像-再模仿的怪圈。甚至,官方借法律移植之名保护落后,却声称“和国际接轨”,也屡见不鲜。比较公司法研究中有一洞见恰与此相悖:世界上并没有一部可以在任何国家发挥作用的“完美公司法”。与其反复地模仿国外制度,不如转变思路,反观自家公司制度是如何在真实世界中一步步形成的?从真实的历史和现实中里找出病症所在、开出药方,比迷信一种理想的西方公司制度更为可靠。
科学史上有“李约瑟之问”:为什么中国一直到中世纪还比欧洲先进,但后来却未产生现代科学以至于落后于欧洲?哈佛的历史学家柯伟林教授提出了一个类似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很早就有改革者主张引入公司制度,从晚清政府开始,北洋政府、国民政府直至新中国在立法上均极为重视,却屡战屡败,目的一直未达到?这个问题,学界称为“中国公司之谜”。方先生的研究将我们带出了“缺乏投资者保护-公司制度不兴”、“公司制度不兴-缺乏投资者保护”的循环论证中,转而关注制度表象之下的问题。
鸦片战争前,单纯比较英国东印度公司和广东行商,中外商业组织都有某种政府的特许权。当然,中英商人的命运迥异。方先生看到,如果单纯考察个体,广东商人在信用、勤勉、谨慎和商业经验至少与英国东印度公司不相上下,而他们的谦恭、忍让和富有人情味的商业作风则远比细铢必较、寸利必争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大班更能赢得商业伙伴的好感。同时,中国商人在中英贸易中,是以逸待劳的,可谓在客观条件上占尽了优势。然而,清政府利用“保商制度”等对广东行商的管制和束缚,使得中国商人始终没有施展手脚的空间。清政府过度管制不但扼杀了中国商人的竞争力,还成了官员索贿的沃土。反观英国政府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关系,英国政府历来把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在华商业利益作为中英交往的头等大事,愿意动用国家力量强化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华的地位,英国东印度公司愿意化钱取得国家力量的支持,国家和商人相互合作,一起通过外交去实现海外贸易的最大利益。“在大英帝国的不遗余力的扶持下,英国东印度公司发育成一个体魄魁伟,好勇斗狠的强人,争斗、冒险成性,攫取永无曆足,其实力、谋略和组织优势足以在全球兴风作浪;在大清帝国无所不用其极的压迫、管制和勒索下,广东行商发育不良,缺乏搏击的体能和创造性智慧,只能凭借一些在当时、当地管用的祖传计谋做一点的小生意。”倘若公司从被第一次移植开始,立法者就没有关注中小股东权益的视角,此后也未有根本改变,那么我们怎能期待在中国建立英美式以聚合资本为目的的大型公众公司?
方流芳先生对晚清商业和政治体制关联的分析,与刚获诺奖的两位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的洞见殊途同归。
在2012年出版的《国家为什么失败》中,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区分了包容性(inclusive)和汲取性(extractive)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包容性,从政冶上讲,强调公众具有政冶权利,能够参与政治活动,选举当权者和政策制定者,当权者和政策制定者是人民或者选民的代理人而不是统冶者。任何人都有希望成为当权者或政策制定者。从经济上讲,包容性强调自由进入和竞争,任何人都没有通过垄断、专卖或者市场控制获得超额利润的机会。人们都可以获得生产性收益的绝大部分或者全部,人们具有很高的生产性激励。比如,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国家。汲取性从政治上讲,是指公众没有选择当权者的权利,也没有选择政治制度或经济制度的权利。当权者或者统治者并非人民的代言人,既得利益者在制度的选择或政策制定中起着重要作用。汲取性从经济上讲,指经济制度或者经济政策都由既得利益者制定,他们通过各种垄断权、专卖权、市场控制等掠夺大众生产者,使得大众生产者只能够得到所生产产品的—少部分,社会获得的产性激励的不足。例如,欧洲殖民者从非洲大量贩运奴隶到美洲、 亚洲等国家或地区进行奴役,殖民地的土著居民被剥夺了所有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被迫为殖民者工作,他们建立起来政冶制度和经济制度,具有典型的汲取性。
两位作者看到,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之间,似乎有一种天然的“粘合力”,包容性的政治制度更容易与包容性的经济制度共存、汲取性的政治制度大概率会和汲取性的经济制度共存;第二,汲取性制度能够实现短期经济增长,但不能持续;包容性制度能帮助国家实现长期经济增长。原因在于,后者可以激励公众从事生产活动,最大程度的避免了非生产性的攫取活动,降低社会整体的交易成本。
晚清政府与东印度公司的交往中,我们看到的是大清帝国汲取性的政治制度与汲取性的经济制度龃龉不断;而彼时的英国已经体现出在包容性的政治制度下汲取性的经济制度(东印度公司)和包容性经济制度(向商人开放股份有限公司的自由设立)相继大获成功。在思考如何翻译company的时候,无论是官员还是通事(翻译),想到的是在中国只有国家权力才有可能赋予company垄断权和专卖权,故此“公”和“司”成为自然的选择。早期观察到的东印度公司之“公”,成为中国公司之“公”的来源。但当英国改变了国家权力的世袭制度,将汲取性的政治制度转化为包容性政治制度的时候,大清帝国仍然延续了权力的世袭和拒绝公众参与的特征。此后,历经辛亥革命、1949,直至今日,中国在从汲取性走向包容性政治制度的路上,一直停步不前。这也是“公司”这一译名直至今日仍然显得如此贴切的缘由。
1904年,晚清立法者径取英国和日本公司法的内容,将其装入《大清公司律》。但实践中,事实上,无论是1867年的出现的中国最早的公司章程《联设新轮船公司章程》,还是1905年郑观应主持制订的《粤路公司章程》,公司制度的实践者在集资办法、内部管理、股东地位以及利润分配等都有曾有各种法律制度实施的经验教训:这些公司发起人、股东和经理人历经波折,最终在公司成立遇到困难草草收场、或公司内部纷争导致管理层无力维持。但是,他们实际遭遇的困难在立法时无深入讨论、立法后也无回顾反思,导致制度无从改善。民国公司立法和当代中国公司立法,也大致如此。这都是缺乏包容性政治制度必然导致的恶果。
与立法的无所作为相对应的是,无论在公司立法之前还是之后,政府或强行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或拒绝维持市场秩序,结果都是让公司成为政府控制经济的牺牲品。在中国公司实践中,始终如一地表现出国家主导的特征。
历史上并非从未出现过国家放松干预的政策松动。但政策松动,也未带来制度改革。这种例子,远的有有1883年前后晚清政府先放任、纵容带来上海股市泡沫、后将矛头指向西方股份制,近的则有刚刚过去的注册制改革,风声甫到即被股市泡沫、市场大跌所打断。与行政、司法整体不匹配的政策松动,往往紧随极端的政策转变,对制度创新并无助益。学术研究如果无视历史背景,难免进退失据。有学者当年是全盘西化的忠实粉丝,如今却对当局经济干预政策照单全收,如果没有机会主义的动机,则显然是缺乏历史知识带来的张皇失措。
中国立法者引入公司制度,名义上是要借引进西方先进制度来提升商业组织效率,实质上是试图以立法来促成政府办企业。这种情形持续至今。无论是1946年国民政府全面修改《公司法》,还是1994年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都并非简单期待借立法提升经济组织效率,而是要用公司法解决国企问题。这导致公司法总是看起来像是一种“半吊子”的市场化改革。
不少法律学者,其中不乏支持市场化和民主改革的朋友,对中国类似公司法的“半吊子”法律改革,往往秉持一种天真的看法。他们认为,即便立法者对主要考量是为了某种其他目的,只要立法多少促进了“真正”目的,就是好的。换言之,哪个目的是决策者真正的目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做法客观上取得了什么效果。当然,以解决国企问题为幌子推进公司制度改革,可能也是一种“政治安全”的策略。无论原因如何,持有这些天真看法的学者,今天也许会后悔当时未曾抓住制度变革的机遇吧。
(本文改编自郭锐:《〈公司词义考〉二十年—再思语言游戏、法律移植和政企关系》,2020年4月《财经法学》2020年第4期)
胡平 | 《新冠肺炎浩劫:一場本來完全可以避免的大災難》自序
2019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黨報《人民日報》在一個不顯眼的位置發表了一則簡短的新聞:「武漢肺炎不能斷定是SARS病例大部份為華南海鮮城經營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