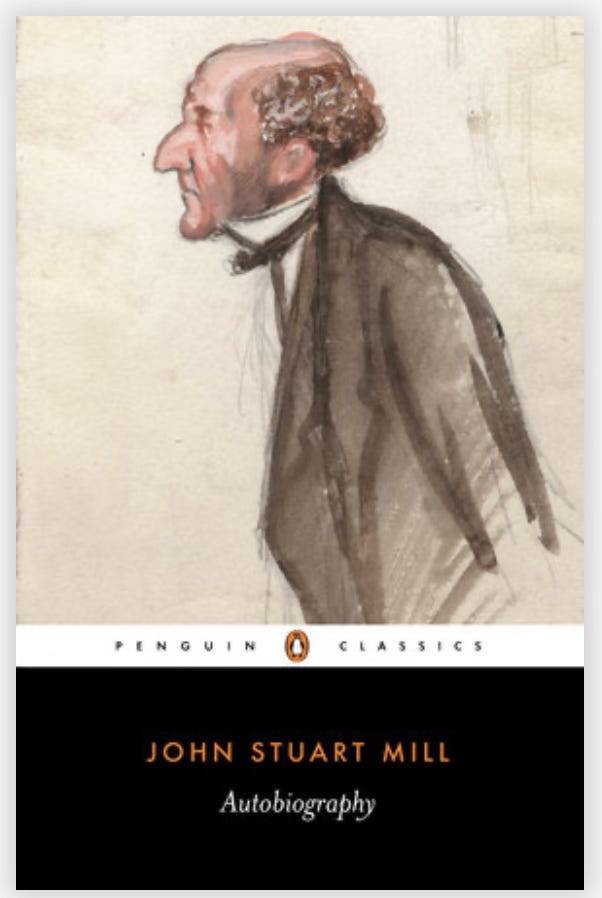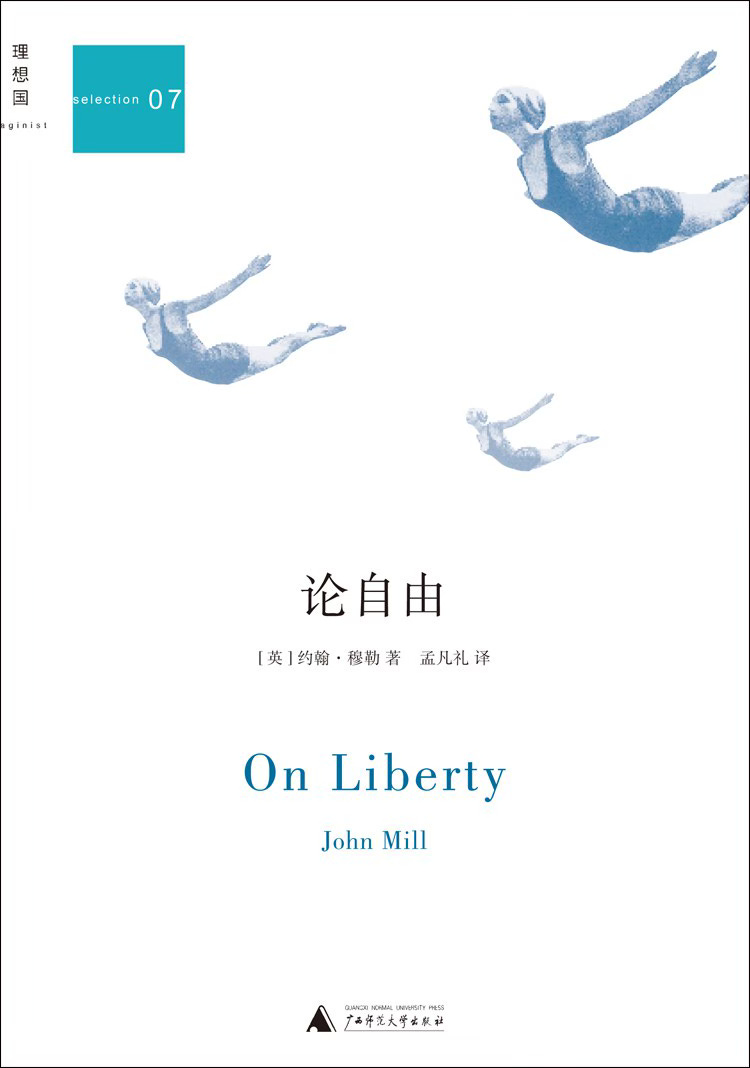孟凡禮 | 约翰·穆勒自传(节选)
編者按:本文是孟凡礼老师为即将出版的《论自由》第3版增译的附录;原文节译自《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自传》第六、七章,翻译所据版本为企鹅出版社重印的多伦多大学出版社《穆勒著作集》。经孟凡礼老师授权,波士頓書評刊發。
就在我目前所处的这个精神进步阶段,我跟一位女士结下了友谊,这段友谊是我一生的荣幸和最大幸福所在,也是我此后为人类进步所做或希望有所建树的一切努力的重要源泉。我第一次结识这位女士是在 1830 年,当时我二十五岁,她二十三岁;在经过二十年的友谊后,她答应做我的妻子。
我跟她的相识,从她丈夫家那边来说,可说是故交重续;她丈夫的祖父是我父亲当年在纽顿格林的邻居,我小时候有时会被邀请到这位老先生的花园里玩耍。他是老派苏格兰清教徒的极好榜样:严厉、朴素、庄重,对小孩儿却十分和蔼,这样的人往往给孩子们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虽然是在我认识泰勒夫人很多年后,我才与她有了亲密或彼此信任的关系,但是我很快就发现她是我认识的人中最令人钦佩的。这并不是说,她在我初次见到她的那个年龄,就是后来她所是的那样了,这在任何人都不可能。
如果说,无止境地追求自我成就、自我完善,就是她天性的法则,这种说法至少是不那么恰当的;因为这同时也是她追求进步的热情和她身上某种才能自发趋向的必然结果——她能把自己接受的每一印象或经历,都变成增加自己智慧的源泉或机会。
从我第一眼见到她时,她那丰沛而有力的天性就通过公认的女才子类型而展现出来了。从外表看,她聪慧美丽,所有接近她的人都能感受一种天生的出众气质;从内在看,她有着深沉而强烈的感情,有着敏锐而直觉的智慧,又有一种爱冥思的诗人气质。
她很早的时候就嫁给了一位十分正直、勇敢和可敬的男子,这个男人见解开明,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欠缺一点智识或艺术趣味,否则就堪称佳偶了,不过他是一位稳重而深情的朋友;她一生都对这个男人怀有真正的尊敬和最热烈的爱意,当他去世时,她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
由于社会让妇女陷入无所作为的状态,她们无法在外面的世界充分施展自己的最高才能;她过着一种内心沉思的生活,在跟朋友小圈子的亲切交往中变化起浮;与她交往的朋友并不多,其中只有一位(早已亡故)天资过人,在情感或智力上与她相仿,不过所有人都在情感和见解上或多或少地与她一致。我有幸被允许进入这个圈子,很快就发现她身上集中了我所认识的所有其他人的品德,在其他人身上哪怕发现这些品德中的一个,我就高兴得不得了了。
在她身上,完全看不到各种迷信的束缚(包括那些把假想的完美归于自然和宇宙秩序的迷信),她对社会结构中许多不合理的东西提出最热烈的抗议,这并不是出于生硬的理智,而是出自与她那可敬的天性共存的崇高感情的力量。在一般的精神特征以及气质和条理方面,我常把当时的她比作雪莱;但在思想和智性方面,雪莱在其短暂的一生中所发展的能力,与她最终成就的高度相比,不过是个孩子。无论是最高境界的思考,还是小到日常生活中最细微的实际问题,她的心灵都是最完美的工具,直指事物的核心和实质;也总是能够抓住本质的理念或原则。
一如她的敏感和心灵官能所在在表现出来的,运用上同样的精准和迅捷,加上她的感情和想象力的天赋,足以使她成为一个完美的艺术家;正如她那炽热而温柔的灵魂和有力的口才,也足以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演说家;她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和对实际生活的洞察力和远见卓识,还会使她成为人类统治者中的佼佼者,假使时代允许这种职业对妇女敞开的话。
她的智力天资辅助着我毕生所仅见的最高尚最平衡的德性。她的无私,不是出于一套被教导的义务,而是出于一颗完全把他人的感受当作自己的感受的心,富于想象地投注自己强烈的感情于其间,以至于常常过度地为他人着想。除了她那随时准备倾注到别人身上而不求哪怕最微小回报的无限慷慨和爱心,对正义的激情可以说是她最强烈的情感。
她的其他道德特征也自然而然地与这些思想和心灵品质相伴而生:她既有最真挚的谦逊之心,又有最高尚的自豪;她把绝对的坦率和真诚给予所有适合接受它们的人;她对任何卑鄙和怯懦的行为报以最大的蔑视,对一切野蛮和暴虐、不忠和无耻的行为和性格表示最强烈的愤慨;同时,对“本质上的恶行”(mala in se)和“违犯法律的恶行”(mala prohibita)给予最明确的区分,即把从情感和品格上表现出来的固有之恶,与那些只是违犯或好或坏习俗的行为区别开来,后面这种违规行为不论对错如何,是那些在其他方面可敬可爱的人们也难免会犯的。
与这样一位集众多美质于一身的人进行任何程度的精神交流,都会对我的发展产生极为有益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只是渐进的,许多年后,她的思想进步和我的思想进步终于达到了完全和谐的伴侣关系。
我所得到的益处远远超过我所能给予的;虽然对她来说,她最初都是通过强烈情感的道德直觉得出自己的见解的,但毫无疑问,她也能从一个以研究和推理得出许多相同结果的人那里,得到帮助和鼓励。在她智识迅速增长的过程中,她那把一切都转化为知识的精神活动,无疑也像从其他来源一样,从我这里汲取了许多材料。就算仅仅从思想上来说,我要归功于她的地方,要说起来也是无穷无尽的;关于这种影响的总体特征,短短几句叙说即可见其一斑。
一如所有的圣明之士,那些对人类生活现状感到不满,并完全赞同对其进行根本变革的人,他们的思想主要有两个领域。一个是终极目标的领域,也就是人类生活可实现的最高理想的那些构成要素。另一个是直接有用并现实可行的那个领域。
在这两个领域,我从她的教导中获得的东西,比从所有其他来源获得的加起来还要多。老实说,真正的确定性主要存在于这两个端点。我自己的长处则主要在于那个充满不确定和不稳定的中间地带,即理论学说领域,或者不如说是道德与政治科学领域。在这个中间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学、分析心理学、逻辑学、历史哲学以及其他学科,不管我以任何形式认可或者首创了什么结论,都得益于从她那里获得的明智的怀疑主义(这当然并不是我非要向她负责不可的智识义务)。
这种有益的怀疑态度不但并未妨碍我诚实地发挥我的思维能力来得出任何可能的结论,而且让我保持警惕,避免以思辨性质所不能保证的自信程度来主张或宣布这些结论;还让我的头脑不仅随时准备承认,而且急于欢迎和热切寻求任何有可能出现在前方的更清晰的认识和更好的证据,即使在那些我已经深思熟虑的问题上也是如此。
我经常受到赞誉,因为与大多数同样沉迷于大而化之的思想家的著作相比,我的著作被认为具有更强的实用性,但是这种称赞我只配部分受用;如果我的著作被发现具有这种品质,那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而是两个头脑的融合,其中一个对当下事物的判断和认知有着非凡的务实感,而又对遥远未来的展望有着高瞻远瞩的胆识。
………………
[……]我在1851年4月与那位女士结婚,她身上有着无与伦比的价值,她的友谊成为我幸福和进步的最大源泉,多年来我们从未奢望彼此有任何更亲密的关系。在我有生之年的任何时候,我自然都是热切盼望跟她的生命完全结合,但我跟她一样,宁愿永远没有这个福分,也不愿以一个我最尊敬的朋友、她最敬爱的丈夫的英年早逝换来这种特殊的幸运。但是不幸的事情还是在1849年7月发生了,出于这一不幸事件的赠与,我获得了自己最大的幸福:在我们长久以来就存在的思想、感情和写作的伙伴关系之上,又加添了整个人生伴侣这一层关系。
在七年半的时间里,我享受了这种福分;但是只有七年半!呜呼,我无法用任何言语来表达,我在那时和现在失去了什么!但是,我知道她会希望我怎样,所以我竭尽可能地利用我的残生,以她的思想所余的力量,渴饮着对她的怀念,为她未竟的目标而继续努力。
………………
在我结束公职生活之前的两年里,我和妻子一直在为《论自由》的写作而通力协作。我最初计划写这个题目是在1854年,那时只草成一篇短文。1855 年 1 月,在我登上罗马朱庇特神殿的台阶时,我第一次萌生了将它改写成书的想法。
我所有的著作没有哪一部像这本书一样经过如此仔细的组织和精心的修改。像往常一样写了两遍之后,我们把它带在身边,不时拿出来重新检查,一读再读,字斟句酌。最终的定稿本该在 1858/59 年那个冬天完成,这是我退休后的第一个冬天,我们计划在南欧度过。然而,这个希望连带其他所有的希望,都因一个谁也未曾料到的最痛苦的灾难而落空了——那是在阿维尼翁,就在我们前往蒙彼利埃的途中,她因突发肺部充血而去世。
从那以后,只要我的精神状态允许,我就会想象她仍然在我身边,希求以这种方式减轻我的痛苦。我在离她墓地尽可能近的地方买了一间小屋,她的女儿(我的同命相怜者,也是我现在最大的安慰)和我,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那里。我的生活目标,完完全全就是她从前的那些目标;我的追求和事业,要么是我们从前共同的、要么是她会赞同的、要么是与她密不可分的那些追求和事业。对她的怀念就是我的宗教信仰,她的赞许是衡量所有价值的标准,是我调整自己生活的指南。
(在结束前面的叙述而搁笔多年之后,我重拾笔墨,主要是受一种愿望的驱使,即不想留下一个不完整的记录,为了这篇传记的完整性,我有义务记录下那些对我的精神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或者对我的著述和其他我所做的公共性质的事务有过直接参与的人。在前面的篇幅中,就与我妻子有关的内容而言,也是有欠详细和准确的;自从我失去她之后,我又得到了其他人的帮助,这些同样值得并需要感谢。)
两个人合作的作品,有时由谁来执笔对原创性来说并没那么重要,只要是:两个人的思考和推理完全一致;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讨论所有智识或道德方面的话题时,探讨的深度也要远远超过面向普通读者写作时惯常的变通;他们是从相同的原则出发,通过共同推究的过程得出结论;甚至,对执笔贡献最小的那个人可能对思想的贡献更大;这样产生的著作是两个人的共同产物,往往不可能把他们各自的部分分开,并确认这部分属于这个人,那部分属于另一个人。
从这个广泛的意义上说,不仅在我们婚后的几年里,而且在我们之前多年的亲密友谊中,我所有发表的东西,都既是她的作品也是我的作品;随着岁月的推移,她在其中所占的分量不断增加。不过在特定情况下,属于她所贡献的东西是可以区分出来并且明白无误确定的。
且不说她的思想对我的思想的那种普遍影响,这些合作著述中最有价值的想法和特征,即那些最富有成效的重要成果,对作品本身的成功和声誉做出了最大贡献的东西,都源出于她;我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并不比我对前人思想的借鉴更大,我只是将这种借鉴纳入我自己的思想体系而造成我自己的思想。
在我文字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之于她的职责,都是原创思想家的解释者,或者思想家与大众之间的中间人的角色——从很早的时候起,我就认为这是我有资格在思想领域扮演的最有用的角色;因为除了在抽象科学方面(逻辑学、形而上学以及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理论原则),我对自己作为原创思想家的能力一直心存忐忑,但在向其他人学习的意愿和能力方面,我认为自己比同时代的大多数人都强得多;因为我发现,对于任何意见,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没有一个人会特别重视考察为这些意见所做的辩护,而我深信,即便这些意见是错误的,在它们的底下也可能蕴藏着真理的基石;我还深信,无论如何,察明究竟是什么让这些意见站得住脚,都会对真理有所裨益。
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有用的领域,我有特别的义务在其中发挥作用:尤其是在我接触了柯勒律治、德国思想家和卡莱尔的思想后,更觉得有必要这样做,它们与我从小接受的思想模式截然相反,这使我确信,除了诸多谬误,它们之中一定还含有许多真理;他们习惯于用先验和神秘的措辞把真理封闭起来,既不关心也不知道如何把真理从这些措辞中剥离出来,从而掩盖了这些本可为人所理解的真理;我自信可以将真理与谬误区分开来,并用哲学中与我站在同一阵线的人能够理解而不反感的语言表达出来。
有了这种铺垫,因此也就不难相信,当我与一个具有最杰出才华的人进行密切的思想交流时,她的天才随着思想的成长和发展,不断提出比我先进得多的真理,但是不像我在其他人那里那样,我在她的天才中察觉不到混有任何谬误,那么我的思想的最大成长就在于吸收这些真理,而我的智识工作的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搭建桥梁,扫清道路,把这些真理与我总的思想体系连接起来。
《论自由》比任何署了我的名字的出版物都更直接、更真实地是属于我们的共同作品,因为其中的每一句话都经过我们一起反复斟酌、反复推敲、仔细剔除我们发现的任何思想或表达上的瑕疵。正因为如此,虽然这本书没有经过她的最后修改,但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创作样本,它远远超过了我之前或之后的任何作品。至于文章的思想,很难说哪一个特定部分或哪一个元素比其他部分或元素更属于她。这本书所表达的整个思考方式显然都是她的。但我也完全浸淫在这种思考方式之下,所以我们俩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相同的想法。
不过,我之所以能够在这个主题上如此透彻,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她。在我的精神成长过程中,曾有一段时间我很容易陷入过度治理的倾向,包括在社会和政治两方面都是;也曾有一段时间,由于相反的过度反应,我可能会成为一个激进派和民主派,尽管未必那么彻底。在这两点上,就像在许多其他方面一样,她都使我受益匪浅,既让我坚持站在正确的位置上,又引导我认识新的真理,使我摆脱错误。
我非常愿意并渴望向每个人学习,并在我的意见中为每一项新知留出余地,让新旧相互调整,如果不是她的稳健影响,我可能会被诱使过多地修改我早期的见解。她对我的精神发展最有价值的地方,莫过于对诸多不同考量因素之间相对重要性的公正权衡,这常常使我免于冒失,不至于让我新近才学会的真理在我的思想中占据超过它们应有的更重要的位置。
《论自由》可能会比我写过的任何其他作品(或许要除了《逻辑体系》)传世更久,因为她的思想与我的思想的完美结合,使它成为一本阐明一条独一无二的真理的哲学教科书,而现代社会逐渐发生的变化往往会使这一真理更加凸显:性格类型的多样化,以及给予人性充分的自由,使其向无数相互冲突的方向发展,对人和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在一个肤浅的观察看来似乎并不太需要这样一课的时代,对这一真理的阐述无疑会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没有什么比这种触动更能说明这一真理的基础是多么深厚了。
我们所表达的担心,即社会平等和舆论一律的必然发展,会给人类的意见和实践强加一个统一的压迫性枷锁,对于那些更多关注当前事实而非未来趋势的人来说,这种担心很容易被当成是无稽之谈;因为到目前为止,社会和制度中正在发生的渐进式革命明显有利于新见解的发展,并让它们获得了比以前更多不带偏见的倾听。但这是过渡时期的特点,因为在这个时期,旧的观念和情感已经动摇,而新的成说还没有赢得上风。在这种时候,思想活跃的人已经放弃了他们旧信仰中的很多东西,但还不十分确定他们仍然保留的那些东西是否能够屹立而不被修改,因而会热切地倾听新的意见。
但是,这种状态必然是暂时的:某个特定的学说经过一段时间团结起了大多数,建立起与其相一致的社会制度和行为模式,教育会把这个新的信条灌输给新的一代人,免去他们经历产生这种信条的精神过程,渐渐地,这种信条就获得了一种压迫性力量,一如它所取代的信条所长期发挥的。这种有害的权力是否能够施行,取决于人类届时是否已经意识到,要想让这种权力失灵,只有人的本性不被扼杀和压制才行。到那时,《论自由》的教诲才会具有最大的价值。令人忧心的是,它将长期保持这种价值。
至于原创性,它当然不外乎如是——每个有思想的头脑都会用自己的方式来构思和表达真理,而真理属于人类的共同财产。本书的主要思想,虽然在许多时代只限于孤立的思想家所持有,但自文明开始以还,人类可能从来没有缺乏过这种思想。仅就最近几代人而言,它明显地包含在欧洲思想界有关教育和文化的重要思想脉络中,这一思想脉络的传开得益于裴斯泰洛齐的天才和努力。书中提到了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对这一思想的无条件支持,但他在自己的国家绝非孤军奋战。
在本世纪初(译按:指作者生活的19世纪),关于个性权利的学说,关于道德本性以自己的方式发展的主张,被整个德国作家流派推崇到了夸张的地步,最著名的德国作家歌德,虽然不属于这个流派(也不属于任何其他流派),但他的著作中处处渗透着道德和生活行为的观点,在我看来,这些观点常常是站不住脚的,但它们不断地在自我发展的权利和义务的理论中,寻找它们所能找到的任何辩护。
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在《论自由》一书写成之前,威廉·麦克考尔(William Maccall)先生就在一系列著作中热情洋溢地宣扬了“个人主义”学说,他铿锵有力的风格有时让人想起费希特(Fichte),其中最出彩的一篇题为《个人主义的要素》(Elements of Individualism)。
还有一位杰出的美国人,沃伦(Warren)先生,他以“个人主权”为基础构建了一套社会制度,获得了许多追随者,而且实际上已经开始组建一个乡村社区(它现在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尽管它与社会主义者的某些计划表面上很相似,但在原则上与它们截然相反,因为它不承认社会对个人有任何权威,除了强制所有个性都有平等的发展自由。
这本署上我名字的书,对里面所宣扬的任何教条都不主张原创权,也不打算书写它们的历史,在我之前主张这些信条的著作家,唯一一位应该提出来说一下的是洪堡,这本书卷首的题词就出自洪堡;尽管我在一段话中借用了沃伦派的说法,即“个人主权”。
这里几乎没有必要指出,我所提到的任何一位前辈著作家对这一学说的构想,与本书所阐述的构想在细节上存在着巨大差异。
在我无可挽回地痛失她之后,我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印刷和出版这篇论文,这里面太多是她的心血,让我把它作为记念,献给她的在天之灵。我没有对这篇论文再做任何修改或增补,永远也不会。这本书尚缺她来过最后一遍手,但是我永远不会尝试用我自己之手来代替她。
陳雨汝, 廖建華 | 春日警鈴 봄알람 baume à l'âme
編者按:本文選自《陳雨汝, 廖建華 | 做書的人:探訪十家韓國獨立出版社快樂的生存之道》一書。 EP1〈女男、媽爸、婦夫〉 春日警鈴 봄알람 baume à l'âme | 李讀盧 이두루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七日凌晨一點,二十三歲的河姓女子在首爾地鐵新論峴站和江南站之間的公用廁所遭到殺害,凶器是三十公分的長刀,凶手是在鄰近餐廳工作的金姓男子。男子犯案前在廁所外的樓梯間徘徊了一小時左右,接著進入廁所埋伏等待下手時機,從監視器畫面可看到,當時進入廁所的其他男性全都平安離開。 數日後在哀悼受害者的集會中發生了衝突,進而引爆韓國社會的女男對立。這樣的對立,源自應將這起事件定調為「厭女犯罪」還是「隨機殺人」。前者的根據來自罪犯側寫師所描述的金男,是對女性有敵意的;後者則主張這與性別無關,不要把男性視為潛在罪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