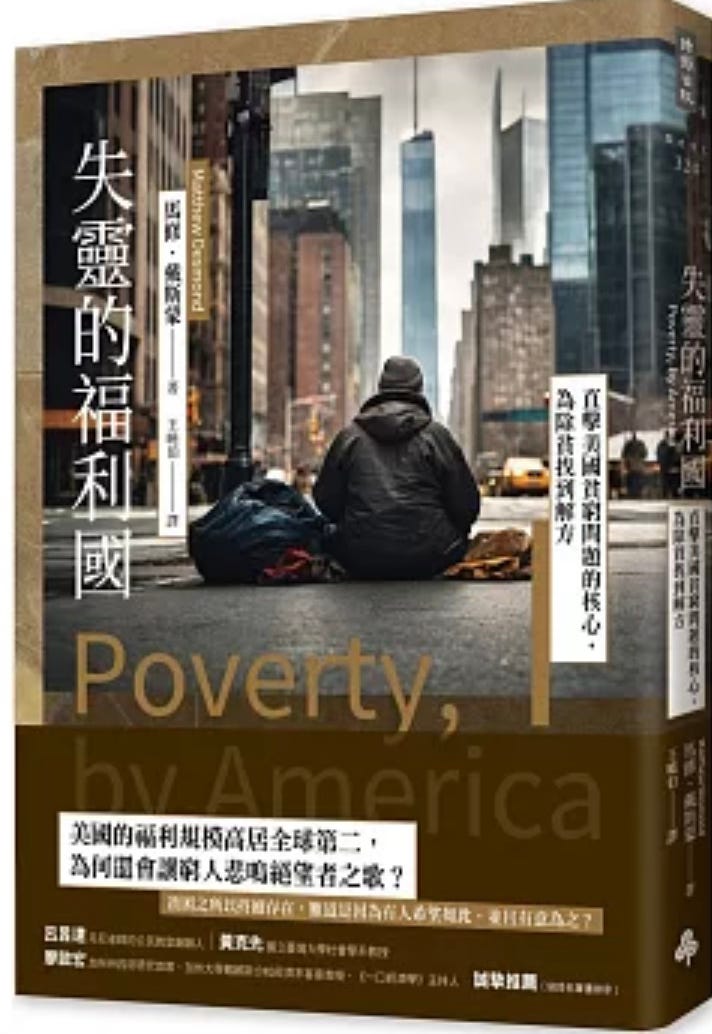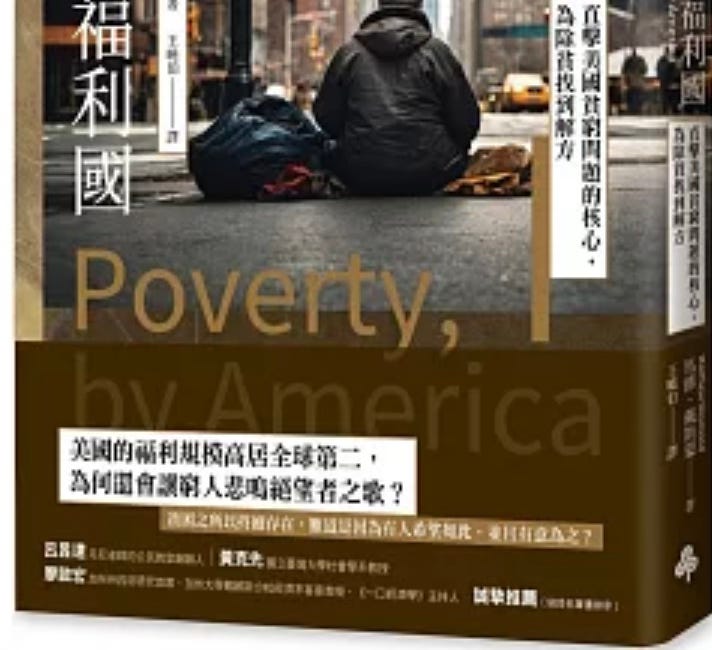馬修•戴斯蒙 | 我們對政府福利的依賴
我們的國家並不是分成透過工作自給自足的「製造者」,與靠著政府救濟、精打細算過日子的「接受者」。其實,美國所有的民眾都受惠於某種形式的公共救濟,不論是共和黨與民主黨、白人、西班牙語裔與黑人家庭皆然。我們都是靠著救濟過日。
政治學家蘇珊.麥特勒(Suzanne Mettler)在其著作《政府與公民間的斷聯》(The Government-Citizen Disconnect)中指出,百分之九十六的美國成年人一生之中總會有某一段時間是依賴一項重大的政府福利計畫。富人、中產階級與貧窮家庭依賴的福利計畫互有不同,但是平均上富人與中產階級家庭享有的政府福利數量與貧窮家庭相差無幾。學生貸款看來是由銀行經手,但是銀行願意把錢交給一位十八歲、無業、沒有信用,也沒有抵押品的年輕人的唯一原因,就是因為有政府擔保貸款,並且為他們負擔一半的利息。恆達理財(Edward Jones)與保誠(Prudential)的財務顧問會幫你規劃五二九大學儲蓄計畫,但是這些計畫慷慨大度的稅賦優惠估計會導致美國政府在二○一七到二○二六年間損失二百八十五億美元。對於美國年齡在六十五歲以下的民眾來說,健康保險是依附於他們的工作,但是支持這項措施的卻是聯邦政府力度最大的單一減稅優惠之一,這是從應稅所得中免除僱主贊助的健康保險成本。二○二○年,這項福利估計讓聯邦政府為六十五歲以下成年人損失三千一百六十億美元。到了二○三二年,估計損失金額會超過六千億美元。美國民眾幾乎有一半都透過他們的僱主接受政府補貼的保健福利,有超過三分之一都享有政府補貼的退休福利。這些主要由富人與中產階級所帶動的參與率,遠超過如食物兌換券(百分之十四的美國民眾)與勞動所得稅收抵免(百分之十九)等直接針對低所得家庭提供的單一最大規模福利措施。
加總起來,美國二○二一年在稅賦優惠上的支出達一兆八千億美元。此一數字超過在執法、教育、住屋、健保、外交與其他所有構成我們任由政府支配的預算總合。然而在十三項力度最大的個人稅賦優惠中,大約有一半都是集中在富人家庭身上,也就是那些所得在最高百分之二十層級的人。所得在最高百分之一層級的人所享受的優惠比所有中產階級的還要多,更是所得在最低百分之二十層級家庭的兩倍。我不知道有多少次聽過某人對我說,我們應該減少軍事支出,轉而增加對窮人的補助。每當這樣的建議出現在公共論壇上,總會引來一陣掌聲。然而我卻很少遇見有人建議我們,鑑於我們在主要提供給上層階級的稅賦優惠支出已是國防與軍事支出的兩倍,我們應減少對上層階級的稅賦優惠,增加對窮人的救濟。
今天,聯邦政府福利的最大受益人是富裕家庭。要享受僱主贊助的健康保險,你必須要有一個好工作,通常還需要大學文憑。要享受房屋抵押貸款利息抵減,你首先需要買得起房子,你能負擔的抵押貸款越大,你能享受到的稅賦扣減也就越大。要擁有一項五二九計畫,你首先需要能夠為你子女的大學費用存一筆錢,你存得越多,你的稅賦優惠就越大,這就是這項補貼為什麼幾乎專屬有錢人的原因。就我所知,沒有博士論文、研究計畫,或是編列專款來討論如何提高美國民眾對房貸利息率,因為這類福利的使用率已相當高了。
但是有人也許會說:有錢人繳的稅也多。是的、沒錯―—這是因為他們的錢比較多啊。但是這和誰的稅賦較重是兩回事。聯邦所得稅是累進制,意味稅賦會隨著所得增加而加重―—在二○二○年,窮人(所得在九千八百七十五美元以下)的稅率是百分之十;中等收入(所得在八萬五千五百二十六到十六萬三千三百美元之間)的個人所得稅率是百分之二十四;富人(所得在五十一萬八千四百零一美元以上)的所得稅率則是百分之三十七―—但是其他的稅賦卻是累退制,使得窮人的稅賦占其所得的比重相對較高。以銷售稅為例,是對窮人傷害最大的,這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貧窮家庭無法存錢,但是富裕家庭可以。相較於每年只支出一部分所得的家庭,每年花光所有錢的家庭,等於自動升高銷售稅占其所得的比重。第二,當富裕家庭支出時,他們在服務上的消費要高於貧窮家庭,貧窮家庭的錢多是花在商品(汽油、食物)上,這些都是銷售稅的大宗。聯邦政府所得稅的累進制設計效果其實已被其他稅賦的累退制所抵銷,包括有些財富所課的稅(資本利得稅)甚至還低於薪資。在計算所有的稅賦後,我們會發現其實我們的稅率都差不多。平均而言,美國窮人與中產階級的稅賦約占其所得的百分之二十五,富人是百分之二十八,僅是略高而已。至於全美最富有的四百人,則是百分之二十三,是所有人最低的。
美國政府是對最不需要補助的人給予最多的補助。這就是我們福利國的本質,而其影響深遠,不僅關係到我們的銀行與貧窮水準,同時也左右了我們的心理與公民精神。
研究顯示接受勞動所得稅抵免優惠的美國民眾,相對於類似背景但是沒有申請此一福利的同胞,反而比較不認為自己是政府福利的受益人。但是接受現金福利的人則是傾向視自己為政府救濟的受益人。同樣地,依賴學生貸款或五二九計畫的人,相對於同樣背景但是並未依賴這些福利的人,反而不會承認政府在其生活中所發揮的功能。不過受益於美國軍人權利法案(GI Bill)的美國民眾則是相當清楚自己因為政府的作為而擁有新的機會。總體而言,主要依賴看得見的社會福利(如公共住宅與食物兌換券)的美國民眾,最有可能認可政府是改善他們生活的力量,但是依賴隱形福利(例如減稅等稅賦優惠)的人就比較不會承認政府對他的幫助。
因政府慷慨大度而受益最多的人―—通常是有成員為會計師的白人家庭—―反而具有最強烈的反政府情緒。這些人的投票率要高於那些感激政府幫助其改善生活的同胞。他們支持承諾要削減政府支出的政治人物,他們心知肚明自己所享有的福利不會遭到刪減。這完全是屬於壓倒性的局面,享有房貸抵押利息抵免優惠的選民反而也是最強烈反對政府投資平價住宅的一群人。同樣地,接受僱主贊助健康保險福利的人,反而都支持廢除《平價醫療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這是美國政治生活中最為弔詭的悖論之一。
但是每隔一段時間,不合理傾向美國非貧人口的福利政策都會搬上砧板。到了這時,那些隱形的社會福利就突然現身了。二○一五年,歐巴馬總統提議撤除與五二九大學儲蓄計畫相關的稅賦優惠,但是美國富裕地區的民主黨立刻起來反對,他們擔心此舉會對他們的選民帶來傷害。結果歐巴馬政府在提出該議案後的第一天就宣布撤銷。民主黨領導階層了解如果聯邦政府撤除五二九計畫的稅賦優惠,或是削減房貸抵押利息減免,或是開始對僱主贊助健康保險課稅,中產與上層階級家庭一定會暴跳如雷,由此顯示,這些福利其實也並非真是隱形的。
我們應該如何處理這樣的情況?我們應該如何調整中產與上層階級對他們享有的政府賦稅優惠視而不見的情況,因為此一現象會在這些家庭中散播不滿,對政府救濟窮人不以為然,進而導致富有選民反對政府對窮人的支出,同時大力保護他們當初視而未見的稅賦優惠?
就我來看,這樣的情況之所以形成,有三種可能性。第一個是我們有許多人都曾經歷過一段苦日子,而把減稅視為類似政府支票的福利。我們視繳稅為負擔,減稅則是政府允許我們增加保留原本就該屬於我們的財產。心理學家證明相對於得到,我們對於損失更為敏感。損失一千美元所感受到的痛苦明顯要比贏得一千美元的喜悅感強烈。稅賦也是一樣。我們對於要繳多少稅的感受(損失)要比減稅(獲得)深刻得多。
這其實是經過設計的,是美國有意讓報稅成為煩人與耗時的工作。在日本、英國、愛沙尼亞、荷蘭,還有其他一些國家,人民不需報稅,政府會自動幫他們處理。在這些國家,納稅義務人只需檢查政府的算術,在表格上簽名,然後寄還政府就行了。整個過程只需要幾分鐘而已,而且最重要的是可以確保人民繳納該繳的稅與收到他們應得的稅賦優惠。如果日本或是荷蘭人民認為政府超收了,他們可以提出申訴,不過他們大部分都不會這麼做。事實上,沒有理由認為美國政府不能以這樣的方式課稅,除了企業說客與一堆共和黨議員希望有一個令人痛苦萬分的報稅過程。「稅賦應該令人痛苦。」這是雷根總統的名言。如果他們不是如此堅持,我們也許就會有一套簡單直接的報稅程序,而不是把政府每年取走我們錢財的報稅季視為最討厭的時刻。
這是包裝與禮物同等重要的問題,而我堅信社會福利提供的方式與課稅的方式會影響我們對它們的觀感。要讓繳稅不致令人感到痛苦,而且感覺稅賦優惠基本上與政府救濟有所不同,其實不難,不過需要一些魔術性思維。社福支票與稅賦優惠都能增加家庭的所得、都會增加政府的財政赤字,都是設計來鼓勵一些行為,例如就醫(醫療補助)或是儲存大學學費(五二九計畫)。我們可以更動提供系統來達到相同的目的,例如藉由削減低所得勞工的工資稅來擴大對窮人的福利(例如法國),同時以每月寄出支票給屋主來取代房貸抵押利息的抵減。聯邦預算就是一個巨大無比的金錢圈,資金在其中不停迴轉,由納稅義務人轉至國庫,再由國庫轉至納稅義務人手中。你可以靠著減稅或是增加福利來幫助一個家庭,其實都是一樣的。
在聯邦所得稅方面,有些人認為是中產階級的納稅義務人在照顧窮人。但是讓我們來看看相關數據。二○一八年,中產階級家庭平均所得是六萬三千九百美元,在經過所有的抵減之後平均納稅九千九百美元,同時接受一萬三千六百美元的社會保險福利(例如失能與失業補助),再加上三千四百美元的經濟狀況調查後福利(如醫療補助與食物兌換券)。換句話說,中產階級家庭平均每戶獲得的政府補助,要比其所繳納的聯邦稅要多出七千一百美元,這樣的投資報酬相當不錯。因此,宣稱美國中產階級以繳稅來補貼窮人,而且沒有任何回報的說法是不對的。
但是更根本的問題是如果只看聯邦所得稅,無異於你只有在早餐時記錄你吃下的卡路里。當評論人士由於窮人的稅賦在標準扣除額與稅收抵免之後接近於零,因而完全聚焦於所得稅而將窮人歸類於「免稅階級」時,他們其實是有意忽略窮人所繳納的其他稅賦與富人無須繳納的稅賦。底線就在這裡:根據最近有關社會保險、經濟狀況調查後福利、稅賦優惠、對高等教育財務補助等方面的支出調查,在所得分配最低百分之二十層級的家庭平均每戶每年可以自政府手中獲得約二萬五千七百三十三美元的福利補助,然而在最高百分之二十層級的家庭平均每戶每年可以得到三萬五千三百六十三美元的政府福利。由此顯示每年美國最有錢的家庭得自政府的補貼竟然比最窮的家庭還多出近百分之四十。
有鑑於此,我覺得其中一定還有更深層的因素在作祟,我們不願承認美國是隱形福利國的另一個原因:是美國中產與上層階級―—不是美國窮人―—相信他們有資格接受政府幫助。這是自由派人士長期以來的觀念:美國深信菁英體制,因而將物質上的成功與應得的權利併為一談。我不予苟同。我們其實已看到太多相反的例子。我們真的認為在所得分配最高百分之一的層級比全國其他人更值得擁有一切嗎?我們真的還要在二○二三年爭論美國白人比黑人富有是因為白人工作比較勤奮嗎―—或者婦女只因為是女性就應該拿少一些?我們難道還敢宣稱清潔人員因為頻繁接觸化學品而導致脫皮,或是莓果採收工人無法直立久站,或者數以百萬計的美國窮人表示自己走投無路,都是因為他們懶惰嗎?「我吃了不少苦才有今天的地位」,你或許會這樣說。好吧,沒錯。但是窮人又何嘗沒有吃苦。
即使是在我們的私人生活,我們也常常看到某人飛黃騰達並非因為他的進取心與奮發圖強,而是因為他長得比較高、較具有魅力,或是認識某位高層或是繼承了大筆財產。我們也經常看到一位能幹的同事無法得到升遷,然而一位表現平平的人卻是搬進角落的主管辨公室。一個家庭可能會因為一項重大的醫療診斷或是交通意外而一蹶不振。我們一生中會遭受各種衝擊―—不僅僅是我們無法控制的,還有許多無情且毫無道理可言的打擊。我們每天都要面對生活中的反覆無常,我們的未來是由背景與機會這種不公平且愚蠢的因素所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