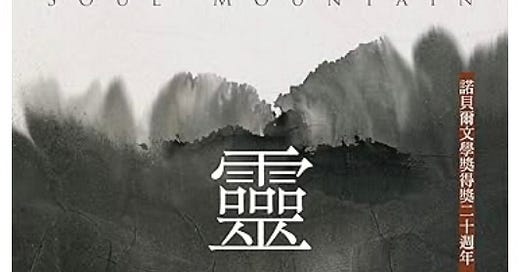我爱《灵山》是爱它形式的美,然而形式无论怎样的美,都激不起刻骨铭心的爱。这倒不是认为《灵山》作为小说怎样怎样地存在着不足,应当有更好的写法或思想,而是说,仅对于形式本身的追求是所有现代作家的通病,换用一个更为中性的词:“现代性的烙印”。
比如说,灵山的这个书写形式就很吸引我:它在奇数章节里都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讲述“我”在被误诊肺癌,虚惊一场之后,独自游历中国西南部的故事;而在偶数篇里以第二人称“你”的视角,讲述“你”寻找传说中的灵山的故事。这种构思方法,首先让我想到村上春树《海边的卡夫卡》里那种双线结构,其次让我想到了昆德拉的“实验性人格”,在高行健的作品里,人物本身不但是实验性的和虚拟的,而且也失去了他们的姓名和身世,成为了一个简简单单的人称:“你”、“我”、“他”。这就像毕加索画牛一样,画布上完整的一头牛,脱落了牛皮、牛肉、牛腱,眼睛、内脏、筋骨,变成了几何的线条。高行健告诉我们,将性格、姓名、面容、身世从一个人身上抹除,最后剩下的,是人类掌握语言之初,咿咿呀呀指指点点借以指代的人称。
“你”。“我”。“他”。三个指代,于是我们的时间就开始了。这个时间是白话文的时间,是象形文字的时间,更是普遍的人类的时间。“我是自我的苏醒,是亚当的苹果,金字塔,尼罗河的河水和人们对初升的太阳神的朝拜,这个“我”是惠特曼《自我之歌》中的那个我,是草尖的露水日日破裂而日日复生,是兰波的诗,爱伦坡的诗,拜伦的诗,人类王子的诗。当我们谈到《诗经》、《荷马史诗》的时候,人们说:“是我们创造了它!”而当我们谈到《离骚》、《神曲》、《浮士德》的时候,作家们呐喊的则是“是我创造了它!”第一人称就是从“我们”向“我”的过渡,是群体的盲目中忽然迸发出来的自我意识。而“她”则是远方的世界,池塘里睡莲的盛开,是砂砾、群山、万籁俱寂的星空,千万年反复升起于东山之上的月亮,是一种远观的状态。如果说“我”是诗人对身世的快乐和忧伤,是他们的直抒胸臆,那“她”毋宁说是冷静的小说家的笔调,理性、沉默、细致,充满了知性的观察。
相比之下,第二人称的“你”更接近一种折衷,一种第一人称“我”与第三人称“她”的折衷。一个谈天的对手,一个倾诉的对象。在《灵山》第五十二回中,作家揭示了这种“你”、“我”、“她”的关系:
在这漫长的独白中,你是我讲述的对象,一个倾听我的我自己,你不过是我的影子
当我倾听我自己你的时候,我让你造出了个“她”,因为你同我一样,也忍受不了寂寞,也要寻找一个谈话的对手。
你于是诉诸她,恰如我之诉诸你。
她派生于你,又反过来确认我自己。
第二人称的“你”,处于这样一个过渡的状态:它在主观和客观之间,在诗歌和小说之间。当作者的自我意识觉醒的时候,他发现书中的主人公是自我的写照,“你”的称呼变成了一种自言自语,一种梦呓或一种谵语,“你”变成了我假想的倾听者和讲述者,变成了我对舞蹈、火焰和自身的迷恋;反过来,当作者忽然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无意识的倾诉和暴露出来的软弱,带着强烈的自尊和羞愧,他用力将这个假想的“你”推向远方,保持足够的距离。尼采说:“美是一种远观的状态”,作为一个行吟诗人,一个说书人,一个小说家,他需要客观而平等地述说“你”的故事……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妨肯定,高行健的作品已经是极具现代性的了,我们也反过来说,现代性的人称是第二人称,是记录“你”以及对“你”的倾诉。这不是要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作家那里寻找高行健的师承来,恰恰相反,是在现代性这个词里找寻出文学脉络来。
高行健的《灵山》,代表了一个白话文的女性化进程,而这似乎预示着,白话文作为一种文体,终于摆脱了它的童年,一个由徐志摩、鲁迅、张爱玲、郁达夫、周作人、沈从文他们支撑起来的童年。童年是孤独的,是淡蓝色和桃色的,但是童年也是不区别性别的。在海子的诗和高行健的《灵山》里我看到了两种不同的倾向,在海子是对父性的迷恋,对太阳、星辰、土地的迷恋,而《灵山》是一个追寻女性的思考和生活方式的尝试。千万不要忘记“灵”这个字里的阴性意味;不要忘记在荷马和诗经的时代,天才型的诗歌王子尚未诞生,创作和表达由群体的智慧和群体的体验完成;也不要忘记最初的创作是火焰中的舞蹈,是节奏,是跳动的步伐,是巫女和预言家创作出来的,而《灵山》的“灵”这个字,就是要回到这种创作模式。
从这个意义上说,高行健文学上的师承与其说是沈从文,不如说是马尔克斯、米兰昆德拉他们,向更远处追溯,是伟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小说《群魔》种所采用的那种记述方式:小说家一开始以第三人称的视角讲述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寄居人下的生活和性格,而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小说家无意识地滑向以加尔嘉宁的第一人称的叙述,并且在长篇小说的进行中,分裂成了两个不同的记叙者,一个自称为“我”,一个自称为“他”。
归根结底,陀思妥耶夫斯基渴望一种全新的表达结构,这种表达不但自称为“我”,也自称为“他”;不但沉迷在书中角色的精神分裂和哲学思考中,设身处地地替他们思想,同时也满足于对角色本身的冷静观察。于是第二人称的“你”就这样诞生了,这次诞生,是一个痛苦的、目眩神迷的、伟大的过程。它是有预谋的。我相信,在很久很久之前,我们的先人们就梦见过它,就熟悉它的面容。于是我们给与它生命。先是在陀氏,在尼采,《尤利西斯》梦呓般的语言是对假想的“你”的自言自语,卡夫卡小说中主人公始终觉得没有任何私密的空间,是因为第二人称的“你”始终存在。“你”存在于现代性的朝霞之中,现代性的诞生好比就是那次预谋已久、等待已久的日出,那时一个怎样的诞生呢?海子概括说:
这是夏娃涌出亚当,跃出亚当的瞬间(人或是亚当的再次沉睡和疼痛?)卢梭是夏娃最早的喘呼之声……她的自恋与诉说……自然的母体在周围轰响,伸展的立方主义,抽象表现,超现实主义……
“夏娃涌出亚当”,这是第二个人的出现,第二个人称的出现以及“你”的出现。这个“你”当然不仅仅是亚当眼中的夏娃,也可以是夏娃眼中的亚当,是“我”眼中的“你”,以及“你”眼中的“我”。当然,我们再也无法再看见那次诞生,但是我们梦见它。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二人称的诞生在很早很早之前就完成了,就像现代性一样,它诞生于一个不可预知的时间,然而这不是说高行健在《灵山》中的努力就没有意义了,真正的作品,不但改变我们对于未来的文学的看法,也改变我们对于过去的看法,这就是说,《灵山》也改变着我们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卡夫卡,对现代性的看法,它让我们重新审视人称与视角,男性与女性,唤醒“我”眼中的“你”,也唤醒“你”眼中的“我”。
付润石,十七岁,十五岁考入西安交通大学少年班,十六岁少年班预科直升进入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学院物理学(国家拔尖计划),十七岁转入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物理系。十一岁时参加傅国涌老师的课童实验,爱好文学数学物理学,霞关阅读论坛、《霞关》杂志创始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