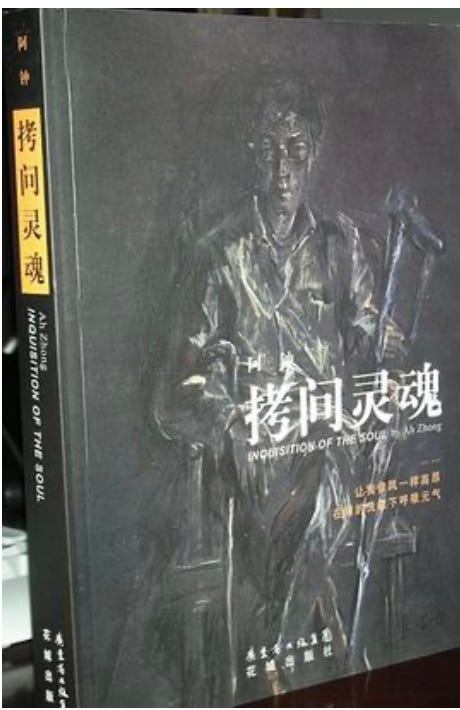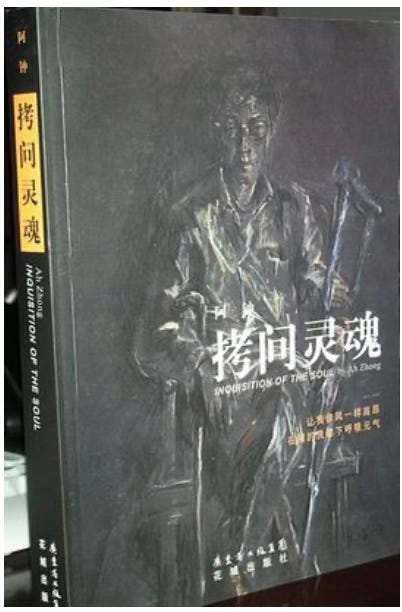阿钟 | 多余的话
編者按:“讲些多余的话,无异于是在消遣生命。如今,“生命无意义”之说突然流行了起来,于是我讲的话就更显多余。”
此诗最初以《当我面对一片灵魂的荒野》为题,刊登在由艺术家苟红冰创办的艺术文学民刊《文化与道德》第二期上。2000年第7期《诗生活月刊》也刊登了此诗,当时一个名叫高草的编辑写下这样一句评语:
“这个作品可真不象它的题目那般老气横秋。我特别推荐,一篇狂乱的乐章。”
那时马骅在《诗生活网》当编辑,但我却没问过他高草是谁。
后来我曾一度把诗题改为《我开始在白云上安睡》,但总觉得缺乏原标题所传达的当时当刻那种氛围,所以经历多年之后,尽管《我开始在白云上安睡》这个题目已广为人知(尤其是在被收入默默的《撒娇》之后),还是决定改回原题。
这首诗是1995年7、8月间在北京东坝河一段生活的记录,某种意义上说起来,那段生活不堪回首,那种无助、对未来的幻灭,在一个特定时空、一个小村庄里弥漫的情绪,在此诗中得以曲折呈现。
当然,诗不是日志,不是对现实照相式定格,诗是某种情感的抽象化,诗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其实那段生活带给我的也并非完全负面,我与几个朋友的相濡以沫,并建立起深厚友谊,也只有在那个特定环境中才有可能。一种低俗情绪最终在诗中得以升华,这就是诗歌神奇的作用,并使我们获得某种程度的净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写诗确实是一种祈祷。
(2016/11/20 SanJose)
1996年6月,这组以第一人称书写的诗,我一共写了21首,其中13首被编入诗集《拷问灵魂》,这是其中的两首。这组诗,对我而言,标志着一种风格的转变,我开始用直白的语言直接抒写内心的感受。
(2020年04月25日)
这个六月诗兴索然,只是在月初的时候写了几首诗,一不留神,公号还被关了一个星期禁闭,所幸没被封号。
最近几个月,写了几十首诗,但我很少发新诗,因为一个约定,我希望完成一百首后,有一个完整的版本,甚至出一本诗集,也算是对一段无以名之的岁月的纪念。
无望的未来,却隐藏了我们无法预知的秘密,那就一步步往前走吧,秘密终将会有显露的时候。我是一个形而上战士,因为没有现实感,每迈出一步都倍感艰辛。
也许我的家园在别处。
(2020/6/26 phila)
我的整个状态都是莫名其妙的,所谓的诗也是莫名其妙的,自动组合的一些字词,它们自洽,词不需要达“意”,自己照耀自己,自己关怀自己,自己找自己取暖,在这个冷冰冰的世界上,自己碰撞出一些可见的光来。不过,我现在比较倾向于神的预设性,就是被拣选的过程,虽然我的思维还达不到这个维度,仅仅算猜想,神意组合了所有的一切。阿门!
(2020/8/22 phila)
诗是我人生的记录,它替代了我的日记,尽管我在80-90年代有写日记的习惯,但写诗替代了这个习惯,一生的思想和情感历程,可以在诗中找到线索。不过,把玩诗就够了,不必在意这这歪歪扭扭的人生。写诗让我愉悦,我没什么崇高感,我只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悲喜。
(2020/9/6 phila)
写下这几行文字,也是为了记录。事实的描述往往也是隐喻,而上帝的应许就是让我等待,我是一个贪婪的人,请上帝宽恕我。阿门!
(2020/9/22 phila)
这一年所剩时间已经不多了,但谁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上帝眷顾我,让我有所思念。
(2020/9/19 phila)
当遇到撒谎成性的人,你便会感到人的世界之荒诞。我年轻的时候交过一些恶友,这是我的业障,也是我内在恶的显现。我年轻时代的恶友,你好自为之,谁也躲避不了上帝的审判。
(2020/10/5)
我们常要承受莫名的羞辱,甚至是极限的考验,上帝的试炼不免残酷,当约伯落在撒旦手中,这个玩笑证明约伯还不够纯净,表象即是本质,而因果本来共时。主祷文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阿门!
(2020/10/8)
诗是写给世界的谜语,只有一个人会知道谜底,这个粗糙时空的有限交流,使我们最有可能接近整全的上帝。
(2020/10/12)
诗是废话、箴言或谶语,有时是与生命退化的对抗,在与世界的关系中,有时还是通往秘密未知的通道。诗是见证,是保守,是上帝暗中告诉我们要在明处说出来的话。阿门!
(2020/10/23)
美国大选进入倒计时。
旁观者总在寻找惊慌的理由,我在梦的边缘,我冷静地面对一切纷争,星辰耀眼的弧线。醒来时,大地落叶金黄。
(2020/10/27)
这两天天气转冷了,一年也就快走到末尾了,这一年最大的事就是瘟疫大流行,四年一次的美国大选也将在明天出结果,目前看,谁赢还是一个未知数。
前几天,我家小凤凰(猫咪)走了,与我们相伴将近十年。未满月就和小喜鹊(一胎的小猫)一起被从纽约抱来,到了费城,然后跟我们一路到过新泽西的巴德湖、阿肯色的拉斯维尔、加州的圣何塞,最后又从圣何塞一路穿越美洲大陆回到费城,从美国东岸到西岸,又从西岸回到东岸。小家伙从小体弱,最害怕去医院,小天使来又小天使去,如今回到天国,也是回到了本家本国。
现在小凤凰就安葬在我们的院子里,依然和我们在一起,尽管灵魂已去了天国。唯愿上帝接纳、看护与保守,阿门!
(2020/11/2)
我是1990年前后曾在上海衡山路国际礼拜堂受洗,但我对基督教的了解其实非常肤浅。圣经的启示性语言曾经深刻地吸引过我,但当时我只是把圣经视为一般的神话传说或是说教性的低级思维。
人常会不自量力自以为是,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所控制却自认为大,最终也逃不过宿命的无情制约。
我不是一个狂热的宗教痴迷者,但是上帝话语的无可置疑的律令,不是某种小心思所能揣度,除了服从没有选择。对于某些个人的理性自负,愿上帝的悲悯垂顾于彼。阿门!
(2020/11/5 phila)
我的梦是一个没有色彩的世界,人物苍白,往事的回光返照,从不怀恋却时时闪现已被遗忘在记忆深处的影子,梦是反现实的。平庸的现实在梦里获得一些戏剧性,而白日梦却从不激荡人心。
时值美国大选,一场人间大戏,但缺乏某种阴暗的诗意,梦里有。梦里黑白相间的诗意也许可以改变现实的质量。
(2020/11/13 phila)
当我面对一堵墙,就是面对一个梦,一个可疑的世界。沙子都在世界的表面,但它们最先接触到阳光,它们很渺小,更大的东西都被埋藏在沙子的深处,那是阳光照不到的地方,那是至暗的地方。
(2020/11/20 phila)
世界常常会让我们错愕,人事也一样。我很高兴2020的最后一天,记忆中的污浊可以随着这可憎年代一起被带走。感谢神,在我们这一生中,给我们机会见证灾难与丑陋。
(2020/12/23 phila)
人在伊甸园的时候,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被神逐出了伊甸园,圣经给出的答案是明确的:“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 知善恶是神性的一部分品质,但不是全部,如果再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那就永远活着,和神一样了。于是人走向全面神性的路被封堵,人只完成了一半神性,而一半的神性就是魔性。(2020/1/13 phila)
人总有一些痴心妄想,我当然也不例外,按照圣经话语,就是无知无耻无力,既然这是宿命,那么人的罪性只有神的全知全能可以救赎,阿门!
(2021/1/18 phila)
大黑暗时刻,所有幸福都会让人忧心更黑暗时刻的降临,但幸福虽然短暂却光亮闪烁。
(2021/1/25 phila)
很长时间都打不开新浪博客,昨天无意之间却又能打开了,但原来我写有五百多篇博文,却只剩四百多篇,被删掉约一百篇。不过有些文章又找回来了,我还是很高兴。
(2021/1/29 phila)
积雪还没有化完,又一场大雪不期而至,北美这个疯癫之地,它的宁静是疯癫之源。但是赵国呢?就是蛮荒之地了,一帮精神土著的蛮荒之地。
(2021/2/15 phila)
整一个月没更新。
刚刚过去的一个惆怅的冬天,已经来到了也许有点希望的春天。
我在头脑中勾勒一个亚洲。
昨天还看见墙角的一堆残雪,今已了无痕迹。
亚裔们在高呼口号,没有阳光,夏天就在左近,头上无须戴冠。
(2021/3/25 phila)
总算把冬天熬过去了,宜人的季节才使人想起写一首诗。
所有耸人听闻的言论,总是趁乱沉渣泛起,然而,太阳照常升起,那些说着鬼话的鬼们最怕这灿烂的阳光!
春天的太阳,你好!
(2021/3/28-4/8 phila)
诗的个人史才有意义,群体史没有意义。1985年我与一个群体发生碰撞,回首观之,一群人聚在一起,不过是一个乌有之乡的集体幻觉而已。
群体没有我的位置,这是保持自我完整性的必要前提,我很庆幸这一边缘化的存在方式。
当年孟浪曾说,要杀开一条血路。是为一个群体杀开的血路吗?
诗的群体是一个虚妄的说辞。
而只有个体突围才是思想史、诗史可能的景观,所有群体最终都消失在历史的烟云里。
(2021/4/15 phila)
我在三十年前就看到有人用油脂玩所谓的装置艺术,后来才知道这油脂其实是从博伊斯那儿偷来的,一些当代艺术的大玩家,原来只是窃贼。博伊斯那玩意儿本来粗鄙得很,而窃贼们一个个都很光鲜,成了博伊斯之后的时尚达人。这些人模狗样的高等华人数量众多,他们漫山遍野一个个长得膘肥体壮…
(2021/4/17 phila)
① 诗写于1985年,三十六年后的今天正好也是礼拜六,不过这是在北美,而不是三十六年前的那条上海穷街。词语没变,但场景可以置换。
② 把一周的每一天都冠以“礼拜”似乎不当,“礼拜”二字是专属礼拜天的,那是主日,一周中敬拜主的日子才叫礼拜天。
(2021年04月25日)
现在看1984年的诗,真是幼稚的可爱。
以前隔段时间总要毁掉一批稿件,这应该算是幸存下来的一首。
不过现存八十年代的诗,基本上都属于未被毁而幸存的作品。
既然年代久远而未被毁掉,那就至少还有点文献价值。
放在这里,仅供自赏。
(2021年04月28日)
诗歌的伟大技艺本因澎湃的灵魂而生发,那些聒噪通过学习获得诗艺进步的聪明人可以休矣。面对伟大的诗歌灵魂脱帽以示敬意吧,此时除了谦卑无别事可干。
(2021年09月27日)
去乡下是为了疗愈,但愿是正向的。
每天都有阳光,前后晒一晒。
看到书,就是对往日时光的礼赞。
睡眠,刻下的功课。
乡下有一二友人,那是历史的远景,却不包含未来。
(2021年10月29日)
很久没在七古村写诗了。时值冬天,这个人类的冬天,写诗无疑是残酷的事。
(2021年11月22日)
冬天总有那么几天让你产生怀疑,而希望永远只是一个空洞的许诺,人生的圆圈快画完的时候,我们就去寻找我们的源头,最终仍然面对的是一个空无的存在。
(2021年12月04日)
有没有一种可能,一种世间没有的东西,被我们的语言创造出来。语言的神奇性不可思议。我相信我们可以用语言创造出某种未知。
(2021年12月07日)
事实是无法描述的,因为事实的逻辑无法面面俱到。
阅读中遇到的事实是你可以理解的部分,或者是你以为的东西,或真或假都是基于事实的逻辑。
(2021年12月16日)
2021年只有三十几首诗。
五月份从美国飞回中国,世界就阴沉下来。
心是寂寞的,诗也寂寞。
(2022年01月01日)
写这诗的时候,俄乌打架进入第6天。删帖删到了非理性,不过,也无所谓,删就删吧。但我们总要说人话,哪怕人间不再有人说人话,至少我觉得自己说的是人话而不是鬼话。
(2022/3/1 HQ)
人对往事的迷恋是一种无意义的情感惯性,而对未来的幻觉则是人的一个可悲属性,所谓中间状态,也即当下的种种说事更是不可即的虚妄。人是悬浮在宇宙空间找不到支点的可怜生物。所以,我们需要上帝给我们一个支点,阿门!
(2022/3/10 HQ)
每天都处在一种迷离的状态,多么不幸,当我们置身在这个可疑的时代,不知向何处去,甚至无法选择对于“物”的自我的表达,我们仅仅是一个可悲的物种。我们是物的观察者,还是灵的至高的归顺者?耶稣说,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
(2022/4/29 HQ)
四月刚过去。五月开始的此刻,阳光依然稀薄,内心充满寒意。我在昆山花桥,核酸检测的官方叙述是48小时有效,但我们必须24小时做一次,这是幽默呢?还是幽默呢?……
(2022/5/1 HQ)
劳动节。最为醒目的是远处一个个看不清面目的裹着白色防护服的所谓大白,这是这个春天令人沮丧的标志。四境无人一片寂静,一两只鸟儿在远处的河面上翻飞。
(2022/5/1 HQ劳动节)
今天邻居群里通知说不做核酸,小区也开放了,只要出示电子通行证就可以自由进出,还听到了暌违已久的收废品电喇叭的吆喝声。
(2022/5/3 HQ)
文字总有它的惯性,顺着文字的逻辑,我们走到了一个我们没有预料到的方向。但我们真实的处境是什么?我们习惯性地隐藏了什么样的内心密码?我坦言相告,面对文字的时候,我们可能并非是一个诚实的人。我们需要参与对一个共同谎言的粉饰,以文字的表相设置圈套,当人们迷失在文字的迷宫里找不到出路的时候,诗歌终于露出了它狰狞的獠牙。
(2022年05月20日)
安倍被刺令人震惊,这是人类的正常反应,但是非人类在那里欢呼,这些可怜生物受苦太久了,他们需要借别人的不幸稀释一下自己的不幸。怜悯他们吧,这些地狱众生的苦难将永无止境。阿门!
(2022/7/7 HQ)
一个神奇的地方,一有机会就开始比傻,于是那个叼盘装得像个人似的,高八度声调,假民粹跟着哭天抢地,真是一出人间活剧。
(2022/8/6 HQ)
史无前例的连续40°高温,也算是让我们幸运地赶上了,每天体验过剩热能与我们的过度亲密,老天啊,你的爱让人承受不起。请宽恕天底下所有的罪人吧,阿门!
(2022/8/14 HQ)
简中区所谓的亚文化,就是次一等的文化,是不被主流认可退而求其次的一种文化。简中区的亚文化不是东欧地区的亚文化,把东欧亚文化翻译为第二文化是有道理的,因为它是反抗和不妥协的,它有明确的关于政治的主张,最终哈维尔成为了捷克的总统。
(2022/8/16 HQ)
讲些多余的话,无异于是在消遣生命。如今,“生命无意义”之说突然流行了起来,于是我讲的话就更显多余。这个时代冒出很多十分有趣的人和事,比如一个只会在电视上照本宣科的主持人突然变成了哲人,许多人视其为人生导师。至于某些狗屁不通的人也开始出来装叉,就更让人觉得一切良言皆多余。傻叉,你能不能多读几本书再出来装叉啊哈哈……
(2022/9/8 HQ)
11月19日本“公号”(真是一个让人别扭的词)被解封。过去快十天了才来更新,也就是还活着的一个告示。奥斯维辛之后,写诗很无聊,天天做H酸,写诗就更无聊了。
(2022/11/27 七古村)
懒得写诗,懒得更新,人生就是百无聊赖。
(2022/12/27 阳第五天-花桥)
这么长时间不写诗,于我而言是罕见的。不过,不再写一首诗的那一天终会到来。写诗不是一件重要的事,但我却几乎穷尽了一生的时间,这也是罕见的。我青春年代的几个好友甚至密友,他们离开人世已经多时,他们已经超越了生与死的界限,他们是先行者。他们常常让我去回想他们,是因为他们曾经留下过闪光的作业。他们是人生的英雄,也许他们一生充满了败绩,他们虽没有在生前暴得大名,但他们从未染上平庸之疾,我为他们骄傲。诗歌从来不是展示平庸的地方,但如今,无数庸人聚集在诗歌的名下,庸人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2023/2/8 HQ)
春天来了。好多人都在关心乌克兰的事,我也关注,但我懒得说话,因为愚蠢无处不在,愚蠢天天都在。三年疫情,一半的时间是在简中区度过,终于也赶上了这一波折腾,元气大伤,总算还活着。此刻墙上斜阳,毕竟春天总是带来了温情,为我自己以及所有与我相关的人送上祝福吧,愿未来依然有希望。阿门!
(2023/2/20-26 HQ)
时间过得真快,一看日期,这首诗差不多写于快一个月之前,恍如梦游,洞中一日,世上千年,难道我现在就在洞中?发一首诗上来,标注一下我在世上的方位,我在世上的漫游仍在持续中……
(2023年03月22日)
今年以来一共只写了五六首诗,对我而言比较罕见。写诗是我的呼吸,如果不写诗,就意味着不再呼吸。我必须一直写,因为我必须呼吸。
前几天京不特来花桥,我们是四十年的老友,老友的每一个成就,我都将之视为自己的成就,他从丹麦原文翻译的克尔凯郭尔著作全集16卷,这一浩大工程已经基本完成,商务印书馆正在紧张编辑出版中,我为老友感到自豪。
我依然认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最好的时代,因为会有一个充满魅力的未来在等着我们,不要悲观,周期性疼痛总会过去,世界末日说只是虚无主义者的调味剂。我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那些言说人生无意义的扯淡,如果他们真的相信,他们还活着干嘛?
(2023/5/7 HQ)
我们面对的不是同一个世界,人们啊,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只有部分的重合,如是,在这宇宙长河里,这个短暂重合的瞬间,实在不可思量,乃至算数譬喻不能及!
(2023年08月29日)
我以为我能离诗而去,但是不能,诗是我灵魂的原液,抽去诗之原液,灵魂自然死亡。
(2023年09月02日)
我们是一种幻觉生物,在这个五颜六色的现实世界里,我们的幻觉也给八十年代披上了虚幻的色彩;只有在梦中不醒的人才会怀念八十年代,那种贫瘠荒凉的理想主义幻觉。人总是对幻影充满了迷恋,最后弄假成真,已致不知身在何处。我们最终将成为这个世界的幻觉,而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个幻觉,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那时我们会醒来……
(2023年10月03日)
某电视剧有一句台词说,秘密是经不住议论的。这个比较有意思,与当下倒也切合,不过不让议论终究使秘密仍是秘密,瓜虽多,不缺瓜吃,但吃的时候不准砸吧嘴,也是时下表现出来的“特别色”的特色,嘿嘿……
(2023年10月30日)
早年读古诗词,接受关于诗是什么的训诫。当知道什么是诗,便知诗即不可说;或曰可千百种说。所谓了悟何为诗,即非了悟,是为了悟。
(2023年11月15日)
2019年突然就走到了一个时代的末端,那时候,谁也没有预感到后来的三年会让所有人都惊慌失措。这首诗之后,人类命运再次面临存亡考验。
(2023年11月25日)
2023年已到尾声,但今年的诗作却出奇地少,区区13首,一个欠收年。人间多难,个人也难幸免;前一年(22年)岁末突然被“阳”,伤害颇烈,于是灵魂与肉体间的跌宕至今未休,不过生死既已看破,余年皆为净赚。一笑。
(2023年12月20日)
6月16日发了三首新作,被删了,理由不明。17日又写了一首,合在一处,自我审查一番,仍发不出来,只能删掉一首,再发一次。
今年没做几首诗。不是不想做,而是没有精力了,从精神到肉体都有所不济。诗乃智勇者所为,衰朽之辈不足以言诗。所有的话都是多余的,诗是思想的化石,在无意识深处被挖掘出来。与其不说人话,不如在诗歌的象牙塔里,或许可以找到人性的真相。
再:7月3日中午发出来三首,到下午5点多又被删了。于是再删掉一首,只剩两首重发。是为记。
(2024年07月0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