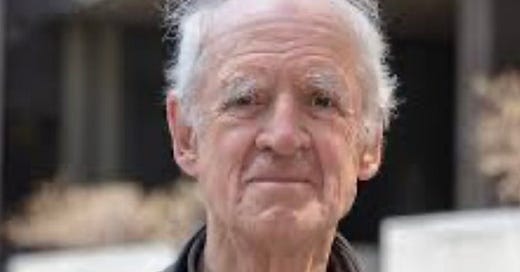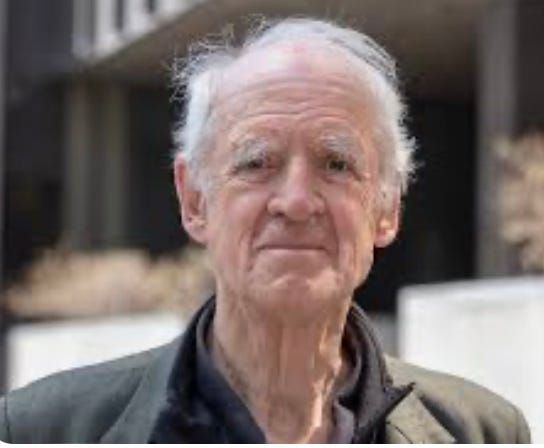郭锐 | 时间和记忆
編者按:本文書評專欄作者郭銳文章。这是一个阅读被抖音和今日头条塑造的时代。每一个读者都能感受查尔斯.泰勒所说的“现代共时性“。
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加拿大哲学家。本文引用來自其長文 On Social Imaginary,第31頁。
今天的日常中文阅读,充斥着对“突发新闻”的狂热。明星丑闻、小人物悲剧、官员落马、科技产品发布……人们沉醉在这种现代共时性之中,如同依赖某种刺激神经的毒品,不断追逐下一个热点。奇怪的是,人们对未来却不抱盼望。就像毒品一样,需要越来越强烈的刺激,这种沉醉才能维持下去。
这是一个阅读被抖音和今日头条塑造的时代。每一个读者都能感受查尔斯.泰勒所说的“现代共时性“:
”仅仅因为事件在同一时刻的共同发生,毫无因果或意义关联的事件被联系在一起。现代文学以及新闻媒体,再加上社会科学,使我们习惯于用垂直时间片段的方式来思考社会,将无数相关和不相关的事件联系在一起……“
这种背景中,当重大的历史事件,那些上一代人付出生命、热血和青春的历史事件,被新一代人忽视和忘记:“我们没有经历过,死去的人已经死去,我们为什么一直要记住?”
为什么要记住?我们是不是有、何时有记住某些人和事的义务?
妻子因丈夫忘记她生日对丈夫动怒,很少有人会质疑这是否合理。这些生活小事似乎告诉我们,记忆是有道德面向的,或者说,记忆不仅仅关乎个人的忘性大小,而且也是一个伦理选择。妻子绝不是因为这件事本身而生气,而是认定这件事可以一定程度上预测丈夫未来如何行事。
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应该是对记忆最有发言权的作家之一,因为他一生的努力都在于提醒人们记住某些东西。索尔仁尼琴2008年去世。他活得比人类历史上最大、也最血腥的帝国长,这既是他本人的胜利,也是他文字的胜利。他的一生就是为了不遗忘过去而写作。《古拉格群岛》开篇就说:“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
道德哲学区分了人类社会的两种关系,一种关系是深关系,类似于父母、朋友、夫妻、同乡;另一种关系,是浅关系,比如同为女人、病人、学生等。浅关系建立的基础只是因为同属某一类人这样一个事实,深关系建立在共享的过去和共同的记忆中。把自己放置在深关系中,记忆就成为责任。索尔仁尼琴用自己一生的工作,诠释了自己与这块土地上的人生死相依的关系。
索尔仁尼琴目睹了苏联统治者将谎言正常化的过程。贪婪、嫉妒、仇恨,被冠以冠冕堂皇的名义,如阶级斗争、集体利益或国家利益等,肆虐横行,将世界撕裂。统治者一方面用枪杆子威胁镇压,另一方面用笔杆子创造另类“真理”。这是索尔仁尼琴和与他一同努力的现代知识分子共同的看见:守住记忆和历史,是反抗的最大武器。
记忆,就是让自己与深关系的人血肉相连,这是一种伦理意义上的有意选择。记住代表了宣告自己的身份,也预示和这个身份相称的行为。在圣经《旧约》中,以色列人人向上帝呼求:“我如亡羊走迷了路,求你寻找仆人,因我不忘记你的命令。“ 与之相反的忘记,就意味着失去上帝的选民这个身份。《申命记》里摩西对以色列劝告:“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和合本申命记4:9)” 以色列人的种种节日,都是防止他们忘记的,如除酵节、逾越节、住棚节等。
以色列人必须记住,也生活在一个这些被记忆的事件组成的时间线中:这些事件指向的,是最终的圆满,无论经历何种打击、漂泊、苦难和生离死别。
对新的一代人而言,记忆是为了见证,对罪恶的记忆是对公义的承诺;记忆也是为了盼望,只有记住才知道什么是真正活着。
存在着记忆的时间,才能离开“现代共时性“,不再是穿起毫无因果或意义关联的事件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