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左翼作家张承志在参观完原爆纪念馆之后曾经写过一段在中文世界振聋发聩的感悟:“日本和中国都必须记住:扩张的民族主义,迷狂的大国崛起,常使人类丧失良知,两手肮脏。”文章原标题为《从原爆到靖国:东亚社会的集体记忆与战争罪责》,新标题为编者所加。
新干线划过漫长的山阳线,天空蔚蓝,阳光刺眼,我的旅途的下一站是广岛,穿梭在日本的不同城市之间,似乎并没有太多焕然一新的体验。
濑户内海的海风炽烈,烈日炎炎,这座港口都市有一种属于海洋的气质。街头随地可见的自动贩卖机、拉面店,身穿JK制服在电车上叽叽喳喳的少女,以及下班后一脸倦容却准备在居酒屋容光焕发的上班族们,提醒我其他日本城市并无本质上的不同,漫长而宁静的日常生活,似乎在这一刻成为这座城市的符号与永恒。静静凝视着都市霓虹的广岛城天守阁,以及雅致小巧的缩景园,则彰显着这座城市的现代源自于并不遥远的古典。
一
1945年8月6日,原子弹“小男孩”使这座曾经的军港,战时日本的军都,彻底成为了世界历史上无法略过的一页。作为世界上第一座被原子弹袭击过的城市,受害者的记忆成为了广岛永远的伤痕。曾经有人说,核爆记忆前的日本人只有作为“我”的个体存在,而核爆的记忆,则使得作为“我们”存在的日本人诞生了。代表着当时人类科学的最高成就,却不掺杂任何责任与伦理的犹豫和考量的杀人武器,第一次降临在广岛这座工业城市之上。那些在核弹的高温一瞬间逝去的生命,凝结着日本近代历史上对于亚洲诸国的罪恶、超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狂热以及二十世纪国际秩序内在的残酷,似乎都在这一刻成为永恒,成为历史书上难以卒读却无可回避的一页。在受害者与施害者模糊的身份之间,在政治的裹挟与时间的冲淘之下,暧昧的日本人必须面对的一页历史就以这样惨烈的方式摊开。这一节历史与道德的阶梯,依旧等待着今天以暧昧所著称的日本人来抉择方向。
参观广岛的和平纪念馆也许是在所有参观活动中,最为肃穆的一次经历。漆黑漫长的甬道之间,设计者尝试复制出核爆当天的压抑与恐怖,而动人心魄的,是长廊之间受害者的照片与遗物——校服上的肩章、被高温熔化的铝饭盒、残破的课本……1945年的八月五日本应是一个再日常不过的时刻,尽管战争的阴霾已经渗入到了生活的边角,每个人都已经习惯了夜晚不再宁静,防空警报成为最熟悉的噪音,习惯了每天配给变得少的可怜。但是某种程度上,活着就意味着明天,也许他们并不懂得绝对国防圈、ABCD包围圈。
那些似乎可以长久延续的日常生活,似乎在一瞬间就被摧毁。那些被未被战火劫持的生命,在这一瞬间被野蛮剥夺。当我凝视着受害者照片中那一个个青春洋溢的少男少女时,幻想着如果没有这次天降横祸他们的人生:是以另一种方式与这个彻底堕入疯狂的国家毁灭,还是有机会在废墟上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他们的心灵是否有机会意识到自己所身处世界的荒谬,和大国政治逻辑的傲慢与狭隘?一个国家的歧路与民族集体心灵的迷狂,历史教科书上郑重其事的一个单元,却是无数人一生的劫难和心灵的伤痕。我们在拥有集体记忆之前,首先葆有的是属于自己的个人经验,而对于广岛的受难者与遗属来说,核爆使他们第一次有机会从被国家和权力绑架的叙述中挣脱出来,真正有机会讲出自己的体验,真正有机会思考自己与国家的关系。而政治学家将日本战败称之为“八月革命”,也许正是因为战争与核爆,使得作为平民的日本人不再为皇国与天皇所绑架,真正有机会说出自己的战争体验。
黑色的雨,彩虹般的烟霞……这种奇妙的景观是许多广岛核爆亲历者的第一反应,也正是在这种病态乃至癫狂的末世景象中,日本荒谬的国家体制以及膨胀自大的国体论所孕育的极端意识形态,迎来了它的非自然死亡。而日本军国主义的畸形与抉择,是如何形成的?在畸形的宪制与民主体制之下,被天皇制国家所绑架的普通人,真的可以免于良知的诘问?这样的诘问与背后尴尬的沉默,则留给了所有战争的幸存者慢慢咀嚼。或者,更严肃的问题是,这些看似毁于一旦的日常,这些青春鲜艳的生命,在日本政府“十亿玉碎”的本土作战面前,又会有什么样的未来?
二
在某种程度上,广岛和平纪念馆的叙事逻辑是一种“去政治化”的语言,压抑与悲痛的氛围中,我们无从看见施害者的身影,这些逝去的生命的被陈列,犹如面对着一场虚无的自然灾害。因为展厅的设计者与参观者所共有的默契与内在逻辑是,广岛灾难的直接责任人是作为战后日本民主的建设者与东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美国。而作为胜利者的美国,却是以道义和战争的名义投下核弹。对于日本而言,追索施害者的责任,犹如追问自己的盟友,而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理念以及《宪法九条》中对于战争权利的放弃,也是基于施害者与受害者的双层逻辑。而对于饱受军国主义之害的日本周边国家而言,战后日本对于历史责任的暧昧态度,以及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美苏冷战格局而从未彻底进行的对帝国日本的转型正义的清算,则使得广岛、长崎的集体灾难缺乏一种基于现实的道德力量。没有施害者的灾难的陈列,也自然听不到忏悔与自白的声音。而我们所有人在沉浸在这场悲痛之际,都知道日本既是战争的直接受害者,也是挥舞屠刀的施害者。如果说广岛与长崎的原爆使得日本人真正拥有了共同的集体体验,而凝结成为新的政治民族,那么一个没有“他者”存在与周边存在的公共记忆与公共空间,只能是一场旁人看来自怨自艾的喃喃自语,无法走向真正的“善”与经过普通人良知与常识共同检验的正义。
以战时的广岛作为背景的动画电影《在这世界的角落》的海报,在广岛的诸多景点之前随处可见。那位热爱画画,渴望着普通人的爱情的女主角小玲,在困惑与未能为力之中,眼看着自己的日常生活是如何被战争毁掉。在电影里我们既可以看见她无私的帮助邻居,笨手笨脚地应付生活和婆媳关系,但是她也会为吴港中黑烟滚滚、耀武扬威的战列舰感到骄傲,甚至在听到裕仁天皇的终战宣言时歇斯底里喊道“为什么不战斗到底?”这部电影在上映后也受到了毁誉参半的评价,随着战争经验的褪去以及日本左翼运动的衰落,类似于《赤脚阿元》和《萤火虫之墓》对战争时的国家体制和集体无意识下的狂热的批判已经悄无声息地落幕。作为与战后和平主义对照存在的战时已经彻底凝固,在无数个生活的日常的流逝下,回归到它应该有的位置。而这种以生活化逃避政治判断和抉择的“回归”,在作为战争的受害者的其他国家来说,却是一种尴尬乃至冒犯的存在。平淡、温柔却苦涩的故事,背后是一个民族迷狂的过往,而最终消解这一切的,是东亚式的“过日子”的基础叙事。国家主义的狂热泄露到日常生活的痕迹可以随着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改良逐渐消逝,但是却也正是这种过日子的逻辑,使得普通人逃避着责任,以一种“无思”的态度面对现实,直到大难临头。
三
政治学者丸山真男当时作为一名军人(1945年四月开始,丸山真男在广岛市宇品町的陆军船舶司令部参谋班任职)目睹了原爆的过程,当原子弹投下的那一刻,这位亲历了战前日本特务统治与左派运动的知识人,意识到此刻正是日本帝国的彻底终结。而他也将之后一生的志业,设置于解释此刻,以及此刻背后那个看似复杂而暧昧,却在责任伦理和政治决断上异常幼稚的日本。“任何专制制度的基础是人的意见。”丸山真男想解释的是,是什么样的体制与结构,使得看似陈腐、墨守成规的官僚,成为了军国日本最坚实的基础。出乎不少人意外的是,丸山真男在《超国家主义的心理》一文中,把日本在亚洲的暴行归咎于日本扭曲的政治文化和宪制结构,(“在我国,只要有与‘卑贱’的人民相隔距的意识,仅此一点就等于与最高价值的天皇拉近了距离,由此更强化了与人民隔距的意识。”)却反对日本政界所主张的“一亿总忏悔”,因为把战争责任均等地洒向每一个人头上,其实却使得在战后逃过审判而被新政府接纳的“大人物”们真正逃脱了良心的谴责。如果未能按照每个人在体制中所处的地位来清算责任,空洞的忏悔实际上在为已经在战后政府登堂入室的“大人物”们推卸责任。看似国运一路坦途的明治时期,尽管有了宪法乃至政党政治,却并未诞生属于真正的国民主义,在日本真正具有自由意志并承担决断的只有天皇制(日本论理学家和辻哲郎认为天皇制是日本国民统合的象征)本身。而只有建立了真正的民主主义,使得判断和记忆的权力回到每个人手里,那么跨越历史与地域的和解才会成为可能。
然而民族国家的时代却从来没有给过以伦理和共同历史记忆的集体以和解与超越的机会,尤其在后冷战的国际秩序逐渐消解,新的地缘格局暗流涌动的东亚,对于战后东亚秩序主导权的争夺,也是以集体记忆和战争罪责的讨论作为焦点。尽管看来,战后的日本早已在美军的指导下完成了民主化改革。但是新的民族主义,以历史认识和正常国家化的讨论作为方式展开,而这种叙述中,战后的历史责任被稀释,作为牺牲品的广岛受害者和为“帝国”而牺牲的“殉道者”,要么被等量齐观,作为“统一的国民主体”(加藤典洋《败战责论》)而存在,要么被刻意遗忘,以受害者的身份,以强调日本国民在战争中的悲惨境遇。
今天的国际政治中,民族主义依旧作为一种“必要之恶”存在,在当下政治体制和国际秩序下高度扭曲的日本社会,去发掘源自作为公民与集体的主体性,也使得民族主义以一种同样扭曲的方式展开。无论是日本右翼自90年代以来对于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案以及“东京审判史观”“自虐史观”的批判,还是对美国的战后改造的怨恨以及日本在国际事务上的尴尬位置的愤怒,某种帝国的遗绪依旧在看似“现代”与拥抱和平的日本社会暗流涌动。这种帝国的想象,不再是以古典式的“国体论”和万世一系而存在,而是一个“非正常国家”对历史所造就的现实而形成的怨恨与不甘。而这种新型的民族主义,也悄悄地散落在每一个国民的心底与记忆杂糅,在东亚的历史世界里世界纠缠、激荡,形成了新的迷宫。
四
如果说原爆的纪念是战后日本“记忆之场”的重要的声部,那么另一种曾经被压抑今天又被可以释放的声音,则显示出这一片记忆之场的驳杂与扭曲。记忆不仅在收藏过去,却又按照现实的方式在塑造着“永恒”。在距离广岛原爆纪念馆几百公里之遥的靖国神社,就是再以一种截然不同,乃至对立的方式,宣誓着不同历史形式的存在,以及政治对于记忆的操弄。同样是牺牲者的面容,原爆纪念馆中的年轻人使我感到的是还未展开的青春的凋零,而靖国神社游就馆中那些“牺牲”的“英灵”,那些绝望地驾驶着零食战斗机冲向美军航母的飞行员,那些怀揣着写给母亲和妹妹的信向着铁丝网与机枪阵地冲锋的士兵,却让我感到一种肃穆的“恐怖”,战后日本的国民心理的重建,并不是在“白茫茫一片真干净”的废墟上进行,建设者们依旧凭借着旧帝国的心理与记忆的沉淀,裹挟着争议与属于日本精神中的扭曲再次启程。
作为游客的我们也许只能把原爆受害者叙述与靖国神社游就馆导览词背后的“自由主义史观”(自由主义史观是由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提倡的历史验证法。它把它的攻击对象称为“自虐史观”以及“东京审判史观”。)史观的并行不悖,视作一种民主国家对于不同言论与表述的尊重。然而,这种内在的纠结已久使我困惑,这并非是一种号召和解与宣扬仇恨的对立,而是同样作为受害者的广岛再向全世界展示着这道伤痕,并希望用自己的遭遇向全世界昭告战争与核力量的残酷。但是却又另一批人用属于上个世纪乃至追溯到古典的方式,向人们宣告今天的日本有多么“特殊”,第一群日本人面对的是今天的整个世界,那么第二群日本人面对的则是作为“历史共同体”甚至“血缘共同体”的日本。(江藤淳,“最为重要的、只要是日本人自然皆会珍惜的东西,就是日本之为日本的特质”)靖国神社之于今天的日本人,仿佛是一场过去与今天的连接,只有在属于日本的市民宗教的国家神道(日本民俗学者苇津珍彦对“神道”的定义是,所谓神道与起源于天才创始人的教义的佛教、基督教等等不同,那是在数千年日本民族大众生活中自然成长式地被培育出来的民族固有精神之总称。)中,才能真正成为“日本人”。然而他们刻意忽略的是他们祈祷乃至渴望回归的日本,恰恰是造成广岛悲剧的施暴者本身。
文学学者加藤典洋有一个颇有意思的说法,靖国神社所供奉的“牺牲者”之于今天战后的日本人的关系,如同一场大火之中,用身体架住坍塌的建筑的牺牲者,没有他们的牺牲,就难以有日本的“战败”认识。同样,在备受争议的电影《永远的零》中,作为神风特攻队的男主人公宫部久藏在最后一次行动时的动力也是希望用自己的牺牲去证明战争的“荒谬”,去为活着的家人开拓出战后生存的道路。然而对于施害者与受害者双重身份的日本人来说,这场战争仿佛是意外之灾,是明治与大正时代的“正轨”之后的一段意外的歧途。拥有这样记忆和认识的人们,靖国神社是他们的安顿心灵之所。两种记忆的交锋,乃至国家权力利用两种记忆的冲突,试图压制另一种,也正如战后日本国家建设本身“非正常国家”的尴尬。
高桥哲哉在《靖国问题》一书中曾经举过一个例子,一位老太太岩井益子是如此描述她作为战争遗属对靖国神社的情感:“丈夫生前从未怀疑过假如自己战死的话一定会被祭奠在靖国神社,他就是怀着这样的信念奔赴战场的。对我来说,靖国神社受到玷污,这比我自己受到玷污还要耻辱几亿倍。只要听到哪怕是一句谩骂靖国神社的话,我的身体就像是被劈开了似的,全身的热血倒流,溢出体外。放眼望去,我的热血变成了战士们的血的海洋,向四周蔓延开去”。高桥哲哉将遗属们的这种反应定义为感情的炼金术,国家体制和神道信仰悄无声息地将普通人对失去亲人的悲痛,以意识形态偷换为国家情感的介入。靖国神社所供奉的英灵背后,是另一片血的海洋,而战争的残酷以及不义,为了这种国家主义介入的历史记忆,已经被刻意滤去。这种悲痛并非在现实与历史的真空中存在,在作为牺牲品的日本国民之前,亚洲各国已经提前被狂热的军国主义蹂躏过了。丧失了历史意识与责任感的恸哭,是否有资格遗留在公共记忆的悠长回廊之中?
即便站在文明和历史的角度,我们也无法苛责这种情感的存在,历史的惯性是如此强烈,历史的遗留物也在一直提醒我们,熟悉并作为常识存在的历史,是充满了不安的噪音乃至压过一切噪音的冲动。当我们试图理解这种噪音如何存在,我们才能理解靖国与原爆之间的冲动以及彼此之间隐秘的关系。然而也借用思想是学者子安宣邦在《国家与神道》一书中对日本战争体制与靖国神社背后政治神学之间的关系“政教合一之国乃是战争之国,为臣民提供一个死后安居的场所是使臣民投身战争的前提。”如果我们没法挥手作别旧帝国的亡灵,国家绑架个体的历史继续出现,类似的悲剧与留下的巨大的历史空洞,恐怕依旧会继续存在。
五
走出原爆纪念馆仿佛走出了另外一个世界,这里没有战争的阴霾,也没有历史责任的沉重。广岛纪念公园背后的商店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流,公园里的游船上布满了来自各国的游客,然而回看今天的世界,却又难以给予我们告别战争的欣慰。日本的历史记忆与解释权并不是日本人独享的,因为今天东亚成熟的民族国家体系之中,20世纪日本的战争以及遗产,是浇筑冷战体系下新的政治民族的骨肉,它们既渴望彻底埋葬战争与帝国的亡灵,却又无法摆脱帝国本身的诱惑。
或许,更现实的说法是,日本近代的战争与国家体制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作为互联网亚文化存在的“原子弹下无冤魂”“真理在大炮射程之内”“李梅烧烤”使得战争的认识已经彻底本质主义,成为一种以民族乃至血缘的立场之分,历史的真实与残酷被段子化的“三分钟读懂历史”的叙事稀释到极致。所有人习惯以战争的决策者思考,另一种国家主义的信徒借助着日本帝国的废墟借尸还魂般重复着相似的话语。这也使我开始思考丸山真男无责任体系的解释性:借助这些没有实体的想象,也缺乏主体自由意志的空洞符号而释放着狂热的年轻人,真的有资格在泡沫破碎之后,以无责任自辨的自由吗?在帝国肆虐之前,帝国主义的人民也许早就跃跃越试了。
左翼作家张承志在参观完原爆纪念馆之后曾经写过一段在中文世界振聋发聩的感悟:“日本和中国都必须记住:扩张的民族主义,迷狂的大国崛起,常使人类丧失良知,两手肮脏。”我们面对历史的态度,也许决定了我们的未来。无论是在暧昧的历史观中继续沉沦的日本,还是以历理直气壮地嘲讽和平与政治正确,执拗地以十九世纪的帝国秩序想象今天世界的的中国网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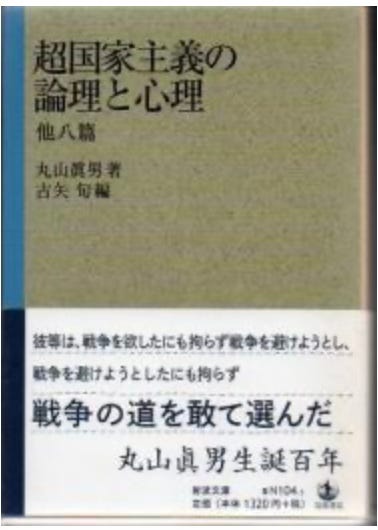

日本國民從不承認日軍在菲律賓、印尼、星加坡、馬來亞、泰緬、和香港所犯下了奸邪殺戮的戰犯罪行!這種片面之反思只會埋下軍國主義復辟的伏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