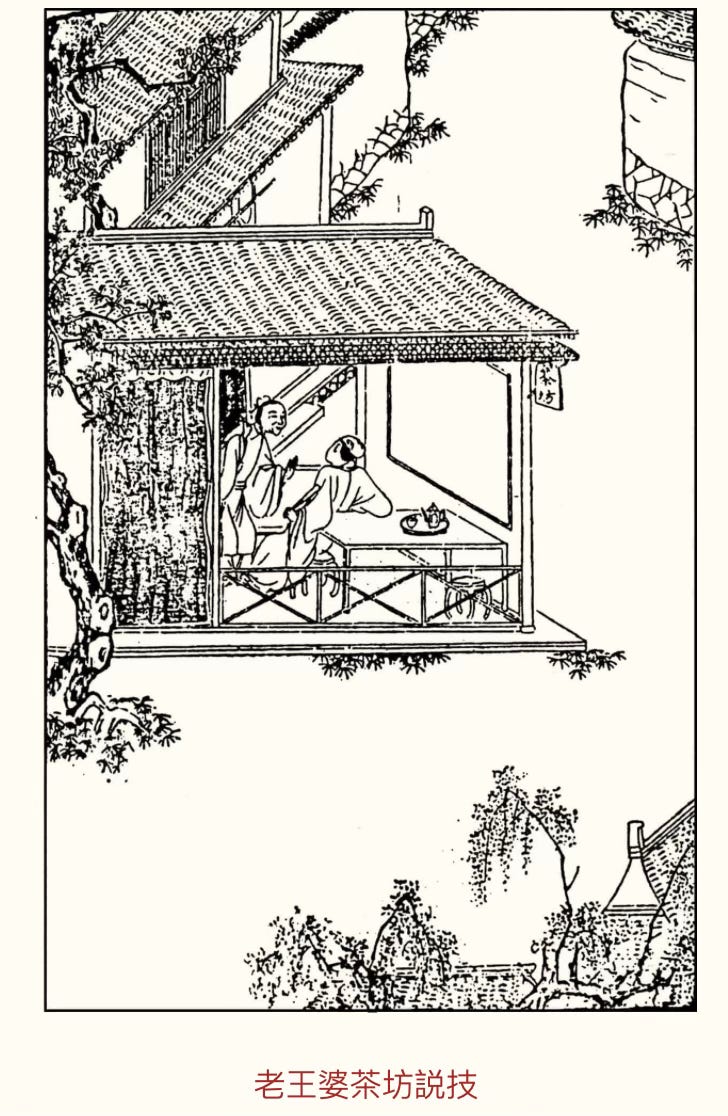刘晓蕾 | 每一个配角,内心都有一个黑暗的江湖
編者按:兰陵笑笑生却专写卑琐的凡人,一心“祛魅”。所以,在《水浒传》里,被一笔带过的西门庆、潘金莲、王婆、郓哥们,来到《金瓶梅》的世界里,却成了主流,构成市井人心,世俗生活。本文为刘晓蕾最新专栏。
一
《金瓶梅》的故事源于《水浒传》。后者是绿林好汉的世界——打虎、倒拔杨柳、打家劫舍,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水浒是英雄传奇,作者喜欢非凡的人事,对普通人缺乏兴趣。
兰陵笑笑生却专写卑琐的凡人,一心“祛魅”。
所以,在《水浒传》里,被一笔带过的西门庆、潘金莲、王婆、郓哥们,来到《金瓶梅》的世界里,却成了主流,构成市井人心,世俗生活。
隔壁老王王婆开茶馆,还兼职媒婆、卖婆、牙婆,“马泊六”。“牙婆”是人贩子,“马泊六”是拉皮条,“开言欺陆贾,出口胜隋何”,什么钱都赚。潘金莲一叉竿打到西门庆,她看见的是钱——又是贡献“挨光计”,又是出幽会的场地,跟西门庆一起算计潘金莲。又是殷勤准备酒菜,还出主意毒死武大,关键是她还知道砒霜中毒的症状,最后亲自上阵,把武大尸首处理干净,真让人细思极恐。
《金瓶梅》的世界里,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黑暗的江湖,王婆的内心是无底的黑洞。
这么费劲心机,她一共赚了多少呢?我们算算:西门庆一次性给了10两,还有一套送终衣裳,再加上每次幽会打酒买肉赚差价,前后也就是几十两银子。
钱真不算多,却赔上了一条人命,真让人唏嘘。
后来西门庆死了,潘金莲偷女婿,吴月娘让王婆带走她重新发卖,她非要卖105两,只给月娘20两。可惜,这笔横财,她来不及消受,就死在武松刀下。
以贪财始,以贪财终,王婆也算死得其所了。
古语云:“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但传统的乡土社会,发财的机会很少。“力田树艺,鲜为商贾”,人人安分守己,不商贾,不远游,崇尚的是稳重、质朴。
但在《金瓶梅》的世界里,几乎全民皆商:上至朝中大官,蔡御史、宋御史,下至媒婆、小厮、丫鬟、虔婆、帮闲、走街串巷的货郎,“佛门中人”王姑子、薛姑子,乃至回家养老的刘太监、薛太监……三教九流,都不事稼穑,只为赚钱。
人心散乱了,欲望在升腾,连空气里都飘荡着金钱的味道,这是一个崭新的新世界。
王婆的同行有薛嫂、文嫂、陶妈妈,还有冯妈妈。她们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冯妈妈是李瓶儿的奶妈,却给西门庆和王六儿拉皮条。每次都帮着王六儿整治酒菜,生怕错过一次赚钱的机会。李瓶儿快要死了,她还忙着给西门庆和王六儿做饭,无暇去看她。
第7回,薛嫂向西门庆介绍孟玉楼首先说:南京拔步床也有两张,四季衣服,妆花袍儿,插不下手去,也有四五只厢子。珠子箍儿,胡珠环子,金宝石头面,金镯银钏不消说;手里现银子,他也有上千两。好三梭布,也有三二伯筩。
最后才说年龄长相、弹一手好月琴,这是抓住了西门庆的贪财心理。果然,西门庆一听,还没相看孟玉楼,就去拿银子争取杨姑娘的支持。
不过,在两人相看时,西门庆和薛嫂两人合伙演了一出双簧——
西门庆开言说:“小人妻亡已久,欲娶娘子管理家事。未知尊意如何?”那妇人偷眼看西门庆,看他人物风流,心下已十分中意。遂转过脸来,问薛婆道:“官人贵庚?没了娘子多少时了?”西门庆道:“小人虚度二十八岁,不幸先妻没了一年有余。不敢请问娘子,青春多少?”妇人道:“奴家是三十岁。”西门庆道:“原来长我二岁。”薛嫂在傍插口道:“妻大两,黄金日日长;妻大三,黄金积如山。”
看出来了吗?西门庆的第一句话可是暗藏玄机,“管理家事”是正妻的职责,小妾是只有被管理的份儿。孟玉楼听着,满心以为嫁给西门庆是做填房。等西门庆走了,她又问薛嫂:
“但不知房里有人没有人?见作何生理?”薛嫂道:“好奶奶,就有房里人,那个是成头脑的!我说是谎,你过去就看出来。他老人家名目,谁不知道的!清河县数一数二的财主,有名卖生药放官吏债西门大官人。知县知府都和他往来。近日又与东京杨提督结亲,都是四门亲家,谁人敢惹他?”
玉楼想确认西门庆到底有无正妻,她本是一个谨慎的人。结果薛嫂没正面回答,只是含糊了一下,然后话锋一转,开始大赞西门庆有钱有势。
待玉楼嫁过去,才发现西门庆非但有正妻吴月娘,还有二房李娇儿,自己只是第三房小妾。
这次,薛嫂得了多少谢媒钱呢?书里没明说,但薛嫂曾自承:“我替你老人家说成这亲事,指望典两间房儿住哩。”做媒真的收益这么高?未必。主要是因为帮西门庆娶了有钱寡妇孟玉楼,谢媒钱自然水涨船高。
孟玉楼却惨了。后来西门庆死了,李衙内看上了孟玉楼,托官媒陶妈妈来说亲,孟玉楼连珠宝一般发问:“妈妈休得乱说!且说你衙内今年多大年纪?原娶过妻小来没有?房中有人也无?姓甚名谁?乡贯何处?地里何方?有官身无官身?从实说来,休要揭谎。”
她这是被骗怕了的。
王婆曾自承:“我们这一行,都是狗娘养的。”一副豁出去,完全不怕报应的架势。
坑蒙拐骗的可不只是媒婆。佛门也不清净,薛姑子跟王姑子来西门府来得甚勤,帮吴月娘找胞衣坐胎,劝李瓶儿拿钱念经……无利不起早。最后这两人,因5两银子闹翻了,王姑子骂薛姑子独自把钱给吞了,是老淫妇搞鬼;薛姑子反过来又咒王姑子,死后堕阿鼻地狱。
这薛姑子又是什么来历?原来她曾嫁过丈夫,在广成寺前居住,卖蒸饼儿,生意不好,便与那些寺里的和尚勾搭成奸。和尚们帮衬她。丈夫死后,她干脆做起了姑子,专往有钱的人家跑,包揽经谶之事,什么赚钱做什么。
西门庆在家里看见薛姑子,告诉吴月娘:“你还不知她弄的乾坤儿哩!她把陈参政的小姐吊在地藏庵儿里和一个小伙偷奸,她知情,受了三两银子。事发,拿到衙门里,被我褪衣打了二十板,叫她嫁汉子还俗。她怎的还不还俗?好不好,拿来衙门里再与她几拶子。”
吴月娘的反应是:“你有要没紧,恁毁僧谤佛的。他一个佛家弟子,想必善根还在。他平白还甚么俗?你还不知,他好不有道行!”
吴月娘、李瓶儿还有潘金莲,都有自己的欲望和恐惧,离不开王姑子薛姑子们。更何况,她们还懂奇怪的民间偏方,可以帮她们生儿子——
“你老人家倒说的好,这件物儿好不难寻!亏了薛师父。──也是个人家媳妇儿养头次娃儿,可可薛爷在那里,悄悄与了个熟老娘三钱银子,才得了。替你老人家熬矾水打磨干净,两盒鸳鸯新瓦,泡炼如法,用重罗筛过,搅在符药一处才拿来了。”月娘道:“只是多累薛爷和王师父。”于是每人拿出二两银子来相谢。说道:“明日若坐了胎气,还与薛爷一匹黄褐缎子做袈裟穿。”那薛姑子合掌道了问讯:“多承菩萨好心!
这就是民间宗教。对于普通人来说,有道行,有用,才信。
《金瓶梅》的世界里,全是这样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算盘,十分精刮,又善于说谎。
二
很多研究者认为《金瓶梅》里的人心败坏,是商业经济发达,旧道德瓦解,新道德还未形成的结果。
在《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一书中,作者卜正民引用了1543年的一份地方志,地方志的作者朱肜这样描述他那个时代:
“近数十年来,士习民心渐失其初,虽家诗书而户礼乐,然趋富贵而厌贫贱。喜告讦,则借势以逞,曲直至于不分,奢繁华,则曳缟而游,良贱几于莫辨,礼逾于僭,皆无芒刺,服恣不衷,身忘灾逮。”
朱氏痛斥商品经济,导致高消费,阶层混乱,贫富差异也更赤裸,让人触目惊心。这其实是儒家读书人面对商业时代的普遍态度:“兴贩贸通之利以侈其耳目而荡其心”。
商业到底有没有腐蚀人心?导致了更严重的社会危机?
事实上,这种感慨由来已久。两千年前,孔子就说:“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孔子所说的“今”,可是《金瓶梅》里的“古”,可见“人心不古”早就是传统了。而民间流传的“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两人不看井,三人不锯树”,这等劝世之言,更是提醒我们:人心一直不怎么好,莫对人心期待过高。
这关涉对人性的认知起点,是人性善,还是人性恶。
人心败坏这口锅,商业经济背不了。不如借机来体察一下人性,毕竟,《金瓶梅》里有世俗生活,有人间烟火。而这些,是儒家道德一直无视的真实的人性世界。
在《金瓶梅》的世界里,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能引发人际关系的坍塌。
书童受了贿,买酒肉托李瓶儿走后门,多余的请同事吃,却忘了平安。平安一肚子不快,便向潘金莲告书童黑状,说书童去李瓶儿房间里呆了很久,吃酒吃得脸红红的。金莲又借此讥讽李瓶儿和书童,不知干了什么茧。然,书童是西门庆的娈童,备受宠爱,西门庆到底借故打了平安一顿,一时间鸡飞狗跳。
稍有点走神,就捋不清其中的爱恨情仇。
第30回西门庆当了清河县的副提刑。他的老相好妓女李桂姐趋炎附势,认了吴月娘当干妈,也端起半个主人的款儿来——
那李桂姐卖弄他是月娘干女儿,坐在月娘炕上,和玉箫两个剥果仁儿、装果盒。吴银儿三个在下边杌儿上,一条边坐的。那桂姐一径抖搜精神,一回叫:“玉箫姐,累你,有茶倒一瓯子来我吃。”一回又叫:“小玉姐,你有水盛些来,我洗这手。”那小玉真个拿锡盆舀了水,与他洗手。吴银儿众人都看的睁睁的,不敢言语。桂姐又道:“银姐,你三个拿乐器来唱个曲儿与娘听。我先唱过了。”月娘和李娇儿对面坐着。吴银儿见他这般说,只得取过乐器来。当下郑爱香儿弹筝,吴银儿琵琶,韩玉钏儿在旁随唱,唱了一套《八声甘州》“花遮翠楼”。
居然自己坐在一边,让三个小姐妹唱曲听。吴银儿气不过,跟应伯爵说了,应伯爵帮她分析:她这一是惧怕你大爹权势,二是恐怕他去院里的机会少了,不如认个干女儿,长期往来。你到明日,也买些礼物,认与六娘做干女儿就是了。
应伯爵真是人情练达,世事洞明。果然,看到吴银儿跟李瓶儿关系好,轮到李桂姐“一声儿也不言语”,只跟吴银儿使性子,两个不说话,闹崩了。
不过,事情还没完。后来,清河县又有了新的青楼头牌郑爱月,她凭着出众的美貌,精心打造的文艺范儿,成了西门庆的新欢。她心思更深,为了笼络西门庆,巧妙出卖了李桂姐,李桂姐遂失了宠。
每个人都在热切地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充分体现了“他人就是地狱”。
第41回,吴月娘做主,给李瓶儿的儿子官哥和乔大户的女儿结了娃娃亲,众人贺喜,给吴月娘、乔大户娘子和李瓶儿簪花递酒,很是热闹喜庆。潘金莲被冷落,一肚子不痛快,先是怼了西门庆,又被西门庆骂,越发急了,便跟玉楼诉苦——
金莲道:“早是你在旁边听着,我说他甚么歹话来?他说别家是房里养的,我说乔家是房外养的?也是房里生的。那个纸包儿包着,瞒得过人?贼不逢好死的强人,就睁着眼骂起我来。骂的那绝情绝义。怎的没我说处?改变了心,叫他明日现报在我的眼里!多大的孩子,一个怀抱的尿泡种子,平白扳亲家,有钱没处施展的,争破卧单没的盖,‘狗咬尿泡——空喜欢’!如今做湿亲家还好,到明日休要做了干亲家才难。‘吹杀灯挤眼儿——后来的事看不见’。做亲时人家好,过三年五载方了的才一个儿!”玉楼道:“如今人也贼了,不干这个营生。论起来也还早哩。才养的孩子,割什么衫襟?无过只是图往来扳陪着耍子儿罢了。”
这就是“两孩儿联姻共笑嬉,二佳人愤深同气苦。”欢乐是别人的,荣耀是别人的。一向情绪稳定的孟玉楼,也不淡定了。
如果韩愈看见,必定脱口骂:“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如是哉!”孔子也叹:“小人长戚戚”,“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里的“小人”,是指低层百姓。孔子的道德要求,是针对君子即贵族阶层的,“礼不下庶人”。
然而,“小人”虽无德,那些被孔子寄予厚望的上层,不也礼崩乐坏,战乱频仍?道德状况实在也不怎么样啊。
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当然知道,所谓贪婪、嫉妒等人性的弱点,并非“小人”的专利。奥地利学派就分析过经济领域的攀比心理,“有些人当自己的愿望得到满足后,还希望看到他人的努力遭到失败。”所以,“价值是主观的”。
在《金瓶梅》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和考量,都是“理性经济人”,禁不住打量,也经不起考验。
西门庆的女人里,老大吴月娘最本分也最愚钝,首先,一心保自己的地位,只要不挑战自己大房的位置,就和稀泥。其次,就是贪财。李瓶儿要转移财物,是她提醒西门庆,不要走大街,要从墙上偷运过来,最后堆在了自己屋里,极其精明。
花子虚死后,李瓶儿要嫁给西门庆,吴月娘却对西门庆说:你不好娶她,她孝服未满,花子虚又是你兄弟,咱们还收着她这么多东西。此处张竹坡批:“然则不娶她,此东西将安然不题乎?写月娘欺心险行,可恨!可恨!”
李瓶儿死后,金莲跟西门庆要李瓶儿的皮袄,吴月娘忿忿不已,她觉得李瓶儿的东西都应该是自己的,对西门庆发牢骚:
“他死了,嗔人分散他房里丫头,相你这等就没的话儿说了。他见放皮袄不穿,巴巴儿只要这皮袄穿。早时他死了,他不死,你只好看他眼儿罢了。”
后来,还梦见金莲跟她抢皮袄。待西门庆死后,刚过二七,吴月娘便吩咐:“把李瓶儿灵床连影抬出去,一把火烧了,将箱笼都搬到自己房里堆放。”张竹坡评曰:“久矣想其如此,今日方遂其意。”
西门庆死后,伙计韩道国和来保从扬州贩布回来,韩道国在船头站立,看见对面街坊坐船而来,对方举手道:“你家老爹从正月间没了。”船很快过去,韩道国却顿起歹心,打定了主意,不告诉来保。到了码头,卖掉一半货物,拿着一千两银子回自己家。一开始韩道国还想自己留一半,给吴月娘一半,是王六儿的一番话让他改了主意。
王六儿的逻辑是:当初他包占了我,我要这银子应该。这逻辑当然不对,因为西门庆生前,已给王六儿买房子送银子,交易两清了。而韩道国跟西门庆是合伙做买卖,还拿了一部分股份,一码归一码。但在王六儿的世界里,“有天理就没饭吃哩!”韩道国也被说服了。于是,二人带着银子到东京投奔女儿去了。
家人来保,见韩道国卷银而逃,自己也不甘落后,偷偷昧下一千两银子的货,赖到韩道国头上,把自己打扮成不沾便宜的好人。
月娘与了他二三十两银子房中盘缠,他便故意儿昂昂大意不收,说道:“你老人家快收了。死了爹,你老人家死水儿,自家盘缠,又与俺们做甚?你收了去,我决不要!”一日晚夕,外边吃的醉醉儿,走进月娘房中,搭伏着护炕,说念月娘:“你老人家青春少小,没了爹,你自家守着这点孩儿子,不害孤另么?”月娘一声儿没言语。
他在外面偷偷买了好房子,还开了杂货铺儿。老婆惠祥在自家房里,穿金戴银,出门串亲戚坐轿子,一下子阔了起来。一回到西门家,立马就换了惨淡衣服,装穷,里外只瞒着吴月娘一个人。
应伯爵虽没银子可拐,迅速挂靠了张二官,撺掇他花三百两银子买了李娇儿,把春鸿也带了过去,还建议张二官买五娘潘金莲。他还是以前的应伯爵,只是西门庆换成了张二官。
十兄弟中的吴典恩和云理守更是十分奸险,一个捏造平安和吴月娘通奸,一个想吞掉西门庆家产。
三
作者感慨:“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这是《增广贤文》的谆谆告诫,揭开的是四书五经之外那个暗流涌动的世界。这本书恰好也集成于明中叶,跟《金瓶梅》成书的年代差不多。
再看先贤们的教导:“出淤泥而不染”,“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在思想史上被称为“大传统”;民间箴言却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马瘦毛长人穷志短”。后者见招拆招,创造了一个悠久厚黑的民间“小传统”。
于是,一面是思想史的“大传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另一面却是现实世界“小传统”:“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如此悖谬,如此黑色幽默。
这种名实不符的现象,《金瓶梅》里,处处皆是。
开头就是西门庆和应伯爵们“热结十兄弟”,玉皇庙的吴道官点香烛,念疏纸,又是桃园义重,又是管鲍情深,还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仁义礼智信齐全。
再看西门庆忙着勾搭兄弟花子虚的老婆李瓶儿,应伯爵们帮嫖丽春院,吃西门庆喝西门庆,以及西门庆死后,这些兄弟的所作所为……这一幕“热结”是多么讽刺。
与此同时,“武都头冷遇亲哥嫂”,武松当了都头,在街头偶遇哥哥武大,是潘金莲盛情邀请武松回家居住,武大一言不发。
书里读书人很少,倒有一个温秀才,被西门庆请来当秘书,每月3两银子管吃管住。西门庆没文化,但很尊敬读书人,每有酒席,都请来温秀才。西门庆应伯爵满嘴荤话,后者却满口之乎者也,
西门庆从东京述职回家,应伯爵和温秀才来看他:
说起一路上受惊的话。伯爵道:“哥,你的心好,一福能压百祸,就有小人,一时自然都消散了。”温秀才道:“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休道老先生为王事驱驰,上天也不肯有伤善类。”
还有一次,在妓女郑爱月处的酒局,另一个妓女吴银儿也来了,应伯爵开玩笑说这两个人倒是伙计,温秀才说:
“南老好不近人情。自古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同他做伙计亦是理之当然。”
其实他人品低劣,好男风,喜告密,奸画童,还喜欢窥探西门庆的房事。
至于上层的读书人比如蔡状元、宋御史们,也好不到哪里去。第74回“潘金莲香腮偎玉”,潘金莲在床上百般讨好西门庆,为他吹箫,趁机提出想要李瓶儿的皮袄。随后,宋御史来到西门庆家,商量借西门庆家里宴请侯巡抚——
见屏风前安着一座八仙捧寿的流金鼎,约数尺高,甚是做得奇巧。炉内焚着沉檀香,烟从龟鹤鹿口中吐出。只顾近前观看,夸奖不已。问西门庆:“这副炉鼎造得好!”因向二官说:“我学生写书与淮安刘年兄那里,央他替我捎带一副来,送蔡老先,还不见到。四泉不知是那里得来的?”
西门庆当然心知肚明,第二天就让家人包好送给了宋御史。
西门庆巴结上了东京的蔡太师,并当了其干儿子。蔡太师的管家翟谦给他来了一封信,信上提到:“新状元蔡一泉,乃老爷之假子,奉赦回籍省视,道经贵处,仍望留之一饭。”下书人又另外告诉西门庆:“翟爹说:只怕蔡老爹回乡,一时缺少盘缠,烦老爹这里多少只顾借与他,写书去,翟爹那里如数补还。”
西门庆何等精明,立刻心领神会。
果然蔡状元和安进士来了。西门庆设宴招待,还叫了四个戏子,让书童扮小旦。安进士好男风,拉着书童的手,一递一口吃酒,连曰:“此子可爱。”吃到掌灯时节,出来更衣,蔡状元拉西门庆说话:
“学生此去回乡省亲,路费缺少。”西门庆道:“不劳老先生分付,云峰尊命,一定谨领。”
同样是要东西,宋御史蔡状元们似乎也不比潘金莲、宋蕙莲们更高明。在金钱面前,在清河首富西门庆面前,读书人也不再矜持。
读书人的世界早就沦陷了。四书五经,成了升官发财的工具,岳不群层出不穷。比兰陵笑笑生早一点的王阳明,疾呼“知行合一”,致良知,为鼓舞人心向善,还说“满街都是圣人”。结果他死后,满街都是欲望。
说商业经济激发了欲望,也没错,但它充其量是一个契机,一个放大器。不仅欲望被放大,人性中的恶,也被激发。在《金瓶梅》里,我们会经常看见,那些隐匿的恶意如何浮现,以及人性多么经不起考验。
潘金莲步步黑化,在命运的岔路,选的总是最黑暗的那条。
还有李瓶儿,不仅跟西门庆偷情,还转移财产。花子虚刚吃了官司,她就把三千两银子和成箱的财宝,搬到西门庆家,说:“到明日,奴不就也是你的人了。”她成心等着这一天呢。所以,后来花子虚出狱,得了伤寒,李瓶儿也不找医生,故花子虚因气丧生。
就连孟玉楼,也有人性的至暗时刻。下人蕙莲跟西门庆勾搭上,孟玉楼们打牌,她在一旁指点,玉楼不悦:我们玩牌,有你什么事!孟玉楼还挑唆金莲,他爹要给蕙莲买房子,编银丝䯼髻,“就和你我辈一般,甚么张致?”金莲怒从心头起,发誓不放过蕙莲,她笑道:“我是小胆儿,不敢惹他,看你有本事和他缠。”
西门庆死后,她嫁给李衙内,陈敬济跑来敲诈她,她处理得相当狠辣,设计捉住陈敬济,还编织了罪名。连一贯赞她恬淡的张竹坡,也叹:“直如夜叉现形,钟馗出像。”
这就是《金瓶梅》,人心诡诈,暗流涌动。如果你是道德家,几乎所有人都会触怒你;如果你是老古板,这些人会让你如坐针毡;如果想寻找生命的意义,必然一无所得。
性本善,是儒家思想的逻辑起点。《大学》里的“明明德”,即人本来拥有纯净美好的品性,我们要发现它,保持它。儒家内部虽有理学和心学之争,但双方都承认性善,恶不过是私欲、人欲遮蔽了善。
然而,“大传统”终究敌不过“小传统”。前者太高调,不愿直面人性里的恶。因此,不管是“仁即爱人”,还是“善养浩然之气”,还是“存天理灭人欲”,都像沙上的城堡,经不起风吹雨打,也无法解释并应对真实的生活世界。
庄子讲过一个“盗亦有道”的故事,我们不妨把主角盗跖换成西门庆:
西门庆泡女人,从不霸王硬上弓,总提前试探知会,是礼;对女人不吝钱财,对朋友慷慨相助,是仁义;擅长跳墙偷情,却没被捉,是智;最后把潘金莲和李瓶儿娶进门,没始乱终弃,是信也。
庄子说儒家“明乎礼仪陋于知人心”,然!
人性如此复杂而幽深,远非抽象的道德理念所能涵盖。“它有自己的风暴,它有自己黑夜的奴隶”。
四
《金瓶梅》里的人怎么个个都是脏的,烂的,灰的,没一个好人呢?如果兰陵笑笑生听见这话,一定会诧异:这个世界上真有纯粹的好人吗?
恶有无数理由,善却往往命悬一线。对人性,对善恶,我们知道得太少,太单薄了。
在某种程度上,《金瓶梅》以绝对的写实,颠覆了我们对人性的浪漫想象,提醒我们睁眼看自己,看众生。
在中国传统文学史上,《金瓶梅》一直备受误解。有人说它是小黄书,有人说它太黑暗。可是,文学一旦背上“文以载道”,教化人心,就不诚实了,不敢踏入人性的暗河。结果,不是善恶有报,就是大团圆喜相逢……甘于“瞒与骗”。
《金瓶梅》是另类,堪称真正的写实主义。
我们来看妓女郑爱月。她一出场,“穿着紫纱衫儿,白纱挑线裙子。腰肢袅娜,犹如杨柳轻盈;花貌娉婷,好似芙蓉艳丽。”西门庆说她可恶,居然三番五次来叫了来。她一声儿也不言语,笑着同众人一直往后边去了。
到了后边,又是用洒金扇掩着粉脸,只是笑,非常特别。惹得吴月娘和潘金莲对她评头论足,又是看她的脚,又是拿她头上的金鱼撇仗儿看。她的房间叫“爱月轩”,摆设清雅,俨然青楼白莲花。
正是她,给西门庆出主意,去勾搭王三官的母亲林太太,再打王三官媳妇的主意:“爹难得先刮剌上了他娘,不愁媳妇儿不是你的。”人家王三官娘子没招她惹她,她为啥要算计人家?她这是投西门庆所好,牺牲别人,无所不用其极笼络他呢。
还有薛姑子和王姑子。李瓶儿生了儿子官哥儿,她劝其舍钱念经,因为富人孩子最易遭小人恨;官哥儿死了,她也振振有词:你儿子是你前世仇人,多亏你舍银子念经,不然早被他害死了。如今他害不了你,自己倒死了,阿弥陀佛!
这番说词,居然天衣无缝。李瓶儿死后,她该如何自圆其说?书中写李瓶儿死后,众人忙乱,且看王姑子口中喃喃呐呐,替李瓶儿念《密多心经》、《药师经》、《解怨经》和《楞严经》……就问你服不服!
弗洛伊德发现了人的潜意识:“人的心中好像一直有一片荒芜的夜地”,这让他眩晕。东野圭吾也说:“只有两种东西无法直视,一是太阳,一是人心。”
兰陵笑笑生这样剥皮见骨,鲜血淋漓,把人生,人性写尽写透,是为了什么?真的便如张竹坡所言,《金瓶梅》是一部愤世嫉俗之书?就是为了骂尽一切奸人坏人,要榨出他们袍子底下的各种“小”来?
非也非也。
所谓愤世嫉俗,骂尽一切奸坏,是站在道德高地,俯视众生的姿态。想要进入《金瓶梅》的世界,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甩掉道德优越感,扪心自问:我们真的比《金瓶梅》里的这些人更好吗?这些人真的有那么坏吗?
《金瓶梅》这本书,歧路重重,进入它并不容易。
初读时,你可能后背生凉意,感慨人心之恶;再读,优越感会逐步瓦解,开始承认:西门庆、李桂姐们其实就是普通人,他们有私心,也贪婪,还损人不利己,但也并非大奸大恶。
其实,他们也就是我们。
想想智人是如何成为地球主宰的,就知道人类多残忍。霍布斯说,你以为淳朴的“自然状态”,其实意味着“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
人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第58回来了一个磨镜老头,磨完镜子不走,哭诉儿子不争气,老婆生病。玉楼和金莲见他可怜,又是腊肉又是小米接济。结果平安说:
“二位娘不该与他这许多东西,被这老油嘴设智诓的去了。他妈妈子是个媒人,昨日打这街上走过去不是,几时在家不好来!”金莲道:“贼囚!你早不说做甚么来!”平安道:“罢了,也是他的造化!可可二位娘出来看见,叫住他,照顾了他这些东西去了。”
在兰陵笑笑生的笔下,几乎所有的恶,都是可以理解,甚至可以原谅的。写尽人性的破败,依然能心怀慈悲,这比讽刺、揭露和愤世嫉俗,更高级。
所以我们看,薛姑子们那么贪婪,但她们是李瓶儿的寄托。她临死前,格外依恋她们,她太孤独,太恐惧,太想抓住一点东西,即使是一根稻草。
当应伯爵在酒席上唱:“老虔婆只要图财,小淫妇儿少不得拽着脖子往前挣。苦似投河,愁如觅并。几时得把业罐子填完,就变驴变马也不干这营生。”李桂姐哭了起来,她也很苦的。此时此刻,我们原谅了她的刻薄、虚伪和小聪明。
应伯爵帮嫖贴食,没啥格调。但这样的人,也有温暖一刻,比如替小优李铭说话,帮穷朋友常峙节跟西门庆借钱。他感慨兄弟祝麻子被官府带走:“似这等苦儿,也是他受。路上这等大热天,着铁索扛着,又没盘缠,有甚么要紧!”这样的应伯爵,似乎不那么令人讨厌了。
很多人都以为西门庆是恶人,其实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他死前交代后事,抽抽搭搭地哭,很可怜;在潘金莲“淮洪”般的伶牙俐齿面前,他束手无策,只好呵呵笑了,又有点可爱;郑爱月的伪文艺范儿,他分外迷恋,应伯爵一番话说到他心坎里,立马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又肤浅又虚荣。
这样的贪念和软弱,其实人人都有。
只有跳出绝对的善恶视角,才能看见这样多元的世界,这样丰富的人性。
卡尔维诺言:“阅读就是抛弃自己的一切意图与偏见,随时准备接受突如其来且不知来自何方的声音。”相信我,读《金瓶梅》便如此。
张爱玲说《金瓶梅》和《红楼梦》是她一切的源头,她自己也写尽了人性恶。阿城喜欢她,北岛不解,阿城说:“把恶写尽,回过头,一步一光明。”
福楼拜写偷情,陀思妥耶夫斯基写杀人,马尔克斯写乱伦,我们为什么读他们?因为伟大的文学,让我们看见世间的深渊,以及人性的深渊,照见自己,并承受自己。
看兰陵笑笑生写他们说话,就像唱歌一样。王婆买酒菜淋湿了衣服:大官人要赔我。西门庆道:“你看老婆子,就是个赖精。”婆子道:“也不是赖精,大官人少不得赔我一匹大海青。”
西门庆要去山洞私会蕙莲,金莲骂他:“你是王祥?寒冬腊月行孝顺,在那石头床上卧冰哩!”
蕙莲埋怨西门庆:你那嘴,“就是个会走水的槽。”“把你到明日盖个庙儿,立起个旗杆来,就是谎神爷!”
小厮钺安给蕙莲说来旺被流放:“俺哥这早晚到流沙河了。”
占卜婆子说李瓶儿:“你尽好匹红罗,只可惜尺头短了些”。
李瓶儿安慰西门庆:“往后的日子多如柳叶”。
这就是人性,就是生活,藏污纳垢,却活色生香,生生不息。
写到这里,想起木心说:“诚觉世事皆可以原谅”。
兰陵笑笑生早就原谅了他们。所以,他笔下的人尽管复杂幽微,却不一味阴暗。他甚至爱着他们,不然没耐心写下他们的卑琐,以及他们的哀乐。
劉曉蕾專欄
劉曉蕾:作家,大学教师,现居北京。得到APP《刘晓蕾讲透〈金瓶梅〉》课程主理人。著有《作为欲望号的〈金瓶梅〉》、《刘晓蕾〈红楼梦〉十二讲》、《情僧、英雄与正经人:14位人物解透〈红楼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