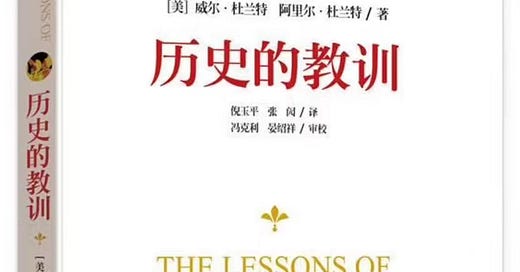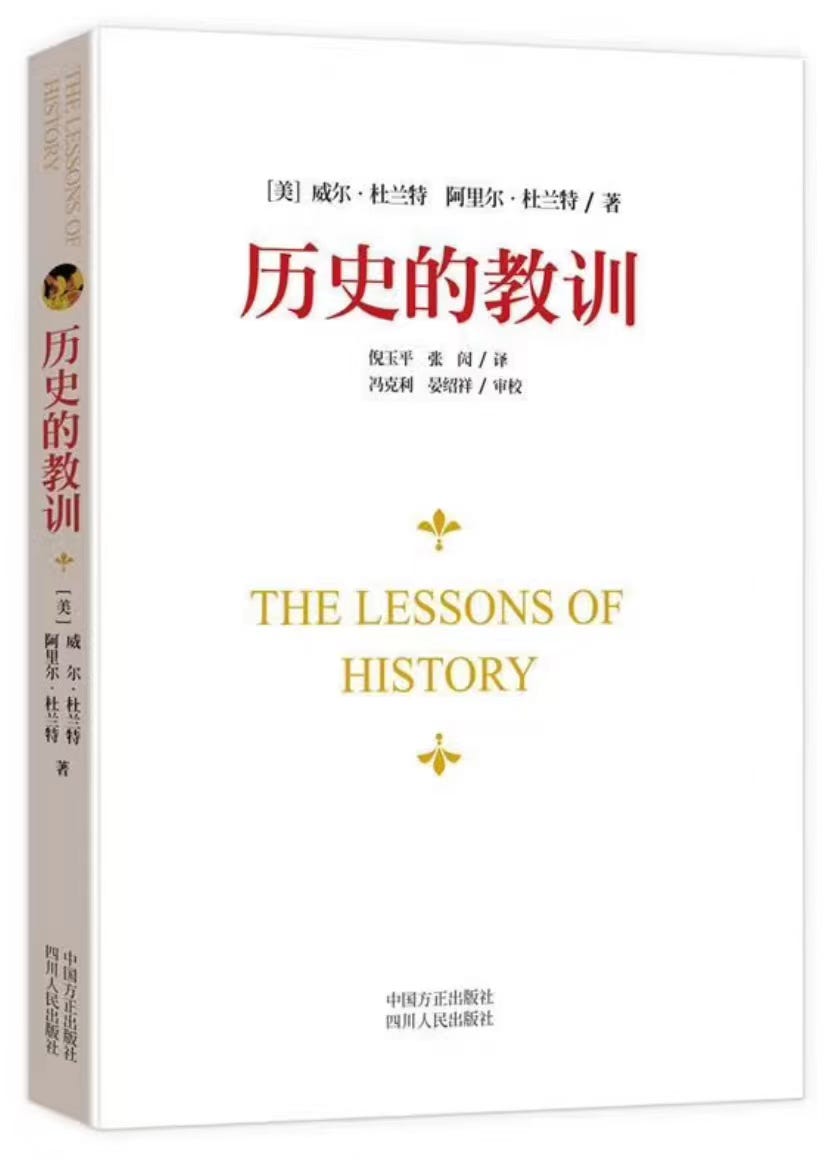劳伦斯 | 寒风中的乐观主义者
人在冬天是容易忧郁的。天很早就黑了,冷飕飕的风,凄惨惨的雨,地铁口里钻出一个个缩着肩膀匆匆而行的人,幽灵般消失在越来越深的夜色里。刚说着Winter is coming,凛冬便已骤然而至,让人猝不及防。
国人最常说要以史为鉴,以至于如今的中老年男士们都宣称爱好历史,尤其津津乐道于引人入胜的野史,并从中钻研人生智慧;女士们也不甘落后,不过她们更喜欢从绚丽的宫廷剧中,去寻找应对现代家庭生活的攻略。历史丰富多彩,它可以为任何目的和结论提供证据。正因如此,我们才有必要提防某些不怀好意的人,他们会像韦小宝那样,通过细节的生动和真实赢取信任,在不经意中转移视线,撒下弥天大谎。
秋雨绵绵之际,我抄起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的小册子。这位大学者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经济大萧条、宗教信仰的崩塌、社会道德的变迁,终生笔耕不已。除了和夫人共同创作十一卷《世界文明史》,他还写下《哲学的故事》、《论生命的意义》等名著,九十五岁写完《落叶》,和携手七十年的太太相差两周离世。
在杜兰特看来,历史的梗概会让人心平气和,以较为“乐观的偏见”来选择证据,也许可以从中引申出更为惬意的思想。六十年前,在《历史的教训》最后一章,他如此写道:“历史学家从不悲伤。”
几十万年里,地球就像孕育历史的子宫。依照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地理环境论,很多民族可能会责怪他们的祖先不够进取,没有选个风水宝地。不过,随着技术的发展,地理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小,未来可能只有极少数的小学课本还会赞美地大物博。地形特征和资源或许依然会为某些实业提供机会,但人类的本性在于迁移、远行和探索,他们的步伐不会停止,他们的目标是虚拟空间和宇宙太空。扎克伯格正在勾画元宇宙的蓝图,而马斯克也想到火星上去寻找人生的意义。
扎克伯格和马斯克都是富有想象力的领导者,我们拥有很多方式去关注甚至追随他们。杜兰特说:“是人类,而非地球,创造了文明。”虚拟世界和太空里会建立起新的文明,我们已经处于并可继续憧憬这样的未来:重要的将不是你在哪里,而是你想在哪里。
生物学给历史的第一个教训是,生命即是竞争。选边、争夺和对抗,是人类自带的生存基因,我们的血液中,一直都在流淌着千万年的部落故事。哪怕今天已拥有后现代的科技,我们的情绪却依然停留在石器时代。
随着信息、交通、武器和宣传方式的进步,部落身份的认同范围在扩大。历史表明,野心家向来都是部落心理体系的黑客,是他们将竞争扩展为大规模的人民战争,使无数生灵涂炭。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六千万生命消失;如今核武器的威力,足以炸翻若干个地球。爱因斯坦悲哀地感叹:如果爆发第四次世界大战,人类使用的武器,将重归石头和木棍。
人类从远古走来,历经狩猎与采集、农业、工业三个时期,如今进入信息时代,也许我们终于可以向竞争的更高层次迈进。当物理的边界渐渐消失,生命畅游于现实与虚拟之间,数字资产成为人类生存最重要的资源,为任何领土而战都将显得愚不可及,杀戮和牺牲更将失去意义。地球上的我们,可能会面对其它星球上野心勃勃的物种,可能会面对共同的危机,那时,我们也许会真正成为一家人。
生物学给历史的第二个教训是,生命即是选择。其实我不必对自己和布拉德-皮特之间天然的不平等耿耿于怀,大自然早就对我梦想中自由和平等的结合付之一笑。自由竞争会使人们之间天然的不平等呈几何式增长,乌托邦式的平等早已被遗传学判了死刑。
我们应该接受这个残酷的真实:最有“能力”的总是少数人,财富的集中,是“能力”集中的结果。人类连接的程度越高,财富集中和不平等的程度也越高。所有的经济史都是社会有机体缓慢的心脏跳动,财富的集中和再分配,便是它巨大的收缩和扩张运动。再分配肯定会发生,其方式可以是和平的,也可能是暴力的,中间的差距,代表着制度的智慧。
革命最常以消灭不平等为口号,历史却并不为这样的革命辩护,与过去断然决裂所导致的狂热,可能会带来更大的灾难和毁灭。强制性的再分配很快就会产生新的占有和特权的不平等,形成新的少数人权力。
立场温和的哲学家倾向于法律和教育机会的大致平等,而历史一再表明,只有那些让所有个人潜能得到发挥的社会,才能在群体间的竞争中获得生存优势。我们应该记住杜兰特的话:“唯一真正的革命,是对心灵的启蒙和个性的提升;唯一真正的解放,是个人的解放;唯一真正的革命者,是哲学家和圣人。”
生物学给历史的第三个教训是:生命必须繁衍。大自然并不嫌贫爱富,她对文明和野蛮也不加区分,她更乐于看到低生育率的群体被繁殖能力更强的群体取代。从基因延续的角度看,体魄上的健康可能比智力上的优越更有价值。尼采认为,德国最优异的血液流淌在德国农民的血管里。对种族繁衍来说,哲学家和电竞冠军都不是最适合的材料。
一百年前,当丹麦人凯伦-布里克森(KarenBlixen)经营她在恩贡山下农场的时候,肯尼亚的人口只有三百万,现在这个国家的人口已达到五千万。五十年前,非洲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是百分之十,如今是百分之二十。据预测,到2100年,非洲人口将达到四十亿,占世界人口的比重接近百分之四十。那时,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很可能将是西非的尼日利亚。
未来几十年里,欧洲人口下降的趋势仍将持续,东亚地区如日本和韩国等地的人口将有断崖式下跌,人们已不再把生儿育女当成人生的必需。如果说基因繁殖、适者生存是进化的第一原则,那么发达和富足显然并非自然之母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爱国主义者都应该好好锻炼身体,回家多生几个孩子。
需要牢记的是,几十万年里,人类从没有停下迁移的脚步,种族在融合中繁衍,文明从废墟中重生。人类在相互交融创造出奇迹,世界更加色彩缤纷。那些获得启蒙的心灵,将会善待每一个男女,欣喜地沉浸于人类的璀璨多姿之中。而那些自以为是的悠久和纯正,都将只能带着偏见悲哀地走进坟墓。
我们需要忧心忡忡地担心人类的道德吗?在历史的进程中,每个阶段的道德观都会有别于上一个阶段。狩猎时代所崇尚的凶残和暴饮暴食,在农业时代即被视为野蛮;乡村生活提倡的贞操、早婚、多生多育,只是依靠土地为生时应对大自然的秩序要求;当进入工业时代,这些美德便显得不合时宜:叛逆而独立的年轻男女离开故土,不再受亲人和村民的监督限制,他们更愿意在素不相识的城市人群中为所欲为。
历史上看,被人们诟病的道德松弛,并不见得是衰败的先兆。杜兰特说:“人的罪恶可能是他崛起时的遗迹,而不是他堕落时留下的耻辱标记。”
可以预见,在信息时代里,美德将重获定义:言情小说家们注定会失业,女士们穿衣服也会更考虑舒适,而非刻意显示某些特征;起源于农业文明的婚姻制度将逐渐瓦解,正念冥想、致幻剂和多偶性体验很有可能取代宗教和主义,用于抚慰人类脆弱的心灵。
时代在进步,历史上到处都是文明被摧毁的遗迹,这难免让人唏嘘。其实历史大体上总是重复着,人类天性的改变和地质变化一样缓慢悠然。对于青铜时期文明毁灭的原因,我们未必有确定的结论。但对于孔子和苏格拉底之后两千多年里发生的事情,我们有足够的把握来总结规律。文明忌讳封闭,理科朋友们在大学时代就用熵增原理推断出这个结论;谎言可能有助于治理国家,但同时肯定也会悄然腐蚀文明的根基。
文明的衰落是个漫长的过程,最后的征兆就像年迈的老人 — 身体不再吸收养分、语言退化、脾气霸道任性。当然,群体并不是真正具有生理功能的有机体,它必须依赖其个体成员的大脑和神经,进行思考和感知。当一个群体或文明衰亡的时候,它并不是由于群体生命的神秘限制,而是由于领导者们在应对时代潮流的挑战中遭受了失败。气急败坏之后的孤注一掷可能会成为最后一击,让一个文明寿终正寝。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说:“政治上的宽宏大量往往是最为明智的,一个伟大的帝国与狭隘的心胸组合在一起就糟糕了。”
旧文明会消失,衰落之前的辉煌往往只是回光返照。但这是一幅令人沮丧的图画吗?不完全是,无论是对个体还是文明,都无法做到生命永恒长生不老。死亡是自然现象,假如死亡来的恰逢其时,它便可以得到宽恕,而且并非无益。文化让人类的灵魂世代相传,人的生命会通过传宗接代而超越死亡,而一个有生命的文化也会脱胎换骨、超越时空,在新的疆域上将遗产传递给它的继承者。
如果将人类文明比喻为操作系统,它的生命力在于能否做到开源、能否持续升级。当技术将全人类连接在一起,开源的文明操作系统也许会趋向大同,而那些封闭的文明操作系统则会被淘汰。在一个开源的操作系统上,可以运行无数的软件。文化元素就像软件,只有开源的文明操作系统,才能支持多元的丰富多彩的文化软件 — 那些诗歌般的古老语言,那洋溢着大自然味道的美酒佳肴,那些弥久不失魅力的古迹,那些生命奔放的舞姿。
文明会真正死亡吗?答案是否定的。古希腊文明就像是一个开放的操作系统,它并没有死亡,而是外壳不在了,栖息地改变了,内涵得到了延伸,以其博大精深,永远刻在人类记忆之中。今天《奥德赛》的读者,人数上已远远超过荷马生活的那个时代。在全世界数不清的剧场、图书馆和讲堂,我们都能听到传诵希腊神话和哲学精神的朗声回响。
在浩瀚的宇宙里,人是微不足道的,历史并没有对善有善报提供任何可靠保证。如果说有宿命,那么它肯定是盲目的,不过这也许是公正的。人类的生存并没什么意义,但人类居然可以亲身赋予生命以意义,甚至有时能让这种意义超越死亡。对此,我们足以深感自豪,为人类盗火而备受折磨的普罗米修斯也会引以为傲。当我们将目光移过那些愚蠢和罪恶,移过无数的恐怖陈列室,我们应能看到一座不朽的英灵之城,一个广阔的思想国度,那里有无数的各种肤色的圣哲贤明、科学家、诗人、艺术家、音乐家和志同道合者,又跳又唱、谈笑风生。
这样的国度没有边界,这里的欢歌没有终场,这座城市欢迎所有人,包括那些衣不蔽体的逃犯和筋疲力尽的流浪者。如果能看到这样的场景,不管寒风多么凛冽,我们的内心都应该是温暖和愉悦着的。
2021.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