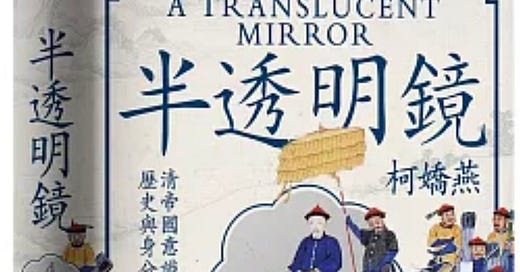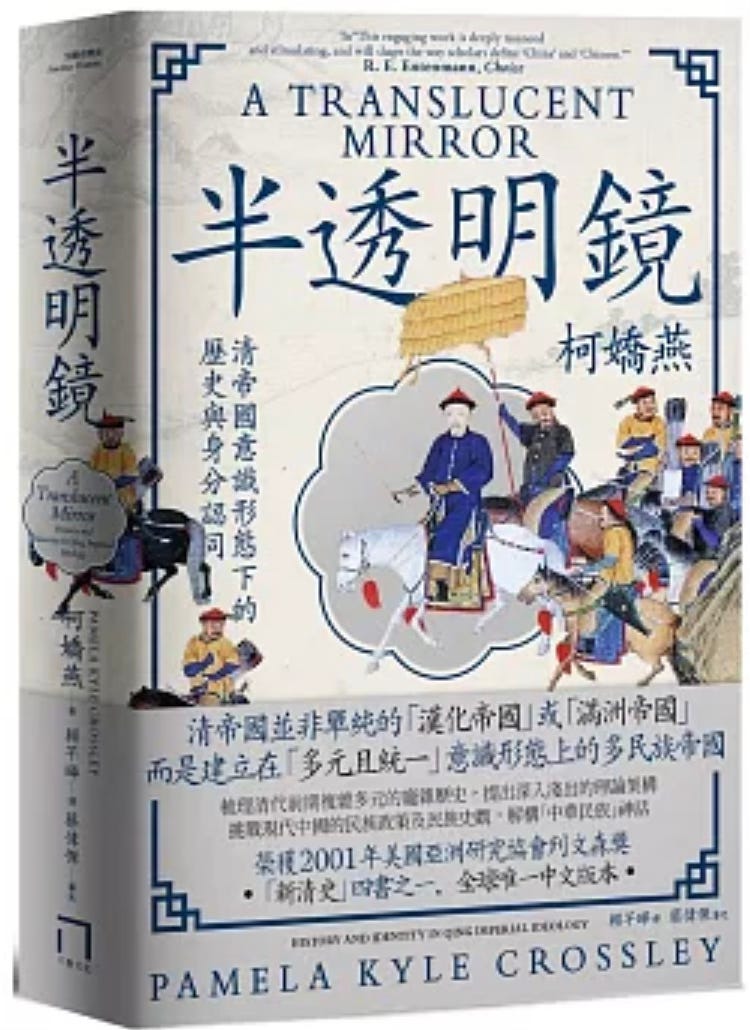柯嬌燕 | 半透明鏡:清帝國意識形態下的歷史與身分認同
半透明鏡:清帝國意識形態下的歷史與身分認同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作者: 柯嬌燕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24/10/09
語言:繁體中文
內容簡介
─了解「新清史」脈絡必讀的四本書──
羅友枝《最後的皇族》、柯嬌燕《半透明鏡》
歐立德《滿洲之道》、路康樂《滿與漢》
──柯嬌燕《半透明鏡》──
榮獲2001年美國亞洲研究協會列文森獎
挑戰中國的民族政策及民族史觀,解構「中華民族」神話
引起中國當局及學者強烈反彈!
◆新清史是什麼?
新清史是1990年代發源於美國漢學及歷史學界的學派,代表學者有羅友枝、歐立德、濮德培、柯嬌燕等人。該學派從「少數滿洲人如何統治廣大且複雜的中國」、「由滿洲人建立的王朝對中國傳統(漢人)的歷史論述有何影響」這兩個問題意識出發,試圖從「非中原王朝史觀」、「內亞/東亞帝國史觀」、「非漢族中心主義」、「多民族」視角,來重新修正、書寫過往的清代史。
◆柯嬌燕的《半透明鏡》最大貢獻為何?
本書梳理複雜多元的清代前期歷史,提出一套理論框架,進而對早期清帝國統治的意識形態,與歷史書寫及身分認同之間的關係,有全面且深入的解釋。
◆半透明鏡是什麼意思?
對古代皇帝來說,鏡子有兩個意涵,一是具有道德或規勸意涵,「歷史之鏡」可以指出統治者的缺失,即「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但「歷史之鏡」在帝國的意識形態上,卻是不透明的,其起源、動機及手段都被刻意隱匿,本書期望能揭露當時的主旋律,進而讓意識形態的形象變成可見的、半透明的。
◆什麼是清帝國統治的意識形態?
由於清帝國是由皇帝所統治,我們可以將清帝國統治的「意識形態」跟清帝國的「皇權」視為互為表裡、不可分割的一體兩面。清代的皇帝會利用政治、文化、經濟、儀式等手段拓展皇權的影響力。具體操作上,皇帝會利用詔令、日記、紀念碑文等官方文件,並以多語言形式(滿文、漢文、蒙文等)來強化皇權的正當性與普世性,皇帝應統御率土之濱,皇帝應撫育普天之下所有子民。
◆清帝國的意識形態跟過往的中原王朝/征服王朝,有什麼差異?
自新清史學派出現以來,「漢化觀點」或「滿洲觀點」就一直是學術討論的熱點。但本書作者柯嬌燕認為,清帝國統治的意識形態當然會受到滿洲皇帝的出身影響,但也不宜過於簡單二分。以「滿洲征服」這個概念為例,柯嬌燕認為「滿洲征服」是多元(多民族)力量的結合,滿洲人不單純是征服者,漢人也不單純是被征服者。大清之所以能成功入主中原,是結合滿洲人、蒙古人、漢人的力量,且主要靠的是漢人士兵,如此還算是「滿洲人征服漢人」嗎?清帝國還算是「征服王朝」嗎?
◆清帝國的意識形態與現代中國
清帝國在試圖在強化國家權力的同時,也同時維持政治組織上的相對多元及獨立性,例如始終維持著高度獨立狀態的蒙古與西藏,這是清帝國從本質上有別中國歷代王朝的關鍵之處。清帝國並非單純的「漢化帝國」或「滿洲帝國」,而是建立在「多元且統一」意識形態上的多民族帝國,這最終深深影響了現代中國(不論是中華民國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民族認同之建構。
得獎紀錄
▸2001年美國亞洲研究協會列文森獎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柯嬌燕(Pamela Kyle Crossley)
1955年生,現任美國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歷史學教授,她長期研究清史、中亞史、比較歷史和全球史,著重於探討現代認同的根源,特別是民族認同與現代早期時帝國統治結構的關連性。曾獲古根漢學者獎,並以《半透明鏡》榮獲2001年美國亞洲研究協會列文森獎。主要著作有《孤軍:滿洲三代家族與清世界的滅亡》(Orphan Warriors,1991)、《半透明鏡》與《什麼是全球史?》(What is Global History?,2008)。
審定者簡介
蔡偉傑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學士、碩士,美國印第安納大學中央歐亞學系碩士、博士。現任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研究方向為蒙古時代以降的歐亞世界史及內亞與中國關係史,著重於帝國、族群、移民與法制史領域。近年來除了從事學術研究外,也透過網路媒體,積極推廣蒙古及內亞的相關歷史知識。著有《從馬可波羅到馬戛爾尼》(八旗文化,2020)。
譯者簡介
賴芊曄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世界史組碩士,譯作有《古代中國與越:中國南方邊境的自我認知與族群認同》、《馬、車輪和語言:歐亞草原的騎馬者如何形塑古代文明與現代世界》、《木蘭與麒麟:中古中國的突厥伊朗元素》等書。
目錄
謝詞
緒論
意識形態、治權,以及歷史/征服與過去的庇佑/帝國普世主義與身分認同界線
第一部 長城
第一章 身分認同的試煉
祖源論述/奴兒干的政治名稱/遼東人
第二章 忠的特質
早期尼堪的政治光譜/征服與區異/忠誠的擬人化
第二部 父家
第三章 統治的邊界
汗權的起源/合議共治的刺激/謀逆罪的重塑
第四章 帝國與身分認同
屈從與平等/帝國權威的生發/真實性/跨越限制
第三部 天柱
第五章 轉輪王
中心/爭辯過往/言語的力量
第六章 普世前景
八旗菁英/隱蔽的過去/滿洲性/追隨成吉思汗/虛空的帝國成員
後記 帝國末期的種族與革命
參考書目
緒論
長久以來,共同體、團結與共同利益等概念似乎滋生出了現代「民族」(national)和「族群」(ethnic)認同,這些概念在幾百年間以不同的形式呈現,並在過去一百年不斷受到印刷與數位媒體的精雕細琢,以及帝國主義衰退的推波助瀾。對此,我們不能完全以謬誤視之,畢竟套句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名言,十九和二十世紀的許多人群確實將自我想像成「共同體」。此解釋之所以流於浮濫,在於其幾乎能強行扣在各種不同的民族歷史之上。然而,在詮釋共同體概念如何被宣傳成民族認同時,不管這個典範(paradigm)有多好用,仍然無法釐清每個民族敘事的本質。鋪墊這些身分認同的文化元素起源各異,而且這些元素在理論上並非中性,也無法互相代換。有鑑於此,史家試圖爬梳出現代民族主義運動中所能取得的各種偶像,能體現出多少過往權威的存續。對一些現今仍存在的民族而言,所謂「過往」是由征服帝國所統治的幾個世紀,其治權亟需構建出一套隸屬類別,以因應並體現出政權合法性與合璧性(編按:下文會加以解釋)的多樣符碼。清帝國(一六三六至一九一二年)就是如此運行其治權,多樣的歷史認同便是其歷史結果,所造就的特殊影響不僅反映在十九世紀萌芽的民族和族群概念,更反映在身分認同的基本概念上。
有清一代,「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觀念互相形塑。同樣在十七世紀,努爾哈赤汗(一六一六至一六二六年在位)與治下各族人群關係的表述方式,就與清朝首位皇帝皇太極(一六三六至一六四三年在位)的從屬概念大相逕庭。十八世紀,特別在乾隆朝(一七三六至一七九五年),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意識形態關係又歷經另一次翻轉。由於征服的腳步日益趨緩,並逐漸深根於文人統治,此轉變不僅讓關係變得更為複雜,對有抱負的官員與在野知識分子菁英的教化,也有了新的支點。為方便介紹,這些轉變的本質可粗略簡化成以下典範:努爾哈赤打造的汗權之下、象徵性的主奴規範(我幾經思考後決定使用這些詞彙,並會在第二章和第三章進一步解釋),在十七世紀中後期的大清皇權治下,被修正成一種高度區異的文化與道德認同體系。十八世紀間,皇權擔負著扮演治下各族人群的重責大任,這成為普世統治中歷史、文學、意識形態、建築和個人的表述主題;但由於治權未能加以定界,當中的朝廷表述日益抽象,亟需對其內部領域定界,因而身分認同的標準必然會植入此種意識形態中。
對於大眾讀者來說,上述的說法似乎不證自明,但對專家來說,可能就流於說教且問題重重。對所有研究清代及清史所涵蓋的眾多學科的學者而言,接下來的說法都失之偏頗,畢竟所有人都試圖在某些要點上,提出與常見歷史敘事不盡相同的觀點。話雖如此,清史研究中的某些基本觀點仍是廣為接受的。一般認為,清帝國是十七世紀初由滿人建立、或說受滿人控制,抑或是由滿人賦予其特定的政治與文化布景。在「滿洲」(Manchu)之名制度化之前,清的前身金國(通常稱為後金)主要由「女真人」組成,在西元八○○至一六三六年左右的泰半時期,他們的名字都能找到漢字佐證。一六三五年,女真正式成為滿洲。除卻女真/滿洲,清廷還招徠了一些蒙古人,於一六四四年攻占明朝首都北京,征服中國。在此同時,清廷已經透過徵募或強行將許多漢人劃為清朝軍事組織「八旗」下的「漢軍旗人」。八旗主導了一六四四年的北京進攻行動,並在隨後的四十年鞏固了清廷對華中與華南的控制。十七、十八世紀之交的清統治者中,最重要的當屬開創不朽盛世的康熙帝(一六六一至一七二二年在位),他大刀闊斧,調和朝廷與既定的漢人價值觀,以賦予朝廷穩定性和正當性,而這是單靠征服難以企及的。清朝在十八世紀迎來頂峰,包括在政治控制上如統御滿洲、蒙古、東突厥斯坦(新疆)、西藏和中國,以及那些承認清朝在朝廷視察制度上具有權威的國家,有時亦稱「朝貢體系」。朝貢體系是指在經濟實力上以茶葉、瓷器、絲綢與其他商品等出口品,使歐洲陷入貿易逆差。在軍事擴張上,則持續於東南亞開戰,並鎮壓「叛亂群體」,無論該群體是由「族群」或帝國內的社會所定義。此等黃金時代在乾隆治下達到鼎盛,乾隆帝是清統治者中最「儒家」、最「漢化」,或可說是最輝煌的統治者。當乾隆帝於一七九六年退位、一七九九年駕崩後,清帝國陷入「衰退」,處處受制於歐洲、美國,乃至日本的擴張主義、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行動。
相較於一般對大清起源與征服的理解,本書最大的殊異之處,在於並未將「滿洲」、「蒙古」與「中國人」(漢人)的整體身分認同,看作是新秩序的基本要素、來源或基石。我認為,這些身分認同是一八○○年之前,帝國集權過程中的意識形態產物。日漸茁壯的帝國制度仰賴地方治權意識形態的抽象概念、忽視與整合,有利於在帝國出版、建築、儀式與個人表述中構建並傳播,此處以「帝國成員」(constituencies)稱之,但通常會具體稱之為「人群」(peoples)、「族群群體」(ethnic groups),以及那些曾被稱為「種族」(races)的事物。如若這些身分認同的先在性(precedence)不再被視為動機,那一般史書常見敘事中的其他層面也必須重新審視。這種先在性尤其適用於解釋康熙朝的特色,也就是戮力展現「漢人」或「儒家」面貌,以抑制漢人菁英對清統治者的反感,以及對於乾隆時期輝煌的理解,將其解釋成「漢人」文化或漢人「世界秩序」勢力與影響下的鼎盛。相較於一般對清帝國治下各種人群的研究方式,本書指出,如果接受這些身分認同的古老性,反而會模糊歷史化身分認同的產生過程。
針對理論上具普遍性(文化上不存在)的皇權與理想化的身分認同符碼化之間的關係,我從一九八三年開始發表一些綜合性的想法。其衍生出的就是試圖更詳細闡釋這些征服、帝國意念構成與建立身分認同標準的同步性,希望找出其方式,如果可能的話,也希望找出原因。本書整體故事與以十八世紀中國為背景的其他作品有許多共通點,例如一九九○年魏丕信(Pierre-Étienne Will)的《十八世紀中國的官僚制度與荒政》(Bureaucracy and Famin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與孔飛力的《叫魂》(Soulstealers, Harvard),不勝枚舉,這些作品指出政府菁英無法忍受社會、文化與政治上的現象,而這些現象在國家權勢的大傘下的相對位置極為模糊。當然我也意識到,清治下的帝國敘事的次要情節,與其他近世(early modern)帝國系出同源,這提醒我們在多大程度上,可將許多所謂十九與二十世紀的新事物,看作是歐亞帝國意識形態遺緒的反射或幽魂。
但我們不應將對於近世連續性的重視,詮釋成某種一般命題(general proposition),也就是將遠至中古或古代的現象,詮釋成清初帝國表述的源頭。雖然許多帝國語言或儀典的元素在時空上與清代相去甚遠,但我們從任何層面都無法解釋它們在本研究所針對時期中的用途、效力或意涵。本書的論述當然也時常會留意到與其他近世帝國的相似之處,但寫一本比較性的著作並非我的初衷,書中對類似現象的觀察也不是為了解釋這些相似之處。最後,我認為本書所論嚴格限制在清帝國經由幾種媒介展現出來的意識形態,以及清帝國與身分認同概念的關係,至於重新闡釋清史的各個層面,則沒有明顯的著墨。「身分認同」一詞本就極為籠統,在於身分認同有千百種,有的牽涉民族(nationalty),有的關乎宗教,有的涉及性別,有的攀扯階級,不勝枚舉。儘管現代觀察者會認為這些似乎是不同的現象,但沒理由設想它們代表不同的歷史過程(十八世紀對清朝朝貢人群的記載恰恰反映了這點,當中無論男女的服飾幾乎都帶有用作身分認同的特殊符號)。此外,這些身分認同中的任何一種,都不符合十七、十八世紀清帝國脈絡下的「身分認同」。首先,其所指涉的身分認同是「民族」或「族群」認同的前身,而非當事者明確的民族或族群;其次,正如那些涉及其他類型身分認同的史家所多次論述的那樣,在帝制時期結束時,民族與族群的認同形式受限於公共論述(public discourse)中所能假設的所有其他類型的身分認同。諷刺的是,本書的組織雖圍繞各種身分認同的類別,卻不得不質疑其真實性;歷史論證少有選擇,只能假設當代是個開端,倒述每一段故事。
本書有更多的局限應當留意。作為政治因素的皇權(或治權)、社會,或者是一般的清代歷史,本書並未談論太多。針對本書該涵蓋多少一八○○年前的清朝統治時期,所必須做出的選擇,加劇了其難度。我也減少了早期研究中所涵蓋的康雍時期(一六六一至一七三五年)的比重,讓位給更早與更晚的時期。我在《孤軍》(Orphan Warriors)中探討了十九與二十世紀初的一些社會與意識形態的身分認同機制,為了探詢其源頭,必須避免重疊太多。本書許多主題與一些個人的記述被分成兩個或多個章節,為了讓本書得以定錨在治權與身分認同這兩個端點上,這種做法無可厚非。我計畫讓它們在章節結構中互為反射,且為顧及整體論述的明晰,一些記述的順序也會有所斷裂。我期盼注釋有助於闡明這種選擇所導致的混淆。讀者還會發現一些清史研究的中心題材是被裁減的、甚至是偏頗的,例如八旗與駐防、朝貢體系、對蒙古領地的管理、生活在清邊界的眾多穆斯林群體的歷史,以及西南人群。幸好其他作品都研究過這些題材,我只需在它們觸及我的主題時,再做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