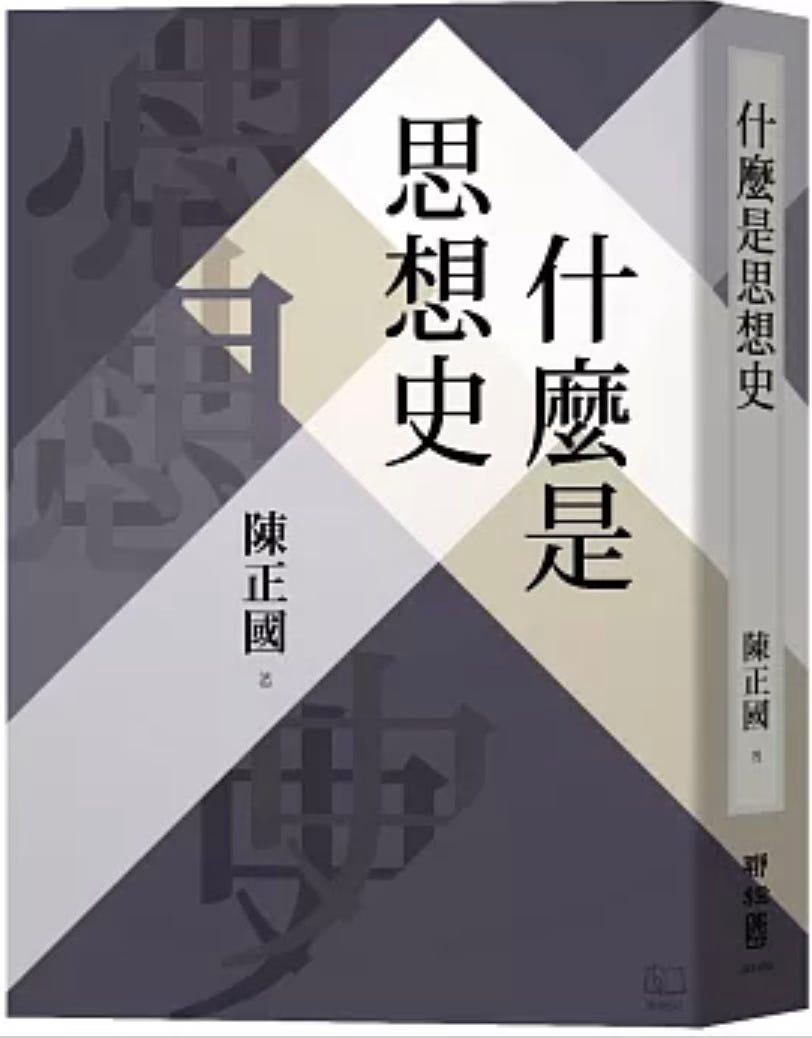陳正國 | 「思想史」—— 從詞到義
顧名思義,「思想史」是研究思想的歷史。但什麼是思想?何種思想應該、值得成為歷史研究對象,則受各國史學發展的影響而有不同的答案。思想史在不同的學術傳統中會呈現出不同的色彩,會有各自的方法學上的偏重,叩問不同的歷史課題。例如「中國思想史上的轉型」是此間史家的重要課題,而在西歐,學者更常追問的課題是重大政治事件如法國大革命、英格蘭內戰、北美獨立運動的意識形態基礎或思想淵源。職此之故,無論是作為一種概念還是一種寫作類型,思想史都有其自身的歷史,所有對思想史的定義都是開放性而非終極或確定的。
今日「思想」一詞,大抵指涉心靈與心智活動的過程與產物。這一詞彙出現的時間其實相當晚,用以代表一種特定學術類型的時間則更晚出。「思想」應該是晚清作家們借自日本漢字的新鑄詞;古人在談論心智活動時,多半會(單)用「思」、「悟」、「會」、「知」等字來表示。一千九百年之前中文文獻中的「思想」一詞,幾乎都是「思」或「想」的疊詞,意思相當於現代白話文「思念」、「想念」。晚清以後,「思想」才開始被用來指涉理性活動本身,或指涉人類利用理性思維所創造出來的事物,諸如抽象的觀念、價值、態度、評價、以及與這些觀念與價值相關的具體作品等等。換言之,在晚清以前,「思想」指涉感性的活動,此後才成為具反思性的心智活動及其產物。一九四○年代,錢穆(一八九五—一九九○)寫道:「西方學者每言經濟決定思想。若此而論,則中國今日所流行之代表思想,亦即一種次殖民地之思想也。」錢穆在此處顯然是以思想一詞來統括所有有關價值、觀念、語言、文本、創造等等心智活動的產物了。
「思想」、「主義」、「民主」這一類的新鑄詞、新觀念在加入中文詞彙世界之後,經常還保有相當的涵括性、彈性、不穩定性—以至於人們在使用它們的時候,如水之流瀉,難免渙漫。近年動物權崛起,有些學者會提出「動物是否有思想」這樣的原則性或哲學問題,這裡的思想顯然包括思考、理性的意思,甚至指涉所有的心智與心理活動。但在另一方面,「思想」又常常被拿來標示一種特定學術研究取徑、研究方式或寫作類型。例如許多學者會使用「文學思想」、「哲學思想」等詞彙,好像文學思想有別於文學,哲學思想有別於哲學一般。這些現象其實不能怪大眾與學者在使用思想一詞時過於輕率,而是我們現代中文的語言與學術經驗還相對年輕;我們還在摸索、試驗現代中文如何精準表達快速膨脹的現代學術。
梁啟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或許是最早使用「思想」一詞的著名作家。他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九○二)將「學術」與「思想」連用,既預示了日後思想一詞的氾濫,同時開啟了中國現代思想史研究的大門。許多當代傑出的中文思想史家如余英時(一九三○—二○二一)與葛兆光(一九五○—)等人都認為思想史的研究對象應該盡量廣取,不應限制在菁英知識分子身上。本書將會對此議題提供淺見,在此我們僅須注意,史家們之所以希望擴大思想史研究範圍,固然有嚴肅的學術理由,但現代中文學術用語中,思想(史)一詞具有語意的延展性、概括性也是重要原因。
古代中國沒有「思想」一詞,不表示古人未曾研究「人類心靈與心智活動的過程、結果與影響」。即便從現代思想史的角度看,《莊子》〈天下篇〉與《史記》〈太史公論六家要旨〉描述前代學術或思維成果的狀況與利弊得失,完全可以視為精彩的學術思想史作品。〈天下篇〉與〈太史公論六家要旨〉在體例與書寫風格與今日學院實踐迥異,固無庸贅言,尤其是《莊子》的作者感慨「道術為天下裂」,司馬遷追求「通古今之變」都透露古代偉大作家行文思考帶有形上意義、整體史的關懷,與今日高度分工與強調實證的現代史學大相逕庭。但無論如何,把〈天下篇〉與〈論六家要旨〉視為人類早期的思想史著作,應該沒什麼疑義。甚至將《史記》中的〈屈原賈生傳〉、《漢書》〈董仲舒傳〉與現代思想傳記相比,雖然古代史書中思想描述的濃稠度明顯不足,但其寫法與現代思想傳記之間仍有許多可比較之處。
從先秦〈天下篇〉、漢代〈太史公論六家要旨〉到正史中的〈儒林傳〉、〈藝文志〉再到清初《明儒學案》、《宋元學案》,都說明了「學術史」本來就是中國的重要書寫傳統。只是梁啟超將思想與學術兩詞並舉,其真正目的並不容易揣度;或許任公是有感於傳統學術「史」的書寫過度強調生平、書目、版本、校勘、以及師承、交往、學派,對於觀念的分析,辯證的過程,理據預設的說明與鋪陳,亦即有關「思考的故事與其現實目的」較少交代,亦未可知。幾乎與〈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發表同時,陳懷(一八七七—一九二二)在《新世界學報》發表的〈學術思想史之評論〉(一九○二)同樣將「學術」與「思想」連用。陳懷說,「學術之辨,史氏之大宗」;指的就是中國的學術史傳統。他又說,人面對萬事萬物,自然會「結而為思想,發而為學術」,這就是既強調思考的成果,也強調其中的過程。或許可以這麼說,中國近代「思想史」的發韌是以特殊的「學術思想史」這一文類或概念進入讀者視野的。質之〈論六家要旨〉、〈藝文志〉、甚至後來的《宋元學案》、《明儒學案》、清代注重家法與師承的樸學等傳統,此一特殊現象並不特別令人訝異。但正如本書以下所要交代,此一特色固然造成中文世界有相對豐富的學術史材料,卻遮掩了其他思想史次類如政治思想史、經濟思想史、科技思想史等等領域的重要性。
陳正國 | 什麼是思想史
什麼是思想史 作者: 陳正國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24/06/20 語言:繁體中文 內容簡介 本書堪稱迄今此類研究中最為詳盡的中文著作,其書寫原則大抵有三。第一,本書從精神史、舊文化史、觀念史等文類開始考察,從長時間的學術變遷討論英語世界思想史的源流與關鍵發展。第二,本書從歷史學的本質開始談起,並比較思想史與其姊妹學科如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之間的關係,從學科邊界的角度闡明什麼是思想史。第三,本書強調歷史研究莫不受到當地歷史與知識興趣的影響,一方面說明「跨境思想史」與「比較思想史」何以在中國與東亞特別活絡,另一方面提醒此地思想史家如何直面這兩種思想史寫作的問題與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