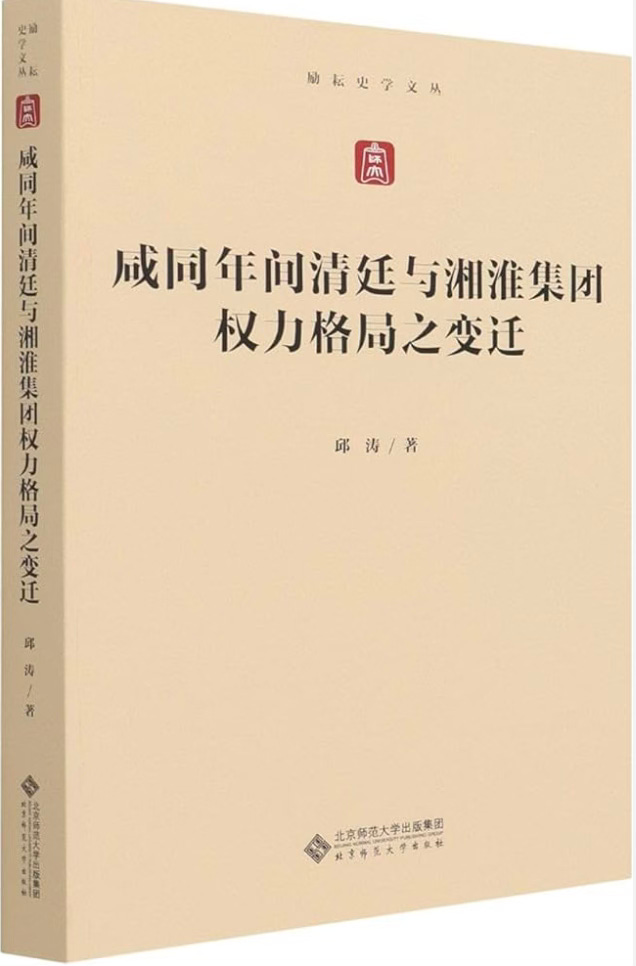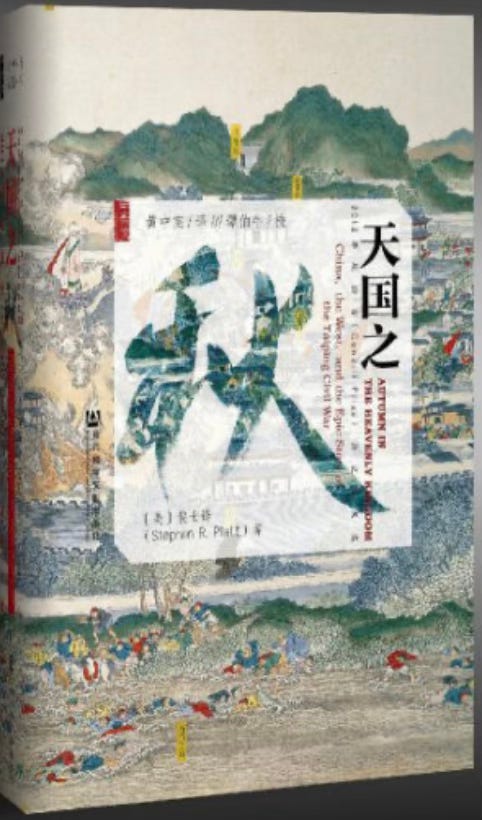羽戈:天国之痒与天朝之痒
《天国之痒》,李洁非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3月第一版
《萧朝贵与太平天国早期史》,刘晨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5月第一版
《咸同年间清廷与湘淮集团权力格局之变迁》,邱涛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第一版
《同光年间湘淮分野与晚清权力格局变迁(1862-1895)》,邱涛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10月第一版
《能静居日记》,赵烈文著,岳麓书社2013年7月第一版
《天国之秋》,裴士锋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1月第一版
十月去安庆游学。按我的习惯,会带一本与游学主题相关的书上路。行前踌躇良久,最后选中了《余英时回忆录》,近世以来,最杰出的安庆人,窃以为首推陈独秀,其次便数余英时。在手边缠绵半晌的李洁非《天国之痒》一书只能割爱,尽管此次游学第一讲便是太平军与湘军的安庆之战,以及太平天国的是非成败,理由是,这本书太重了。
《天国之痒》十六开本,加上配图,超过六百页,重达九百克,当得起大书之谓。从内容上讲,更是如此。太平天国史研究一度乃是显学,简称“太史”“太学”,史料早已被发掘殆尽;至于理论,从捧到天上,至摔到地下,经历了两个极端,似也无推进的余地。不妨断言,时至今日,研究太平天国史,尤其写作“本末”“观念和制度”等,首先是一种勇气的表现,因为实难革故鼎新或推陈出新,稍不留神,便有炒剩饭之嫌。《天国之痒》显然不是什么剩饭,虽然作者用的多是老食材,做的也是家常菜,却凭借妙手(“慎察的实证考释”)与仁心(“知人论世的史学襟怀”,或借用胡适之言,叫“持平”),硬生生把一锅萝卜白菜,烹出了珠翠之珍的味道。
举例来说。太平天国对于基督教,只是拉大旗作虎皮,利用上帝、耶稣、天堂等符号与布道、祈祷、忏悔等仪式,以煽动人心,驾驭百姓,究其实质,意识形态则属巫术,组织体系则属会党。这个论断,想来接近共识,然而何以至此,只怕言人人殊。李洁非着眼于社会动员模式:对“九成九以上乃是杨秀清这种目不识丁、头脑灵魂深受乡土文化束缚的底层民众”而言,真正能够齐其心、导其行的并非“神爷火华”“耶稣基督”等不知所云之话语,而是降僮、显灵、请乩、召仙、感应、巫蛊之类中国传统巫术,民众需要的不是上帝,设想洪秀全以传福音为使命,追随者势必寥寥,而是“可以尽快改变自己现状与命运的力量”,洪秀全的封号“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听上去正是这样一种力量,“肯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李秀成自述》)的传播效应庶几近之。
太平天国所用巫术,以降僮最为著名。这是广西浔州(桂平古称)的特产。所谓降僮,即神灵附体,以人为灵媒。杨秀清伪称天父下凡,萧朝贵伪称天兄下凡,皆如此类。请教广西的朋友,告以在当下,降僮依然有其市场,农村尤为流行。李洁非在书中强调“那时中国人的观念,普遍有神巫色彩,清末两大民间运动太平天国和义和团,都有神巫文化底蕴”,“那时”二字,大抵可以略去。当然,他说这话,意在延伸至另一面,不止太平天国使用巫术,清廷一方也是如此。湘军的先行者江忠源,与太平军一路厮杀,从广西打到安徽,在安徽巡抚任上守庐州,“叫各大门口烧三股香,摆一大碗水。二更后又传令下来,叫各家杀公鸡,滴血碗内,顷刻又吩咐将碗内血水倾地,用菜刀将碗劈碎,抚台在城上屹然不动”;翌日,在民间搜罗黑狗数十条,“大东门止杀一条,北门杀三条,余狗放回,杀狗滴血在城垛上,又将狗爬在城垛上,头对城外贼营”(周邦福《蒙难述钞》)。江忠源以精明强干著称,自己信不信这一套,不好判断,不过既然这么做,说明此举用来安抚民心,提升士气,多少有些效果。
对于太平天国的治国理政,李洁非总结为两面,一面以“公天下”否定“家天下”,并推进到虚无缥缈的境界,一面以“家天下”取代“公天下”,并推进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此外,他还引入后世的“军国主义”一说,“在太平天国,不是一个国家拥有一支军队,而是一支军队拥有一个国家”,这一点堪称洞见。我们平时对比军队国家化与国家军队化,后者不妨以百业俱废、全民皆兵的太平天国为镜像。说起来,国家军队化,比马上治天下还要残酷三分。天国其表,地狱其里,小天堂的幻象迅速灰飞烟灭,根源正在于此。
太平天国由盛转衰,一般认为转折点是1856年天京(南京)事变。李洁非则道,1853年定都天京,既是太平天国时运的顶点,也是衰落的起点,至于三年后的天京事变,“不如说是由盛转衰趋向积累到一定程度,乏中思振,所激发的表现”,其结局进一步验明颓势根深蒂固,积重难返。此前还有一段详论:
天京之变,实际上是太平天国各种矛盾相交集而借权力斗争方式诉诸表面的结果,也是谋求矛盾解决与克服的一番尝试。而事件之终更为可悲,证明太平天国甚至没有能力自我拯救。东王惨败、北王受死、翼王出走,显示此政权全不具备理性处理危机的素质。杨秀清以卵击石式的毁灭,在宣告太平天国仅有的一次变革机遇消失的同时,亦彰显了其惰性与顽疾的坚厚。从此它一直维持着此种情状,缓缓走向崩溃。
细细揣摩,这番貌似标新立异的论调,自有它的道理。以太平军的草莽习性、流寇战术与乌托邦气质,更适合打天下而非坐天下,一旦坐下来,种种短板即刻曝光,就像猴子爬上高处,露出破绽百出的屁股。定都天京,成为小天堂的执政者,依旧持守革命党的思维与手段,走向败亡,指日可待。
要言之,《天国之痒》一书之长,在于对脉络的清理,这得归功于作者不站队、能持平的立场与识大势、有远略的视野,其短处,则在细节,时有浅薄、偏颇之处。譬如论李鸿章的章节,错谬甚多。这里单说论萧朝贵,书中更多在强调他与杨秀清的政治联盟,而淡化以至忽略了二人的明争暗斗,实则天父天兄并非一体化,天兄不甘为天父的跟班,也曾抢班夺权,私植党羽(韦昌辉便是萧朝贵一党)。金田起义前后,时值杨秀成病重,太平天国遂迎来一个刘晨所命名的“萧朝贵时代”。
刘晨《萧朝贵与太平天国早期史》专攻萧朝贵,不仅使西王的形象愈发丰满,而且有助于我们明察太平天国早期的权力格局与隐患。要言之,在天父、天兄陆续下凡之后,太平天国的权力版图,可譬之三足鼎立,洪秀全、杨秀清与萧朝贵各据一方,相互制衡。杨、萧时而联手,把作为教主与精神领袖的洪秀全架空为虚有其表的吉祥物;时而内讧,轮流生病或受伤,则为洪秀全以及老战友冯云山留出一定权力空间。如果说三足相对稳固,那么长沙一战,萧朝贵中炮而死,仅余两足,对立必然加剧,缓冲再无可能。
关于萧朝贵之死与天京事变的关系,二人的推演互有同异,可供对勘:
……权力三角中的萧朝贵不久战死,仅有的平衡打破,三足之鼎变作跛足残鬲,怎能不倾覆倒圮?但归根结蒂,关键并不在于萧朝贵死活,而在于这种权力结构注定具有内耗的特质。萧早死使洪、杨冲突与分裂加剧,若不早死,洪、杨间虽有缓冲,但内耗也可能换作更复杂、更难解的方式释放出来。(李洁非《天国之痒》)
……冯(云山)、萧(朝贵)即使拥有实力,真正改变的也是天京事变的经过而不是太平天国的命运。冯云山是洪秀全的忠实盟友;萧朝贵与杨秀清之间的矛盾有激化的可能。所以,即使冯、萧还活着,即使他们有足够的力量遏制杨秀清,也只是徒增几个卷入内讧的领导人,多为洪秀全预备一些为捍卫天王专制权威起兵靖难的盟友而已。在洪、杨矛盾的基础上,又有可能增加杨、萧矛盾与杨、冯矛盾。而萧朝贵也是一个权力欲极强、野心极大的人,他不止一次地公开在洪秀全面前邀功,甚至有挟制天王的意图,专权之心昭显,洪、萧之间也存在权力争夺的可能。因此,即使萧朝贵还活着,改变的局面仅是谁杀谁的问题,或许天京事变比已发生的更惨烈。(刘晨《萧朝贵与太平天国早期史》)
说到底,太平天国的权力结构,属于典型的内耗式结构,自诞生之始,便埋下了自相残杀、自取灭亡的种子。这一点,连隔岸观火的外国人都能看清楚。1861年,英国外交官富礼赐(Robert J.Forrest)曾在天京工作半年,与天国高层多有交游,后撰《天京游记》,结语云:“我不得不说,太平军欲得获全中国的统治权实是无望的,因为他们自已不能统治自己,只不过施用一种令人反对的恐怖政策和手段而已……”“自己不能统治自己”一语,道中了太平天国权力结构的一大病灶。
看衰太平天国,并不代表富礼赐看好清廷:“但我亦不见得清廷能恢复其从前之势力和地位。现在除去一省之外,其余各省都有些叛乱——并不一定是太平军。由这些大乱之中将有些势力崛起以拔乱为治者——这可从中国历史多次证明。”结合此后五十年历史来看,不得不承认,这是相当精准的预言。崛起的势力当指湘军和淮军,其历史作用,“拔乱”诚有之,“为治”则未必。它们扑灭了太平天国的叛乱,为大清成功续命,与此同时,它们凭借军功潜入体制,渐成心腹之忧——对朝廷而言,太平天国是眼中钉,它们则如肉中刺,都是天朝之痒(李洁非释痒:“以痒来形容的病态,一般皆非突如其来之暴病,而是沉疴日久、缠绵不除、沉沦难脱的顽疾旧症。”)——如果说太平天国企图从外部冲击政权,它们则从内部颠覆了中央与地方、满人与汉人的权力格局,从而肢解了大清王朝。
年初读邱涛《咸同年间清廷与湘淮集团权力格局之变迁》《同光年间湘淮分野与晚清权力格局变迁(1862-1895)》,二书出版相距八年,主题完全一脉相承。大清权力格局,自开国至道光朝,一向是中央重于地方,满人重于汉人,湘军和淮军——邱涛称之为“湘淮集团”——的崛起,则直接改写了这一传统。它们从重构军权起步,渐渐扩张至政权、财权,使权力由中央下沉到地方,由满人转化到汉人。试看同治二年(1863年)、三年(1864年),太平天国覆灭前后,全国总督、巡抚,即所谓封疆大吏,共二十五个职位,湘淮集团竟占十四个之多。大权旁落至此,不由朝廷不惊惧万分,提早下手,飞鸟未尽而良弓欲藏,狡兔待死而走狗已烹,外则牵制,内则分化,一手胡萝卜,一手大棒,观其对待曾国藩如此,对待李鸿章亦然,对待出身湘淮集团的袁世凯也是一以贯之。故此,大清最后五十年政治史,大抵可视作一部夺权史:中央向地方夺权,满人向汉人夺权。以败局收尾,不仅因为湘淮集团及其后裔北洋集团尾大不掉,更是因为,经太平天国一役的持续冲击,大清王朝已经“抽心一烂”,统治能力——包括汲取权力的能力——严重萎缩,不复当年。
“抽心一烂”是能静居士赵烈文的话。赵烈文出自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幕府,尤为曾国藩晚年所赏识,有两年二人几乎无话不谈。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1867年7月21日)晚,曾国藩找赵烈文聊天,“言得京中来人所说,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赵烈文答:“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洲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曾国藩蹙额良久,问道:“然则当南迁乎?”赵烈文答:“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这番话被视作晚清最神乎其神的一则预言,无论对时间(“不出五十年”)还是形势(“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洲无主,人自为政”)的预判都极具穿透力。从语义来看,赵烈文所云“若非抽心一烂”,显然指向未来,我则以为,在此预言之前,太平天国的作用力加上湘淮集团的反作用力,足以使大清“抽心一烂”,从脚跟烂到心肺,稍后虽有“同治中兴”,更像是垂死之人的回光返照,等到甲午战争爆发,世人终于看清,天朝痒到了什么程度,帝国烂到了什么程度。此时,“土崩瓦解之局”已成,任何努力都回天乏术。
赵烈文的预言,有一伏笔。天京陷落,李秀成被俘,他适在曾国荃幕府,曾参与审讯。《能静居日记》记录了二人的一段对话。李秀成问他:“今天京陷,某已缚,君视天下遂无事邪?”他答道:“在朝政清明耳。不在战克,亦不在缚汝。闻新天子聪睿,万民颙颙以望郅治。且尔家扰半天下,卒以灭亡,人或不敢复踵覆辙矣。”李秀成又云:“天上有数星,主夷务不靖,十余年必见。”请其谈星名度数,“则皆鄙俚俗说而已”,令赵烈文判定“余知其无实在过人处”。不料三年后——赵烈文审讯李秀成,正值同治三年六月二十日(1864年7月23日)晚——他竟预测大清国运“殆不出五十年矣”。由此反观李秀成的预言,冥冥之中,似有呼应。
说到预言,再钞一节。1909年,日本政治家伊藤博文接受英国记者采访,谈及太平天国、常胜军的介入与大清国运的终结——我们所评议的话题,皆可从中找到印证:
几乎毋庸置疑的是,太平叛乱发生之时,满清已是山穷水尽,而戈登及其“常胜军”阻止它被推翻,进而阻挡了一个正常、有益的自然过程。自那之后满清的所作所为,无一证明他们值得一救。满清根本不值得救。等到满清垮台,由于垮台是必然且不久后就会发生,动荡将更为暴烈,而且会拖得更久,因为那被延迟太久,老早就该发生。
这番话转引自裴士锋(Stephen R.Platt)《天国之秋》,一位美国学者研究太平天国的书。书名与《天国之痒》仅一字之别,立场与视角却大相径庭。如果说《天国之痒》的主题是大历史,《天国之秋》的主题则是大历史下的人,此书结尾,裴士锋引用了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小说《文静的美国人》中的一句话:“人迟早得选边站,如果还想当人。”
回归到人,则可引出我的一点思索。我们到底该怎么评价太平天国运动呢?从阶级史观(革命史观)出发,它被誉之为代表历史方向的农民起义,从王朝史观出发,它被斥之为破坏社会秩序的太平叛乱,这二者,皆为裴士锋所不取,而称之为“内战”——这倒接近我的想法。作为内战,无关正义,无关文化本位,没有英雄,没有胜利者,无论口号多么昂扬,结局多么悲情,谁也不值得赞颂,谁也不值得同情,太平军如此,湘军、淮军等亦然。因为就内战而言,最大的受害者永远是百姓,而且如民谚所云“发军如梳,官军如篦”,征战双方对百姓的伤害一般惨重。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苍生苦难,不知伊于胡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