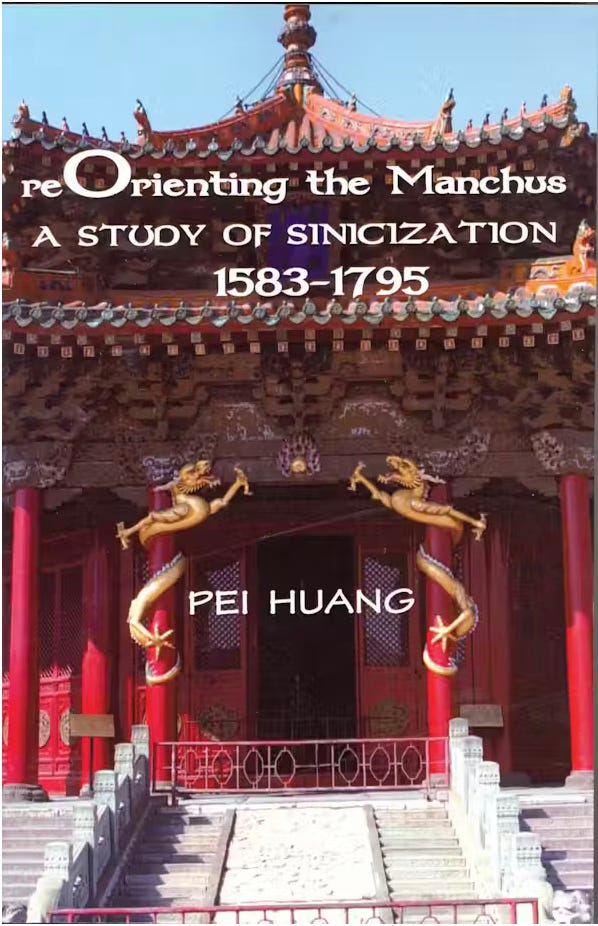蔡伟杰 | 满人有沒有被汉化?——评黄培《满人的再定位:一项汉化的研究(1583—1795)》
編者按:1998年,美国两位中国历史研究学者在满人汉化与清朝本质等问题上产生了争论:一位是匹兹堡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友枝(Evelyn S. Rawski),在《The Last Emperors》(1998)中强调清朝保留满洲文化,通过八旗制度和多民族治理构建独特帝国,反对将其视为汉人王朝;另一位是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学教授何炳棣(Ping-ti Ho),他在《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98)等回应中,主张满人迅速汉化,采纳儒家文化与汉人制度,清朝本质上延续汉人王朝传统。这场争论聚焦于清朝的“满洲特性”与“汉化”程度,一直争论至今。2011年,美国俄亥俄州扬斯敦州立大学(Youngstown State University)历史系荣誉教授黄培出版《满人的再定位:一项汉化的研究(1583—1795)》一书,可视为是支持何炳棣论点的代表作。不过在台湾中正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蔡伟杰看来,作者实际上是向“新清史”妥协。但必须指出的是,“新清史”也从未否认满人采纳、借用汉文化的事实。蔡伟杰认为,黄培一书确实是目前在满人汉化议题方面讨论最为全面的作品;“然而,因为在方法论与立场上的争议以及取材受限,事实上该书并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与其说该书在满人汉化的议题上做出定论,倒不如说是奠下讨论的基础”。
本文选择蔡伟杰刚刚出版的评论集《从马可波罗到马戛尔尼:十三世纪以降的欧亚世界》,原标题为《满洲汉化问题新论》,出版社和作者授权刊发。
免費訂閱《波士頓書評》及相关事宜发送邮件:boshidunshuping@gmail.com,隨意打賞:Zelle,PayPal:boshidunshuping@gmail.com 用戶名:Boston Review of Books;長期支持請點擊下面訂閱,升級為付費訂閱。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匹兹堡大学中国史教授罗友枝(Evelyn S. Rawski)与华人历史学家何炳棣对满人汉化与清朝本质的争论,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焦点。
2011年出版的《满人的再定位:一项汉化的研究(1583—1795)》一书可视为是支持何炳棣论点的代表作。作者黄培,为美国俄亥俄州扬斯敦州立大学(Youngstown State University)历史系荣誉教授,以雍正皇帝(1678—1735,1723—1735在位)生平以及考证满洲族名源流等清史相关研究享誉学林。
该书意图说明满人如何借用汉人的统治方法与生活方式,以及从努尔哈赤(1559—1626,1616—1626在位)起兵反明至乾隆(1711—1799,1736—1795在位)末年之间,满人在经济、法律、社会制度等方面的种种改变,并且主张满人汉化始于努尔哈赤,至乾隆年间臻于高峰。由于意识到北美新近清史研究学派的研究主张,作者小心翼翼地强调,此时的满汉交流并非单向过程,满洲文化同样影响中国,但由于该书主题在于满人汉化,因此暂不处理该论题(第2页)。
有鉴于汉化定义的分歧,该书导论首先梳理“汉化”一词的用法。“汉化”一词最早出现于1898年,当时用来评论日本神道信仰的汉化。有些学者将汉化视同于族群同化,有些则视为制度采借或文化融合。该书将汉化定义为对汉人生活方式的采借、适应与参与,同时被汉化的满人不会意识到自己被汉化,并认为满洲传统是满人对自身文化的再诠释,其中包含透过满汉接触而接受的汉文化成分。汉化与同化(assimilation)、涵化(acculturation)及教化过程(civilizing process)等概念各有不同之处;“汉化”这个词语本身并无问题,有问题的是其用法(第3—11页)。
该书正文共分为八章。第一章“满洲源流与其族群成分”指出,满洲内部除了女真,亦有非女真的族群成分,如蒙古、汉人与朝鲜等。这种异质性是满人汉化的重要催化剂(第44页)。值得一提的是,本章强调朝鲜与汉人传统的共同之处,以及朝鲜对于满洲汉化的作用,此面向过去较为学界所忽略。
第二章“清朝肇建”着重探讨女真从部落发展为国家的历程。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制度与创制满文,有助于女真人维持认同(第72—73页)。而到了皇太极(1592—1643,1626—1643在位)时,他安抚汉民、起用汉官、翻译儒家经典、采用明制、改国号为大清,在其统治下,努尔哈赤所遗留的蒙古制度渐次取消,金国改行汉制(第79页)。最后,清朝在多尔衮(1612—1650)领导下顺利入关,取明朝而代之。多尔衮实行明制的举措,不仅加速满人汉化,也确保清朝征服明朝的成果(第81页)。
第三章“经济力量”主张,经济因素是满人汉化的主要动力,而经济同时也受到地理的影响。作者指出,农业使女真人接触汉文化,边市则增加女真人与汉人的接触,并促使通事出现。女真与明朝、朝鲜之间的边界贸易使其从渔猎采集与农耕的混合经济转为以农业为主(第113页),朝贡则使女真人得以停留北京,进而熟悉各种中国仪式和规定(第115页)。
第四章“边民与越边民人”讨论明清边界的边民与越边民人(包括军户、被流放的罪犯与商人)如何影响女真汉化。由于汉人降臣、通婚与翻译《三国志演义》等因素,女真人对汉文化有了更深入的接触。又因为朝鲜文化近似汉文化,女真人受朝鲜边民文化影响的效果即类似汉化(第144页)。
第五章“行政与法律制度的兴起”讨论满人如何采借明朝行政与法律制度,例如文馆、六部与都察院的设置以及敕编《盛京定例》等。努尔哈赤统治下的早期金国制度仍是氏族联盟,缺乏清楚的分工;1644年以后,清朝数次修订律例,修订结果显示了清朝法律的汉化倾向。但清朝皇帝亦同时修改明朝制度以符合清朝作为多民族帝国的需要(第194页)。
第六章“社会制度的转变”讨论满人日常生活的汉化。这主要反映在婚姻、丧礼、幼子继承制、命名习惯的改变、满洲尚武精神的衰微等方面。清朝皇帝虽然试图重振衰微的满洲尚武精神,推行京旗移垦与汉军出旗等政策,但收效不大。作者亦认为,同治皇帝(1856—1875,1862—1875在位)允许旗人出旗为民,可视为八旗制度的结束(第219—220页)。
第七章“满洲语文与文学”讨论汉文化对满洲语文和文学的影响。失去母语的满人虽然未丧失族群认同,但缺乏共同语言,其族群归属感很可能会消失。1680至1780年间是满人从使用满文转变为使用汉文的重要时期,满洲文学也显现汉文化的影响,满洲文人开始以汉文抒发自己的感怀。康熙朝(1662—1722)则是从书写满文转向汉文最为关键的时期(第231页)。
第八章“建筑、宗教与儒家思想”探讨满人在建筑、宗教信仰与接受儒家思想等方面的汉化情况。在建筑上,盛京是汉化最深的满洲都城,盛京清廷和北京明廷的宫廷建筑差异不大,这主要归功于萨哈璘(?—1636)在出掌礼部期间,将明朝典制引入清廷。在宗教上,满人原本信奉萨满教,其后汉传佛教与中国地方信仰逐渐影响满洲社会,例如顺治与雍正皇帝对禅宗的信仰,以及一般满人对玉皇大帝、城隍以及关公的崇拜等(第275—276页)。至于满人儒化,作者认为,传统中国以儒家文化为主要认同,因此满人接受儒家思想即可视为汉化的表现,其中包括《圣谕广训》的宣讲,《四库全书》与《贰臣传》的编纂,以及逐年增加的满洲守节寡妇(第280页)。
结论部分重申对汉化的看法:汉文化的影响与满人的族群认同并不互斥,满人汉化是个相对性的词语,作者并列举满洲文化对汉文化的影响。至于满人对汉文化的反应,清朝皇帝视满洲文化为体,儒家思想为用;贵族对汉文化影响持负面态度;学者与文人喜好汉文化;一般旗人则对汉文化抱有复杂的情感。清朝与先前的中国朝代并没有太大差异,唯一的差异在于清代的满人是特权阶级。作者最后引用美国汉学家拉铁摩尔的看法总结全书:通古斯民族以其文化适应性强著称,采借汉人的生活方式正是满人重新定位自身的表现(第308页)。
该书运用中、韩、满文史料,并参酌日本与欧美的相关研究,举凡社会、经济、政治、法律、语言、宗教信仰等,作者都纳入讨论范围,可说是目前对满人汉化议题涉及层面最广的研究成果。
就该书的贡献而言,现任香港大学中国研究学程副教授金由美(Loretta E. Kim)认为,该书提供了一个对满洲历史与文化的全面研究,同时也说明,对汉人而言,女真-满人并非完全的异民族政权,因为女真的汉化历程早在入关前就已开始。笔者认同这两点,并认为作者将朝鲜看作满人汉化的媒介,强调其在满人汉化过程中的影响,确实扩充了满人汉化议题的讨论广度与深度。此外,该书还试图从物质文化视角切入,讨论满人汉化,如以女真行军时佩带的用以盛弓箭罩的荷包(满文fadu)逐渐变为装饰用的汉人荷包为例,讨论满人在入关后尚武风气衰微的现象(第220—221页)。这些都是该书在满人汉化议题上试图做出新贡献的努力。
在简述该书的贡献与成果后,以下将讨论该书的一些问题与可能引发争议的论点。首先,作者在导论中批评北美新近清史研究对汉化的拒斥立场(第5—11页),然而深入探究后就会发现,其争议点主要还是在于双方对汉化的定义不同。新清史的研究将汉化等同于满人改变文化与族群认同,因此认为汉化的概念有问题。而该书对汉化的定义则采广义,认为汉化仅仅表示满人在文化上接受汉文化,其仍保有族群身份。作者采取折中的立场,其目的在于让学界重新认同汉化概念。
“新清史”针对汉化学派提出了两大质疑:一是满人采借汉文化后,为何没有改变自身族群认同;二是为何满人汉化后,汉人的反满情结仍旧存在。作者认为这两点质疑都不成立。因为,一方面满人汉化与维持满洲认同两者并不扞格,另一方面汉人的反满情结早已随着时间淡化(第7—9页)。
关于作者对满洲认同之维持问题的响应,笔者认为作者实际上是向“新清史”妥协。但必须指出的是,“新清史”也从未否认满人采纳、借用汉文化的事实。关于对汉人反满情结的响应,笔者认为,作者过度低估清末反满运动的力度,及其对满人造成的影响。
作者认为,辛亥革命仅仅取走满人的政治主宰权(第5页),并举清末保皇党的成立,以及后来学者赞扬清朝建立疆域广大的国家与提倡汉文化为例,试图说明汉人反满情结与排满运动已逐渐消失(第9页)。
此外,该书在重提汉化概念时过度强调满人汉化现象的历史特殊性,使得汉化仅能作为描述性词语,而非分析性的概念工具。作者在解释其使用汉化而不用同化(assimilation)与涵化(acculturation)的原因时,说明涵化为人类学用语,源于美洲原住民与白人殖民者接触的历史;而同化则是社会学用词,用于讨论从属群体移入新社会后,试图融入主流社群的过程(第4页);两者都不适用于满人作为少数统治者,被臣属的汉人同化的情况。
笔者同意满人汉化的情况确实不适合用同化解释,然而,涵化却不失为一个好的分析概念,至少它在原本的定义上与汉化并不冲突。视汉化与涵化为不同概念,不利于将满人汉化的例子放在世界史中进行比较讨论。如果比较17至19世纪的满人汉化与13至14世纪的蒙古汉化与伊斯兰化,特别是元朝、伊利汗国与金帐汗国,将会发现这些现象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些例子都是外来的少数民族征服一地后,采用当地的主流意识形态以便取得统治正当性,并且在不同程度上接受当地文化。我们的确可以分别用汉化与伊斯兰化来描述这些现象,然而在进行分析与跨文化比较时,仍然需要一个可以概括这些现象的概念工具,涵化的概念正适用于此处。因此,在研究上并不需要刻意区分汉化与涵化。
在满文档案的重要性上,作者认为,满文档案至多对清史稍有影响,不致改变其概貌(第8页)。针对此一预言,鉴于目前对满文档案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还难以全面评估其成果,笔者只得按下不表。
八旗制度解体的时间也是该书具有争议之处。作者认为,同治皇帝允许旗人出旗为民之举,可视为八旗制度的结束(第219—220页)。但事实上,此一政策并未收效,旗人的响应并不热烈。此后,八旗制度仍然持续运作,民国初年,仍旧被用以解决八旗生计,并具有行政职能,直到北洋军阀垮台为止。可见八旗制度直至民初仍是管理旗人的有效制度。
作者所谓的满语结构弱点也需要重新检视。论及满语式微的主要原因时,作者认为,满语不适合表达新奇或复杂的思想,因此无法与发展超过数百年的汉语竞争(第239页)。然而所谓的满语结构弱点本身即有疑义,清朝满文译书的成果包括儒家、佛教经典与西学。笔者认为,这些书籍恰能代表作者所谓的新奇与复杂思想。此外,满语的词汇演变亦与时俱进,乾隆朝颁布的《钦定新清语》即为一例。作者所言满语结构弱点一说恐怕过于偏颇。
此外,作者在讨论满语中的汉语借词时,其中一例也有待商榷:即将满语的马(morin)视为汉语马(ma)的借词(241页)。 目前学界一般认为morin是满蒙同源词,蒙语的马即为mori(n)。 不可否认,满语中有许多汉语借词,书中也举出其他恰当的例子,然而就morin一词是源自汉语的意见,恐怕说服力有限。
作者提到满人接受儒家思想,但满人孝道概念的转化也是值得注意的面向。从早期努尔哈赤并举忠孝为统治工具的功利倾向,到后来清朝皇帝借由法律政策的制定、发布与落实,推行孝道为全国性的言行规诫,都反映了满人接受汉人的孝道概念。具体事例如:清初《孝经》典籍的大量翻译、注释与出版;孝子旌表制度的恢复与加强;养老制度与守制制度的执行;不孝罪无分满汉的惩处等。
在评估满人的汉化程度时,作者引用大量的谕旨与奏折,说明乾隆朝时满人汉化的情况达到高峰。这类数据数量庞大且信息丰富,确实是相当好的研究材料。然而作者并未深入讨论皇帝颁布这些谕旨的特定动机,以及其他官员关于满人汉化的奏报是特例还是普遍现象,以至于该书的分析不足以回答满人汉化的细部问题。英国政治思想史家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提醒我们,在讨论政治史中的言论及其意涵时,必须注意其宣传效力以及反身影响。如果清朝皇帝仰赖满人的武力与团结,以便向其臣属证明自己的统治合法性,那么其在臣属面前的行为,自然也会受这些思想制约。例如,乾隆皇帝斥责旗人“国语骑射”废弛,可能是拿特定事件大做文章,以便收杀鸡儆猴之效,当时满人“国语骑射”废弛的情况可能没有那么严重。
该书讨论满人在语文上的汉化时,仅于结论中提到子弟书对汉人的影响(第304页)。 但当我们检视乾隆朝以后出现的满汉兼书的子弟书与笔记,则会发现该书所说明的满人汉化趋势似有过度夸大之处。满汉兼书的子弟书可能出现于19世纪,而内附少数汉文的满文笔记则以道光年间(1821—1850)的松筠(穆齐贤)《闲窗录梦》为代表。从前述材料看来,直到19世纪,旗人当中仍存在满汉双语并用的情况。但若仅从乾隆皇帝与官员的言论来判断,我们得到的印象则是满人汉化情况积重难返,很难相信到19世纪还存在这类满汉兼书的作品。因此仅仅仰赖乾隆皇帝与官员的说法,恐怕不足以完整说明当时旗人汉化的细节,这也导致书中所描绘的满人汉化形象仍旧模糊不清。但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并不全是作者与该书的责任,毕竟我们目前还很缺乏乾隆朝以前底层旗人的相关材料。 因此,未来势必需要发掘更多底层旗人的史料,才可能对旗人的整体汉化情况有更多了解,并避免受限于帝国档案中隐含的意识形态。
最后,列举书中数条校对未尽之处以供参考:第79页,Gūlwalgiya应作Gūwalgiya;第139页,Fushen应作Fushun;第243页,Jinzhow应作Jinzhou;第311页注14,引用《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2084条,该条应位于第833页,而非第83页;第341页,引用华立之《清代的满蒙联姻》一文时,误植为《清代的满蒙婚姻》。
总结以上讨论,笔者认为,该书确实是目前在满人汉化议题方面讨论最为全面的作品;然而,因为在方法论与立场上的争议以及取材受限,事实上该书并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与其说该书在满人汉化的议题上做出定论,倒不如说是奠下讨论的基础。未来研究此一议题的学者显然都无法绕开该书,而应以该书所掌握的广泛材料为基础,继续发掘与底层旗人有关的材料,才可能深化相关的讨论。
本章原题《评Pei Huang, ReOrienting the Manchus: A Study of Sinicization, 1583—1795》,原载《史原》(台北)第25期(2013年9月),第319—3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