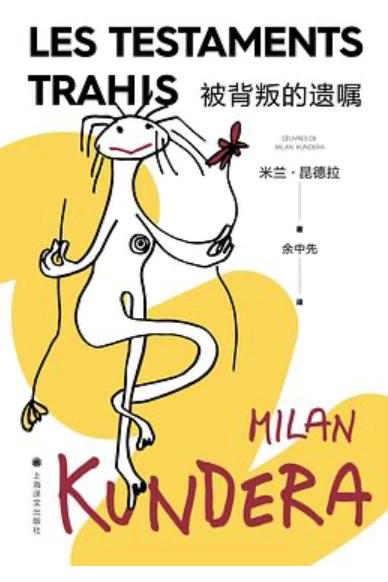路魆创作谈 | 平面镜与通灵者
在《超现实主义宣言》中,安德烈·布勒东对现实主义提出批评:“……以极庸俗的情趣,竭力去迎合公众舆论……作者将每一段文字都描写得很详细,却毫无任何特色……什么也无法与这类空洞的描述相比拟,那不过是画册重叠的画面……”到此,我要暂时停止引用了,要不然这篇文章会变成对此书的大面积摘抄。正如我注意到,当今一些写作者实践的那种所谓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一种镜像式的、社会新闻式的写作——好比拿着一块平面镜,到街上走一圈,在报纸和网络上照照,在先辈的惨痛记忆里投影一些史料,把人们喜闻乐见的事件,把那些以为是深入生活观察所得的鸡毛蒜皮,原封不动地变成镜像,或者机巧地加以粉饰重整后,展示给人看,就心满意足地认为,自己完成了一次社会历史考察的壮举,深入到现代社会的核心中去了,最后赢得一个“强有力地介入现实与反思历史”的功绩美名。
这种不如叫做“无聊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功利性非常显著,迎合各种需要,等同于摘抄和复制现实。但胜在它有市场。也有读者对这类小说的情节非常有共鸣,读得拍案而起,激起了他们对最近社会大事件的沉痛回忆,或者被廉价的煽情和卖惨惹得连连落泪。一些做文学批评的人貌似也偏爱此类作品,无非因为它们符合社会实情,简单反映了人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伟大潮流,贴合狭义上的唯物主义观——物质绝对决定意识(物质规律显然比精神规律更容易推导和理解)——且历经中华上下五千年,表面逻辑有迹可循,分析起来驾轻就熟,而对那些看起来晦涩玄奥、有所质疑的艺术,敬而远之。文学是有高低之分的,但我不否定任何一种什么主义写作,现实主义当然能出好作品(因为我还没来得及读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巨著,不便对他的伟大创作进行指认)。我只是对某些别有用心、缺乏审美、有低级趣味倾向的创作者的态度抱有怀疑,他们正让文学生态变得更迂腐和固守,并逐渐让迂腐和固守成为了主流。也正因此,文学生态中原本属于正常范畴内的、具有现代性的写作,才迫不得已地被称为是“进行了一场对主流的冒犯”。好比一个选择不婚的人,在越来越多进入婚姻的人眼中看起来的那样,似乎在故意挑战传统,而那本来只是一种选择的自由。
这又延伸出了另一种投机取巧的写作:假借先锋写作之名,在主流中塑造一个标新立异的少数派形象,收割成为“先锋者”的利益。然而,他们所采用的先锋写作方式,逃不开玩结构、玩语言那套老旧的东西,却被称作是先锋写作的复兴(回魂)。那些投机者们,一面宣称坚守文学的神圣与纯洁,拒绝随波逐流,另一边却埋头书写迎合公众舆论的作品,暗地里成为快消品的帮凶。一旦面对质疑,他们倒是有不少冠冕堂皇的理由为自己的作品辩护。
相传有种叫做Tulpa的秘术,通过强大持续的想象力物化一种只存在于幻想世界的事物。通灵者对于意念可塑造现实的力量,往往遭到质疑,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可是,不妨现象多元性的存在。我们看不见电磁波,不能否认它的存在,只是需要借助特定的手段去证实它。而我们试图借助小说,通过人物的本质行为和事件构成,去证实一个广阔的精神世界,正被隐藏在表面经验之下的深海中。Tulpa更有可能实现的并非凭空造物,而是把对未来设想和古老愿望转变成为可实践的现实。
还不能忘记这么一群艺术家,一直致力于在创作中坚持探索人类灵魂的深度,以及精神王国的广阔,去呈现“永恒的神秘之中看不见的隐形之物”。他们为我们的精神生活指明了方向,前提是我们没有曲解他们的作品的真正意图。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中的《圣伽尔塔的被阉之影》一文里说,要是没有马克斯·布洛德,我们连卡夫卡的名字都不知道,但同时嘲讽他曲解了卡夫卡的作品精神。马克斯·布洛德认为,卡夫卡的作品为我们描绘“专门为那些不沿着正确道路走的人而准备的可怖的惩罚”。我仍记得,在一篇新书推荐的文章上,作者认为残雪的《赤脚医生》(原名为《一种快要消失的职业》)聚焦的是乡村医疗主题,反映乡村医疗现状。这是对残雪一直以来坚持的新实验文学的巨大曲解,甚至是贬低。我怀疑作者根本没看过《赤脚医生》,对残雪也不甚了解。这样充满误解的解读只会蒙蔽作品的真正意图。
人们主动放弃探索艰涩未知的世界,竟然也满口哀怨,感叹如今世人越来越肤浅,不再阅读真正涉及艺术的书籍,即使发出这样的感叹,他们掉转头依然只甘于成为一部被动接收信息的收音机。布勒东继续说:“提供纯粹信息类的写作风格,之所以在小说中司空见惯,那是因为作者没有什么远大的抱负,我们应当承认这一点。”我们之中不承认这一点的人不在少数,甚至将此美化成是对外部现实的关注。他们共同编织的谎言,没有人去拆穿,谎言最终会如愿变成他们想要的现实,成为楚门的世界。进入潜意识城堡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的,只是不那么容易辨别,哪怕是K,也在日夜试图与克拉姆进行谈话,想找到进入的路径。但有人到了城门外,干脆就地搭起永居的帐篷,不再探索身后的城堡结构,或许是因为他们深知自己根本没有力气,也没有勇气与身为城堡前哨的克拉姆谈判。顽疾般的惰性,在背后不断弱化殊死一搏的精神觉悟。
我的生活基本处于梦幻和幻想中。但我不依靠做梦来写作,也不存在生理层面的视力幻觉,精神的潜意识是时时刻刻存在并启动作用的,用“白日梦”来形容或许更准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主动去感知它,运用它。这也意味着,我所知所感的现实在进入我的思维时——这里特指写作的过程——会进行折射、解构和重构,用我最喜欢的一个词来表达,那就是“变形”。面对现实素材时,潜意识倾向于将其改头换面,使其更加接近能与精神本质产生呼应的形式,因此产生了非现实的梦幻效果,大概是达利在描述超现实主义客体时说的那样:“客体与最低限度的无意识机能融合在一起,并建立在幻觉和表象的基础之上,而这些幻觉和表象则是由无意识的举动激发出来的。”超现实主义客体是无意识的药引。我们天生对蛇感到恐惧,蛇作为客体,激发出无意识中的恐惧经验。你可以通过后天训练,屏蔽这种恐惧经验,达到捉蛇的目的——正如本来该以敏锐感知力为主要创作支撑的作者,却选择性地过滤掉对于抽象意识的感知力,在更为表层的、麻木的经验中捉蛇,而忘记蛇本身对人类来说,是一种危险动物。
以上的梦幻效果,是现实主义所不能达到的。当然,它也不屑于这样做。目前的现实主义不擅长解构,在中国文学的语境下,反而逐渐成为固化和攀附权威的捷径,支配着庞大的利益,没有能力触及真正的现实之痛,它的批判之刃指向了无关痛痒的风波,所反思的东西是早已被定性为可被批判的恶——在这个范围内,一切都是安全无虞的。因此,现实主义越发无力去触及更深层次的认识,也懒得去反抗、不顺从和破坏。
那些梦幻的物质,或者称之为严肃的幻想作品,仍在坚持认识人的本身,劣根性在道德被悬置的架空领域中暴露无遗。这样的写作必须承受抽象的痛苦,让其暴露在思想的强光下。我要再借布勒东的话语,为幻想作品提出抗辩:“惟有想象能使我意识到有可能发生的事……实际上,所有的幻觉,所有的幻想都是不可忽略的快乐的源泉……幻想作品里最绝妙的东西,就是那里面并没有任何幻想的东西,因为那里只有现实。”显然,这样的作品常常因为难以理解而得到类似“胡言乱语”“自说自话”“脱离现实”等的批评。幻觉、梦境和潜意识,在那些人看来,简直跟被证实存在前的黑洞一样不可理喻,难以考究,还不如把心思放在眼前可触可感的机械现实中来。潜意识中的现实,同样是现实的一种,对于它的书写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事实上,超现实主义者没有“选择”成为超现实主义者,因为那是由他们天性中认识世界的方式决定的。超现实主义只是一个概括,是因为他们而形成的一种艺术价值观。
不过,昆德拉指出了超现实主义的困境:“对梦幻与现实的解决办法,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们虽然宣告了它,却没有在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中真正将它实现,这一方法却早已存在了,而且恰恰存在于他们如此贬低的体裁中:在卡夫卡此前十年中写成的小说里。”我做了一番比对,在这句话中,昆德拉的观点似乎有所偏差。他认为超现实主义者贬低小说这个体裁:“(小说)不可救药地堆积了庸俗、贫乏以及一切与诗意相反的东西。”严格来说,布勒东在《超现实主义宣言》中批评的是现实主义,是提供纯粹信息类的写作风格的小说,而非小说这一体裁。毕竟,超现实主义文学的经典作品《可溶化的鱼》,正出自布勒东之手。有人认为《可溶化的鱼》是一部散文诗,但也不妨碍它实际上就是一部小说(诗化的小说?散文化的小说?今天的体裁已经在随意拼接了)。当然,不排除布勒东真的厌恶小说这一体裁(看样子他更相信诗歌能在超现实主义中获得神秘直觉上的写作成功),用厌恶的体裁去写一部表达作者艺术观点的作品,完全是超现实主义者会干出的事。
昆德拉说,卡夫卡在他的作品里实现了对梦幻和现实的解决办法。至于这个解决办法是什么,他在《圣伽尔塔的被阉之影》没有明确指出,只是说卡夫卡的作品穿越了真实性的界限,却没有逃避真实世界,而是更好地把握了它,“在严肃认真地分析世界,同时又不负任何责任地在梦幻的游乐中自由驰骋”。
容许我在这里,把这种解决办法理解为是一种高度分化和浓缩的象征手法,对现实进行变形象征时,保持物质表面逻辑的稳固(至于内部精神,则早已发展成另一种非人世肉眼所见的模样了)。前者抵达梦幻世界,后者把握真实世界。象征仿佛是通灵者的手段,沟通梦幻与现实。在《城堡》中,K苦于无法进入潜意识的城堡,那个永恒高踞的理想之地,与众多象征着无法突破的灵肉障碍的村民和职员,进行谈判斡旋。在《乡村医生》中,“我”在风雪之夜的出诊,是艺术家与世俗之间搏斗:艺术家为世人的痛苦而思虑,而杀身,却难以被他们信任,最终在被利用完后,被彻底流放,进入寒冷的永夜漂泊中。
我们不会要求卡夫卡像乔伊斯那样——“如果都柏林城毁灭了,人们可以根据《尤利西斯》将其复原”——在他的作品中还原一个布拉格的日常生活和当时的阶级状况。因为里面的人物和事件都是现代人精神困境和灵魂焦虑的象征,他眼中的客体,具有一切人类的象征作用。我很难想象,卡夫卡与乔伊斯以及毕加索等人,事实上处于同一个时代,并时常有一个这样的错觉,认为卡夫卡从来都是孤立于一个只有他的古老时代,却在那个封闭的空间里,继续向前百年预言了人类的困境。卡夫卡在作品里呈现的梦幻直觉,让我觉得,他也是一个超现实主义者,利用这些近乎醒着做梦般的作品,在真实性的高墙上打开了缺口。
我注意到,在我们中间,存在一种由于经验缺乏而引发的忧虑,亦即:如果没有新鲜独特的生活经验,文学写作的未来难以为继。从此类忧虑中,可以看出一个问题,那就是作者对现实经验的过度依赖。但我也注意到,这种忧虑似乎不全来自年轻作者,还来自前辈老师们。他们对于新时代的年轻作者有一种期望,期望我们能在这个和平的年代,写出历经动荡年代般的、具有历史沧桑感的小说。但这种期望越往后,越可能落空,因为对于已经无法触及的历史,我们没法回到过去,没法切身体会。然而,历史留给我们的,是一种经过积淀和萃取过后的晶体物质。这堆闪闪发光的晶体,已不是原来浑浊的溶液模样,而是一个参照的样品。我们去博物馆,参观从帝王陵墓出土的华美衣裳,不是非要把它们穿到自己身上,才有资格感叹它们的价值。我认为,对于历史感的营造,对于经验的利用,作者不必刻意为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使命。否则,这里头有多少是真诚的,有多少是虚伪和谄媚的,便很值得怀疑了。
我们应该反思经验本身的正确性。而表面经验的忧虑,是进行镜像式写作和社会新闻式写作的人的问题,只要社会一日平静,他们的文章便一日如死水沉沉。这种忧虑引发的糟糕后果,已经有所显现,而且正在发生中,就是所谓的“疫情文学”。在二零二零年疫情的初期过后,不少与疫情相关的小说冒头,我从未见过中国写作者如此同步且齐心地描述同一件事。在这个人人追求社会平稳,现代传媒又提供了足够娱乐的时代,那种足以写入严肃文学中的经验确实不多了。
因此,不难理解,由于偶发的灾难,不少作者觉得看到了新鲜的经验,对社会骚动和苦难有着文学层面上的最轻浮的狂热——但他们会认为,这是身为写作者应有的社会道义——急于记录历史进程,彰显自己的历史在场感,哪怕是一篇情节与疫情毫无关联的小说,开篇也不忘把事件的时间背景先抛出来:“在疫情期间。”——得到了渲染的光环似的,接下来发生的任何无趣无聊的情节,仿佛也顺势获得了严肃的社会历史价值。有位哲学家说,历史是由小说记录的。但显然,并非所有记录都有意义,还得看记录者的初衷和使用手法。布勒东认为:“经验有其局限性,依赖即时效用,还要靠理性去维持。”狂热又不负责任的写作,在时效过后,无疑会被抛弃。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文学不妨尝试回到潜意识中,像荣格那样,去探索被日常掩埋的精神经验。这样或许可以更有力地感知在疫情期间种种人事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是从何而来的,我们又能为灾难过后的世界,提供什么样的重建构想,而不是急于在小说或叙事诗中,编造和重复与现实雷同的情节,还毫无廉耻地自认切身参与了历史。毕竟,即使不著一字一词,你也无可避免地被卷入这段世界性的历史中去了。我们在文学中秉持的那份真诚和纯洁,那份热切的注视和观察,是这个文学式微的时代中珍贵的良心。
但必须承认,文学艺术并非人类唯一的滋养。现代媒体为人们提供了更直接的感官刺激,与之相比,语言的秘密和句子的逻辑机制难以给予人们与此同等分量的激情。“这种激情确实让人更加珍重自己的生活,但有人却故意对此装出视而不见的样子。(布勒东语)”让文学高居于其他生产活动之上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不过要使其恢复至某个时期的兴盛,同样难以对此抱有期待。但世界仍需要文学。包括超现实主义在内的所有主张,都是作为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而存在的。我们需要更多元的认识。世界也许不会因为人的认识加深而变得更好,但会因为人停止去认识而堕落。在未来的小说里,我们同样可以去实践兰波的口号:“我说过,应该去做通灵者,让自己成为通灵者。”
文中相关引文出处:
(1)《超现实主义宣言》,安德烈·布勒东著,袁俊生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被背叛的遗嘱》,米兰·昆德拉著,余中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