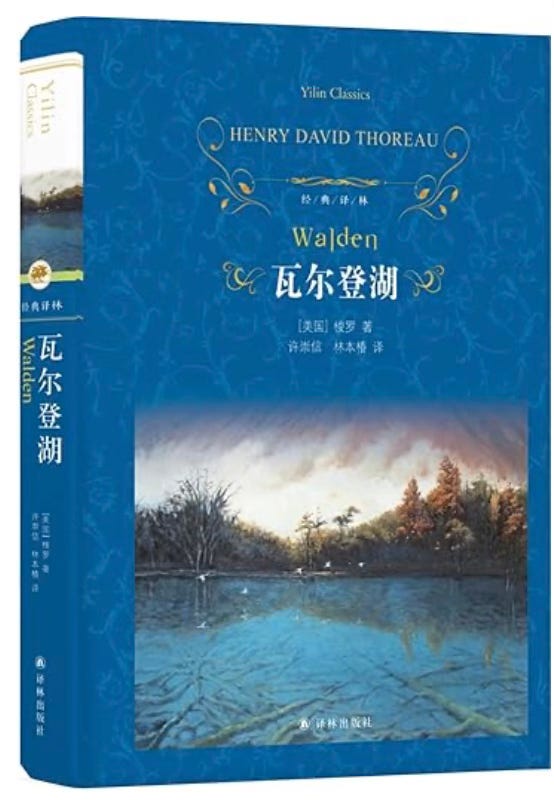当我想到美洲诗人的时候,我总是想到一片瓦尔登湖、一间小木屋、一部《荷马》,我想到梭罗。随着认识的诗人的增多,我对美洲和它的诗歌的看法没有变。首先要有一片湖,这片湖旁长满橡树、桦树、枫树,一整个漫长的秋季,你都踩在潮湿温暖的橡树叶上沿河漫步,橡实落了一地。这个湖没有名字,也没有人想象过要给他起名。既然没有名字,那就叫它瓦尔登湖吧,每一个美洲的无名的小湖都应该起名作瓦尔登湖;湖边该有一间小木屋,这间木屋不该是石头的,也不该是砖头的,一定是木屋。正因为是木屋,诗人才可以将自己世俗的居所完全的和自然连接在一起。布洛茨基在欣赏奥登的诗的时候说,当一个欧洲诗人漫步的时候看见一棵树,他记起来在这棵树前曾经死过哪里的国王,于是他便感叹一番,但是,当美洲诗人看见一棵树的时候,他看见的仅仅是一棵树,他是直接的和这棵树对话的,在此之前,没有历史,也没有诗,诗人是直接的被这棵树启发了,而不是这棵树的历史。我想到梭罗在瓦尔登湖里所说的:
瓦尔登湖一直在那里,在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之前就已经在那里了。而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和它也没有任何关系。
因此,美洲诗人要做的恰恰是亚当的工作。他来到一个新的大陆,他直接地经验地接触每一棵树,每一片湖,而不是通过历史典故和神话传说,反过来,亚当就是最初的诗人。奥登说:
And we are told in the first chapter of Genesis that the God brought to Adam all the creature……Here Adam plays the role of the prato-poet。
这个美洲诗人,或者说,亚当,所做的正是命名的工作。我想起来马尔克斯那个意味深长的开头,那个小说的开头,蕴含了诗歌的缘起:
世界新生伊始,许多事物还没有名字。提到的时候,尚需指指点点
可是,这个新生诗人的手边一定还要有一卷《荷马》:在无名的瓦尔登湖湖边,诗人阅读着荷马。当那个观察着红蚂蚁和黑蚂蚁大战的诗人需要寻求一个诗性的比喻,他想到的是伊利亚特的战斗;当他凝视着深不见底的湖水,他首先想到的是《吠陀经》里的深邃,也就是说,或多或少的,他并不是一个人。在北美诗人命名一件事物之前,每个事物都已经获得了它的名字。亚当命名过他,摩西命名过他,莎士比亚命名过他,华兹华斯也命名过他,他们的影响,不可能简单的忘记了:当《百年孤独》里出现了吉普赛人的身影,出现了他们制作的冰,他们创造的魔毯以及磁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马孔多的历史不仅仅是马孔多的历史,也是波西米亚的历史以及希腊的历史。当梭罗借《荷马史诗》里的意象来描述他所看见的战斗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没有记忆的蚂蚁被赋予了希腊英雄式的记忆,这个记忆不属于自然本身,不属于梭罗,而是属于全人类。
一片瓦尔登湖,一间小木屋,一卷《荷马》,这三个意象和这片大陆真是贴切又自然。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空间,这片瓦尔登湖又叫做曼哈顿,这间小木屋又叫做第52号大街,这卷《荷马史诗》又叫做《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奥登在他的九十九行诗《1939年9月1日》中写道:
我坐在一家下等酒吧里,
在第五十二号大街
犹豫不决,满心担忧
诗中用的Dive, 即“下等酒吧”,绝不是一个英语英国词汇,“第五十二号大街”也一样。我曾去过曼哈顿,在第五十二号大街的星巴克里喝咖啡,阳光下高楼林立,车流不息。五十年代的时候,这里曾经是爵士乐的圣地。奥登写这首诗的时候肯定考虑过这些意象。他接着说:
流亡的修昔底德应该知道
关于语言所能道出的
关于民主的一切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记述了雅典和斯巴达二十六年的漫长战争,在修昔底德的笔下,有伯里克利在战争第二年一个葬礼上的演说。由于希腊人并不重视记载他们出色的政治制度,我们对雅典民主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这篇演说知道的。奥登在第五十二号大街的那个夜晚,伯利克里那天葬礼上的演讲,借流亡的修昔底德击中了同样流亡的的奥登,这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荷马史诗》在诗人的心里平衡了一个新大陆的重量。
这个大陆的重量,在奥登的笔下是矿井和矿井里的生活。奥登在开始写诗的生涯之前,对于他来说最为神圣的东西,是机器、洞穴、炼金术、铅铝合金、沼泽、精灵这样的词汇,而他最为着迷,不断想象的生活,也是在矿井中独身一人,手提煤油灯穿越深深长长的洞窟的寂寞生活。这种生活无疑是欧洲人无法想象的。一个人可以用但丁的地狱中的巨人井来对比奥登的深井,并且发现:但丁的井是宽敞的,奥登的井是狭窄的;但丁的井是神学气息的,奥登的井是工业气息的;但丁的井的是伦理的以及历史的,而奥登的景是新鲜的,在那里面没一块石头都会喃喃低语,石头的自由意识属于他们自己,而不是伟大的创世工程的一部分。我想到《天空之城》里面那个著名的场面:当矿井里的白发爷爷吹灭仅有的煤油灯以后,洞穴里漆黑一片,可是旋即壁岩壁上的石头便发出暗蓝色的荧光来,仿佛是在焦躁不安地等待着什么。奥登眼中的石头也有这样的焦躁不安和窃窃私语:
A word like“pyrites”,For example ,for me,not an indicative sign;it was a sacred name for a sacred being,so that ,when I heard an aunt pronounce it “pirrit”, I was shocked. her pronunciation was more than wrong ,it’s ugly ,ignorance was impiety.
“pyrites”的意思是黄铁矿,奥登在这段话里面指明了“pyrites”的发音方式是用长音“i:”而不是短音“i”,Pyrites的i和impiety,bit,fight,combine是一致的,而不是Galileo,bit,或者kitten。这个音节里面有一种美洲式的浑厚,这个音节是life、 wise、license、riffle,甚至pirate和almighty里面的重音,而不是sophisticated,jingle或者british里面来自“I”的轻轻问候。尼采发狂的30年后,一个美洲的野人号称自己发现了真正的幸福,他写下了《草叶集》,他的幸福指的不是bliss里面的短音,那种只有查拉图斯特拉独特的气喘,而是satisfied的长音,是惠特曼在一花一木里面寻找到的满足感。
总的来说,美洲诗人依然依然采用了古老的词汇和成熟的发音规律,然而时间和地点总是允许他们仔细的咀嚼那些词汇。那时间是时代广场与伊利亚特交汇的时间,那地点是瓦尔登湖,也是曼哈顿。我们不妨继续从以上文中那种卢梭的口吻——谈论社会如何由原始人类演化而来的口吻,仔细的考察诗人如何成了美洲诗人的。
这问未来的诗人,因为上文分析的奥登对长音“I”的偏爱,不如说,这个apprentice,仿佛是“柏拉图洞穴里”比喻的囚犯一样,厌倦了来自欧洲的长时间的说教,并且决定到洞穴之外的世界去生活:如果这个人是梭罗,那么他就抛下了一卷《荷马》,并去瓦尔登湖湖边过鸟兽若比邻的生活了;如果是奥登,那就是去体验困境里的新世界了;如果是罗伯特弗罗斯特,那就是放弃了追随先人的脚步,独自踏上落叶满地的小径了。
然而,这不意味着原来的洞穴的生活是一无是处了。相反,洞穴里墙壁上影子的世界和洞穴外大地上太阳的世界同样是真诚的。只不过,就当下而言,我们暂时忘记了先前的那一个。这就好像是说,生活原来是生活,诗原来是诗,不会因为表现的而失去任何一部分,影子表象下的诗和太阳表象下的诗,原来都是诗,而生育万物的欧洲依然是美洲诗人取之不尽的活水源头。同样是美洲诗人的帕斯,在长诗《太阳石》中写道:
预兆脱离手掌,
鸟儿啄食月光。
预言家是古希腊以来早已经有的了,譬如西比尔、卡桑德拉,而阿尔特弥斯的故事也是世代相传。美洲诗人譬如说是那脱离月光的鸟儿,脱离手掌的预兆。预兆脱离了手掌,才成了真正的不可言说的预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