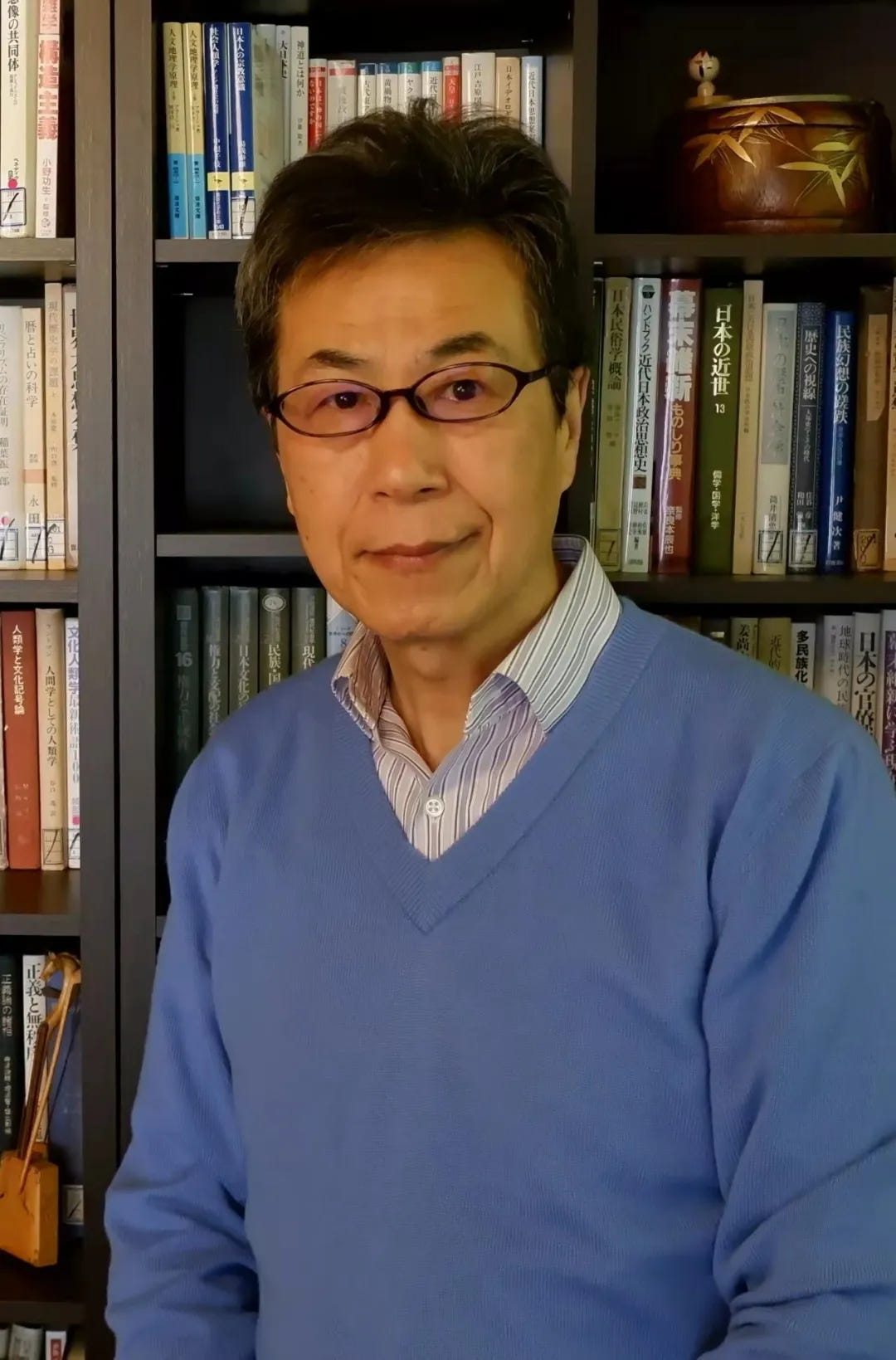訪談 | 王柯:近代日本民族主义的流变及镜鉴
編者按:旅日学者、神户大学的王柯教授多年来一直专攻近现代思想史和国际关系史,在民族与文化的概念与历史演变、民族国家的兴起和建构、政治文明思想史等方面有着深入的研究。同时,由于多年旅居日本,王柯对日本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和军国主义的发展也有深刻的认识。
短短几十年中,日本在各自为政的割据状态上迅速建构起中央集权的现代国家,发展出狂热的民族主义和忠君思想,并最终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将世界和自身都卷入战争的泥潭,给人类文明带来深重的灾难。这一切是如何形成的?这其中,历史又能给我们以怎样的启发?2022年5月,记者对话王柯,交流有关民族国家、共同体、民族主义和近代日本政治等一系列话题。访谈首发南都观察,经作者和王柯教授授权,波士顿书评转发。
王柯:日本神户大学荣誉教授、神户大学国际文化交流中心高级客座研究员
记者:何东马
记者: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现代的意识形态,在政治学者的研究中,其起源与构造有诸多解释。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主义是“想象的共同体”,源自现代媒体的发展以及追求民族解放与独立的现代知识分子的主动构造。安东尼·史密斯与盖尔纳等人则认为,民族主义潜藏于历史之中,只不过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被激发出来。就您所知,日本的民族主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构造,又是如何发展的呢?
王柯 :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两个层面。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民族主义是不是一个历史的存在,是到了近代才被重新激发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需要先搞清楚的是:古代社会形成的各种共同体,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究竟有什么不同?
我认为:说古代存在民族主义的思想成分,而它们又在现代被激活,这里说的,不可能是从近代的nation角度所理解的“民族”。安东尼·史密斯和盖尔纳等人在描述古代共同体时所言及的“nation”一词,并非说为了说明古代也有现代意义上的nation思想。
例如安东尼·史密斯称古代和中世纪的历史为“nation之前的历史(前史)”,当时的“民族的共同体”为“ethnic community”。尽管从词源上来说,nation一词可以追溯到更早,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约1320年-1384年)所翻译的英文版《圣经》中也用了“nation”。虽然近代以前的nation也是被用来形容一种具有共同信仰的共同体,但与法国大革命时期出现的 nation所体现的用于凝聚人民的价值观的概念有所不同。直到进入19世纪,才有人将nation所体现出来的普世价值与种族结合在一起进行论述,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德国哲学家费希特。
因为受近代日本和制汉词的影响和当时的政治背景,中文逐渐习惯于用“民族”一词来翻译nation,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和令人惋惜的问题。因为它造成了一个很大的误会,让许多人忘记了来自于法国大革命的nation思想,其实是为了强调一个将人人平等作为共同价值、一个按照“主权在民”原则而形成的国家共同体而诞生的。
也许有学者会在古代中国思想源流上寻找与现代民族主义思想相契合的成分,但是我觉得那些成分充其量不过是“族”的意识,与近现代政治学的具有规定国家政体性质成分在内的“民族(nation)”思想相去甚远。
个人的国家认同,基于国家对共同体成员的尊重,这在西欧的国家思想中具有悠久的传统。比如说罗马共和国时代就存在“爱国主义”,但其本质上爱的是共和制度,爱的是保护自由人的制度。因为共和制度保障了共同体成员个体的自由,共同体的成员们才会秉持“爱国主义”的观念。这与近代的nation思想可谓异曲同工。而东亚用汉字所表达的“民族”概念,虽然来自于nation,却是建立在“有国才有家”的思想基础之上的。
所以,在用诞生于西欧的概念来讨论和概括问题时,首先就要注意到,从出发点开始,西欧社会就与东亚社会所考虑的使然、应然和所以然有着根本的不同,甚至完全相反。
我们再回到问题的第二个层次,即日本近代民族主义的诞生和发展过程。
日本很多知识分子认为,日本的近代思想其实就是关于国家和人民之间关系性质的思想,或者说就是近代国家思想。而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前期的日本近代国家思想的过程,与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分不开的。
以近代民族主义思想为基础的日本近代国家思想的成长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自由民权运动”的阶段。这一阶段运动的指导思想是法国大革命的天赋人权和自由主义思想,而其标志就是从追求人人平等之社会的愿望出发,接受了nation的概念。
关于自由民权运动的性质,日本学界一直存在分歧。有人认为,运动虽在早期打出了自由和民权的旗帜,但其实并不清楚自由和民权的真正含义;参加者不过是为了反对政府、抵抗威权而聚集在一起,“在自己的理解能力范围内利用了从欧美输入的思想而已。”
自由民权运动从一开始,就将尊皇思想作为自己的合法性根据,其性质无法对应近代西方的Liberalism(自由主义)。如果用林肯的名言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的政府)衡量,自由民权运动的“民权”充其量不过是在追求for the people的层次。但自由民权运动思想家们常常借用“天赋人权说”来证明自己的政治正确也是事实。在运动中,社会契约论和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开始得到传播。日后发展为“民族”的nation的概念也是在自由民权运动时期进入日本思想界的。
从明治十年(1877年12月)起,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多次被翻译成日文《民约论》,这说明19世纪日本对法国大革命和对nation思想的认识,始于对民主与平等思想的认识。到了1880年代后期,nation更是直接被译为“国民”。
第二个阶段是“国粹主义”的阶段。这个阶段的重要标志就是nation被蜕变为“民族”,并被赋予了以地缘为单位的文化共同体的性质。
“nation=国民”的理念之所以没有得到普及,原因是明治日本的政府内部和思想精英中一直存在着主张主权在民(国民主权)和主张国家主义两种思想之间的斗争。
1881年的“明治十四年政变”赶走了政府内部主张采用英国议会内阁制的势力,明治政府得以按照德意志帝国宪法形式,制定了保留君主实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1889年)。
这是一个国家主义思想占据了上风的标志性事件,其社会背景是,许多被政府派遣留洋的青年才俊回国后,占据了重要的政府公职或成为大学教授,成为明治政府中的政治精英。这些人大多接受了德国学派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成为坚定的国家主义者。他们认为必须改变明治维新之前各个“大名”手握重权,人民只知道忠于藩主、而不知忠于国家的状态。他们要把民众改造成真正的“国民”。于是“nation”被翻译成“民族”,被赋予了“共同地域的文化共同体”的意涵。
于是原来强调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nation”,被改造成了强调国家主义的观念。随着和制汉词“民族”一词的诞生,个人被纯粹看作国家的附属品,与第一阶段相反,人民与政府的关系被完全颠倒了过来。
第三个阶段为“国体论”的阶段。其标志就是日本国家主义知识分子对天皇制进行再诠释,将“日本民族”变为“以天皇为祖先的一大家族”,从而给“民族”再赋予血缘共同体的性质,并由此引发出日本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的结论。
由国粹主义者传播开来的“民族”,其实就是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日本国”之“臣民”,与作为文化共同体的“大和民族”之“族”的结合。通过国粹主义的阶段,“民族”作为nation的译词在日语中得到普及;而到了国体论的阶段,在天皇万世一系的话语中,“民族”又被赋予了血缘共同体的性格。与nation的本意不同,和制汉词“民族”强调:民族是构成政治共同体即国家的基础,其成员不仅具有共同的文化背景,还具有共同的血缘关系(血族)。
国体论,是主张日本在国家形式上是一个具有“皇运无穷、天皇神圣和忠孝一体”三点特征的“神国”的思想和学说。大日本帝国宪法和《教育敕语》从制度和精神两个层面上将它变为日本主流国家思想。
在这个过程中,在德国接受了近代国家主义思想的精英们,将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甚至心理学的理论嫁接在神国思想、神话史观上,使国体论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正是在这些具有强烈国家意识的明治思想精英的国体论论述中,近代日本的民族主义完成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单一民族国家思想建构。
记者: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和日本的诞生,离不开“天下”这个观念在东亚范围内的破产。天下观念以及朝贡体系作为一种普世性的观念,在东亚(中国、朝鲜、越南)有着成功的实践。但是在西北地区,则得不到有效的响应(比如清代的大小和卓之乱、浩罕汗国阿古柏的叛乱)。这是否说明,天下观念只能在农耕的、儒家文化圈的范围内推广,在其他文化的范围内则难以产生有效的影响力?同样,日本对于朝贡体系的态度也非常暧昧,除了足利义满曾经向明朝封贡之外,德川幕府等统治者一直要求对中国采取对等的态度。在您看来,朝贡体制的普世性是否被今天的我们高估了?
王柯: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概念,有的时候,一个民族可能存在多种经济形式,所以我想不能简单地用游牧和农耕的二分法,作为区分是否进入天下体制和朝贡体系的标准。关于天下的概念我已经写了很多文章,这里仅就朝贡体系是否会对一个共同体产生吸引力的问题,谈一下个人认识,这个问题可能与当地社会是否实行中央集权制有关。
朝贡体系的中心需要是一个权威所在。而要成为朝贡体系的中心,这个权威的形成,又是和政权的合法性分不开的。任何一个政权都要找到自己统治合法性的根据。中央集权制是一个阶层清晰的金字塔型政治结构,它能让人清楚地看到权力的中心所在。当处于这个中央集权制金字塔顶端的首领以天下思想解释其统治力的来源时,也更容易给其权力披上神圣的合法性外衣,形成一个让人愿意服从的权威。
因此,说天下观念和朝贡体系更容易在儒家文化圈的范围内推广,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似乎难说一定与农耕文化有关。因为日本就是农耕文化,传统的维吾尔绿洲农业也是一种农耕文化,他们就没有进入朝贡体系。
近世日本存在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即使在江户时代,各个“大名”的独立性依然很强,日本一直没有进入朝贡体系中,可能也与他们国内的政治结构有关。其实日本近世以来“大名”林立的状态,有点类似于欧洲,各个藩的地方自治和权利意识都很强。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明治维新视为中国历史上的“周秦之变”。由此,日本才由一个封建林立的国家转变成中央集权制国家。
由于封建的历史,尤其是在江户时代,各个地区的文化都得到了长足发展,因此直到今天,还有很多日本人同情和怀念德川幕府的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和各个藩的末代藩主。当他们意识到自己无力阻挡历史潮流时,并没有激烈反抗,而是选择了“大政奉还”——将权力交还给明治政府。
2017年是日本明治维新一百五十周年。日本学界对如何评价明治维新有过很认真的讨论。肯定明治维新的人认为,明治维新改造了传统的日本社会,打破了锁国的局面,把西方工业化的成果引进日本,日本才有了今天的进步和发展。反对的则认为,明治维新的富国强兵本质上破坏了日本的地方自治传统,尤其是具有浓厚国体论色彩的《明治宪法》和《教育敕语》发表后,地方的权利和个人的权利被完全牺牲,将日本引入了军国主义的歧途。
记者:很多国家近代民族主义的特征,是民族意识主要来自于创伤性的历史记忆——对于西方侵略历史的念念不忘和对于历史上辉煌时代的追忆。相反,日本对于黑船来袭后与西方交往的历史,并没有采取一种屈辱的心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
王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民族主义的动力来自官方。日本逐渐走到通过国粹主义、国体论来追求单一民族国家的道路上,是统治者出于实现中央集权的需要而实现的。
近代日本由在朝的民族主义者所发明的单一民族国家论,其目的在于根除幕藩体制的影响,将人民对大名藩主的忠诚,转化为“臣民”对天皇制国家的忠诚,通过“国民”化来强化现行的国家体制。
黑船事件在日本,当年也被看作耻辱的象征。事实上,任何国家最初的民族主义动员,都是以耻辱的记忆为起点的。但是,今天的日本之所以不再强调这种关于国耻的记忆,就是因为日本国民在开国之后逐渐明白,之前的锁国体制根本无法面对列强的挑战。更重要的一点,是日本国民亲眼看到了,敲开了日本国门的西方列强,其实并没有烧杀抢掠,相反却刺激日本去了解西方先进的科技文明,促使日本接受了与近代世界接轨的社会和政治制度。
简而言之,日本国民明白了,导致日本开国与近代化的西方的刺激,不是民族的耻辱,而是接触和接受先进文明的契机,所以日本逐渐能够以一种积极正面的姿势,看待自己被迫接受外来文明的历史。
记者:民族主义的形成与大众民主和普选制的兴起息息相关。您对日本民族主义也深具研究,能否请您谈谈日本近代以来极端民族主义是如何形成的?为何自由民权运动以来的民主化潮流,尤其是大正民主,未能使近代日本真正成为民主国家?
王柯:我们在上面已经谈到,近代日本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围绕着日本该走什么样的近代化之路,明治的政治精英们发生了严重的对立:究竟是“主权在民”思想还是国家主义,能够主导国家的未来?
最终还是国家主义占了上风。随着和制汉词“民族”一词的诞生,个人被纯粹看作国家的附属品,与第一阶段相反,人民与政府的关系被完全颠倒了过来。
这一变化的发生,还与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传入日本有着直接的关系。1880-90年代中,日本翻译了许多斯宾塞的著作,甚至被称为“斯宾塞时代”。近代日本社会在接受斯宾塞进化论思想上,是各种思想流派各取所需。自由民权运动强调其自由主义的侧面,而明治政府和国家主义者们强调其保守主义的侧面。
在达尔文那里,进化论“物竞天择”的单位本来是个体,但到了斯宾塞,单位被换成了国家/社会这样的人类共同体。斯宾塞强调,国家间的关系就像自然界一样弱肉强食、优胜劣汰。正如列文森所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法则,使国家在生存竞争中成了最高的单位。”
社会进化论的适者生存说,为近代日本的国家主义提供了有力的正当性理论根据。这种思想对加藤弘之、德富苏峰等自由主义者具有非常大的影响,他们纷纷转向,抛弃社会契约论立场而转向社会进化论、转向国家主义。
但是究竟是以“主权在民”思想还是国家主义主导日本国家的未来?这一明治晚期就已存在的争论并没有完全消失。到了大正时期,这种争论愈演愈烈,宪法学者美浓部达吉提出了“天皇机关说”,主张天皇只不过是一个行使统治权名义的机关,而实际的统治权则属于法人的国家。美浓部达吉的观点之后遭到了日本的右翼,甚至是海军军令部部长加藤宽治的猛烈攻击。
同样在大正时期,还有很多人对国体论也进行了隐晦的反思。思想家吉野作造提出的“民本主义”也是出自这一目的,它其实是日本特殊国情下民主主义的改良版本,但是为了避免与国体论者之间发生争议,吉野甚至避免使用“民主主义”一词。
记者:日本近代史上,曾经出现所谓“国体论”。国体论的核心就是天皇与皇室万世一系,将天皇的统治进行神化。日本也成为了“大日本国者,神国也”。国体论最终沦为日本走向军国主义道路上、为其推波助澜的一种意识形态。您认为国体论与日本单一民族的民族主义有什么关系?
王柯:国体论源自江户时期的古学学者本居宣长和贺茂真渊等人,国体论主张,日本在国家形式上是一个具有“皇运无穷、天皇神圣和忠孝一体”三点特征的“神国”。所以在江户幕府的体制之下,国体论是受到打击的,因为国家的实际权力掌握在幕府将军的手中。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走向中央集权体制,需要一个具体的国家统合象征,国体论中的“万世一系”、“八纮一宇”等事项迎合了这种需求,而之后出笼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和《教育敕语》,从制度和精神两个层面上将国体论变成了日本的主流国家思想。
国体论将全体国民在生物学上说成是一个“血缘共同体”,但实际上从日本国家的规模来看,这本来是件不可能的事情。“皇国论”、“神国论”,以及天皇血统的“万世一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虚构和宣传,其目的就是为了改造江户时代“人民只知有大名,而不知道天皇和中央政府”的意识,培养日本国民对日本国家的忠诚。
当历代天皇是你的祖先,而现在的天皇可以说是你的堂兄堂弟时,你怎么能不去保卫他呢?当把“日本民族”塑造成一个地域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血缘共同体以后,近代日本的民族主义也就彻底定型。
日本之所以会由一个民族主义国家走向军国主义国家,是因为在明治维新时期的政治体制中,具有政治野心的日本军人、尤其是“青年将校”(青年军官)们,逐渐成为以“国体论”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的主要载体。
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力量来自于长州藩和萨摩藩的底层武士。在地理上,这两个藩都属于边缘地带,而因为德川幕藩体制的崩溃,武士阶层的传统阶级上升途径消失。既处于地域边缘,又处于社会边缘的底层武士都希望找到一个可以进入政治舞台中心的捷径,最好的选择就是成为维新政府的军人。近代日本军队的阶级制度和士官学校、陆军大学制度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权力与权威的金字塔。尤其是在《大日本帝国宪法》,即《明治宪法》中,规定军队直属于天皇而不是政府,这更使军人变成一个新的特权阶级。
但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出身于地方武士家庭的中下层军官发现,自己的家人并没有能够享受到经济成长的成果,而日本政府面对当时的国际局势也表现得软弱无能。这时他们发现,可以借以国体论为中心的民族主义的口号,名正言顺地“清君侧”和“下克上”,甚至刺杀天皇身边的元老和重臣,提高自己的社会存在意义。就这样,国体论为这些出身于边缘的军人群体,提供了一个干涉政治的合法手段,使日本逐渐由民族主义发展到了军国主义的阶段。
记者:二战后,清算日本战争责任的过程中,日本左翼学者丸山真男曾经提出了有名的“无责任体制”。在国际局势激变的情形下,日本军政高层最终没人依据自己的权限做出判断,更没人挺身而出负责。最终使日本踏上了侵略战争的灾难之路。能否请您谈谈为什么日本的普通人与政客,最终都放弃了自己的责任,酿成了侵略战争的灾难?
王柯: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认为,现代人因为孤独与意义缺失,会自愿放弃自由。人面对危机时也是这样,宁愿放弃自由以逃避责任,这是出于人性的弱点。对很多人来说,用安全换取自由,可以获得更多的在一个社会中生存的机会。他之所以愿意这样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之前获得的自由,不是自己争取来的,更多是被给予的。
于是通过危机来煽动民众,成了为政者常常使用的一种手段。在(被制造出来的)危机下,很多日本人也不例外,他们主动放弃了先前被给予的自由,为了寻求保护而进入一个极权、集权体制之下。这也包括政治家在内,日本社会最后就变成了一种“无责任体制”。
以东条英机为例,他被内大臣木户幸一推荐给天皇时,公认是一个既能抑制军部狂热分子,也使御前会议满意的选择,最后却宁愿自己被军部所绑架。到了后期,他已经感到日本在战争中无法取胜,但即使如此,他也不同意撤军,因为现在撤军,他无法说服日本社会接受已经战死大量士兵的事实。最后在战败后,与德国、意大利签订“三国同盟条约”的近卫文麿也不认为自己有罪。日本发动侵略的一切罪恶,似乎都是形势所驱而不是出自某个个人的决定,甚至包括昭和天皇在内。有些人认为昭和天皇本身的思维和获得的信息也是受限的,所以战争责任似乎也不能完全归罪于天皇。说战争日本是一个无责任体制,不无道理。
记者:在制定《明治宪法》的过程中,支持英国式议会内阁制的大隈重信和支持德国式君主立宪的伊藤博文之间曾经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最终以伊藤博文的胜出而告终。为什么日本政治精英会选择使《明治宪法》倒向德国的国家主义道路?
王柯:伊藤博文和大隈重信之间的冲突被称为“明治十四年政变”,以伊藤博文胜出,大隈重信退出政坛告终。大隈重信希望的是英国式的政党政治与立宪内阁制,而伊藤博文想借用的是德国的普鲁士宪法,天皇大权独揽,预算案未通过议会表决时执行上一年度预算制度等等做法。
明治时期以来的所谓“国家意志”或者“圣断”,其实不过是天皇身边重臣个人的意见。但是如果采用了议会内阁制,权力集中到了议会,使天皇变成“虚君”,天皇身边元老的份量、决定政策时的发言权就会减轻,也会受到民意制约,没有了继续操纵政治、政权的空间。所以通过《明治宪法》的制定过程,元老们成功地驱逐了大隈重信这样深受自由民权派推崇的政治家。
但民族主义的确是一把双刃剑,近代日本政客玩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被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最终的结果也是引火烧身,反而被更加汹涌的民意所吞噬。在民族主义的声浪中,谁也不敢发出不同的声音。民众只能受到国体论论调的不断刺激,最终走向军国主义。对于这种民族主义的未来,民族主义的制造者和宣扬者们后来可能也有所察觉,但为时已晚,已经没有人能够发出理性的声音和反思。一旦被民族主义的绞肉机卷进去,最终将自掘坟墓。
记者:去年的日本众议院选举以右翼的大获全胜告终。今天的日本对于塑造东亚的国际秩序也变得越来越主动。在您看来,拥有“和平宪法”的日本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今天的日本人是否会接受一个在国际舞台追求更多话语权与主导权的日本?
王柯:二战以后的《和平宪法》深受日本国民的爱戴,为日本战后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了保障作用。反思战争也成为日本学界的主流。这是无可置疑的,但是造成当前日本转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围绕着日本的地缘政治环境正在变得复杂多变,日本社会开始弥漫出一种不安定的心理。尤其是今天的国际社会,明显地呈现出重回弱肉强食、丛林法则支配的趋势。一个强权国家,说打其他国家就可以打起来,这个可怕的现实,当然也使得日本人开始重新思考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关系。
记者:很多国家在老龄化严重时,会将引入年轻移民作为一个解决方案。但这在单一民族的国家里可能比较难接受,会引起一系列矛盾和社会问题。这在日本是怎样一个情况呢?
王柯:日本是老龄化很严重的地区,也引入了不少移民。对外来人的歧视肯定是存在的,大家原来生活在非常不同的地域、文化背景和治理结构中,对一些公序良俗的尊重程度,肯定都不一样,自然就会产生矛盾。和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完全不一样,接近于单一民族国家的日本,对于移民的偏见也是比较强烈的。
但是日本毕竟是一个法治国家,不会突然发展到通过运动驱逐移民或针对移民进行民族屠杀;有法治和媒体的存在,也不会允许公开的歧视。比如当年的战争孤儿从中国回日本,媒体一直在为他们说话。如果对日本人和非日本人不能实行同工同酬,就会遭到媒体曝光,司法当局就会找雇主算账。总之,日本社会保障每一个人的人权,这里也有一个保障人类生存权利的底线。因为移民占全国人口中的比例较小,我至今还没有遇到过一起歧视外国人的例子。